
(《敵人》繪本內頁,大塊文化提供)
翻開《敵人》,諾大的黑底白字立刻讓讀者進入一個非現實的情境——戰爭開打了。
翻頁,乾枯的樹枝、荒土裡兩個洞穴映入眼簾,讀者再次被暗示可能是書中唯二角色的關係——他們是敵人。在故事開始前,讀者便被粗暴地置入唯一的觀看位置,被給定了角色的身分及其所處的情境,沒有曖昧的空間,亦無詮釋的可能。而後書名頁出現,幕開,士兵孤身一人蜷縮在台階上,讀者必須進入「戰爭」敘事:人類透過語言塑造出敵人,卻靠肉身進行攻擊。

(《敵人》繪本內頁,大塊文化提供)
《敵人》使用第一人稱單一視角進行敘事,讀者僅能讀到主角士兵的內心獨白,透過他「認識」敵方,猜測開戰的原因,藉由觀察士兵在壕溝裡的一舉一動,推測戰況(似乎不太激烈)。讀著讀著,我們將很快地發現這位士兵的視野與認知既狹隘又封閉,讀者無法從這個角色獲得任何可靠資訊,因為,他對於「敵人」的認識僅來自於一本「手冊」。這本手冊告訴士兵:敵人是根本不配稱作人類的野獸,殘忍無情。為了自保,士兵必須殺戮,先下手為強。

(《敵人》繪本內頁,大塊文化提供)
至此,讀者會意識到,囿於有限的資訊甚至是洗腦,這位士兵其實是個「不可靠的敘事者」,我們讀到的戰爭敘事是片面的,是被恐懼與宣傳扭曲的主觀臆測。讀者甚或能夠理解或同情士兵的處境,他被要求進入壕溝,卻沒有足夠的資訊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隨著故事推進,契機出現了。
士兵感到飢餓、寒冷,雨水滲了進來,他甚至在仰望星空時想著:「這場戰爭毫無意義。」他的內心逐漸動搖:「戰爭真的還在打嗎?是否早就結束了?」肉體的苦痛激發內心的困惑,他決定離開壕溝,為這場戰爭做個了結,故事的轉折也終於發生。他偽裝成灌木叢爬出戰壕,在無人的敵方壕溝看見敵人的家人照片,甚至,他發現了另一本手冊⋯⋯不過,為什麼敵人不在洞裡呢?難道,他也爬到了士兵的壕溝?

(《敵人》繪本內頁,大塊文化提供)
那麼,他們到底該如何停止戰爭?
大衛.卡利(Davide Calì)的文本非常精彩,他不描寫宏大的戰爭場景並賦予道德說教,而是聚焦於士兵的內心世界與生存狀態,讓讀者體驗和想像戰爭裡的「人」如何被非人化、被異化為等待指令的機器。敘事的高潮在於主角士兵發現敵人也有一本「手冊」,一連串猜測揣想也鼓勵著讀者反思「敵與我」的荒謬認知。兩本手冊內容互為鏡像,唯一的差別在於「敵人」的面孔被置換成了對方。這一發現,解構了手冊的權威性,揭示了戰爭宣傳的對稱性與虛構性:仇恨是被製造出來的複製品。
另方面,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的圖像語言為大衛.卡利的文本增加了更多詮釋空間。《敵人》的畫面十分簡約,畫面乾淨,大量留白,僅保留必要元素,利用橫切面的構圖呈現兩個戰壕,即使敵人的洞並不可見或只存在於士兵的想像中,對稱的畫面似乎提醒了讀者:敵人的洞穴可能如鏡像般類似。
值得一提的是,布勒奇把手繪線條與真實物件、歷史照片並置,讓這個故事指涉了現實,而不僅是寓言故事。也像在暗示,戰爭的物質現實沉重且真實,但關於戰爭的敘事反而是人為建構、脆弱而易碎的。

(《敵人》繪本內頁,大塊文化提供)
闔上書頁,回到現實,作為一直被戰爭陰影籠罩的台灣人,可以怎麼閱讀這本作品呢?我們是否躲在自己的戰壕裡,靠各種「手冊」理解世界?當士兵開始仰望星空,開始懷疑手冊的真實性時,他重新獲得了「思考」的能力。《敵人》透過這個過程,或許暗示了:面對戰爭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個體的批判性思考,鍛鍊心理韌性,拒絕盲從權威。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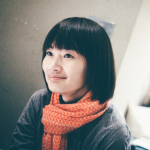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