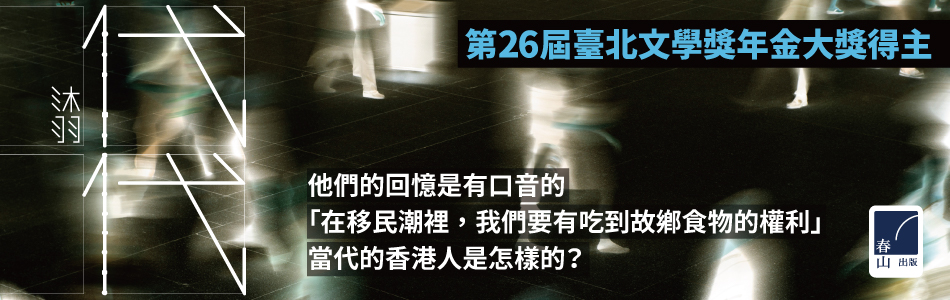
01 廣東話有這樣的說法: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嘴藐藐。意思是親屬關係到了第三代,不免情感淡薄。不過,「嘴藐藐」這個表情豐富的詞說的還不僅是疏淡。藐即輕賤——嘴巴那麼一撇,裡面還包含了不屑與懷疑。
02 這裡有必要對「嘴藐藐」做一些基本的界定,因為我將要借它來指認沐羽的文體風格。《代代》的離散者群像,擺出來是一副相互側目藐嘴的陣勢。不單如此,這些故事的敘述者還近乎炫耀似的,對人物極盡戲謔與調侃。在申請臺北文學年金時,沐羽在他的計畫書裡,提到這幾年對香港的討論「集中在橫向的影響而非縱向的歷史」。嘴藐藐的臉容並不新奇,但這種一面嘴藐藐,一面又不無深情地回望過去的姿態,是這部書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點。
03 沐羽的計畫書還透露了第二個充滿張力的訊息:他引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點明自己要「回到歷史與社會研究」,並「嘗試沿著這個框架接駁下去」,那麼他選取的文體為何不是論文而是小說?從《煙街》到《代代》,沐羽不單遊走於小說與散文之間,其作品也透露出對文體本身的高度自覺。本書〈坎撚筆記〉一篇,基本上由 58 張簡報組成,很難說不是以小說外殻偷渡的論文。雖然沐羽把《代代》稱為小說集,但我傾向把它視為一個在文體上游移不定的文本。在敘述與論述之間的跨界實驗,是它值得關注的第二點。
04 我久在心裡派給沐羽「文學笑匠」的頭銜,並真心嘆服他貫徹經營痞子形象,把各種艱澀的文學文化甚至經濟理論與棟篤笑無縫地揉成一團的本領。沐羽的無賴語調早已爐火純青,但《代代》戴上小說的面具出場,它的語言亦有所轉化。可以看得出受題詞引用的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啟發不少。史密斯憑《白牙》一舉成名,但撰文介紹過「歇斯底里寫實主義」(hysterical realism)的沐羽不會不清楚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對這部大受歡迎的作品做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對史密斯的漫畫式筆法深感厭煩,敘述者跨過人物視點所說的低俗笑話,更被視為寫實主義的敗筆破綻。沐羽在小說的後記裡,伸手擁抱伍德的貶抑之詞,把它們貼到自己的額上,宣示「誇張」與「諷刺漫畫」是刻意的追求,似乎是要搶先向這位暫時還未能讀到《代代》的評論者做出申辯。
05 伍德批評《白牙》(或曰以它作為代表的小說現象),針對的不是技巧(他未有否定史密斯的天賦),而是倫理。他在這些雜耍似的炫目故事百寶盒裡看到一種危機,就是「人性」(human)的匱乏,彷彿這時代裡,那些表面上以狄更斯為教父的寫實主義作家,再也無力塑造真正具有血肉,讓我們共情的人物。我很好奇,伍德會如何閱讀《代代》——他會否認為,這部作品同樣想要展示奇觀多於人生?最少,對於臺北文學年金獎的評審來說,它表現出「深切的同理」,並成功塑造了「高貴的失敗者」。我對年金評審的見解並無異議,但卻無法不追問:沐羽究竟為何、如何通過嘴藐藐的修辭,來呈現失敗者的「高貴」形像?
06 《代代》並不是狄更斯小說的後裔,也不是情節枝葉蔓生的《白牙》近親。如上所述,集子裡的篇章甚至不見得一定要用小說的標籤固定下來。相對於講故事,它更關注的是空間的搭建——沐羽不是說,這本書是要給離散者提供巷口茶餐廳似的安定感嗎?然而,如果要重建一個離散者的聚合空間,為何偏偏要讓我們注視這些人相互藐嘴的臉容——甚至揚言要把他們的邊界圍欄擴張成鴻溝?在我看來,這正是本書的真誠與勇敢之處。它要直面的,不僅是香港人的世代差異,更是他們從革命被拋擲到日常,從理想被驅趕回生活,滿布裂縫的人生處境。
07 《代代》以臺北的鴻記茶餐廳作為座標,很難不讓我們想起陳冠中寫於2003年的〈金都茶餐廳〉:一個失敗者聚首,想以「CAN DO」精神東山再起的故事。但如果要為它追本溯源,我們還可以回到商業電臺於1968年首播的長壽節目《十八樓C座》。自八十年代起,位於灣仔的周記茶餐廳就成了這個廣播劇的主要場景,成了周老闆、祥嫂、鬍鬚仔這些角色每天對時政嘻笑怒罵的主要舞臺。周記茶餐廳不是十九世紀的法國咖啡館,這裡沒有出現高談文學藝術的沙龍,但它的市井形式,卻提供了一個能讓普羅大眾投入想像,尊重差異與言論自由的公共空間。《十八樓C座》在香港歷史上具有標誌性的意義——我們不應遺忘它的源起,乃為了紀念1967年,因為在新聞節目裡誦讀批評暴動的社評而被縱火殺害的林彬。這樣一個能夠喝杯奶茶、吃件西多,於茶餘飯後和平理性地就時事申述己見的空間得來不易。而它入屋的程度,從無線電視臺仿效製作《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一系列處境喜劇,亦可見一斑。

(圖片來源 / 香港商業電台)
08 讓我們重新回到鴻記的現場——在這個失敗者聚首的世界,我們找不到一種向心的精神力量,更多的時候,我們甚至被提醒:茶餐廳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吃飯拉屎的形而下世界,何必提升為什麼精神象徵?然而,這些失敗者是「高貴」的,更是「人性」的,恰恰因為沐羽讓我們看到,拿下運動期間不得不戴上的面具,他們本來就是平常百性。而唯其如此,《代代》才能引發不同於2019年以來,兄弟爬山的共同體想像,讓我們記起,公共空間的存在,首先在於承認個體的差異,接納他們之間的溝渠。
09 讓我們把時針再次往回撥。2012年,回應反國民教育運動,梁文道寫了一篇〈不必去愛的香港〉,精準地道出,把香港與其他華人社會區隔開來的,是它並沒有愛國教育。在這樣的香港裡,「如果移民,沒人罵你叛徒;如果回來,居然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照樣指手劃腳。如果多拿一本外國護照,沒有人會質疑你的忠誠,甚至可能根本沒人考慮過『忠誠』的問題。」香港人無法忍受把「愛」掛在嘴邊,展現的是一種審美與格調,因為這樣做就是「唔型」。正如道長所說,「基於地域身分的愛往往都會演變成一套意識形態的霸權」。如果把他的話再推演開去,我們可否說,香港曾經有過的「自由和理性的空間」,其實與一種抗拒宏大論述、反濫情的美學不可分割?而《代代》要把《四代香港人》接駁下去的方法,正是要通過重新找回這種港式美學,一種有型的姿態。
10 關於如何才算有型,莉莉在〈坎撚筆記〉裡發表了一場發人深省的演講。只是,要談〈坎撚筆記〉,我們不得不先回到它所諧擬的〈坎普.垃圾.刻奇〉。而要談論陳冠中這篇文章,且容我先引述陳氏另一篇開宗明義,提出要重新梳理香港人的主體性,「拯救香港論述」的鴻文——〈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書寫:香港的例子〉。文章的題目如此曲折,當然因為身世複雜的香港故事從來難說。為了抗衡把香港比喻為大企業的論述、「香港市民不愛談政治的謠傳」,陳冠中主張重新回到歷史的細節,勾起讀者對「官僚主導的福利主義」及「本土進步主義」的記憶。雖然在這篇發表於2010年的論文裡,他高聲疾呼「一個地方在自己的宏大論述缺位的情況下,它就會『被論述』、被別人的口水淹沒」,但就像大多數的香港文化人,在找到「一種難以套路化的辯證話語」前,他還是不願意「隨便拼湊一套大敘事」。
11 發表於2004年的〈坎普.垃圾.刻奇〉,似乎旨在闡明幾個當代美學概念,尤其是坎普(camp);引用的,主要是桑塔格的〈坎普筆記〉及寶琳.凱爾(Pauline Kael)的〈垃圾,藝術,和電影〉。然而,與其說文章是在介紹坎普,倒不如說是認同與演示。陳的文章就仿效了桑塔格的筆記形式,一樣分成 58 段。相對於正經八百的高雅藝術,坎普是一種玩世不恭,在投入之餘總帶著疏離與反諷的玩笑態度。陳冠中轉述:「坎普是樂趣、鑒賞、是『慷慨』:一種對人性的愛和享受、對某些物品和風格的愛和享受。坎普是一種解放,讓有良好品位和受了過多人文教育的人也可以享受到樂趣。」桑塔格的原話並沒有強調「過多」,而陳氏文章的副標題表明「給受了過多人文教育的人」,更似乎意有所指。如果試試把「坎普」改換成「香港」,難道我們不可以說,這篇文章就是為被譏笑為文化沙漠的香港發話嗎?從坎普的角度看來,這個城市正正因為沒有被教條化的美學束縛住,使它成了一個感受力的解放空間。而就如桑塔格所說,坎普是一種感性(sensibility),而不是一種概念(idea),一種隨時而變,不能輕易被固定下來的感性。相對於易於僵化的大敘事,它是一種充滿了迴旋、彈性的身姿。陳氏的文章花了不少篇幅,突出桑塔格與凱爾乃當代紐約的重要文化代表,事實上也在宣示香港這座城市所追隨的對象、它的世界性與潮流觸覺。在這篇沒有講述任何故事的文章裡,陳冠中巧妙地示範了一種香港人自我理解的可能方式——不是追問自己從哪裡來,而是想要成為什麼人。
12 讓我們回過頭來讀沐羽這篇洋洋灑灑的〈坎撚筆記〉。《代代》那個時時禁不住拋頭露面的敘述者,假托莉莉的講演,終於能在這一章裡暢所欲言,申說香港人如何從快樂自由的坎普,淪落為痙攣、迷失,再也無從表述自己的 Kam 撚。我不想複述篇中「Kam」的多層意涵,且讓我把這種「格格不入的氣質」、「自說自話的表演者」,歸納為前文所說的「唔型」。如果就像莉莉所說,把 Kam 推向極致的狀況是「人人都相當孤獨,又想表達自己,就變成了自我感動的媚俗寫作狂」。那麼,Kam 撚就是濫情,就是失去了對大敘述保持警惕的唔型姿態。如果把〈坎撚筆記〉讀成對書中離散群像進行的後設評論,書中最 Kam 的,大概就是堅持要把自己的畢生經驗,以回憶錄的方式貢獻給後世的老朱。以半身照作為封面,印成一千多本的巨著《人老茶黃》,最終有近九百本滯留在他家中,說明了出生於五十年代的老朱,與世界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這其中或者有世代隔閡,但更多的,恐怕是自我沉溺。
13 分裂、碎片化不獨是香港遺民的處境。韓炳哲在《敘事的危機》裡,指出能形成共同體的大敘事傳統,能凝聚集體意識的講述,已經被發帖、分享與點讚所取代。在網絡世界,真實臉容被變得可消費的他者所取代。這裡人人爭相講述的故事,不過以自戀的面貌出現。在他者消失的世界,共同體的想像也就不再可能。然而,如果大敘事是當代敘事危機出現以前的原點,那麼香港可說從來都處於危機之中。想要表述香港的主體,從來就得另闢蹊徑,香港之為例外,也因此有了作為方法的潛能。
14 梁文道創立上書局時說過,香港人不愛讀書,《尤利西斯》要偷偷躲在家裡讀,在地鐵裡則只敢拿出《一分鐘經理人》,以免被當作怪物恥笑。但我還想舉他在〈動物兇猛〉這篇訪問裡提到的另一個例子:他在中文大學念哲學時,曾用《龍虎豹》(香港著名色情刊物)的內頁包著《存在與時間》,持之上課。他和當時一起混的那幫同學,並非不尊重學問。他們可是會圍在一起搞讀書會,研討新馬克思主義與詮釋學的進步分子。相反,包書是致敬,而他們顯然覺得用《龍虎豹》來包哲學書比較有型。如果把這兩個例子並列來看,它們不都指向了本文反覆提到的港式美學——一種對被高舉的神聖之物,始終保持距離、嘴藐藐的態度?它的一端是淺薄,把對文學藝術與任何非實用性知識的追求排擠到社會的邊緣,但它的另一端,卻是免於成為 Kam 撚的清醒意識,不單對權威,也對自己的愛執與信念,始終抱持懷疑與戒心。
15 沐羽提出的 Kam,可說精確地點出了他筆下離散者的困境。但《代代》並不甘於只是呈現,它是敘述與論述的雙重奏,它要搭建世界,並在這世界裡出場表演、發表意見、救贖未來。它延續了陳冠中的方法——通過風格的演示,通過一種能屈能伸的感性,來表述香港的主體;也繼承了《龍虎豹》的書皮美學——如果要談論歷史,當然最好從屌鳩撚柒閪五大粗口入手。
16 此文既非致敬,也非諧擬,也就沒有用心湊成 58 段。然而,我認同桑塔格的話:要用文字捕捉一種感性,尤其是一種仍然鮮活有力的感性,輕盈的筆記比板起面孔的論文更為合適。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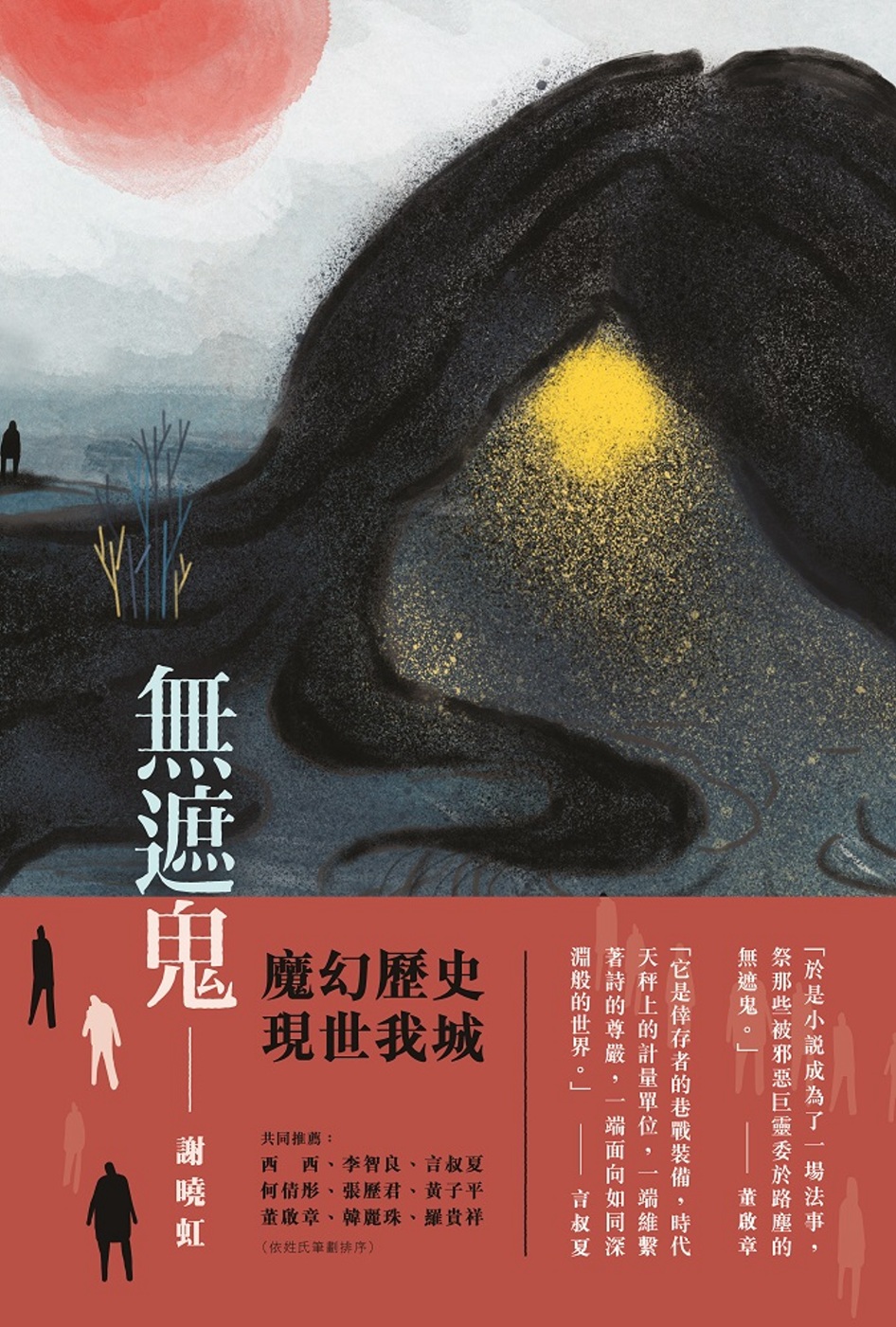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