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留的重量
很多時候,我逛展或閱讀時,並不急於理解,而是更願意等待某種感覺慢慢浮現。它不必命名,也不一定成句,只是在身體裡留下微小重量,像夢醒後的短促眩暈──明明清醒,卻尚未完全回到現實。
這是一種介於知道與不知道之間的狀態,意識彷彿與尚未辨明的事物保持微弱聯繫,讓我忍不住回頭追索。若無急事打斷,這種餘韻往往是我最珍惜的暫停時光。
在北美館本屆以「地平線上的低吟」為主題的台北雙年展中,這種停留感反覆浮現。觀看的猶豫與遲疑成為常態;感受暫時散落,彼此靠近又保持距離。觀看被拉長成過程,在偏離與回返間試探尚未被說清的地方。這樣的未知仍由既有語言與形式構成,與每個人、每件邂逅作品的「來時路」與內在慾望密切相關。
▌思慕的厚度
策展人提出的「思慕」主軸,未必指向明確對象,而是一種持續狀態:對缺席之物的反覆想像,對無法抵達的敘事長時間凝視,甚至帶著執著。我想到喜歡揭示故事裂縫的作家──安潔拉・卡特與奧爾嘉・朵卡萩。
卡特在《染血之室》(台版收錄在《焚舟紀》套書)中重寫童話,保留原結構,卻讓被遮蔽的慾望、暴力與權力結構浮現;《魔幻玩具鋪》揭示父權滲入日常與身體;《明智的孩子》透過錯雜的家族敘事動搖血緣、正統與文化傳承。卡特不拆毀童話,而是讓它失去安撫與指引功能──形式在,卻不再引導清晰結局,而是將人留在裂縫中,停留於慾望未被命名、秩序未重組的狀態。這種延宕閱讀的感受,正是我觀看高田冬彥《公主與魔鳥》的聯想。
朵卡萩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中刻意讓歷史失去線性。記憶、傳說與日常細節交錯,人物意識自身位置不完整,世界因此保留空缺。敘事低聲持續,不急於解釋,也不收束,而是讓缺席本身可感知。
而在她《收集夢的剪貼簿》中,並置收藏夢、筆記、軼聞與日常觀察,則是對無法完整理解之物的溫柔靠近。夢並非解碼象徵,而可以是一種暫時停留,允許模糊、不確定與偏離。
▌童話的不安
色彩斑斕的「魔鳥」引導我進入高田冬彥的空間,很快就與影片中酣睡少年合而為一。跟著其他觀者一起躺在圓形床墊上,睡意迅速襲來,熟悉感中滲入不安。
童話在此仍承載慾望與情感,卻不再提供庇護;訴說故事的話語在空間漫漶,影像拒絕形成穩定敘事中心。公主有魂無體,卻是核心。特寫捕捉少年耳廓邊緣汗毛逆光閃爍,魔鳥們貼近耳邊低語,啾啾喳喳「代言」不可名狀情境,也似夢中反覆出現的片段。
A.S.拜厄特的《夜鶯眼中的幽靈》浮現腦海:博學且幽微的敘事中,人類與非人的視角高度交疊。鳥類與精靈奪回了發言權,人類不再是唯一的敘事主宰,而是故事結構中的觀察與博弈者。這種「敘事權移轉」與高田冬彥的作品異曲同工——當非人聲息(魔鳥)成為詮釋核心,主客體的位置於焉震盪;當敘事不再定錨於理性,情慾、情感與身分認同,也隨之進入浮動且自由的過渡地帶。

高田冬彦,《公主與魔鳥》,2021/2025,單頻道錄像,Full HD,鳥籠,18 分鐘,循環播放,尺寸依空間而定 © Fuyuhiko TAKATA,藝術家及WAITINGROOM版權所有。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攝影呂國瑋。
▌線所記得的時間
法國藝術家西爾維・賽利格(Sylvie Selig)的刺繡與裝置帶來另一種時間感。站在《達芙妮》(Daphne, 2025)三聯畫前,我不自覺靠近辨認互相纏繞的各色線條的路徑,它們不指向明確圖形,而停留於「尚未結束」狀態。達芙妮變成月桂樹(逃避阿波羅熱烈追求)的神話時間被拉長,逃離不再是一瞬,而是一段漫長的進行式。思慕,因而也是未完成。
這也讓我想起朵卡萩小說無數偏離主線的段落──故事斷斷續續暫停,轉向不起眼物件、傳說旁支與難驗證的說法。敘事權威鬆動,歷史顯現多重宇宙入口,也因此積攢了極為可觀的故事時間。
賽利格刺繡也讓我想起韓麗珠小說《縫身》中縫補、身體與裂痕的書寫。縫線非遮掩裂痕,而是保存裂痕,確認身體與時間持續存在。另一件作品《我的花園有隻獨角獸》(There's A Unicorn In My Garden, 2024)靈感源自詹姆斯‧瑟伯的短篇:男子堅信在花園見到獨角獸,無視他人否定。持續相信,在刺繡中轉化為可感知的線條,在每一處穿針引線的時間落實。刺繡線條因而象徵信念的堅持,與情感自主的決絕──這也成為《達芙妮》三聯畫的另一解讀路徑。

西爾維・塞利格,《達芙妮》,2025,刺繡、漿硬薄紗、蕾絲、線,每幅 250 × 150 公分,藝術家版權所有。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攝影呂國瑋。

西爾維・塞利格,《我的花園有隻獨角獸》,2024,刺繡設計與骨、麻布,80 × 70 公分,藝術家版權所有。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攝影呂國瑋。
▌缺席仍然在場
丹麥藝術家西蒙・迪布羅・莫勒的《骨之袋》讓我停留良久。暗室微光、濃濁呼吸聲,以及起伏的金屬質地皮膚與氣孔、無邊雨水忽落忽止,這些感官訊號在空間循環,呈現「活著」的最低限與艱難狀態──既是「雖死猶生」,也是「雖生猶死」。
作品取材距今約二千三百年前鐵器時代人類遺骸,轉化為數位影像,僅讓其「單純存在」。這讓我想起吳明益小說中反覆出現的物件──被翻閱過的書、失竊的腳踏車、森林中的殘骸。在吳明益筆下,這些並非死物,而是時間的標本,它們無須完整解釋,卻以一種「缺席的重量」提醒某些事曾發生,且仍在場。莫勒的遺骸影像亦如出一轍:其中並沒有完整的故事,而是為了讓觀者在胸中直觀感受那份難以消化的、時間的塊壘。這種「物」的沉重在場,迫使我們直面觀看的倫理。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指出,攝影(或影像化)往往帶有一種「掠奪性」的凝視,易將痛苦或歷史抽離脈絡,轉化為可供消費的審美標本。彷彿回應桑塔格的擔憂,莫勒的作品在此產生了辯證與抵抗:他拒絕將遺骸轉化、簡化為一則聳動的考古故事,而讓其以近乎幽靈般的存在占據空間,使觀看不再是觀者單向的掌握,而是一場無法輕易安放的對峙──在生與死、過去與現在的震盪間,迫使人意識到自身作為觀看者的位置與責任。

西蒙・迪布羅・莫勒,《骨之袋》,2023,電腦生成HD 錄像、有聲,3 分 54 秒,尺寸依空間而定,藝術家及Francesca Minini 和Palace Enterprise版權所有。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被生成的夢
英國藝術家克里斯多福・庫倫德蘭・湯瑪斯呈現另一種低語般的思慕。畫作取材斯里蘭卡戰爭與殖民記憶海灘景象──先由人工智慧生成,再由藝術家手繪,使圖像承載記憶、想像與敘事斷裂。畫面看似完整,卻更像漂浮於時間縫隙的碎片拼湊而成。
我聯想到卡夫卡未完成長篇《失蹤者》:主角卡爾在一個作者從未親臨、純由想像與二手資料構築的「美國」中漂泊流轉。正如卡夫卡以文字在經驗與地理空缺上織就一座異質之城,湯瑪斯則在歷史的斷裂處生成了一片模擬的故土。兩者皆呈現了「未完成」且「非原真」的景觀,讓個體與觀者在碎片化的宏大敘事中顯得格外孤獨。
站在頂天立地的巨大畫幅前,當觀者移動身體,也持續重組視域與焦點,觀看同時是身體經驗。湯瑪斯的作品從創作起點到完成,亦是迂迴提問:哪些記憶被數位保存、重構?哪些又在演算法中被消解?
這更是一份警示:當歷史能被演算法輕易生成,辨識真偽將愈發困難。他以作品巨大的手繪量體、物質性與耗費的時間,對生成技術展開刻意抵抗——藉由手繪的身體感,將演算法召喚出的可疑「他者風景」,轉譯為一段屬於此時此刻、具備溫度且無可取代的創作者個人見證。並且突顯:那些因證據匱缺而被輕易略過的歷史,仍具有龐大且無可忽視的實存意義。

克里斯多福・庫倫德蘭・湯瑪斯,2024,壓克力彩、畫布,350 × 777 × 4 公分,藝術家版權所有。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我在這裡,卻不知道
離開展場,身體仍攜帶那些縫線、筆觸與影像交錯的節奏,像停留在歷史與夢縫隙中,不必急於整理。觀看因而可以是緩慢而連續的長期行動:不追求完整故事,也不急於理解,而在斷裂、缺席與漂浮中感受當下。每個斷裂、離開、保持距離,都成為思慕的理由,以及重返的契機。
站在作品前感受到疏離與陌生,其實正提醒每一次躊躇都是對敘事重新衡量──誰被看見,誰被忽略,誰作選擇與控制,誰的曾在被保存或消解。這也是卡特、朵卡萩、拜厄特或卡夫卡帶來的啟發:故事從不中立,其形式隱含權力與政治,有無數選擇、壓抑與妥協,也可能是守護與抵抗。
在此,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的事」──那些無法完全掌握、尚未言說,卻被允許存在、被邀請停留的空間。「允許不知道」,本身就是靠近,一種對敘事、對世界保持敏感與負責的方式。
回望展場,空氣中仍留一縷低音,未知與此刻同在,在時間與記憶縫隙間,悄悄迴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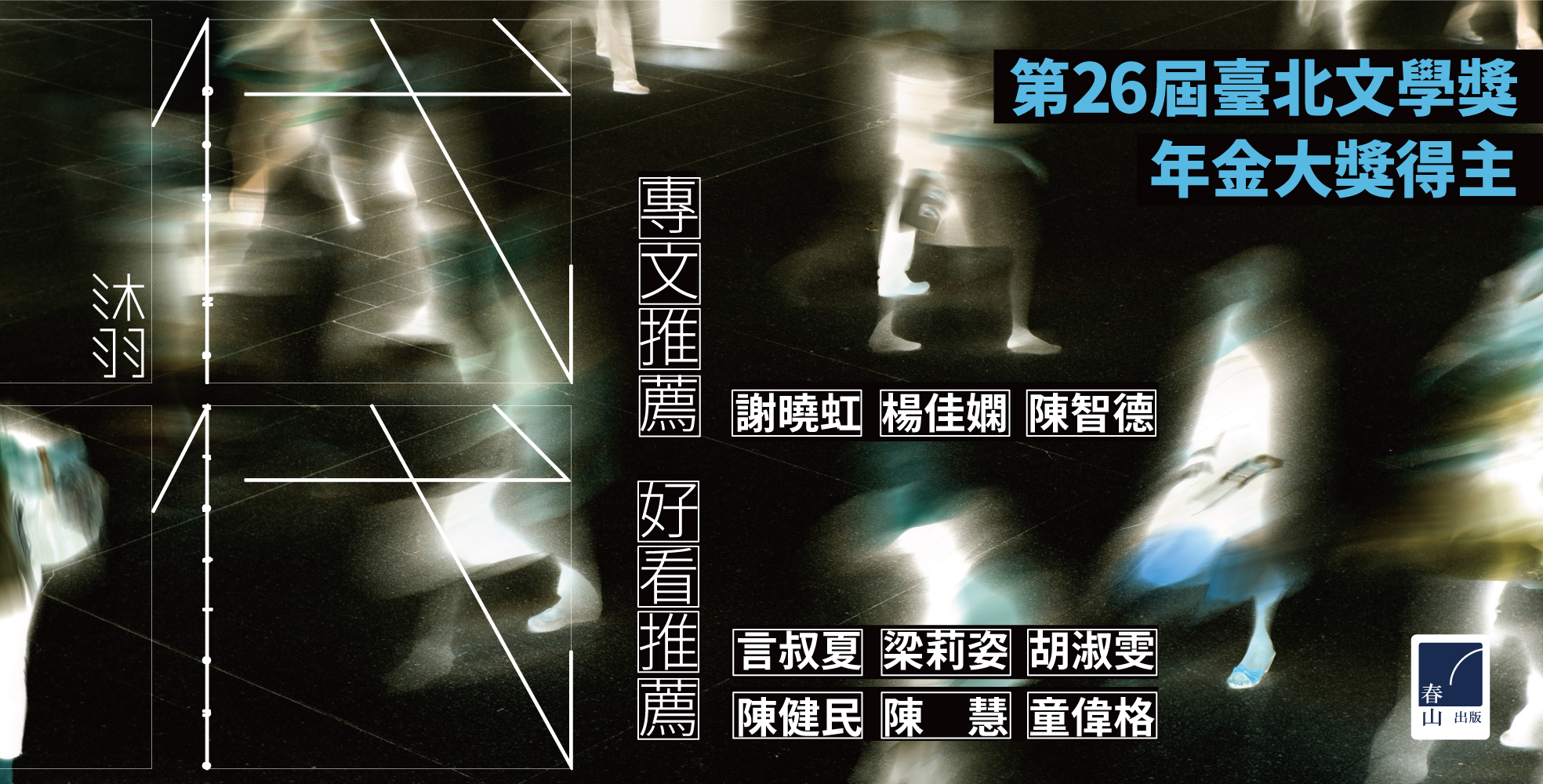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