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次,這是我目前重刷《魔法公主》的次數。
120次,這是我重刷《紅豬》的次數。
22次,這是我重刷《風起》的次數。
80年,這是廣島長崎原爆至今的年數,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的第八十年。
在局勢隱隱不安的二戰終戰八十周年,我想回顧我摯愛的幾部吉卜力電影,同時談一下對於戰爭與反戰的思考。
說吉卜力動畫電影陪伴了七零年代的觀眾長大,一點也不為過,然而吉卜力公司的作品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級的經典,並非來自中年人對童年情感的懷舊,而是來自電影開啟的迷惑命題——所謂戰爭,所謂世界,所謂個人選擇,到底是什麼?
關於世界大戰的思考,有幾部可以相互對照共讀的改編影劇。例如2022年描寫一戰的《西線無戰事》,改編自德國小說家雷馬克的反戰同名小說,充滿寫實的斷肢與爆破壕溝戰。而2023年的電影《奧本海默》,則改編自凱.柏德和馬丁.薛文共同撰寫的傳記《奧本海默》,以傳記體討論物理學家如何帶領團隊為美國建造原子彈,以廣原與長崎的原爆空襲結束二戰,同時也開啟了核武競爭的全新恐怖時代。
《奧本海默》原作紮實記載了物理學家與國家機器工作的過程,包含國家機密文件、親友訪談,如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一看,這不僅僅是一部傳記,而是一頁的近代史縮影。尤其是奧本海默在戰後被政府監視、被中傷算帳的紀錄篇章,相信許多台灣讀者會有強烈既視感。
世界大戰的毀滅幅度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主戰場在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擴及全球,熱武器從槍砲發展到不可控制、足以毀滅全球的核子武器。奧本海默所協助研發製造的原子彈,帶來勝利,代價是日本廣島與長崎人民的死亡。第一枚原子彈落下時,當場奪走廣島七萬名民眾的生命。後續的放射線與落灰則持續作用,造成二十多萬人陸續死於原爆後遺症。當時位於爆炸中心三公里處的青年詩人峠三吉,目睹了原爆的恐怖,以及後續救護現場的煉獄場景,在憤怒與哀慟之下,寫出了《原爆詩集》並自費出版,描繪少女的屍身脫糞且無人能收殮的醜態,描繪碎裂的肢體與腐爛的傷口,詩人直白地發出呼喊:「把爸爸還來∕把媽媽還來∕把老人家還來∕把小孩還來∕把我還來∕把那些與我有關的人還來∕只要還有人∕還有人的世間∕把不會崩壞的和平∕把和平還來」
這樣的血,染在誰手上?是杜魯門?是奧本海默?是昭和天皇?是東條英機?還是堀越二郎?
▌戰爭時代中所謂的「個人追求」,是不可能存在的必須存在
10,449架(一說10,938架),這是零式戰機總生產量。
《風起》動畫劇本主要改編自堀辰雄的小說原作《起風了》,並部分取材了作家另一部小說《菜穗子》。動畫內容以半傳記、半虛構的方式,講述昭和時期日本的航空工程設計師堀越二郎的成長,以及在三菱重工企業帶領設計部門,開發生產零式艦上戰鬥機的故事。
既是改編,則諸多情節不與現實相符。宮崎駿筆下的主角堀越二郎,其實是用來回答宮崎駿對於戰爭的質疑—戰爭何義?何謂反戰?個人抉擇在戰爭之中又有何意義?
《風起》之中,主角堀越二郎與心儀的偶像—義大利航空工程師卡普羅尼伯爵,多次在夢中相會談話。最後一夢裡,伯爵問起二郎是否有把握自己的黃金十年,在體力與智力都達頂峰時完成夢想?二郎回答:有的,雖然最後心力交瘁,但我盡力追求了我的夢想。此時畫面是美麗的零式戰機一一滑過天空,逐漸形成壯觀的飛機流雲,最後匯聚為一片閃爍的飛機海。
二郎說,我主導設計的零式戰機,一架都沒有回來。
那一萬多架向上飛升,再也沒有著陸的飛機雲,全由陣亡的駕駛員、以及工程師團隊全力打造的美麗飛機構成,他們魂魄歸屬於天空。這個奇幻場景,其實是宮崎駿對於1992《紅豬》的遙遠回響。在《紅豬》中,主角義大利飛官波魯克因為目睹同期優秀的飛官全部在戰爭中犧牲,最後國家政治的情勢卻走向了荒謬可怖的法西斯獨裁政權,憤而施法術,讓自己變成豬,宣布再也不參與人類的事務。這是憤世,是隱遁,是對於自身才能被政客所操弄的憤怒與消極抵抗。夜夜笙歌、貴客雲集的亞德里亞海酒店,則是戰間期失意者的美麗魔山。
《紅豬》中,宮崎駿以一個超自然經驗來解釋波魯克如何在空戰中孤身一人回來。他在戰鬥到最後的眩暈中,看到了不可思議的高空流雲,全部由戰機殘骸組成:有己方的,也有敵方的飛機,以及更加古老的異國戰機,而一齊出戰的童年好友正緩緩升空加入上方的死者,自己的飛機卻不斷下沉,無論波魯克如何催動引擎、如何喊叫也沒有用。生與死就這樣分開了,沒有回家的飛行員成為雲,回到家的飛行員在憤怒與內疚中把自己變成豬。
所謂飛行,是立體的概念。假設,你在都市抬起頭,看見天上飛著一隻麻雀,而不遠處有一架飛機,兩者看起來似乎要交會相撞了,但你知道不會撞的,因這兩者所在的高度不一樣。鳥與飛機往往不是同一個平面,而這兩者一旦真正交會,就會是歷史性的爆炸。
吉卜力工作室的戰爭主題作品中,我始終感覺到,動畫創作就是那一隻麻雀,輕輕飛掠過真正的飛機時,你會感受到相似的氣流,你會聯想航道的相遇,可是那中間存在著不可能相遇的「空隙」。
2013年的《風起》,宮崎駿回頭爬梳日本在二戰的野心與創傷。《紅豬》裡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監視,換成了日本特高秘密警察的監視。而在國家機器發展軍武的政策之下,單單一次德國容克斯公司的戰鬥機技轉的金額,足以讓全日本的孩子每天吃上天婦羅蓋飯與蛋糕,一整年都不會挨餓。宮崎駿利用劇中三菱工程師憤世的對話,抨擊軍國主義選擇犧牲國內民生發展,將資源投入侵略行動的錯誤政策。而,作為勢必會被捲入戰爭的一流工程師,你要如何抉擇?要選擇辭職抗議不造飛機,像《紅豬》的波魯克一樣隱遁逃避?還是奮力向前發展自己的長才,爭取那一個成功機會?
那就是麻雀與飛機之間的空間,是後代創作者在觀看歷史、以自身角度理解歷史時,會產生的「空隙」。
而不同的空隙處理不同維度的問題,我認為《風起》接下了《紅豬》尚未能處理的部分,並且深化了所謂「反戰」的探討。《風起》是一部悲觀主義之作,明知道貧窮的日本打不過船堅炮利的美國,但人民也無法翻轉日本軍國主義內閣的決策,作家李拓梓曾在《改變日本歷史的總理大臣:從伊藤博文到岸田文雄》一書中,以六十四位總理大臣的任期為基礎,細述了日本近代史的內閣人事更迭;閱讀此書,就能深切理解《風起》中以諷刺手法描述海軍與陸軍大臣只顧著爭權奪利,而基層的工程師能做出甚麼選擇?
與其讓政客製造出爛到不行的飛機送年輕軍人去死,不如盡己所能製造出優秀的飛機,爭取戰勝的機會。這是《風起》悲觀主義下的堅強,這是充滿希望的人本精神。而這樣的微弱希望也只會存在後代創作的「空隙」之中。畢竟歷史都是後設的,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展出原子彈?如果,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戰勝了呢?那麼,今天的世界情勢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三菱重工造出的零式戰機,具有高度靈活性與速度,極難纏,在空戰確實有贏面。而這個「如果」,就是《風起》創作的核心—堀越二郎必須面對的時代之難與個人之難,同樣的,也是《奧本海默》必須面對的艱難。奧本海默與堀越二郎,都是研發神之武器的人,但是他們也都背負了罪,因為,神之武器被製造出來,就會被操控,就會犧牲無辜之人。
《風起》中,二郎的同期工程師好友本庄,聽到二郎在路邊想把剛買到的西伯利亞蛋糕施捨給貧窮的小孩遭拒,直接痛批二郎的行為是「偽善」。今天你救得了一個小孩,但是全日本的小孩都在挨餓,你怎麼救?你區區一介工程師,能翻轉軍國主義政客的盤算?為了打贏戰爭取得富庶未來,日本得先造出神一樣的戰機,而神一樣的戰機,基礎卻構築在眼前孩子們的飢餓之上,全然的諷刺。
依照《紅豬》的邏輯,二郎可以選擇隱遁,可以選擇不要造出好飛機,讓日本輸得更快一點,然後全部的人一起挨餓更久。本庄用嚴厲的話語說出了二郎的抉擇之難:你可以空度此生唯一的黃金十年,選擇不影響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你的無作為變得更好。
那,世界有因為二郎的作為變得更好嗎?答案是沒有。日本戰敗了,零式戰機一架都沒有歸國,二郎並不想要送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去死,可是,血也沾在他的手上了。
《風起》之中,我覺得宮崎駿最為大膽僭越,也最為感人的一段劇本,是零式試飛成功以後,飛行員走下來,對二郎握手說:「謝謝,這是非常好的飛機。」
那是導演虛構的情節,因為沒有飛行員活著回來對工程師說出這句話。但,仔細想一想,坐上零式戰機的年輕飛行員,難道會咒罵工程師造出如此優秀的戰機讓自己去送死嗎?不,優秀的戰機是每個飛行員的靈魂伴侶,是他們在不可違抗的軍令之中活命的關鍵。那是飛機設計者和使用者共同的夢。
那個夢已經碎了,堀越二郎的黃金十年換來了一場殘破的夢。所以,劇中的少女菜穗子,不是真實人物。我認為宮崎駿把菜穗子剪接進《風起》的劇本,是讓病弱卻充滿希望的少女菜穗子成為零式戰機的隱喻,同時也是日本國運的隱喻在國家與國家的競爭之下,所謂個人追求,所謂夢想,所謂相愛,都不可能,那只會發生在遺忘一切的魔山。戰爭時代中所謂的「個人追求」,是不可能存在的必須存在,艱難的地方在於:明明知道結局是悲劇是殞滅,我們仍然滿懷勇氣,把握時間相愛。
▌逃避不是反戰的最佳手段,平衡才是
最後,岔出來談一談我深愛的《魔法公主》,同樣在談戰爭,只是幅度更廣,將戰爭從人類之間的殘殺,推到了人與環境的競爭生存。
《魔法公主》劇中的山豬神,因為棲地遭受人類的開發,族群滅亡,怨恨使山豬神化身詛咒邪魔,惡臭的詛咒會毀滅有生命的一切。為了保護村莊而射殺山豬神的蝦夷族少年阿席達卡,被迫背負詛咒,踏上追尋答案之旅—古神守護的「山獸神森林」,以及新興發展的人類城鎮「達達拉城」之爭,正是全局的「劫」之所在。
圍棋中有一個棋型叫做「打劫」,雙方棋子各擁一定的優勢,死掐著對方的喉嚨不放手,在勒索中進行談判。打劫意味著你必須犧牲才能有所得,這種棋型凶險,殺性重。但是,通常走到打劫都是不得不的局勢。當雙方的領地發展到一個程度,明爭暗鬥殺到一個程度,「劫」就會成形。古人說流年大劫,大概就是引用圍棋的這個意思。
達達拉城象徵人類的興盛,該城以煉鋼技術發展熱武器,成為戰國諸侯間的兵家必爭之地。而領導達達拉城的「黑帽子大人」,是人類政治家的代表。她能覺察未來的世界局勢所需,以煉鋼做為基礎,建立城鎮的經濟與防禦力。同時又要與天朝打好關係,避免勢力過大遭到征討,黑帽子大人象徵「人類」的存活,人類只要活著,就會對自然需索,就會對自然產生擾動,這一點是不可能改變的。
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競爭關係無法迴避,當人類族群壯大,對資源的需索提高,衝突就開始了。黑帽子大人不可能放任達達拉城萎縮或停滯不前,因為那意味著這個城鎮未來會被其他諸侯勢力併吞。在戰爭之中,只有強大的一方才有資格談和平。黑帽子的領導位置是要確保達達拉城的強大,這一點使她對自然環境採取極為強硬的態勢。另一方面,山犬莫娜保衛的「山獸神森林」象徵的是人類絕對不可能撼動的整體平衡,自然環境的力量遠強於人類,當人類發展太過、打破平衡時,自然會以洪荒之力反撲。雙方爭戰的結局是達達拉城被毀,山獸神亦不復存,這樣兩敗俱傷的結果,阿席達卡說出一個極為平淡的結語:「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
看似廢話、軟弱無力的結語,在《風起》之中,竟然藉著菜穗子的聲音再次出場了:「二郎,你要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你才能有所作為,只有活下去,你才能作為「存在」去干涉世界的各種存在。只要世界有人類,有生命,必定會有競爭,戰爭是絕對不可能消失的。只有活下去,你才能成為翻轉棋盤,取得平衡的棋子之一。
真正的反戰,其實是阿席達卡一再呼籲的,卻被雙方所恥笑為空談的呼籲:「山獸神森林與達達拉城,難道沒有共存的方法嗎?一起活下去吧!」黑帽子聽到阿席達卡的並存言論,反應是嗤之以鼻。守護森林的山犬神莫娜聽到阿席達卡的共存言論更忍不住放聲大笑,她們都是身陷劫爭中的戰士,也都死於劫爭。而目標是「平衡感」的阿席達卡,以及身跨兩個敵對族群的混血少女小桑,活下來了。
一路看宮崎駿從《紅豬》的避戰,走到《魔法公主》的劫爭,再發展到《風起》的個人抉擇之問。我認為,在人類世界真正可能實現的反戰,絕不是一味避戰,更不是主戰,而是戰爭開始之前,就盡可能強壯自身,並且在必要時進行最有效的戰鬥。所謂和平,是於無窮無盡的爭鬥之中,取得勢力的平衡。「活下去」何其沉重,絕不是一句溫情空話,對於反戰,正確的答案恐怕正是在平庸的「活下去」裡,履行個人的抉擇,一日復一日,在細微之處爭鬥、防禦、再爭鬥,養育趨向「和平」的可能。
作者簡介
1984年生,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曾獲楊牧詩獎、府城文學獎新詩獎等。著有散文集《玩物誌》;詩集《如蜜帖》、《如廁帖》、《妖獸》、《失語獸》、《負子獸》、《雞卵糕仔雲》等八冊;主編詩選《媽媽+1》;藝術文集《藝術家的一日廚房》;插畫作品有《暗夜的螃蟹》、《虎姑婆》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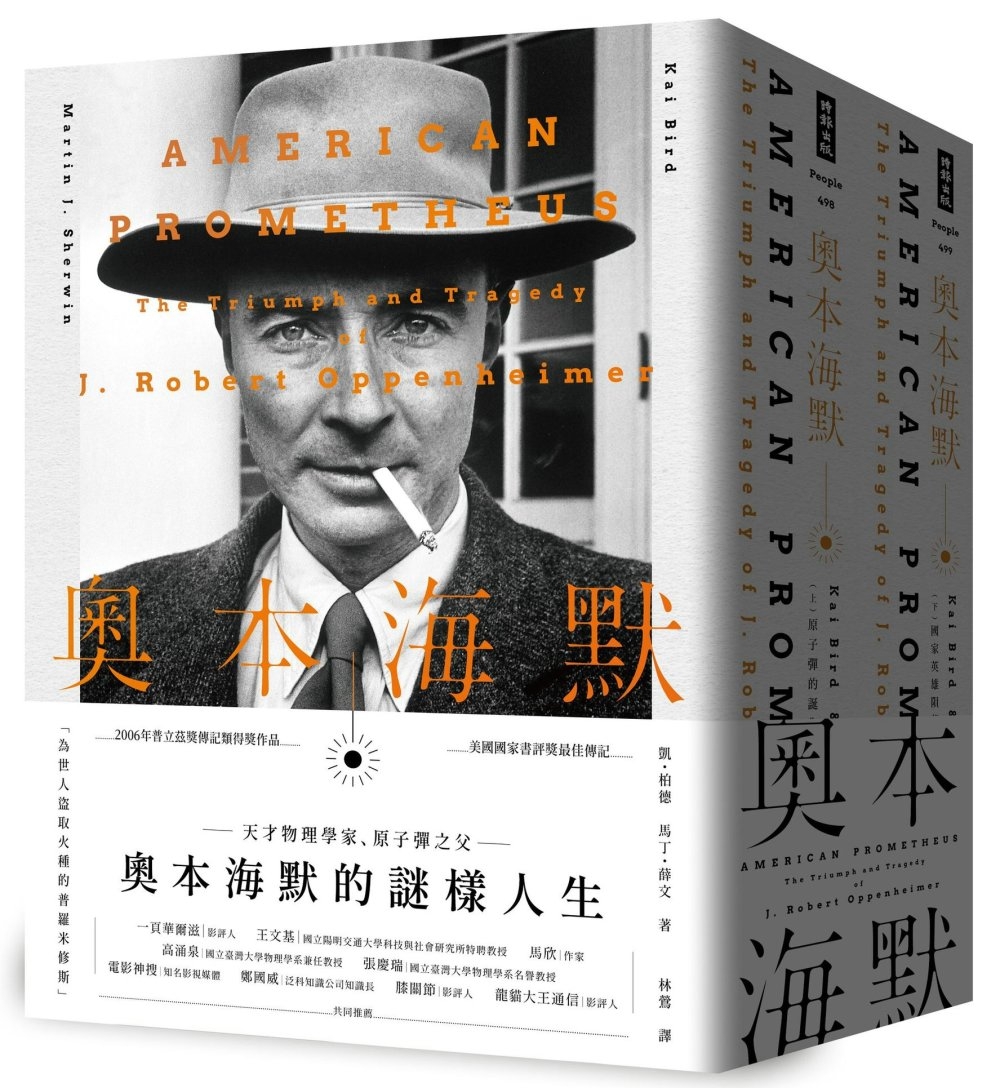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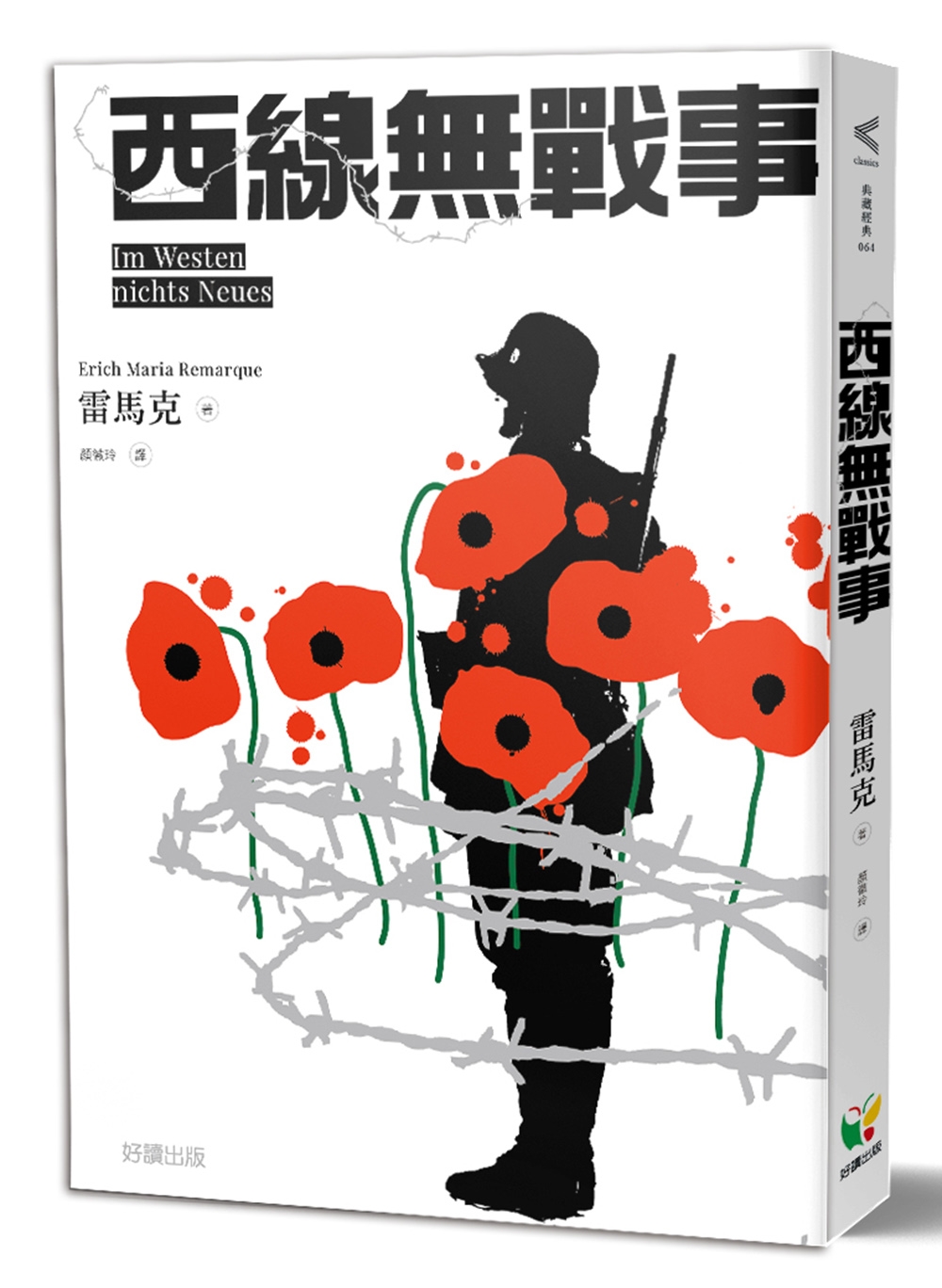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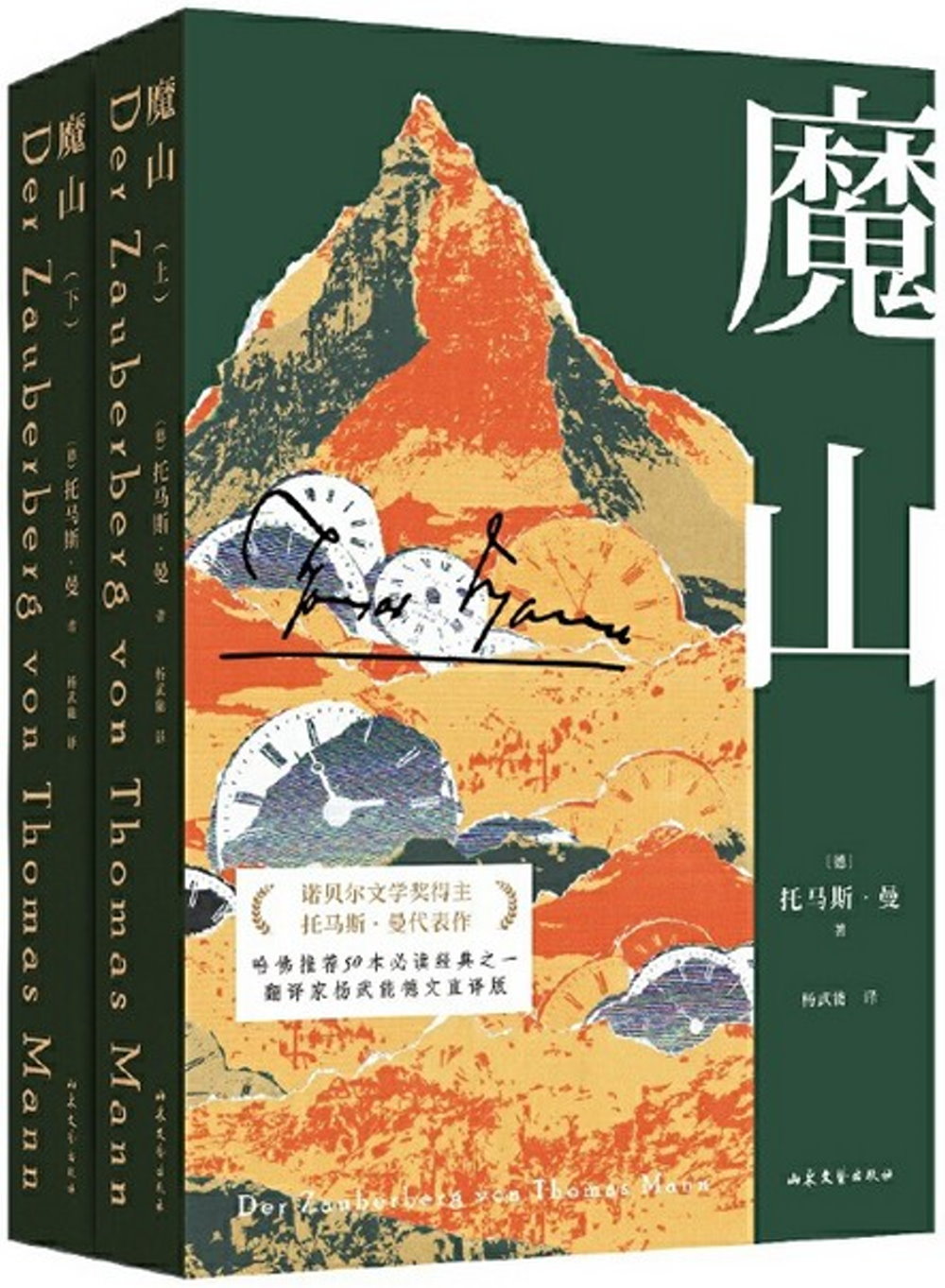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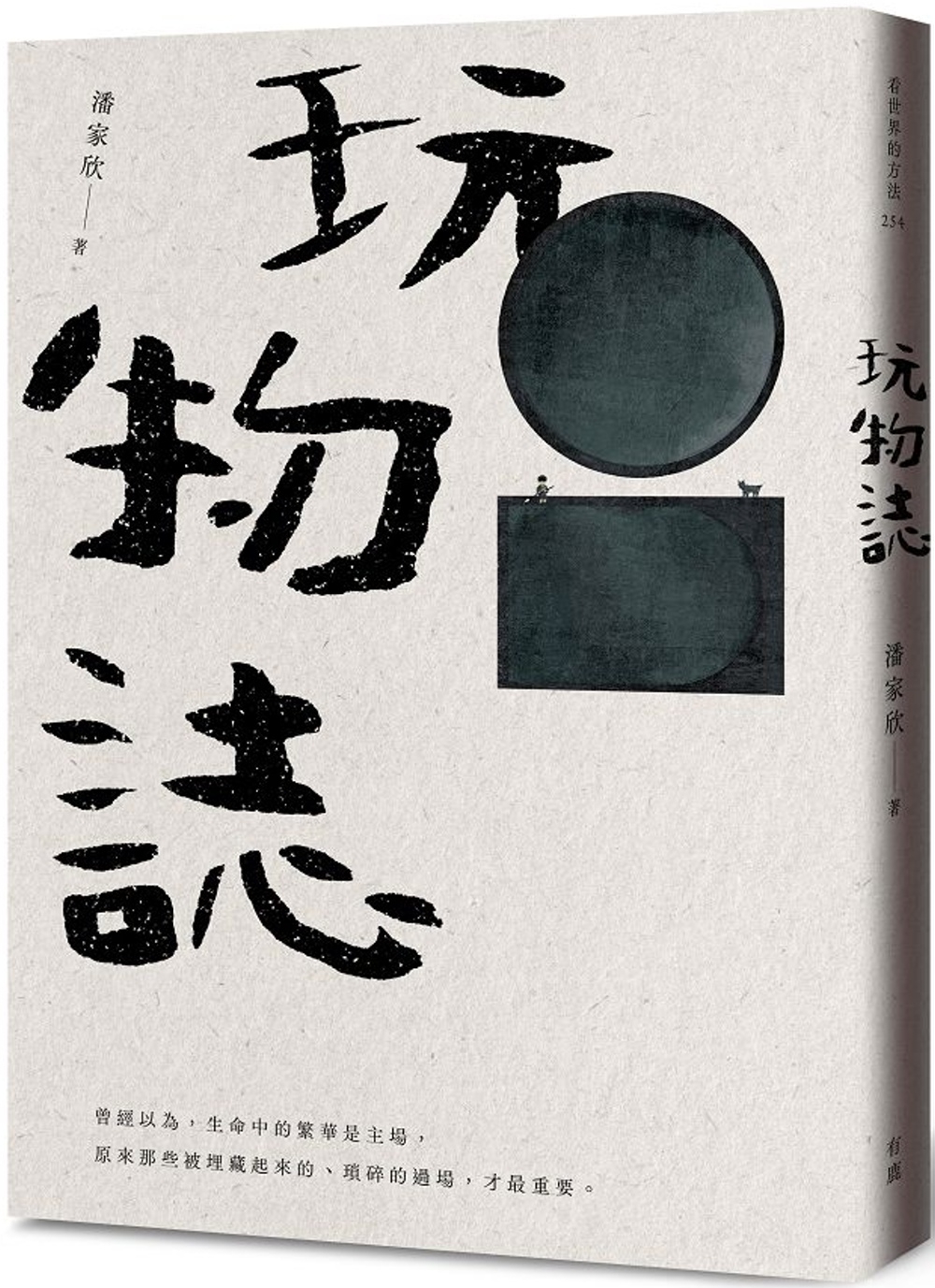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