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在三月出版了《受苦的倒影:一個苦難工作者的備忘錄》。七月,我與作者魏明毅在三餘書店對談,主題是「那被稱之為發作的受苦」。感覺極巧,這本書我最先讀的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在談發作,談受苦,談「人與其苦難,可以發展出什麼關係?」前陣子我陷入自己人生的困境,很久沒有那種陷在困境中,想脫離卻找不到施力點的感覺;與其說害怕那個困境,不如說害怕自己的無力。而「人與其苦難,可以發展出什麼關係」這句話令我感到好奇,因為多半時候人們只想逃離痛苦,誰會去思考自己與苦難能發展出什麼關係?
▌混亂中有誠實的聲音
我翻開第三章,開頭是兩段備忘──
(一)
我們都害怕混亂,喜歡安穩清晰;
然而,混亂裡有誠實的聲音,
我珍視它,如同珍惜安定的時刻。
如果你在那樣的時刻遇見我,沒問題,
你可以用瘋癲來形容我,那是貼切的語彙;
但請不要,誤以為在那瘋癲底下,什麼都沒有。(二)
後來回想起來,有哪一次自己不是從那細瑣磨難裡又活了下來。一想到這裡,便不再害怕自己的害怕。
我突然有種被理解的感覺。雖然作者所描述的「我」,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發作的人;但我也因此突然明白,混亂是因為有什麼變化了,改變了。我意識到常人也有混亂,也有苦難;當我們陷入混亂,我們討厭,只想趕快脫離,卻忽略了混亂裡誠實的聲音。但倘若我能細細感覺與檢視自己的混亂,便能從那倒影中辨識出真實的影像。混亂是倒影,當我能看出真實的害怕,就有機會不再害怕自己的害怕。
《受苦的倒影》是魏明毅在諮商與社會工作時觀察到的備忘錄,但當我思索對談角度,我想連結到「一般人小小的苦難」。因為苦難離我們並不遠,不是那些被貼上標籤之人的特權,只是在某些人身上特別重、特別難、特別長。而常人所各自面臨的小小苦難,若未能找到觀看、理解、與之相處的方法,那原本極其微小的苦難也可能蔓延開來,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而除了連結到個人的苦難,我也想談談個人如何看待他人的苦難,這個他人包括家人、親近的朋友。關於他人的苦難,我該旁觀還是涉入?涉入又能「解決」什麼呢?是否有除了「旁觀」與「解決」這兩者之外的其他選項?這是我一邊閱讀一邊思考的問題。
▌什麼是「發作」?情緒是一種發作?
關於「發作」,書中有這麼一段備忘:
「症狀/發作」所需要的,並不總是趕緊刪去以由失序恢復到有序;相反的,它是生命的逸出求生之處──指出那些被普遍略去的珍貴覺知,是檢視生活世界重要且關鍵的線索與證言。
「發作」令我聯想到「情緒」。我回顧五月所寫的日記:
我意識到,我太想「解決」自己的困境,我不想待在這令我心神不寧的狀態,我想要排除狀況,我想要穩定。而當我想突破卻找不到頭緒,我就生氣。不同於白天的談話,晚上的我整個人在情緒中,我不想要在情緒裡,但無法。情緒是我的一部分,而我不想接受它。
我意識到自己不想被困在困境裡,我想趕快脫離,快速找到一個方法。我不是真正接受自己的狀態,我把自己視為問題。因此我才會如此焦慮。我擔心我卡在這裡無法前進,我想將這樣的自己從這樣的困境「救出來」。
但這不該是困境,雖然我確實感到痛苦與辛苦。真正困住我的,是那個想要逃出去的我。我不知道該怎麼做,覺得自己很遜。我對自己不滿意,我不喜歡不滿意自己的自己。
──2023‧0524
我檢視自己的日記,發現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關,不論再小,苦難總是難。對當下的自己來說,那就是一個過不了的關,卡關時情緒便隨之而來。而人們總是急著消除「症狀」與「情緒」──大人對小孩說:「不要哭,有話好好講。」大人對大人說:「哭不能解決問題,你該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人們沒有時間去看症狀底下、情緒底下的東西。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餘裕,就有機會好好面對自己的關卡,有機會去「辨識」它──究竟是事件本身是關卡?還是自己對待那件事的想法使它成為關卡?魏明毅在書中如此備忘:
唯有視情緒為必須捨去的困擾時,人才真正受縛於其中。是人對它的回應方式,定義著情緒將如何作用於自身與世界的關係。
人需借助著那些來來去去的灰階意念,去促成意識與行動;人需要節制將自己作為宇宙或世界的中心,既關注到自身且略過自身,那不是克制或忍耐,而是當人將眼光從自己身上移開,去對身體所寓居的歷史、文化政經有所感知與回應,能動即有機會由中而生。
這段話令我受用──當我將眼光從自己身上移開,我發現困住我的,是我仍然在意主流價值的眼光。我以為我沒有框,但其實有。而魏明毅說:「當你覺得被困住了,通常代表目前所知道的,不夠回應,那,就去補。用想像,用對生活的在乎,用知識,用你擅長的邏輯、用思考、用知識去補。」
受苦之所以難,不在於困厄,而是人們盼望那能揮之即去,但無法。而當我們仔細去看生活,會發現困境不止於單一感受,更多的是五味雜陳,你會發現自己的在意與在乎,會認識自己的不同面向。處在痛苦中時,經常只感覺到痛苦而感覺不到其他,但當我有餘裕細切與感受,會發現痛苦中不是沒有別的。當我察覺到這樣的狀態,儘管痛苦還在,但不那麼大了。
魏明毅說:「將度量的尺度收縮地愈小,愈能發現人與困境,是瞬間即變的動態關係。」瞬間即變,因此能動。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取回直視痛苦的權利,即刻重生
但所謂的「瞬間即變」是什麼意思?如何能瞬間即變?
書中有個案例:
當小新開口問能不能找我會談時,說的是:「我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而不是「我到底怎麼了」。直到第一次談話之後,我才明白這兩句話在本質上有根本的差異──「我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指的是在受苦中,人在心智與行動上,決意將自己重新生出來──躍過原本父母臍帶所孕育的第二次出生。
人可回應的方式之一,是取回那直視痛苦的權利,將自己重新生出來──指的不是刪檔重來/return,是立基於對以往受苦的來龍去脈、瞭若指掌後的有意識的即刻重生/rebirth。
讀這段時我想到:有些人處於極度邊緣極度痛苦的狀態,能有直視痛苦的力量嗎?能做到所謂的即刻重生嗎?我曾經感到悲觀。但魏明毅不斷在書中提到「能動」──作為一個苦難工作者,他相信人是能動的主體,或是說,他必須先如此相信。而就算還沒有直視痛苦的能力,但當人感覺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就有改變的可能;如同小新開口求助,就有機會將他人的幫忙轉變成自己的力量。
我聯想到日劇《重啟人生》。重啟人生,並不是毫無所知的從頭來過,而是在「已知過去曾經」的情況下,再活一遍,再做一次選擇。但重啟就一定能做出「對」的選擇嗎?人生不是「對」與「不對」的問題,而是在選擇之後,如何去承擔與回應。當然現實人生不可能重啟,但某些境遇會重覆。當人面臨似曾相識的困境,是否能從已經有過的經驗裡,「即刻重生」?
▌當苦痛被指向個人,意味不良的社會結構被漠視
我找到觀看與回應自身困境的方法。那麼,我能夠如何看待與回應他人的困境?關於他人的苦難,魏明毅點出的是社會結構。
讀大學時,我曾經試圖想「幫助」一個朋友。現在回頭看那段歷程,我發現我把他當成一個需要被幫助的「病人」,而不是一個「人」。我陪他去看身心科,第一次進到診間,醫生在診單上寫著「情感性精神分裂」(現稱思覺失調)。我看著那個病名,以為自己就此明白他的病。但其實我不懂,我只是得到一個名詞。我看到的是名詞,是現象,我看到他發作就叫救護車急診,而我不明白為何要如此頻繁急診;我看著他急診住院,無法上課,反覆進出醫院;我看著他因吃藥的副作用,導致遲鈍、變胖、對自己沒有信心。他的家庭只能給他做最低限度的經濟支援。我看著他進一步退兩步。
當時我天真的以為,若他能養成自律生活,就能妥當控制自己的病情,但前提是先有基本生活所需,穩定的住處、實習工作的機會。我以為幫他回到正常生活,他就能像個「正常人」。我與朋友一起寫計畫跟教會募款,以一年為期,提供住宿費與生活費,為他找房子與工作。而當他因藥物副作用不舒服而自己停藥時,我說你是醫生嗎?為什麼自己停藥?我不認為他有與醫生討論病情的能力,只覺得他應該要聽醫生的話。當他無法達到預設的工作目標時,我覺得他不認真努力。他的生活一團亂,他在租屋處囤積了許多廢品,他不會整理自己的生活空間。我覺得自己處處為他著想,而他不替自己想。一年過後,我放棄了。
現在回看,我才發現當時的自己將生病這件事指向個人,認為只要努力就可以康復;而「康復」也不是以當事人為主體,而是以這個社會對一個正常人該有的樣子去判斷。我並未將朋友視為真正的主體。我認為他對未來的夢想毫不實際。
魏明毅書中提到的「小新」是個重鬱患者,但他與小新互動時不是將他視為病人。他問小新喜歡自己現在的生活嗎?有什麼是自己想要找回來的呢?小新說:「我喜歡寫歌詞,想學吉他。」「現在的房間有合適的地方可以做這些事嗎?」「沒有,不過,我想我應該可以整理出一個地方。」「如果你喜歡,那就去生出那樣一個空間吧。」
魏明毅沒有質疑小新是否真能做到。沒有一開始就否定。
像小新這樣一位被診斷為重鬱的「患者」,若在診間內,能不被以簡而易之地消去「不美好」症狀為終極目標;在診間外的關係裡,亦並不只是被厚密的同理溫情所呵護包覆、被離地般的病理式分析,而是,被待之以常人──有悲有喜能有所思有所行動,人就有機會在受苦的狀態裡,去決意採取不同行動,逸出社會文化價值所給出的道,返回生命裡的主體位置。
當我試著去了解朋友的苦難,才知道那真正影響他生活與生命的,並不是因為他的病,而是「他人看待病症的眼光」。他高中時生病休學在家一年,他的父母不知如何面對他的病,把他關在家裡。而後是如何進到醫院獲得診斷,已不得而知。但獲得診斷後所面對的,是主流社會對生病者回歸正常生活的想像──你們該有「病識感」,你們該努力「變好」,回歸正常生活。不是生病這件事將他們推到邊緣,而是我們這些「正常人」將他們推到邊緣。
標籤,是一種指認,而非真正認識。生了什麼病,是否確診,都不是讓生命之所以變好的關鍵。「痛苦與災難,考驗的不是司法與醫療的圈禁範圍,而是島上每一位個人的良善、思辨與倫理行動,能否意識到那資本之網所構築的單薄與荒謬。齊同接手推展社會政治文化成豐厚沃土── 一個可納含不同生存方式與生活型態、可接容多樣性生命的喧嘩世界。」
此書我讀得極慢,因為每字每句都是作者經歷與思考的濃縮,為的是點出倒影的真實樣貌。重點不在他們生了什麼病,而是我們如何看待、與他們相處。我們是否將他們視為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是一樣的,而是我們是否能坐在一起,平等對話。
▌社會安全網的隱喻,分界出「被助者」與「助人者」
魏明毅在書寫《靜寂工人:碼頭工人的日與夜》時,曾期待讀者能有「他們即是我們」的共感。後來發現,《靜寂工人》雖然獲得不錯的迴響,但大部分的人並沒有因此將自己與書中描寫的工人連結。因此他寫《受苦的倒影》時,希望做到喚起讀者「他們即是我們」的感受。我不知道其他讀者的反應為何,但我確實因為此書而連結到自身,不只是如何觀看個人苦難,還包括如何回應他人苦難。
從前我覺得回應他人苦難極其困難,無法假裝沒看到,但涉入後又怕自己被耗盡。而魏明毅在書中提到了一個新的概念,他將心理師與諮商師視為「苦難工作者」而非「助人工作者」。他說,助人就是手心向上,就是承接,但只要是人就一定有受不了的時候。但如果將自己視為「公共參與者」,工作的對象不是「那個人」,而是「那人所面對的苦難」,關鍵就不會是助人,而是營造一個大環境的改變,或是透過互動讓當事者能動。
魏明毅也挑戰「社會安全網」的概念。他認為社會安全網的隱喻,將人分類成「受助者」與「助人者」,將其中一方視為接受幫助的弱者,忽略其主體性與能動性;而另一方得承接受助者,並且承擔受助者發生意外或造成意外的風險。但是,「當整體社會仍將精神疾患或弱勢底層界定為社會問題的來源,隨之張開的安全網,不論其處遇介入是來自醫事人員的生理心理介入,或者社工的濟貧,就業促進、安置、家庭維繫與重整,此問題解決的觀點與模式,仍將高度受囿於個人主義。」
我非常認同「公共參與者」的概念。因為不只社會工作者,環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是,若以助人為念,那就像薛西弗斯在推石頭,永遠沒有終止的一天,最後不是倒下壞掉,或是只好袖手旁觀。但工作者若能將對方視為能動的主體,即使短暫的接觸,與之走過一段的陪伴,就有機會讓對方與自己意識到──我們雖然如此軟弱,卻又充滿力量。
「那被稱之為發作的受苦」,有時會苦到想要去死,但若能細看那受苦的倒影,會發現那想終止的不是生命,而是想逃離現在的自己,「尋短,所誠實表述的不是求死,而是尋生──對重啟一個新的生命世界的深切渴盼。」
最後,再分享書中的三段重要備忘:
- 問題叢裡何者是「關鍵」,何者是隨之而起的「煙霧」。
- 讓經歷慢慢推展出生命的軌跡與氣味,需要的是由時間鍛鍊出來的耐心,而不是忍耐。
- 永遠對現象發出疑問,並窮其力探求更清晰而深刻的理解,直至能夠發問。
作者簡介
大學讀了七年,分別是工業產品設計系與新聞系。認為生命所有經歷都影響創作。著有詩集《沒用的東西》;非虛構長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曾獲第二十屆台北文學獎年金,2020年臺灣文學金典獎。
瞇是細細地看,慢慢地想。現以文字為生。
【OKAPI專訪】「真實的去認識一個人吧,然後,再多知道一些。」──專訪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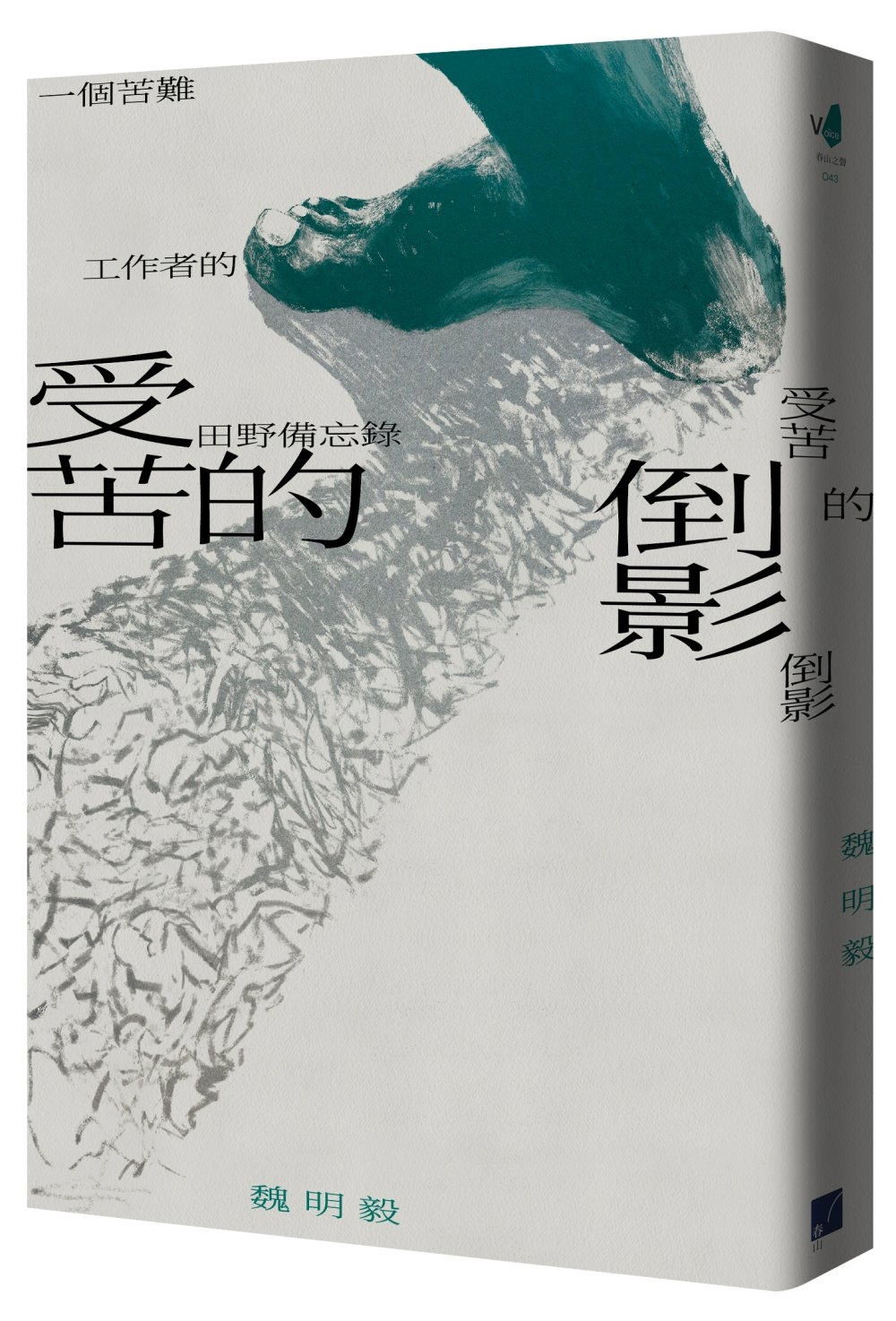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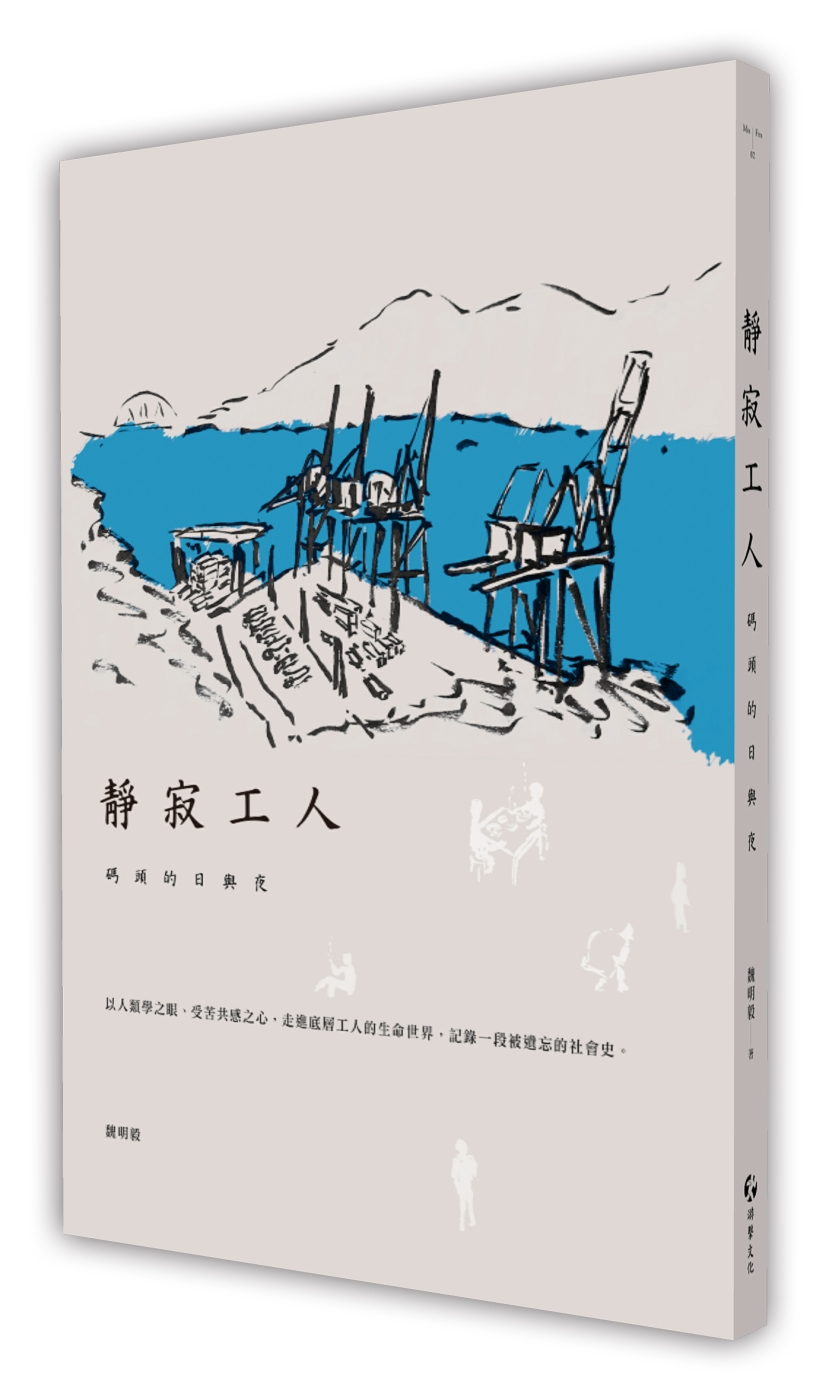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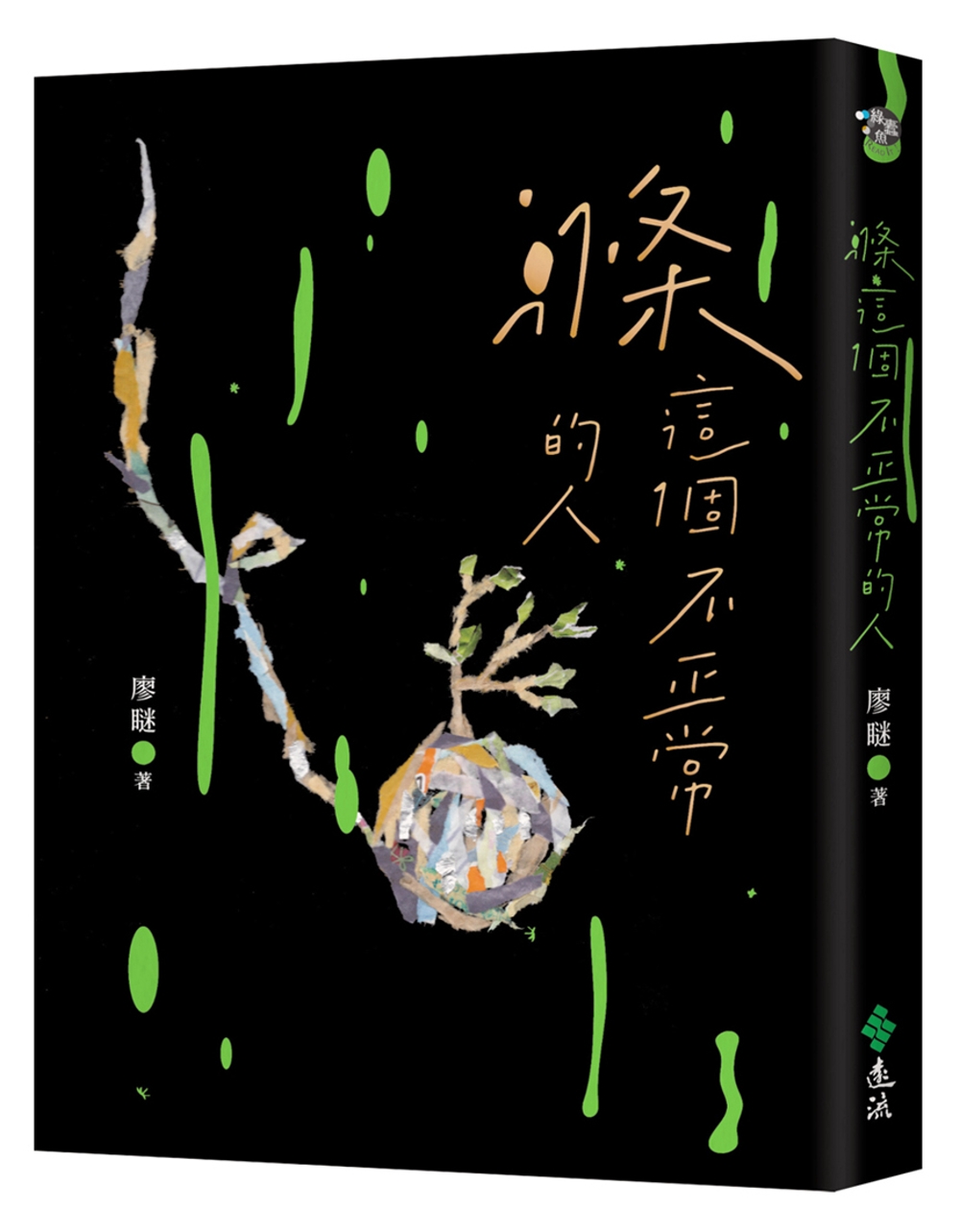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