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末期,日軍為挽救頹勢而祭出殺手鐧,派遣神風特攻隊偷襲,人機同體撞擊美國軍艦,同歸於盡。行前,日軍飛官團隊知道這是此生最後一役,紛紛留下訣別書。透過遺言,久野正信隊長期許兒女「長大後和父親一樣所向無敵,報殺父之仇。」
誰殺誰?報什麼仇?暗算敵手,自願捐軀,有什麼仇好報?難道隊長慫恿小孩立志刺殺天皇?另外,自詡「所向無敵」也不像大和民族的語氣。我翻譯到這封信的英譯版,怎麼讀也不對勁,實在動不了筆,索性投筆尋根去。久野的遺言全文以片假名書寫,方便幼童閱讀,信末盼子女青出於藍,「不輸父親,不枉我成仁。」由於我的日本語能力一級合格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早已蜘蛛網密布,再也稱不上「大丈夫」,所以我虛心請教旅美的日語教授友人糸満真之,證實英譯版有誤。照本宣科就中鏢了。
「二手翻譯」潛藏無形陷阱,譯者很容易誤踩前一位譯者留下的泥淖。這好比接力賽跑,上一棒來了,你伸手向後接棒,接到卻發現是隊友的手機,回頭見隊友一溜煙鑽進人群,怎麼辦?去追討接力棒嗎?或不顧一切跑完再說?接力譯者的辛酸就在這裡。因此,我毅然決定,從此洗手不再做英譯本的二手翻譯。
在飛官遺書之前,我翻譯過以性愛譬喻心靈高潮的《愛的十一分鐘》,原文是我一竅不通的葡萄牙語,作者是以心靈文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享譽全球的巴西作家保羅.科爾賀,英文版譯者是獲獎無數的英國翻譯家Margaret Jull Costa,文筆平實流暢,我翻譯時零障礙,只遇到單複數前後不連貫的幾處,不影響中文。而我對巴西人的認識也趨近零,所以英譯本讓我察覺不到類似「報殺父之仇」的違和感。
對於這種輾轉式翻譯,一般人應該不陌生才對,眾所皆知的例子是古今中外暢銷書《聖經》,原文是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臘文,而中譯版印行最廣泛的《和合本》譯自《英國修訂本》並參考《英王欽定本》。佛經源於梵文,中譯版的根據是東漢時代的西域語,也屬於間接翻譯。遍尋不著通曉原典的譯者時,輾轉翻譯是退而求其次的變通之道。讀者可能認為,華人圈不可能找不到葡語的譯者吧?葡語達人不是沒有,但坐得住、勇於接受薄酬的譯者是稀有物種,文采傲人的小語種譯者未必排得出檔期,何況編輯另覓新人合作的未知數也太多。
到了2019年,春天出版社簽下瑞典驚悚作家約翰.提歐林(Johan Theorin),總編莊宜勳找我翻譯他的成名作《霧中的男孩》。我欣賞瑞典的千禧系列,仰慕挪威的奈斯博(Jo Nesbo),長久以來一直想深度認識北歐推理,如今開門看見提歐林站在門口,怎可能不請他進來坐?我試讀前三章欲罷不能,竟心癢難熬,一口氣接下兩本書約。說好的「不再做二手」呢?
《霧中的男孩》以厄蘭島特有的石灰岩草原為布景,故事滄冷而懷舊,我讀完後,非但不後悔,更堅定決心把這本書翻譯到盡善盡美。既然不通瑞典文,我除了忠於英國譯者Marlaine Delargy的譯本之外,也只能在原文專有名詞下功夫,透過Duolingo初探瑞典文的皮毛,因此Julia、Gerlof 和作者姓名不循英文發音,虛構地名Stenvik照瑞典文 sten 和 vik 意譯為「岩灣」(地名動輒四五字多礙眼),有問題直接提問作者提歐林,確認地名的譯法無誤,還因而發現英譯本搞錯說話者的小瑕疵。
在英日語地位仍屹立不搖的年代,雖然還不到式微的程度,但往昔所謂的小語種如今已逐漸嶄露頭角,《小王子》不但有直接從法文譯中文的劉俐版,更有蔡雅菁的法譯台版本。幾年前,義大利名著《玫瑰的名字》也推出新譯本,由旅居威尼斯返台的倪安宇直接詮釋,讓中文讀者撥開英譯薄紗,一窺作者安伯托.艾可的素顏。
《聖經》的原文不僅是小語種,而且年代古遠,其中的亞蘭文更失傳已久,《新譯本》集結數十名學者和文字工作者,直接溯源取經,新增近代出土的《死海古卷》,修正二手版的漏譯和誤譯,但金句仍儘量承襲原譯本,以順應百年來的習慣。然而,信者恆信,在教會中,無論是《新譯本》或《現代中譯本》,仍無法動搖二手《和合本》的寶座。

《死海古卷》是目前最古老的希伯來聖經抄本(舊約),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庫姆蘭出土。(圖片來源 / wiki)
雖說每一部譯本都可視為新創作,但若能跨越中介語,貼近原文,失真度絕對小於間接翻譯,這對於字字計較的《聖經》控而言,可謂一大福音。在可見的將來,中文圈的瑞典語譯者如果推出《霧中的男孩》新譯本,我一定率先預訂,投下肯定票。原譯本善盡宣傳、奠基的義務,拋磚引玉成功,退場也了無殘念。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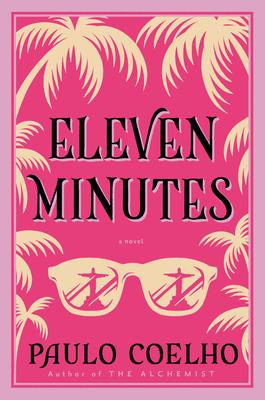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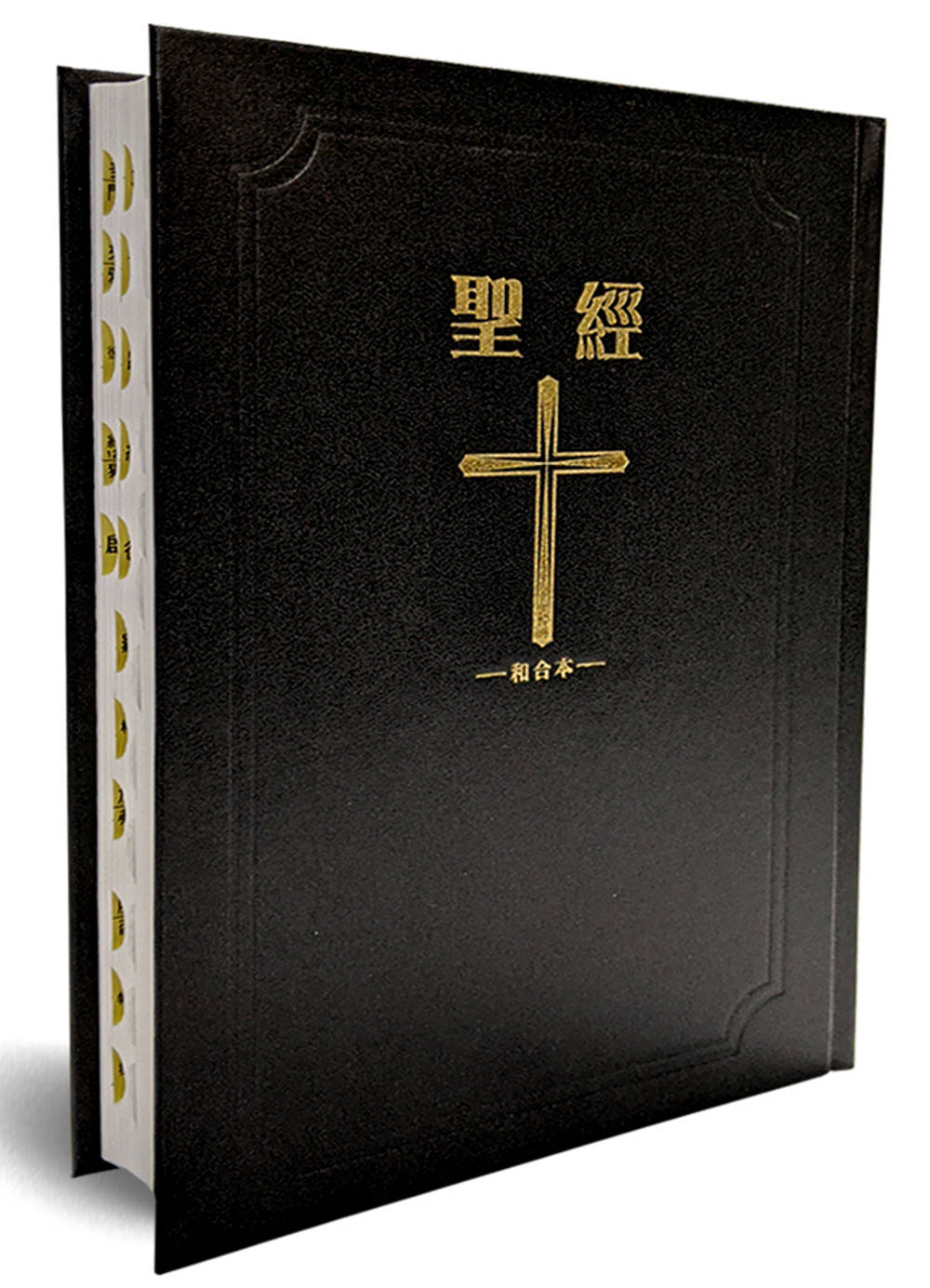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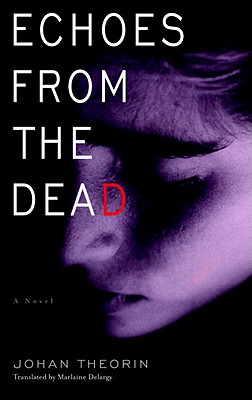
 《霧中的男孩》瑞典版
《霧中的男孩》瑞典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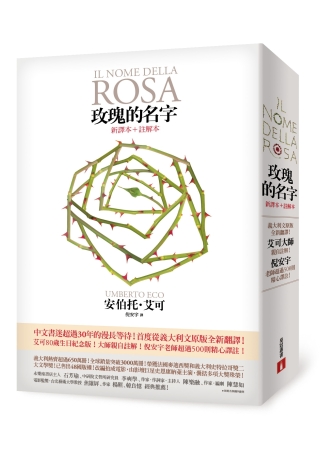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