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踏進翻譯組織召開的研討會,專職文學翻譯24年的我總抱著菜鳥心態參加,因為北美洲的文學譯者協會以學者和白人居多,而且壓倒性多數的譯入語是英文。更何況,在這些場合裡,討論內容以詩掛帥,左看右看都是詩人,而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文類是 prose,也就是「非詩」。
難道詩集在美加洛陽紙貴?在2024年美國文學譯者協會(ALTA)的年會,我請教魁北克大學的詩人教授譯者麥德琳.史卓弗德(Madeleine Stratford)。最近九年當中,她的英翻法譯作五度名列加拿大最受矚目的「總督文學獎」決選,類型包括小說和散文,而且她在2023年的決選譯作是詩集,所以由她來闡釋最適切不過了。
 左起:阿根廷詩人教授Lisa Rose Bradford、詩人Susanna Lang、美國詩人教授Gary Racz、美國譯者教授Armine Kotin Mortimer、加拿大譯者Madeleine Stratford。(圖片提供 / 宋瑛堂)
左起:阿根廷詩人教授Lisa Rose Bradford、詩人Susanna Lang、美國詩人教授Gary Racz、美國譯者教授Armine Kotin Mortimer、加拿大譯者Madeleine Stratford。(圖片提供 / 宋瑛堂)
美國譯者佩吉.安乃亞.莫里斯(Paige Aniyah Morris)附和。她現居南韓,最近合譯諾貝爾桂冠小說家韓江《永不告別》(We Do Not Part)。她說她發現上一代的韓翻英譯者幾乎只譯詩,「我這一代被明言勸阻不要碰詩,因為現代詩都『滯銷』。」
在這兩位感嘆之前,我在會中結識一名銀髮族詩人。吉姆.凱茨(J. Kates)是麻州西風出版社(Zephyr Press)聯合社長,也曾擔任美國文學譯者協會的會長。歷年來,西風曾推出瘂弦等二十多位華文詩人的作品英譯本。凱茨寫詩也譯詩,謙稱「小詩人」,精通英、法、俄、西班牙、拉丁文,自己執筆的英文詩也曾被翻譯成外語,所以他「特別能體會同時置身於哈哈鏡裡外的滋味」。
由於凱茨明瞭詩的「不可翻譯性」,他曾寫一首「可翻譯」的英文詩,才寫完,就接到法文雜誌社邀稿,對方請他自行譯成法文。以法文改寫,他可照個人意志,想怎麼譯就怎麼譯,內心有一股異樣的自由感,簡直自我膨脹到不可一世,但他總不忘告誡自己,「譯成外文不是給我自己讀的。」他進而指出我從未思考過的一點:所有文類當中,唯獨文學譯本和童書的評論者通常不是作者的目標讀者群。
童書的小讀者不擅論述,以成人代言無可厚非,但有些譯本讀者懂外語,可溯源比對譯作,只不過,譯者的重點是服務單語讀者,有時卻不得不兼顧雙語讀者的口舌。作者寫東西時,可想像背後有個讀者在監看;譯者翻譯的時候,背後不只有讀者,還有雙語讀者在虎視眈眈。
為此,凱茨表示,「我身為譯者,是因為我寫詩,而不是因為我懂外語。」他認為再好的譯本,充其量只是從一人的視角進行批判式閱讀。他說,「我的詩被翻譯成外文,能教我認識自己的作品,能讓我明白哪些文字達到了我預期的目的,哪些不符合我的原意。」哈哈鏡裡鏡外的境遇不是單語人士能體會的,只能單向翻譯的譯者也未必能懂。
但嚴格說來,悖離作者本意並不算誤譯。凱茨以俄國為例指出,俄國人雖然歡迎有朋自遠方來,卻比任何國家更愛批判譯本,所以在書展期間,西風出版社鄭重以俄文標示:「敬告俄國讀者勿抱怨翻譯之不可行」。他在翻譯俄文詩的時候,俄國詩人准他犯錯,但要求他「犯正確的錯誤」。

西風出版社給俄文讀者的告示。
在俄文以外,可發揮的詩地生態如此遼闊,「正確度」的尺度彈性超高,難怪北美文人熱衷於譯詩。相形下,「非詩」的譯者被綁手綁腳,用語較容不下譯者奇思異想的文字遊戲。此外,工作上的現實層面是,小說動輒三四百頁,一氣呵成的譯作較能封存原味,反觀留白寬廣的一首詩,譯者可隨興細細咀嚼字字推敲,可輕輕拾起重重放下,遇障礙可換換口味,玩玩另一首毫不相關的詩,少有前後不連貫的難題。小說譯者也能這樣玩,沒錯,但保證玩到錯置人物和年代,和詩人一樣邊玩邊聽肚子練聲樂。
國內刻意標榜詩人的譯者不多。簡述譯者背景時,華人譯者多以學歷起頭,有些譯者提一提闖蕩社會的旅程,然後列出作品,但在我參加的年會中,最常見的自介順序是「詩人、文字工作者、譯者、某大學教授、作品」,頂多附加族裔背景,學歷則可有可無。這現象反映出一個赤裸的事實:在美加,文學翻譯是一種相當於寫詩的文學創作,是一種抒發才情的嗜好;但在東亞,翻譯屬於知識產業,和法庭口譯、技術文件筆譯並列同一行,是憑學經歷或證照一磚一瓦砌築而成的專業,是否精通文學創作並非要件。
東西方的文學翻譯市場無法對比,讀者/譯者依存度也不盡相同。英語系國家遍及五大洲,英語人士不必透過譯本,就能直擊印度、奈及利亞、加拿大、南非、紐西蘭、貝里斯、新加坡文學。同一語言能囊括多元人種和繁花文化,翻譯的需求因此受英語原創文學擠壓。北美讀者因較少接觸譯本,多數難以辨識英譯本書封上的東亞原作者。
我曾聽美國朋友稱讚「西金路」寫的科幻小說,對文壇不熟的我客氣反問哪位,才知是《三體》的大作家。在性別不清、姓與名混淆的情況下,英文讀者不得其門而入,想瞭解作者必須先認同英文姓名的譯者,何況多數外文書籍需透過譯者主動試譯並推銷給出版社,西方讀者對譯者多一份依賴,甚至索性把英譯本視為原創。反觀華文,人丁浩繁,僑民遍布全球,九成以上的原創文學卻只能無縫接軌亞洲的一隅,華文讀者渴求井外的天地,翻譯文學的角色因而吃重,但不少中譯本讀者對原作者略有所悉,能接受姓名動輒七八字的歪果人,也知道譯者和編輯之間的發書接譯流程,不至於盲從譯者。
國內讀者也因學過外語,較常接觸英日韓影音文化,比美加更講究譯筆精準度,雙語比對的焦點包含字義、節奏、時代感、筆調、雙關語、信達雅、心聲、反諷、隱喻、諷喻、翻譯腔、語境、語域、語感等等,但在美加的文學譯者年會上,這些重點全可用籠統的 voice 一字打盡,評論空泛至極,無限寬容著譯入語是英文的譯者,我忍不住在心底為國內譯者抱屈。
Announcing the winner of the 2024 Lucien Stryk Asian Translation Prize:
— 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LitTranslate) October 26, 2024
DECAPITATED POETRY by Ko-hua Chen,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Wen-chi Li and @brambrella, published by @SeagullBooks! https://t.co/HsWVAwhCdu pic.twitter.com/Y4QKJDY1vj
幸好我和凱茨、莫內一樣,從不自稱「大」什麼「家」,哈哈鏡裡的我仍是我,不至於被扭曲成豬八戒。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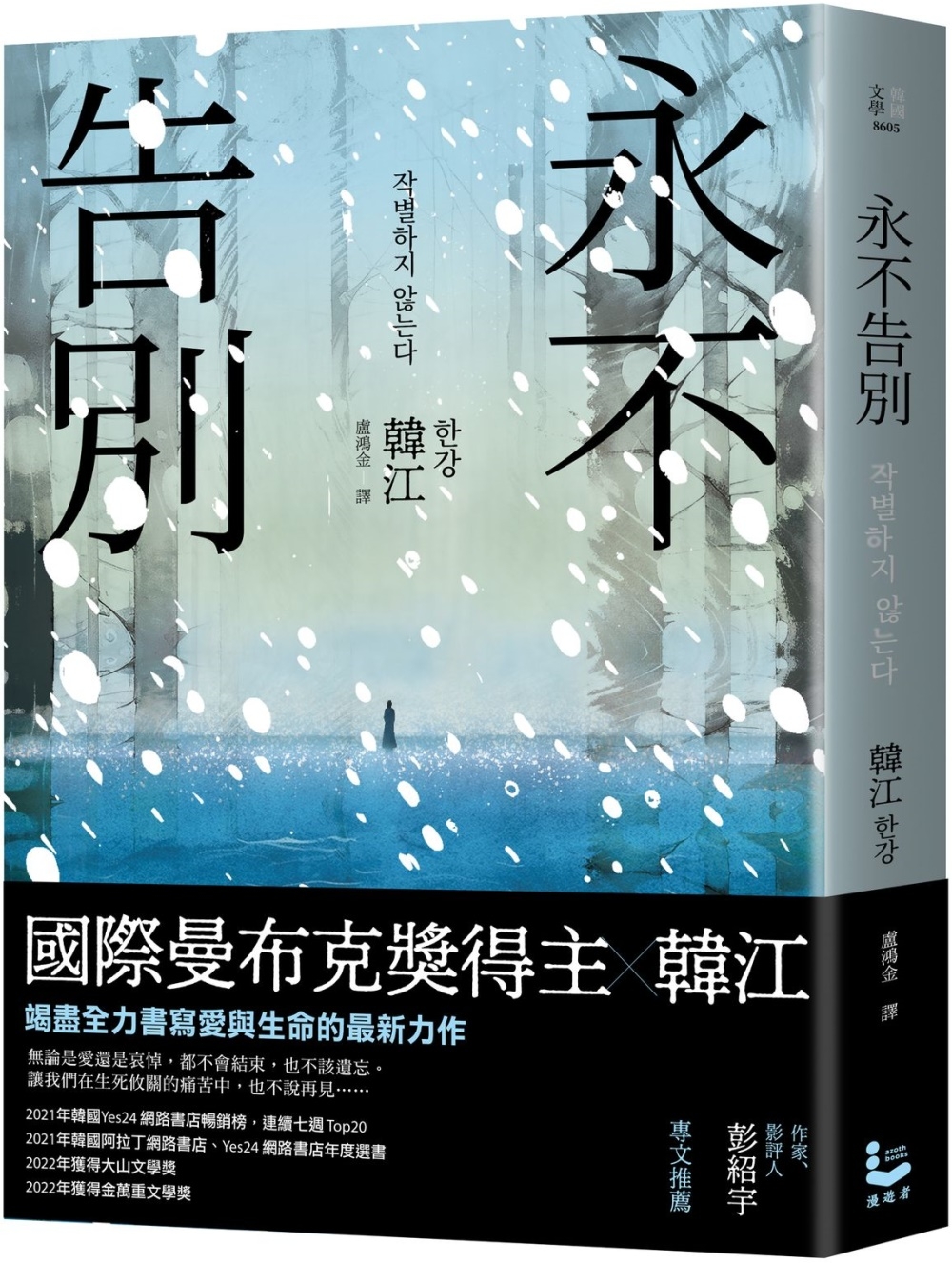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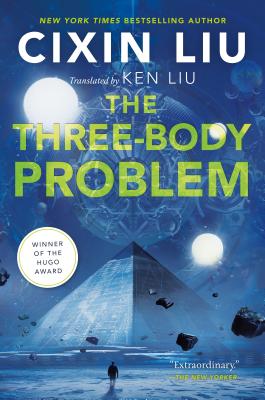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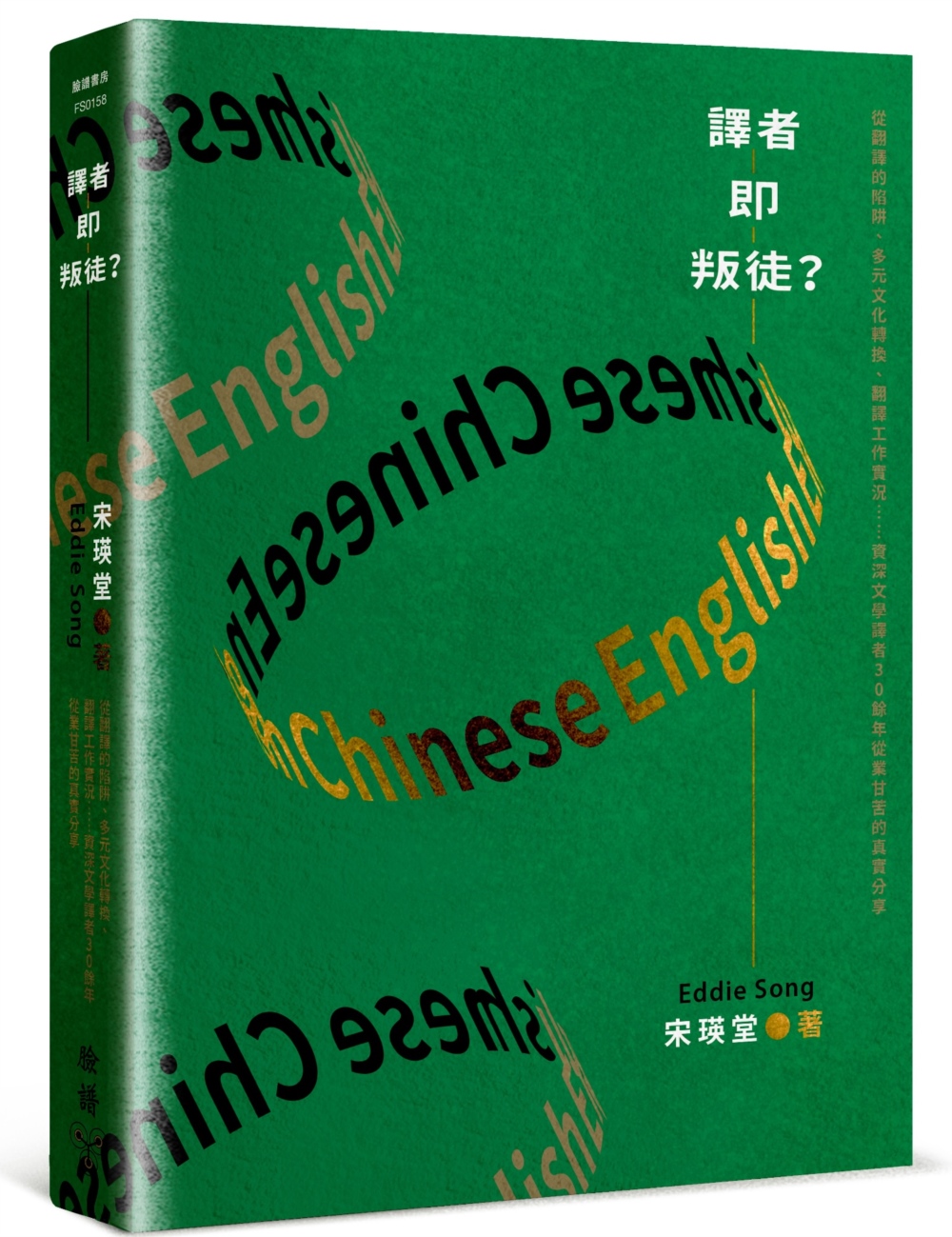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