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人余光中(1928-2017)先生逝世迄今,匆匆已近四年。他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往往首先是被當成一位現代詩大家、一位英美文學教授,似乎很少人記得他曾將自己的許多詩作譯為英文,也曾有過《錄事巴托比》(梅爾維爾著)、《老人與海》(海明威著)、《不可兒戲》(王爾德著)與《梵谷傳》(厄文.史東著)等堪稱經典的翻譯作品,更少人記得他除了「詩論」非常精彩,也曾經寫過許多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的「譯論」。究竟「翻譯家余光中」曾經有過哪些關於譯者與翻譯活動的論述?在我看來,九歌出版社這次推出的《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余光中翻譯論集》可說是這方面的「定本」,就各個面向來講都難有往後的類似文集可以超越之處。想了解他的翻譯思想,甚至要進入所謂「余光中學」的領域,未來這本書將會成為任誰都不可或缺的經典。
與西方翻譯理論對話
余光中的譯論篇篇精彩,儘管言簡意賅,但卻每每能與西方翻譯理論傳統進行對話,其中〈作者、學者、譯者〉是最好的例子。在這篇文章中,余先生表示,若要維護文化之風雅,主領風騷,就有賴一群「專業讀者」來認真讀書,無論作家、學者、譯者、編者、教師都是專業的讀者,而這馬上就讓我聯想到翻譯理論名家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把廣義的翻譯當成一種「重寫」(rewriting)的活動,進行此一活動的包括各種「專家」(professionals),而譯者只是其中之一,其餘如編輯、批評家、教師等也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外,在這篇文章中余先生也挑戰了以「信實」為首的傳統翻譯觀,就像西方翻譯界從1980年代以降挑戰原有的「對等」(equivalence)原則。他認為,譯者的工作是把一本書,甚至一位作家帶到另一個語境中,「不是改裝易容,而是脫胎換骨」,好的譯者可以讓自己翻譯的作家變成「那位作家的子女,神氣和舉止立可指認」,至不濟也該變成該位作者的姪女、外甥,「雖非酷肖,卻能依稀」。
其次,若論源自於德國的「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此一理論把文字區分為訊息類、表述類、操作類文本(informative, expressive, and operative texts),其中文學作品堪稱表述類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不過,余先生在〈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更深入地指出,即使是文學文本也各有不同的表述目的。因為在台下看戲的是大眾,所以他力求把譯文「調整到適度的口語化,聽起來才像話。同樣的字眼,尤其是名詞,更尤其是抽象的名詞,就必須譯得響亮易懂。否則臺下人聽了無趣,臺上人說來無光。」他認為既然小說的對話是給人看的,戲劇對話則是給人聽的,所以翻譯上的要求就有所不同,而《不可兒戲》的翻譯原則是讓「觀眾入耳、演員上口」。當年,中國舞台劇大師級演員英若誠之所以要親自重新英譯老舍的經典劇作《不可兒戲》,也是因為原譯過於佶屈聱牙。
獨領風騷的譯者: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論
細讀余光中的譯論,我感覺到他是非常有意識地要樹立譯者的明確地位:譯者絕非純粹的模仿者,而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他在〈作者、學者、譯者〉中先以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為例,其譯作的語種遍及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德文,只不過他的詩名過盛,光芒掩蓋了其譯作。(余光中自己何嘗不是如此?這難道是詩人譯者的宿命?)他認為,世人對譯者的一般評價是「名氣不如作家,地位不如學者,而且稿酬偏低,無利可圖,又算不了學術,無等可升,似乎只好為人作嫁,成人之美」。
但他有意逆轉這種俗世之見,舉聖傑洛姆(St. Jerome)翻譯《聖經拉丁通行譯本》、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譯德語版《聖經》來說明譯者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影響有多大,玄奘大師取經回國後長安萬人空巷歡迎,唐太宗親自安排其於大慈恩寺內譯經十餘年,受盡榮寵,至於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則是因為翻譯荷馬的古希臘經典史詩《伊利亞德》而獲得英王喬治一世與太子以重金相贈,出書後獲利五千英鎊。(還記得朱學恆曾靠翻譯《魔戒》而一千萬台幣入袋嗎?)不過,他也不忘記提醒大家,譯者這一行有時候仍有喪命風險:魯西迪(Salman Rushdie)爭議小說《魔鬼詩篇》的日文譯者就慘遭暗殺身亡。
譯者的限制與創意
〈《守夜人》自序〉一文是余光中自譯詩作為英文的精要心得,若能拿來與白先勇自譯短篇小說集《臺北人》的相關論述來對讀,想必能相得益彰,對「自譯」(self-translation)這種特殊的翻譯實踐有更深入了解,一窺譯者所受到的種種語言限制和採取各種翻譯策略的心路歷程。余光中在該文中聲稱:
「詩人自譯作品,好處是完全了解原文,絕不可能『誤解』。苦處也就在這裡,因為自知最深,換了一種文字,無論如何翻譯,都難以近達原意,所以每一落筆都成了歪曲。……有時譯者不得不看開一點,遺其面貌,保其精神。」
這番話除了像是在呼應中國翻譯家傅雷曾說的「形似/神似」之辯(神似才是「譯藝」的最高境界),也指出翻譯活動跨越語言、文化的兩端,往往無法在「求真」與「求美」之間得以兩全——所以法國人才說「美文不忠」("Les Belles Infidèles"),義大利人說「譯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
不過,譯者終究還是可以靠創意獲得最終救贖。例如在〈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他提及自己把主角的原名Ernest譯為「任真」,因為Ernest與「earnest」(認真)諧音,以此反諷他在鄉間使用假名Jack;他還把另一個角色的假身分Bunbury譯為「梁勉仁」,與「兩面人」諧音。Miss Prism被他改譯為「勞小姐」,與「老小姐」諧音。余光中身為譯者的創意,還展現在另一個也很有名的例子:在英譯自己的詩作〈蓮的聯想〉時,其中有一段原文是:「戰爭不因漢明威[即海明威]不在而停止/仍有人歡喜/在這種火光中來寫日記」,他改譯成:“War stops not at Hemingway's death./Still men are fond/Of writing their diaries in the light of Mars.”不直譯「火光」而是改為“light of Mars”堪稱詩人的高招:這個翻譯雖然失真而有所減損,但余光中把詩句帶入西方文化更深層的神話結構裡,因為Mars除了指火星,也有「戰神」之意,與前面提及的“War”(戰爭)相呼應。(〈蓮的聯想〉的譯例引自馬耀民教授的論文。)
餘論
2002年,中國某家出版社也曾將余先生的一部分翻譯論述集結起來,以《余光中談翻譯》為名出版,但其完整性絕對遠遠不及這本《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誠如其弟子單德興教授在〈推薦序〉中所言,這本選集中37篇專文原先的出版年從1962到2012,橫跨了半個世紀,按照主題分為三輯,讓人更能有條理地全盤掌握其翻譯、語言、文學思想的精要,而且書末收錄〈余光中翻譯文章年表〉、〈余光中譯作一覽表〉與〈余光中翻譯相關評論索引〉,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過去我曾呼籲學界應該更深入研究余光中的翻譯思想與翻譯實踐,因為迄今比較有創見的研究成果,除了台大外文系馬耀民教授曾寫過的〈詩人/譯者的內在對話:閱讀《守夜人》〉與〈余光中的翻譯論述試探──以《不可兒戲》為例〉,還有單德興教授於2019年出版的專書《翻譯家余光中》以外,相關研究其實並不算多。如今在《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出版之際,我想更是深入探掘「余學」這個博大精深領域的絕佳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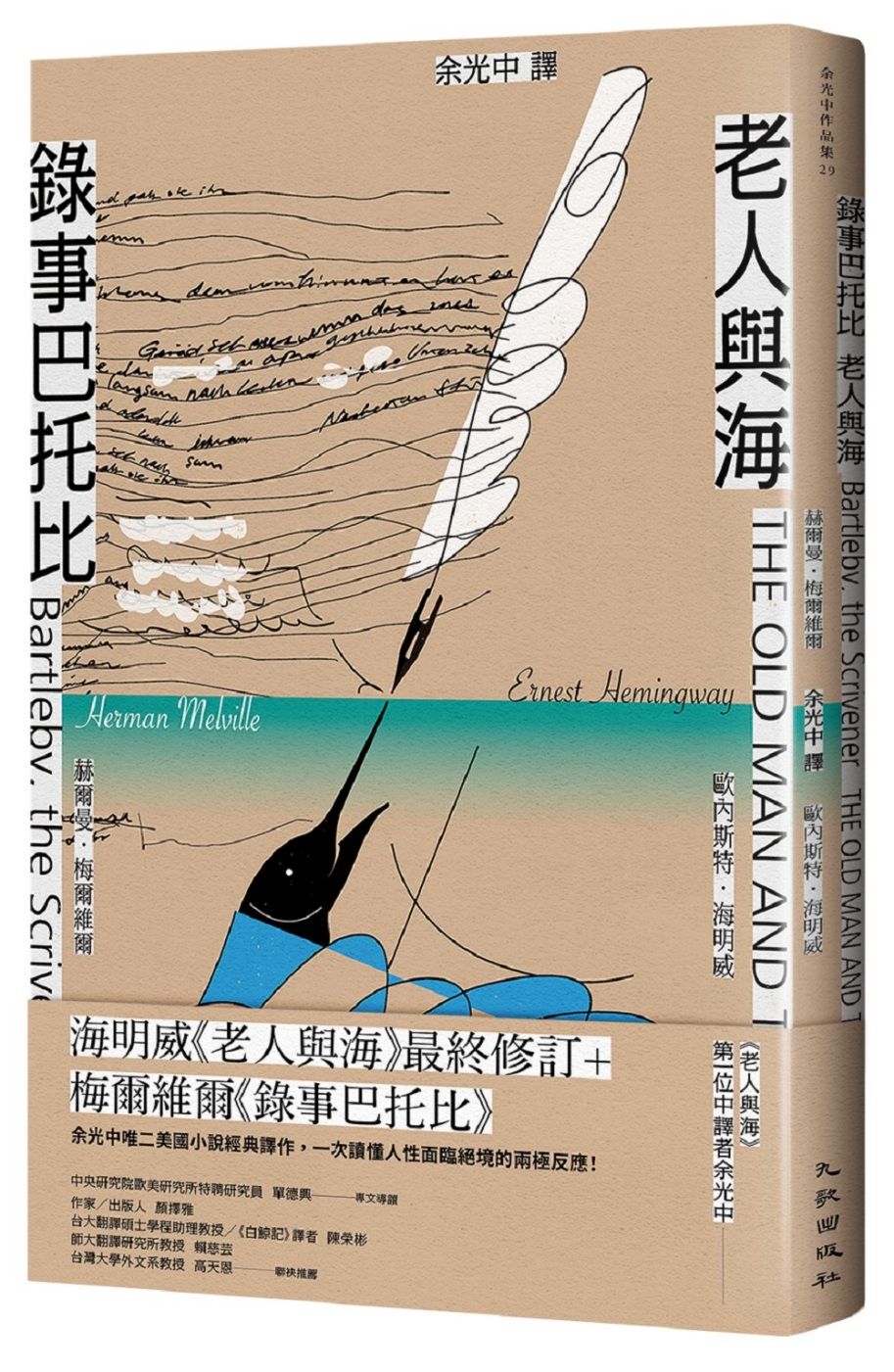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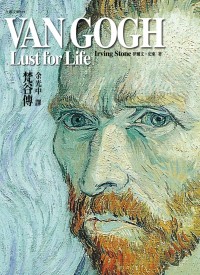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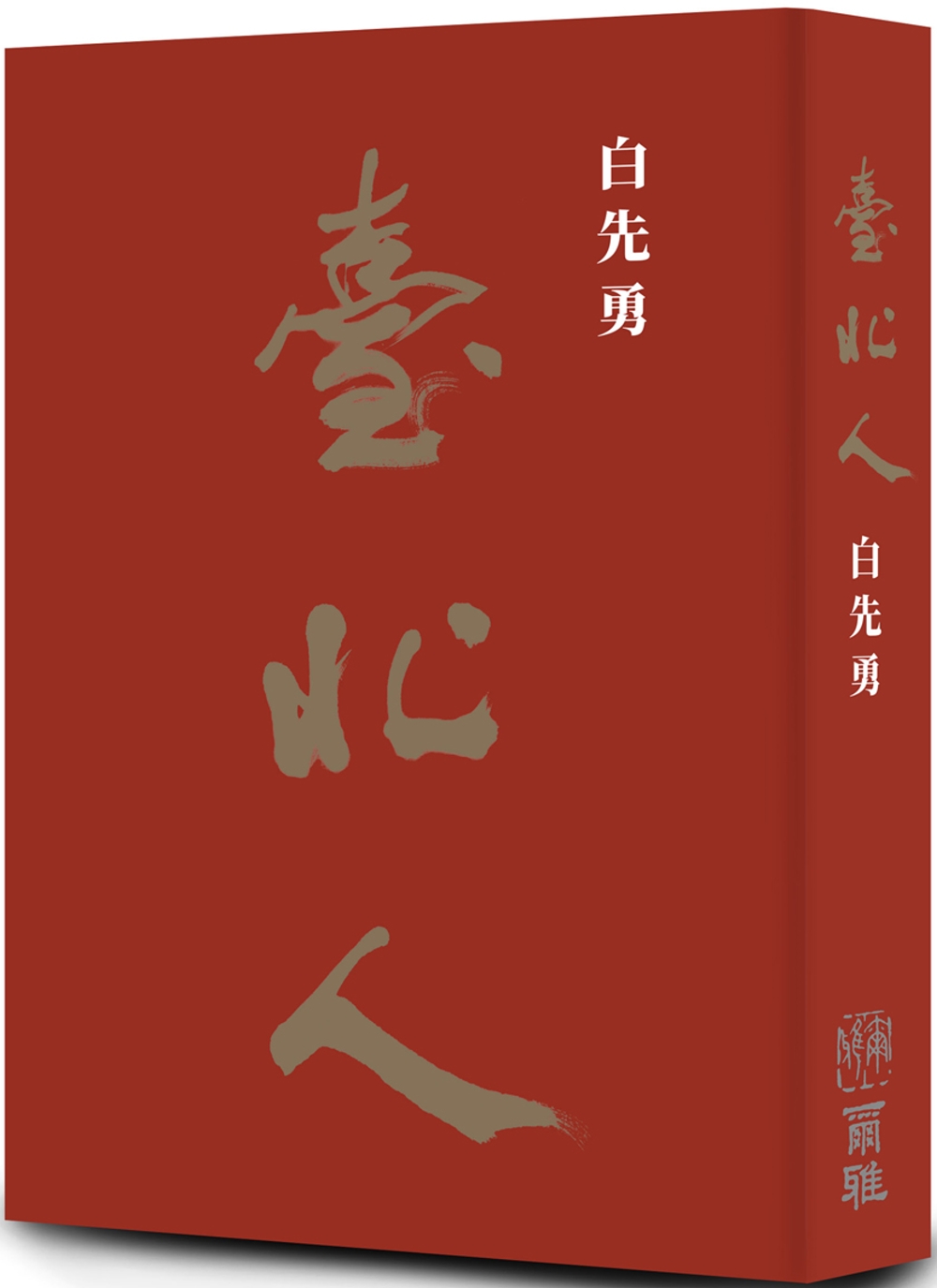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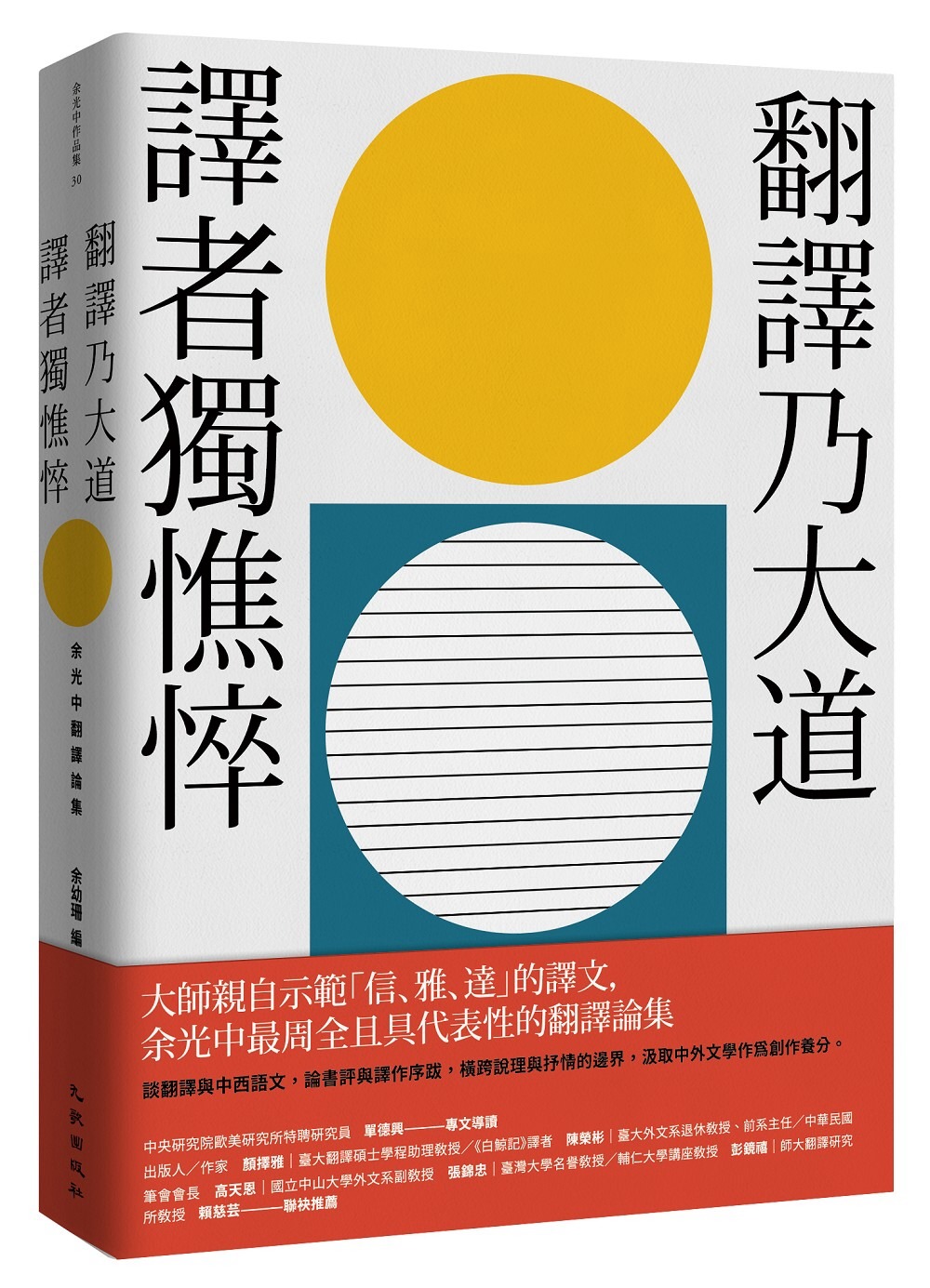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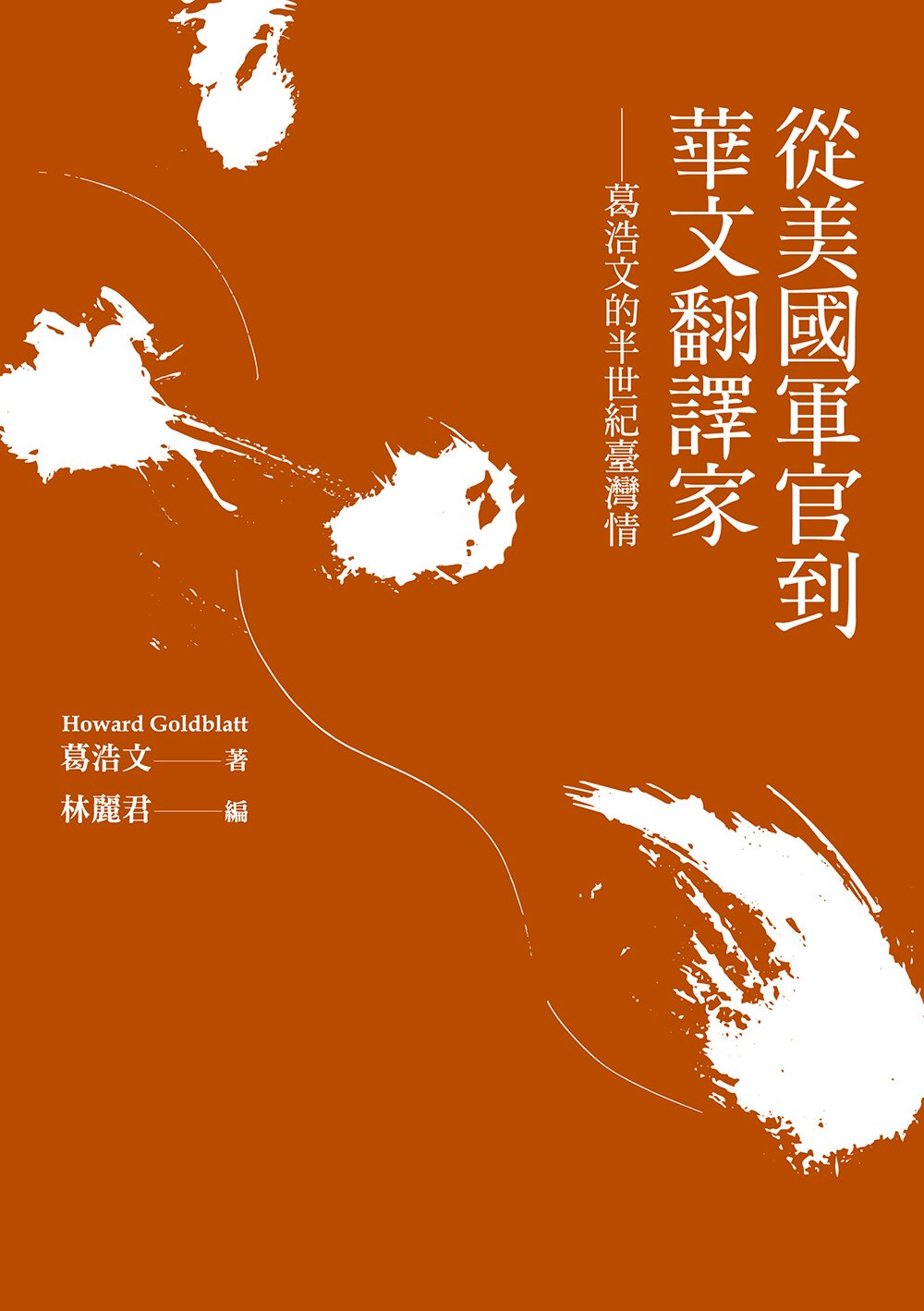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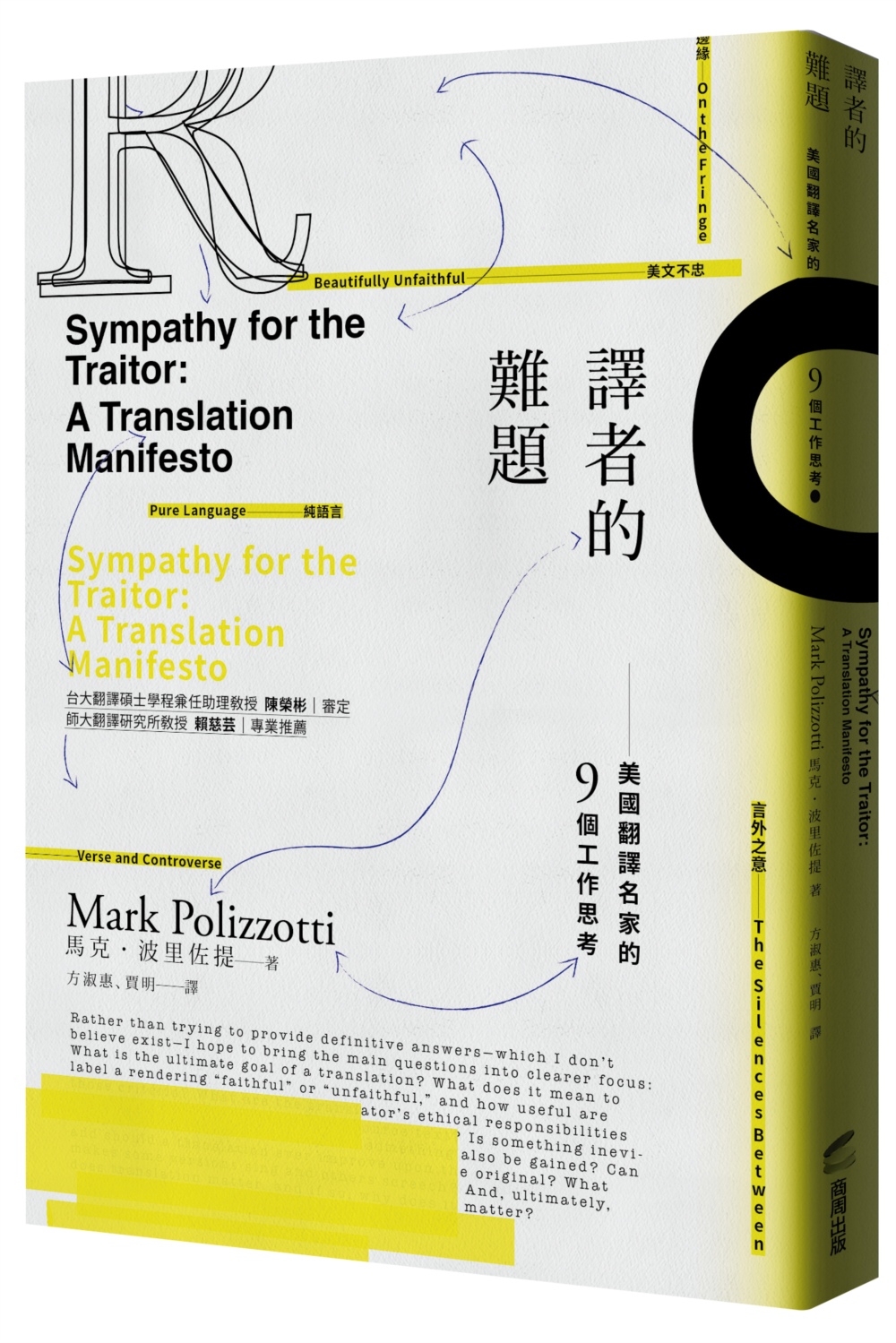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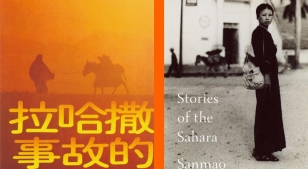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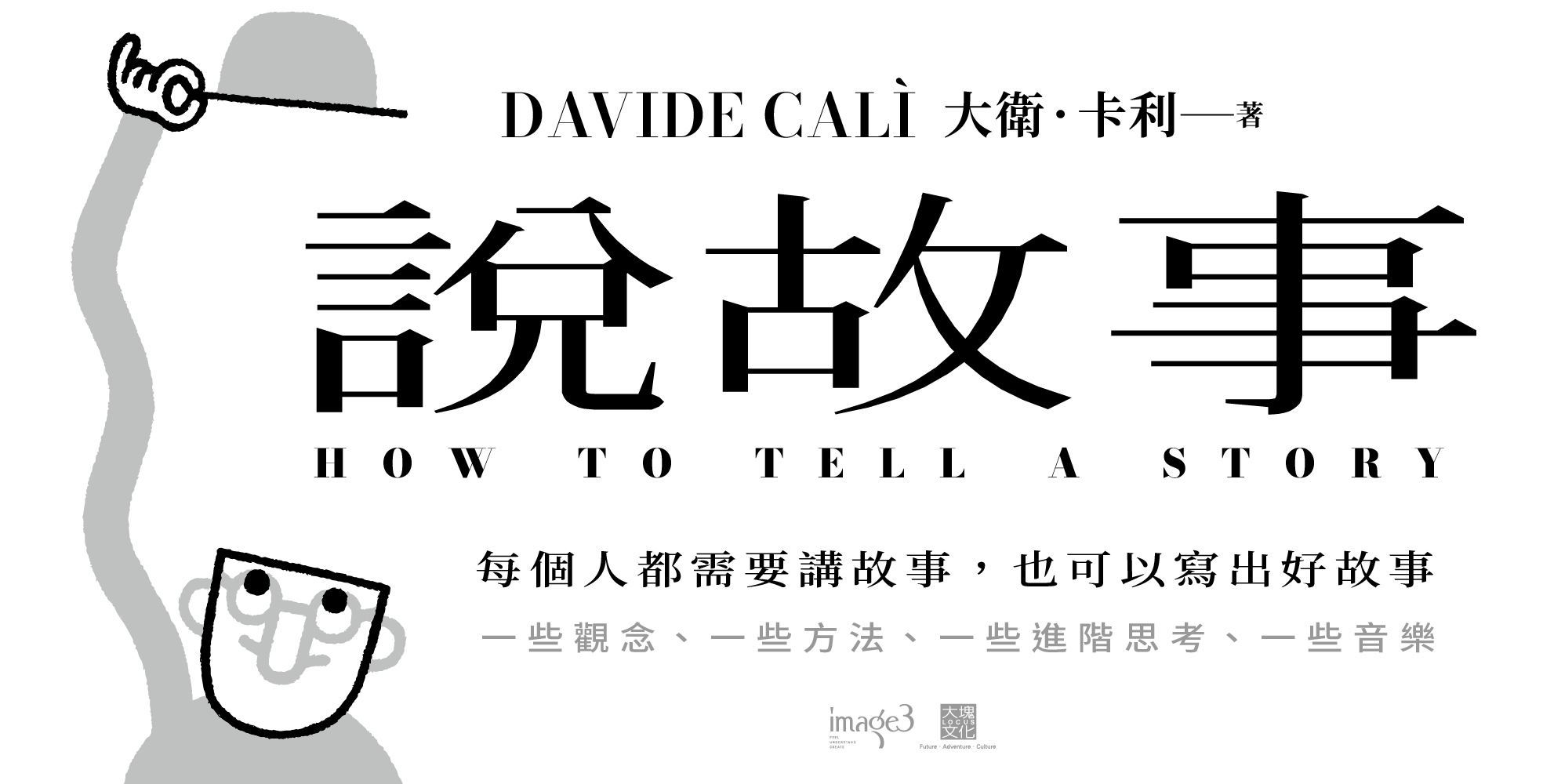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