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疫情席捲全球,「出國旅行」成了夢話。本以為2020秋天可出門晃晃,但沒完沒了的疫情只好讓人寄望2021下半年;但眼看著病毒變種、疫苗不夠威風,讓我對今年也死心了。死心不代表2021作廢,我想還是可以有一些和「酒途」有關的事,或是讓我繼續成為酒徒。
過去我一直是酒的消費者,在意的是開瓶之後的風味,香氣、韻味、酸度,酒,只在口舌與餐桌間打轉。但2017年在智利中部酒區和阿根廷門多薩(Mendoza)旅行點燃了我對葡萄園的興趣,2018年比較長的時間在玻利維亞的塔里哈(Tarija)酒區、卡馬戈(Camargo)酒區、以及阿根廷北部的卡法亞特(Cafayate)酒區晃蕩,讓我可以在葡萄園裡生活,除了品酒之外,還能和從事農作的主人相處,甚至一起除草,那時我意識到酒在裝瓶之前比裝瓶之後有更開闊的世界。
葡萄園栽植的坐向左右吸收陽光的角度,葡萄園裡的「雜草」涵養了土地的水分、釀酒師製酒的手法左右了酒的風味。在Cafayate的烏塔馬(Utama)酒莊的釀酒師薩恰(Sacha)就說:「喜歡喝酒的人,最後都會走上製酒的道路,因為你一定會好奇這個滋味怎麼來的?」當時我和他相約2020年阿根廷的秋天(約三月)再重返Utama,想要體驗採收和製酒,想明白葡萄酒裝瓶之前的故事。
疫情打壞了所有的計畫。2020的三月,我當然沒去阿根廷,而阿根廷也在三月時鎖國了。疫情影響了人的行動範圍,但無法封鎖大自然的生長,花照樣開、葡萄依舊結實累累、農作如常要進行。國境的封閉讓人必須更正視自己的土地,凝視在自己眼前或腳邊的事物。
我以為製酒這件事已經消失在我的計畫裡,疫情期間只能在各國的酒瓶之間旅行。但去年夏末,友人問我有沒有興趣用在花蓮栽植的酒米「吉野一號」來製酒,我眼睛一亮。我沒想過要做米酒,但對於把水變成酒的「神蹟」太著迷,況且「吉野一號」在日治時期被稱為「天皇米」,是用來做清酒之用。在范雅鈞的《台灣酒的故事》裡就提過當時必須把吉野一號的米運到板橋酒廠做清酒,該清酒的品牌是「瑞光」,是殖民時期台製清酒中的最佳品牌。

瓶裝瑞光清酒的酒標。典藏者:中央研究院。(圖片來源/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吉野一號」的米粒是一般米的兩倍大,而且還可清楚的看到米心,我們把米蒸熟後試吃,有糯米的Q勁。礙於製作清酒的環境需要低溫且嚴格的條件,我和友人決定以蒸餾的方式,看看這批米可以提煉出什麼樣的滋味。我們跟在桃園製酒的朋友,從蒸米、入麴、發酵,一步一步地看這一粒粒剔透的酒米怎麼變成酒水。製酒這件事,成了疫情高漲時刻最能轉移焦慮的旅程。看著入麴後的米,在溫度濕度控制得宜後長出滿滿的米麴,可以興奮一整天;將水注入長滿麴的米粒中,桶裡冒著大大小小的泡泡,泡泡的「力氣」甚至會把不銹鋼蓋撐起來,菌種的生命力堪比健身教練的肌肉迷人。守著一缸濁色的發酵液,嗅著飄散出的百香果味、莓果味……,就像看著萬花筒,氣味的變化遠超過我對米的想像。

酒米「吉野一號」比一般的食用白米大兩倍,且可看到米心。(攝影/黃麗如)
發酵的過程是活生生的,會好奇溫度、濕度、方位對這一缸神奇之水的影響,不同的變因就像是不同的旅程選擇,沒有真正走過,不會知道抵達後風景長什麼模樣。要蒸餾之前,友人突發奇想的說:「我們應該營造一種俄羅斯的製酒環境,在蟲桶冷凝器裡用大量的冰塊讓水降溫,蒸餾出來的酒質應該會很不一樣。」酒,真的是一門創造的工藝,任何的突發奇想都可以嘗試,最差最差的代價就是酒很難喝,這跟踏上未知的旅程不也是同樣的道理,最爛最爛就是知道這趟旅程很無聊,然後更明白了無聊的等級。
我們把結冰的礦泉水放入銅製的蟲桶冷凝器,讓來自五酒桶山的水迅速降溫,然後眼巴巴地盯著出酒的龍頭。第一滴酒頭,吞吞吐吐的流出,透澈的酒質帶有香蕉水的氣息,但過於厚實,一測酒精濃度,飆破80%,不是我可以承受住的重量。接著,龍頭滴出的酒到了75%、到了65%,每到一個新的濃度,我都會嘗一口,酒米的甜味漸漸跑出來,熱帶水果的香氣若隱若現。龍頭流出的酒徐徐流下,我們則思索要蒐集哪一階段的酒質最為完美,一直到酒精濃度落到52%時,發現這一階段酒氣優雅、甜味柔軟、香氣也非常飽滿,到底是酒米,蒸餾出的酒多了點溫柔,而非一般糯米或蓬萊米蒸餾的米酒表情剛直。因為喜歡這個風味,我們把52%的酒全部收集起來,做為典藏。至於後段酒精開始掉到45%、40%、38% ……品味起來,就沒有像52%那麼滑口,於是放任酒水流到大缸裡,最終混合成30%左右的米酒。至於這一階段大雜燴酒要怎麼使用,我還沒想到。
品著自己呵護出來的酒,投入的時間、心力和想像,都讓眼前澄澈的吉野一號米酒散發著不同的風味。單喝的話,口感和香氣柔順、兌入一點水後有屬於清酒的氣味竄出,加入氣泡水和幾顆新鮮的馬告後又有琴酒的風味……。以上幾句都是開瓶之後常見的形容語法,但在裝瓶之前所經歷的等待、推測、實驗過程(還沒算米農的栽植時間),非一起經歷的人可以體會。裝瓶之前的種種「現場」,是製酒人才看得見的風景。

左:透過葡萄牙的銅製蒸餾器,體驗水變成酒的神蹟。
右上:不同階段蒸餾出的酒質有不同的風味,自己蒸餾才知道這過程的變化。
右下:麴能左右酒的滋味。近期的新實驗是養黑麴來製酒。(攝影/黃麗如)
時序到了隆冬,家常料理難免想要加一點酒或整鍋酒煮一隻雞。我到超市找料理米酒、米酒頭,價格都百元有找,甚至50元可買兩瓶。我不禁納悶怎麼可能那麼便宜?製酒的朋友說:「米酒一點都不簡單,很費工,純米酒不可能便宜。」仔細看市售料理米酒的成分,發現除了米之外,都加了食用酒精。加酒精不是過錯,畢竟一些好喝的日本清酒也兌酒精來調和風味。不過要讓酒賣得便宜,加的酒精必然是用糖直接發酵成酒的液態酒精,速成的酒精有貪方便而有的酒氣,至於那千迴百轉的純米發酵過程都是奢侈成本,這樣華麗的戲碼不會發生在一瓶不到30元的料理米酒裡。
實際操作過,才知道事情酒食的真相、事物的原委,好米酒的價格不下於一瓶優質威士忌。在裝瓶前的真實酒世界,應該可以讓我的2021年玩味許久。
作者簡介
個人部落格:享樂遊牧民族
Fb:享樂遊牧民族
※本篇文章由作者個人創作授權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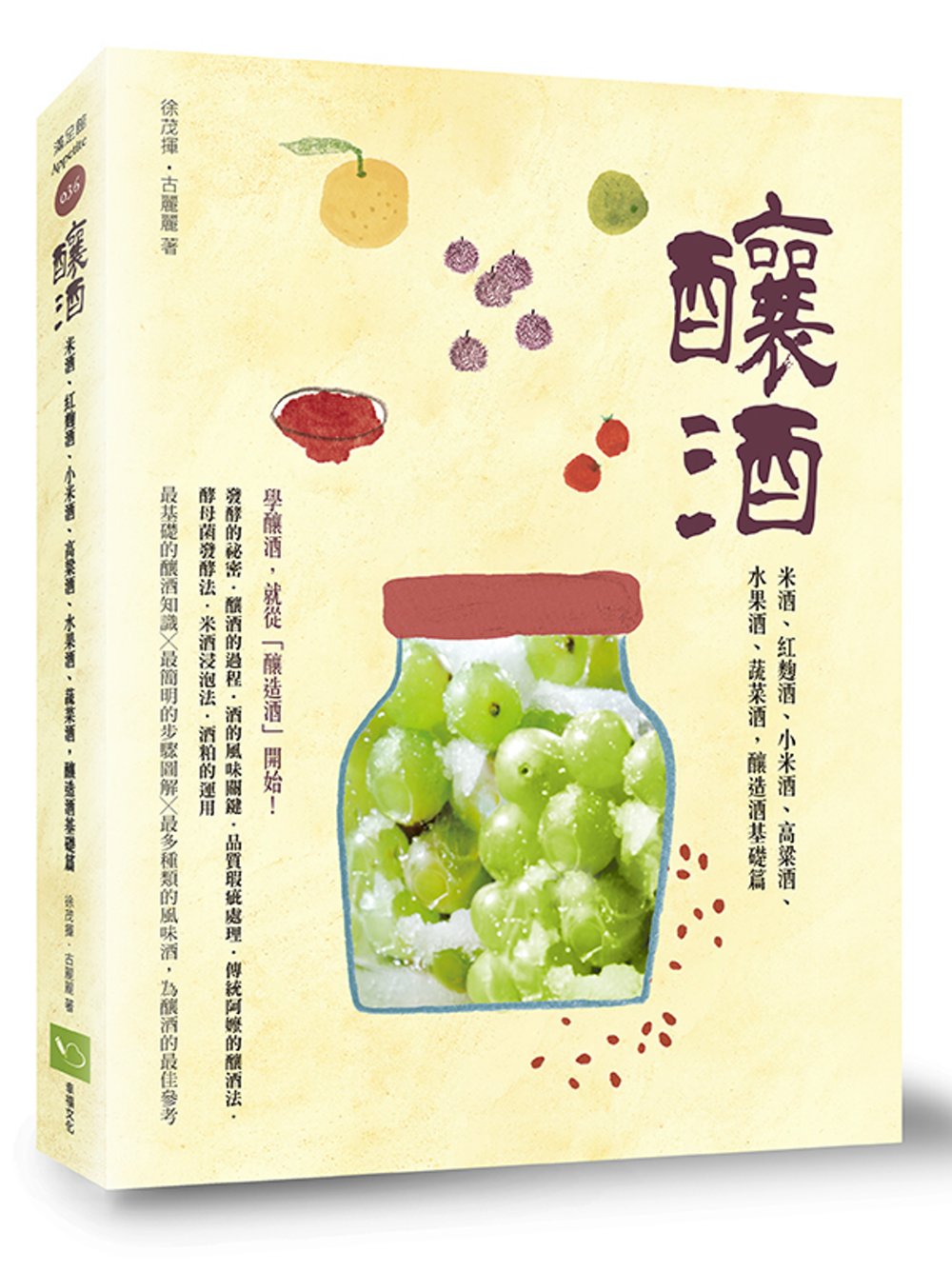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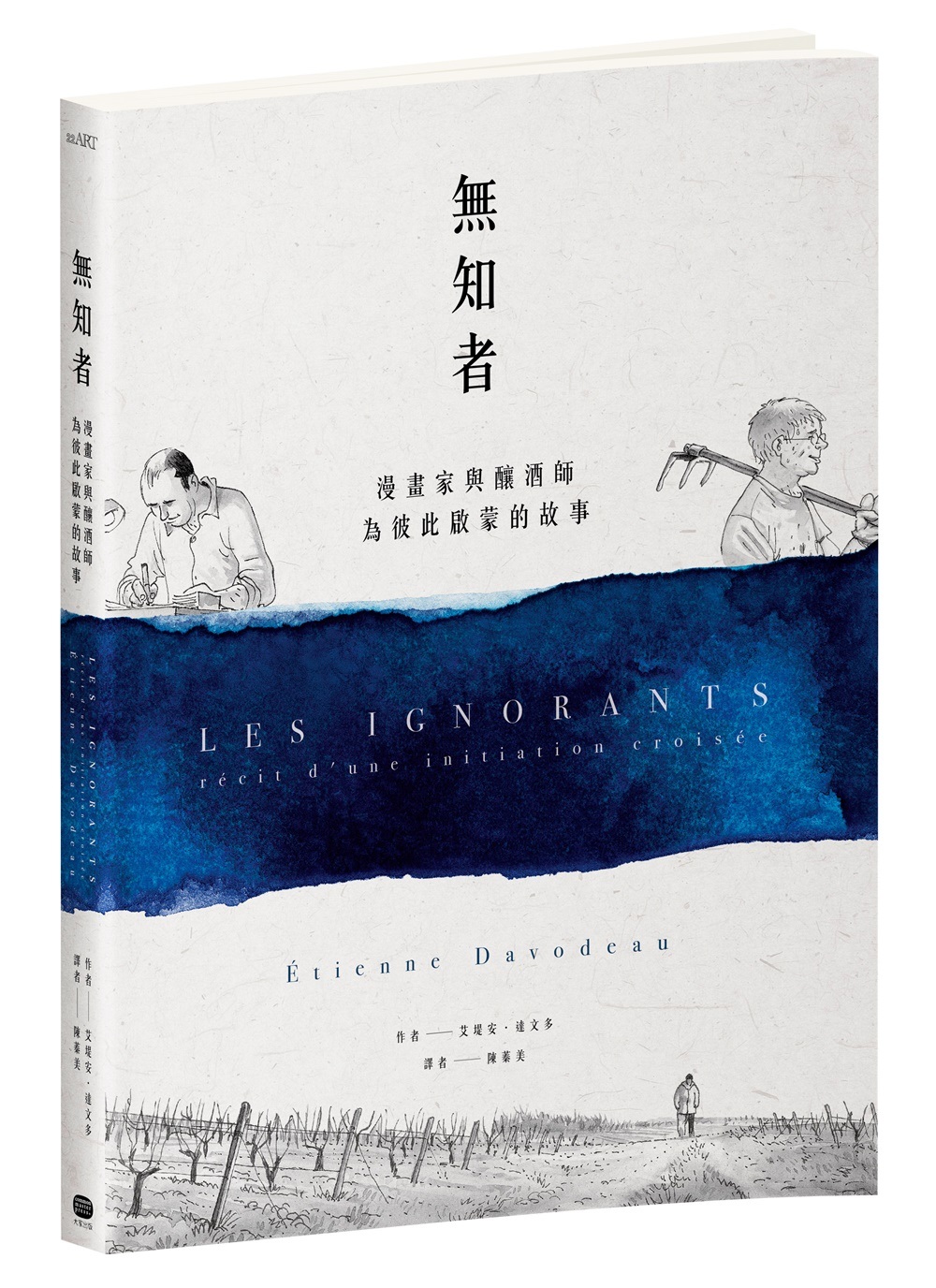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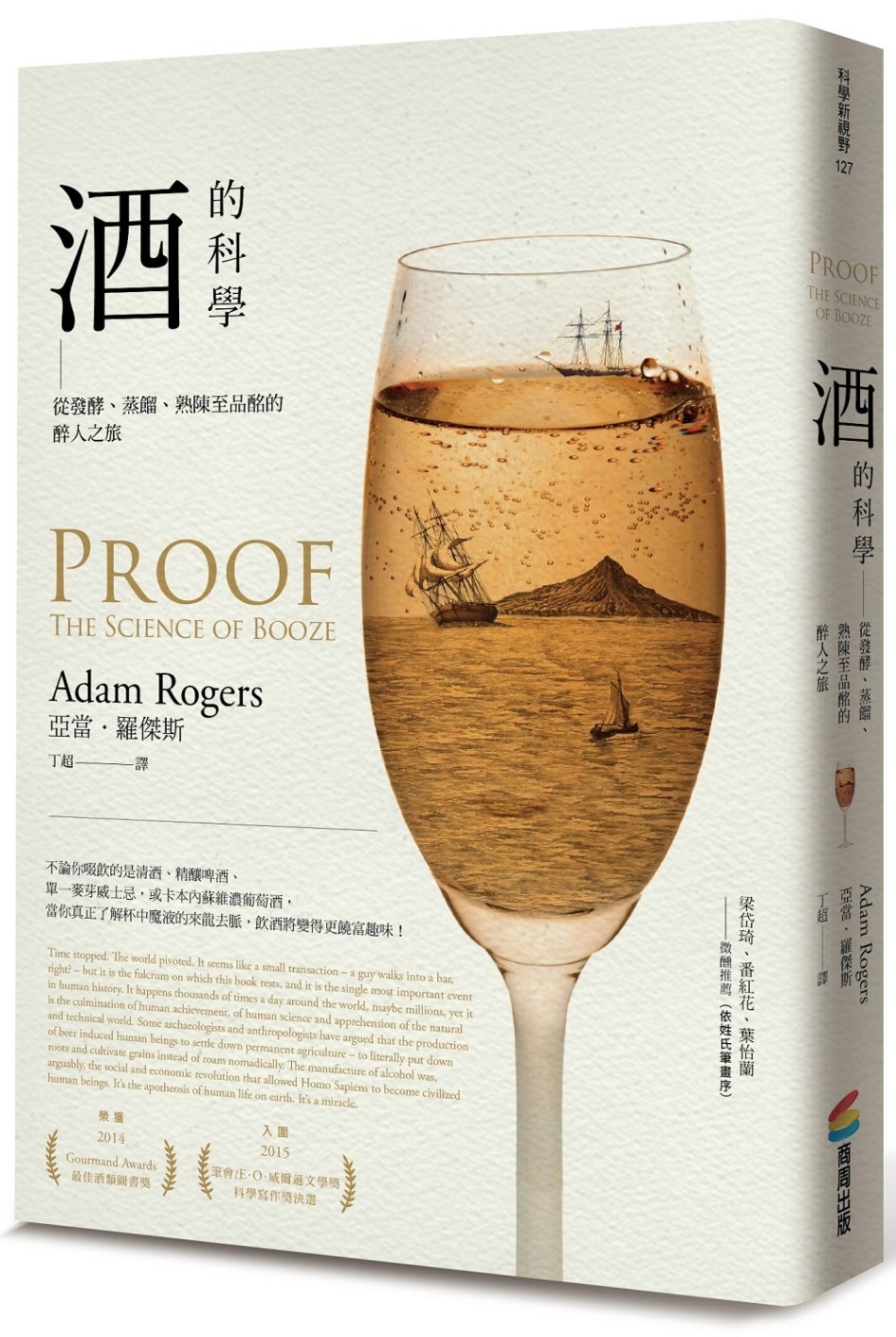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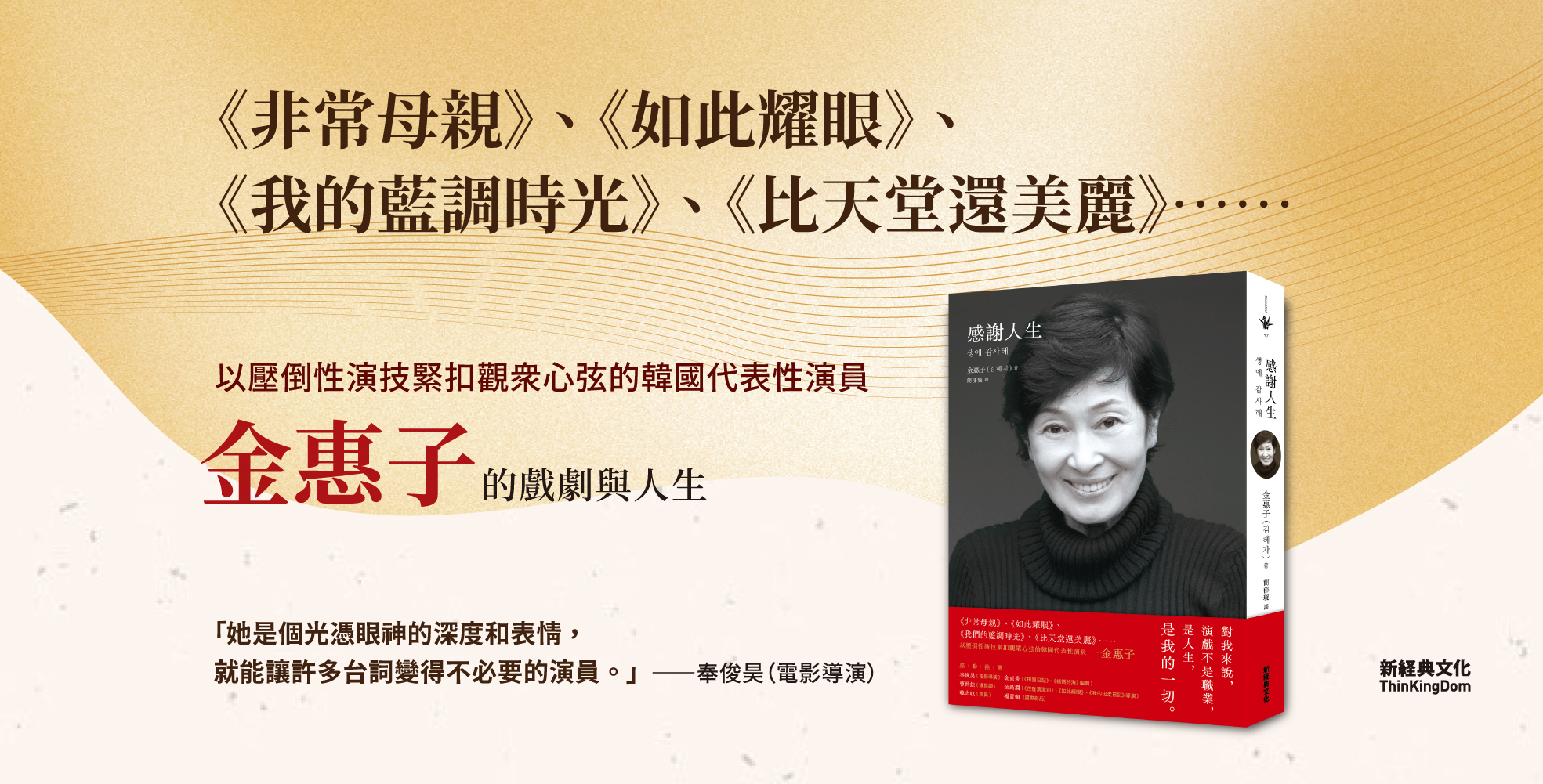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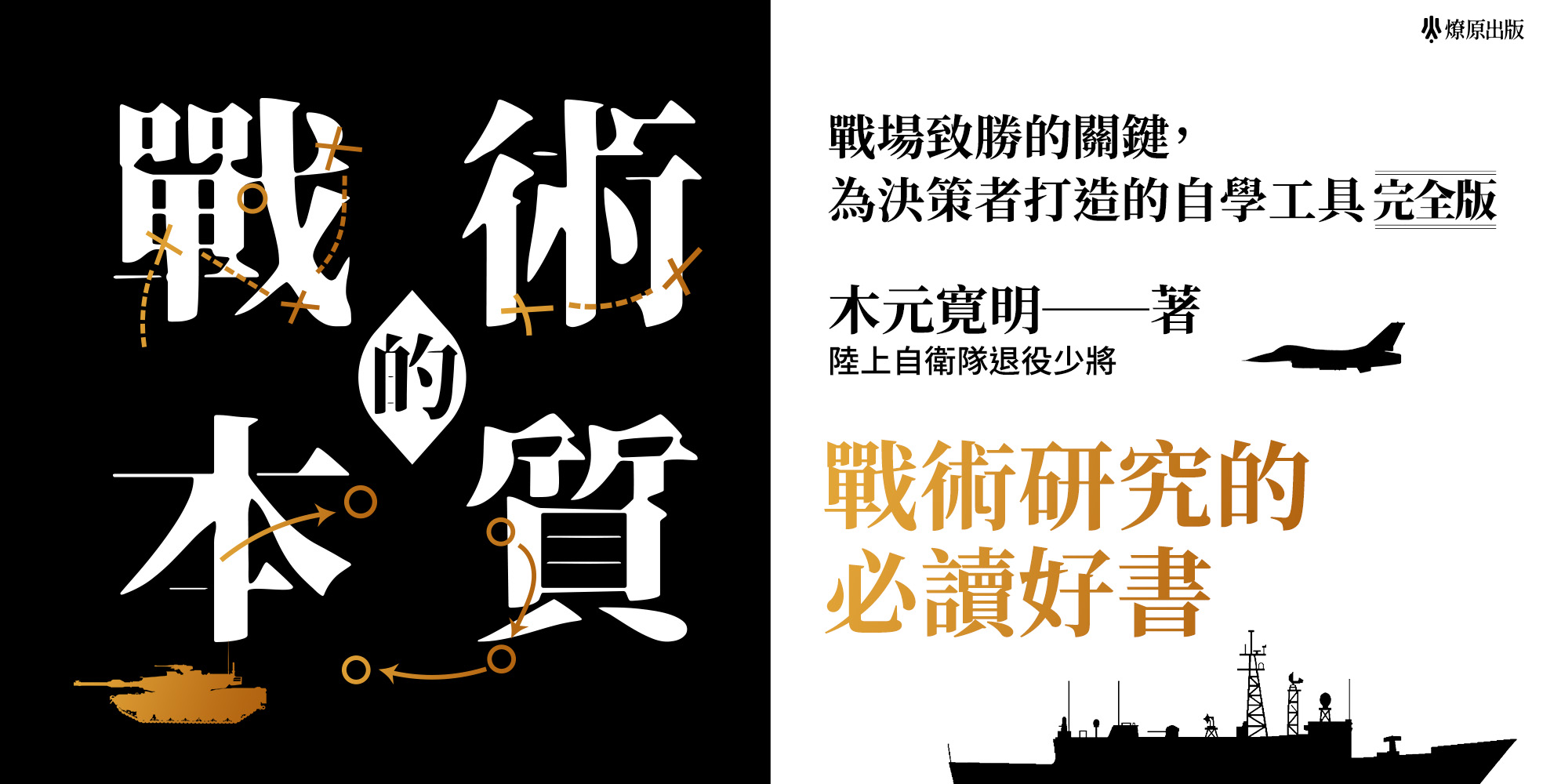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