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作家強納森.法蘭岑合影。(圖片提供/ 宋瑛堂)
與作家強納森.法蘭岑合影。(圖片提供/ 宋瑛堂)
2013年,法蘭岑前來波特蘭演講,會後,主辦單位安排我和他見面。話沒兩句,文豪就問我,你翻譯《修正》時,怎麼沒聯絡我?我「呃—」了幾聲,以「趕稿沒空」搪塞,急忙話鋒一轉,兜向法蘭岑最健談的賞鳥話題。
翻譯遇到自己查不清問題,我總是先找幾個英文母語人士討論,喬不出共識,才向作者求救,不然作者打開電郵一看問題一大串,極可能乾脆來個冷處理。法蘭岑問題容我先賣個關子。
在輕取文學大獎的輕小說《分手去旅行》裡,主人翁亞瑟回想前男友霍華德(Howard)個性隨和,廚藝也棒,可惜床笫間太愛發號施令:「捏那裡...摸那邊,不對,高一點...再高(higher)!」事隔六年,兩人在紐約偶遇,第三者為他們拍照時,霍華德叫他再拍一張,相機「高一點...再高,再高!」亞瑟這才豁然想起「Howard」。我認為Howard和higher發音有點類似,是作者暗藏的笑點,所以我考慮為他改名「史高特」。我先後找四人討論過,正反意見各兩票,最後才請作者格利爾裁決。他說,取名霍華德的本意與「更高」無關,但如果中文能改得幽默就改吧!為忠於原著,我依樣霍華德。反正就算改成「史高特」,中文讀者也未必特高興。然而,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回頭再讀一遍作者回信,發現信裡頭他說,「幽默在翻譯時鮮少能面面俱到,所以如果遇到兩難時,就以詼諧為重。」如此看來,作者以兩票支持我,我後悔當初不史高特。
改與不改,有時候由不得譯者。在《緘默的女孩》中,醫學懸疑天后泰絲.格里森中西合璧,題詞引用《西遊記》英譯本,一語直摳譯者心中永遠的痛。譯完故事全文後,我為了開頭這句,拿著翻拍再翻拍的粗顆粒古照,栽進吳承恩的時空,在火焰山和女兒國尋尋覓覓,跋涉到天竺邊境還是找不到原文,深入節譯版的英譯更像鑽進水簾洞伸手不見五指,只得向作者求救。
讀者或許覺得,照原作直譯不就好了嗎?既省事,又符合忠於原著的原則。麻煩在於,作者在書中屢次援引美猴王,並提及武術,也提到「Chen O的故事」,我磕磕絆絆之下查到〈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英文完全符合《西遊記》,所以才確認身為華裔的泰絲沒有瞎掰,小語種的譯者怎敢便宜行事?由於我在翻譯《祭念品》時請教過泰絲,和她已建立默契,我譯完《緘默》的初稿才再向她請教題詞的出處。她回答說,她參考Arthur Waley譯本第十八章的第三頁,為求精簡有力而刪改過。我查到第二十二回,總算才在流沙河找到變裝再易容的四不像,我只好照明朝古文斟酌拼湊原貌。
入行之初我覺得,向作者發問,不怕自曝其短嗎?作者見我這麼笨,該不會向經紀人告狀,要求出版社換譯者?但是,有些書錯別字多如夏蚊(「槍準心」寫成site,「位置」寫成sight),試閱本裡出現亂碼,電子稿前後文不連貫,紙本書一版再版還有錯,紀實文學裡親屬繁雜,譯者自由心證亂翻,責任誰負?一兩年後,我翻譯到醜小鴨變天鵝的回憶錄《宙斯的女兒》,直覺作者芭芭拉.墨斯個性親和,於是厚起臉皮和她搭上線,筆談甚歡,編輯知道後,也叫我從加州電話專訪她,請她暢談手足們如何看待她公諸家醜於世。有了這次體驗,我明白作者不是想像中那麼高不可攀,作家能拓殖讀者群,放煙火慶祝都來不及了。從此,我特別在交稿前騰出一星期,以充分和作者溝通。
讀者或許以為,大牌不太可能理會小譯者吧?我曾同時聯絡兩書作者,一本是談企業組織學的《創意無限公司》,另一本是《斷背山》,哪位作者先回我信?安妮.普露不但在一小時內閃回詳解,多年後更在波特蘭演講臺上,對一千多名觀眾稱讚我問題問得好。《創意》作者是新人,我發給他的電郵從此遁入〇與一的虛空,他至今當了16年的新進作家。
以我的經驗,新人讓我吃閉門羹的比例偏高。有一次,我翻譯一位和我有地緣關係的當紅新作家,上網找到她的部落格,立刻以譯者身分發電郵向她打招呼,沒等到回音,卻被編輯狠削一頓,不准我再聯絡這作者,日後通訊一律透過編輯和經紀人轉交。新人反而更跩的原因是什麼,我在此跪求答案。
一竿子打翻所有新人也不厚道。作家瑟芮.哈維森以親情小說《幸福的抉擇》初試啼聲,曾上部落格發文提到已賣出多國翻譯權,樂不可支,想問中譯者如何翻譯「高興到詞窮」。即使是影帝湯姆.漢克斯擔綱的《怒海劫》原著,船長理查.菲利普雖不是執筆人,卻也盡心為我闡明書中親屬的稱謂。探討九一一紀念碑爭議的小說《穆罕默德的花園》作者艾米.沃德曼,和我交流前後長達一個月,逐一澄清對照新舊版本的歧異處,連第二頁十八呎的圍牆都長高九呎,她也詳述緣由。
不厭其煩為我釋疑的知名作家也不在少數。紀實文學名家蘇珊.歐琳曾在洛杉磯書局辦《蘭花賊》簽書會,我到場跟她認識,她為答謝我曾幫她抓出書中的一個瑕疵,當場簽名送我巨幅壓克力海報。從《惡魔的淚珠》起,懸疑大師傑佛瑞.迪佛多次回覆我的疑問,更在前來波特蘭打書時請我吃午餐。奇女子尋父小說《霧中的曼哈頓灘》,作者珍妮佛.伊根百忙中抽空為我解惑,主編嘉世強也是她的書迷,讀完譯稿後請我代為再問她兩個問題,她以Jenny自稱,我回信時也改稱呼她Jenny,每次發問都不禁臉紅一下下。

左:作家珍妮佛.伊根;右:《斷背山》作者安妮.普露。(照片提供 / 宋瑛堂)

蘇珊.歐琳贈送的《蘭花賊》簽名海報。(照片提供 / 宋瑛堂)
碰軟釘子的例子也不是沒有。2004年翻譯到美國夢幻滅的《美國牧歌》時,我以傳真請教文壇巨擘菲利普.羅斯,他以打字回覆並附上親筆簽名,比電郵多了一分真摯。後來我從編輯得知,羅斯在美國另請中文譯者逐句審核我的拙稿,幸好過關了。據說,羅斯也曾嫌法文譯者的筆法有別於原著的韻律,譯者當場反駁:「我只能盡全力貼近原文」。是作者嫌我的問題太蠢,或他對譯者一概不信任?我只能說,我盡力而為了,感謝他在世時為我的譯稿背書。
 菲利普.羅斯的傳真。(圖片提供/宋瑛堂)
菲利普.羅斯的傳真。(圖片提供/宋瑛堂)
我翻譯法蘭岑時,截稿日期確實是迫在眉睫,但我沒聯絡法蘭岑的真正原因有三,主要是網路論壇對他作品的討論甚多,我有疑問能加減參考,其次是,在我翻譯時,《修正》已有11年歷史,作者當時正忙著推銷近作《自由》,我估計他無暇反瞻舊作。最後一個原因是,電郵透過兩國編輯、版權代理、作者經紀人接力傳遞,等我接到答案時,譯稿早已碾過截稿線。然而,在演講會後,我當面被他那麼一問,汗顏想起,法蘭岑本身是德翻英的文學譯者,而我翻譯那幾個月期間,連最起碼的「哈囉」都沒有,如今再怎麼推託也是枉然。在同業的面前穿幫,我感到無地自容,比被作者嫌笨更慚愧,今後自我期許哪怕是提問石沉大海,或被美女新作家當成怪叔叔,只要作者仍健在,我不會再託辭省略請教作者的這項功課。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畢業,台大新聞碩士,曾獲加拿大班夫國際文學翻譯中心駐村研究獎,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鼠族》《薩賓娜之死》《冷戰諜魂》《分手去旅行》《霧中的曼哈頓灘》《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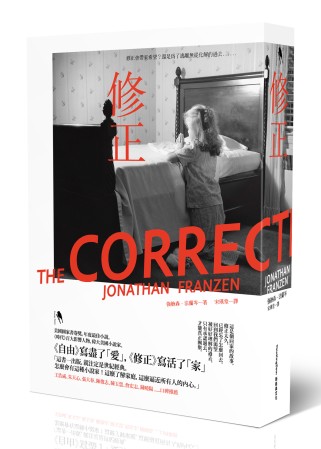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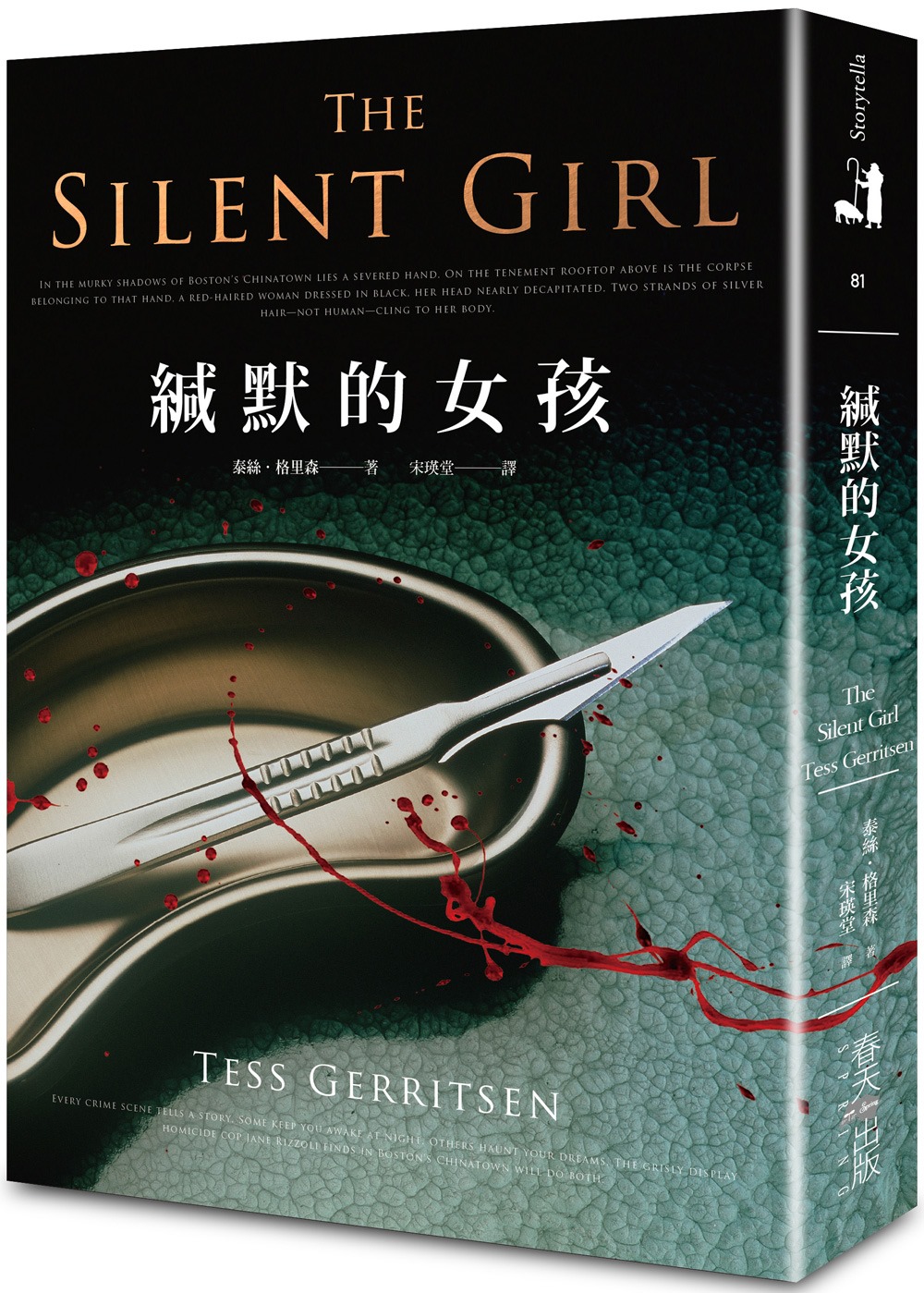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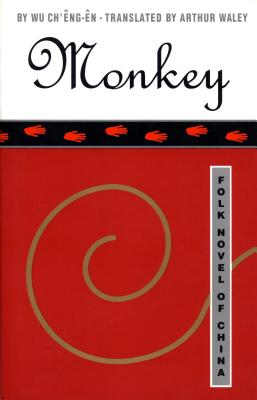

 怒海劫
怒海劫 《怒海劫》傳主理查.菲利普船長
《怒海劫》傳主理查.菲利普船長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