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嘉漢在2018年的第一部小說《禮物》裡,早早顛覆完古典的小說形式,從巴黎捎來他混音般的文字樂章,展現了新一代寫作者如何於一本小說中展現各式想像,不只是向各方經典致敬,而是實踐。那些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追尋過不知是拾荒或蒐集式的夢想:「以引文完成一篇作品」,朱嘉漢也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我」之段落靠近了,更別說對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與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虛構、翻玩。在我當時的閱讀,燃起了震撼卻也警醒的一記煙花。
從致敬到翻玩,其實都是朱嘉漢小說家意志的實踐,讓我先從「翻玩」(sampled)說起。如今的潮牌Supreme到早些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大約都是成功的翻玩,成功者比起致敬,更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寫得更好(賣得更貴)。但一不小心,也可能淪落「迷因」(meme)。「迷因」,是由美國開始普及的二次創作網路現象,最早是先以18世紀歷史人物為藍本,進行有意義或具諷刺性的二次創作。朱嘉漢在《禮物》裡,像是踩在繩上的表演如何致敬、偶爾翻玩,繩上的他沒有落下來,但繩下的人仍看得心驚刺激。
到了《裡面的裡面》,朱嘉漢循著歷史虛構起自己的時間,「白色恐怖」只是舞台布幕,在真實的家族史與時間線中,布幕拉起,你會看到小說家輕輕放下了這條繩子,甚至將繩子放大審視,它的存在將於小說裡造成什麼效應。
單一語言或字詞,難免匱乏與缺乏想像力,我們勉強以「理論」來替代這繩子的存在。《裡面的裡面》,朱嘉漢以不同人物事件為章,讓角色自然飽滿起來,這於小說家而言,是絕對聰明卻相對輕鬆的一種寫法。直到小說的最末,第九章〈遠方的信〉,忽然變換語境,成了秀異於其他篇章的存在。裡頭出現了寫者的「他」,與「他」的祖父阿寬、阿寬的三舅公阿信等小說主角,大量裡外對話。看似完全不同的三個時空裡,三個男人的交集,不,或許說整部小說中主要男性角色的共通之處,都是對各自「繩子」的思考,也是朱嘉漢自己的思考,更是做為讀評者的我一直以來的醒戒。
裡面的「他」,將理論知識稱作「裝備」,當你拿到一套裝備,便得以拆解任何人說的話語、反應當代現象,世間一切都可以被套用理論、引述名言。可最動人的一句卻是:「如果你並沒有切身之痛,理論的威力不過是種智力的消遣。」竟與「他」的外祖父阿寬,其一生景況與失意,相對而成,或許也與現世相扣,如小說所寫:「這些才華,與所知道的一切,折磨著阿寬的一生。」再強的裝備與火力展演,也都有盲點,「他」繼續坦承:「所謂盲點,許多時候並不是遮蔽或隱藏。而是這些都在你面前,你卻建立不了這些事物彼此的關係,以及與自己的關聯。」
於是,這本小說就像是朱嘉漢的盲區,可總是要意識到盲區,才有動力看清。就像得靠近真實,才更能體會遠方、失蹤、缺席、無聲與空白的意義,真實就是,真實不具備意義,虛構才有。比如小說裡的三個鮮明的女性角色,阿信的妻子「盆」、阿信的姊姊與阿寬的母親「笑」,再到阿寬後來所娶的「鶯」,她們各自具備的「無」能。「無」能不是「無能」,而是無的能力。「盆」的無是「不在意」,不在意才允許存放更多記憶跟故事;「笑」的無是「無法笑」,心情與祕密,才得以被藏起;而「鶯」的無,則是「無知」,無知才幸福、無知更踏實。這次的強虛構,也是強溫柔,或許也只有藉著形構這般的家族女性,才能裝載住整本小說裡不斷以書寫對話的三代男性,逼顯他們共同的另一種「無能」。
重量來自細節,比如小說中的小說寫者「他」,回憶祖父阿寬因為懷有祕密與記憶,而選擇拋棄自己的「知」,知是知識也是知道,知總是危險,於是阿寬選擇守望下一代,不再傳遞於他們更多的知,就是隔絕危險。小說裡,選擇以沙林傑的名作《麥田捕手》做為阿寬的心靈寫真,阿寬心想:「像是那本美國小說裡所寫的,自己要站在懸崖邊,如果有任何小孩可能衝過來,都要把他們攔住。無論如何都要在,都要攔住。」真實的缺口,以虛構的溫柔補上,成了小說家煉出的五色石。
朱嘉漢善於以小說再生小說,這在《禮物》裡我們就知道了。在《裡面的裡面》,他寫出被後代描寫與虛構的「阿信」,躲避於藏身的閣樓時,推開小小天窗,竟開始與書寫他的人對話:「那位書寫者可能要過許久以後,在文字裡將他重生之後,才會驚覺,他能被寫出來,是因為他的空白。他的空白,不占記憶。」至少在這部小說裡的所有真實,從時間到記憶,都只是突顯了我們其實無法操控時間,只能不斷被它吸引。那些家族中留存的記憶瓦片、影像殘字,雖然真實,卻並不重要,不過成就了小說的野心,讓虛構有了影子邊緣,有了重量。
關於虛構,朱嘉漢的野心一如書末小說家洪明道與林新惠評述的一般,是「佳構」,也是能精準投放在缺席上的「複寫」,不是無中生有。透過小說人物,縫進自己想說的話,本就是小說家的特權,於是二部合唱裡,如此定義了自己的書寫、所有的書寫:「書寫永遠是複寫,世間沒有一張空白的紙等待著我們寫。他在放上最後一本書時,突然想到這麼一句話,終究沒有寫上去。」小說裡的阿信沒有寫,可朱嘉漢寫了,就算真的沒人寫,也有人唱完了。「草東沒有派對」破題般的早早唱著:「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
過了就過了,《裡面的裡面》的意圖,本就不是要拿一張白紙寫上自己的字。複寫也是複聲,是穿越時間、挑戰時間的兩種聲音,聲音不只來自小說內外,更是小說的遠方。
比如,另一本小說。在《禮物》的第一章,有過這樣一段文字:「辨認其實不需要,最表層即是最內裡的,沒有排除的問題。我們異鄉人,是裡頭的外頭。所謂的機制,不是通過一個個的關卡而成為『同』,一直一直是在差異化,一切的團結,都是分崩離析前的暫時景象。」他一直在定義裡面與其外,如果說《禮物》的五個異鄉人(四個主角的故事加上小說家本人)成了裡頭的外頭、局外人般的故事。那麼這次,小說家走回島上、走回家鄉,「台共」的家族標籤,撕不撕下都無妨。因為「他」說了:「留下什麼都無所謂,那裡頭的更深之處一定還藏有某些東西,可以傳遞下去。……他看著她的形象,走到裡面,再往裡面一點,有個房間,播放著影像。不屬於她而被她觀看紀錄下的。」兩種聲音相遇,複聲和音。
朱嘉漢沒有去別的地方,異鄉與歷史都在他的裡面,他只是持續寫著。在裡面的裡面,「信」在寫著信、「盆」裝載記憶如盆,一切人名與事件都隨著他的結構枝蔓在伸出處瞬時凝結。你若好奇,那裡面的房間,住著什麼樣的人?人總是各式各樣,可能拿著繩子或找不到紙寫在書角,有人全知、有人無知,但他們總是不斷寫著,確保小說一直被發生。而我好奇的是,一定還有更裡面的地方。
作者簡介
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 2017年出版《寫你》, 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OKAPI專訪】散文是「看自己」和「怎麼被看」的遊戲──蔣亞妮《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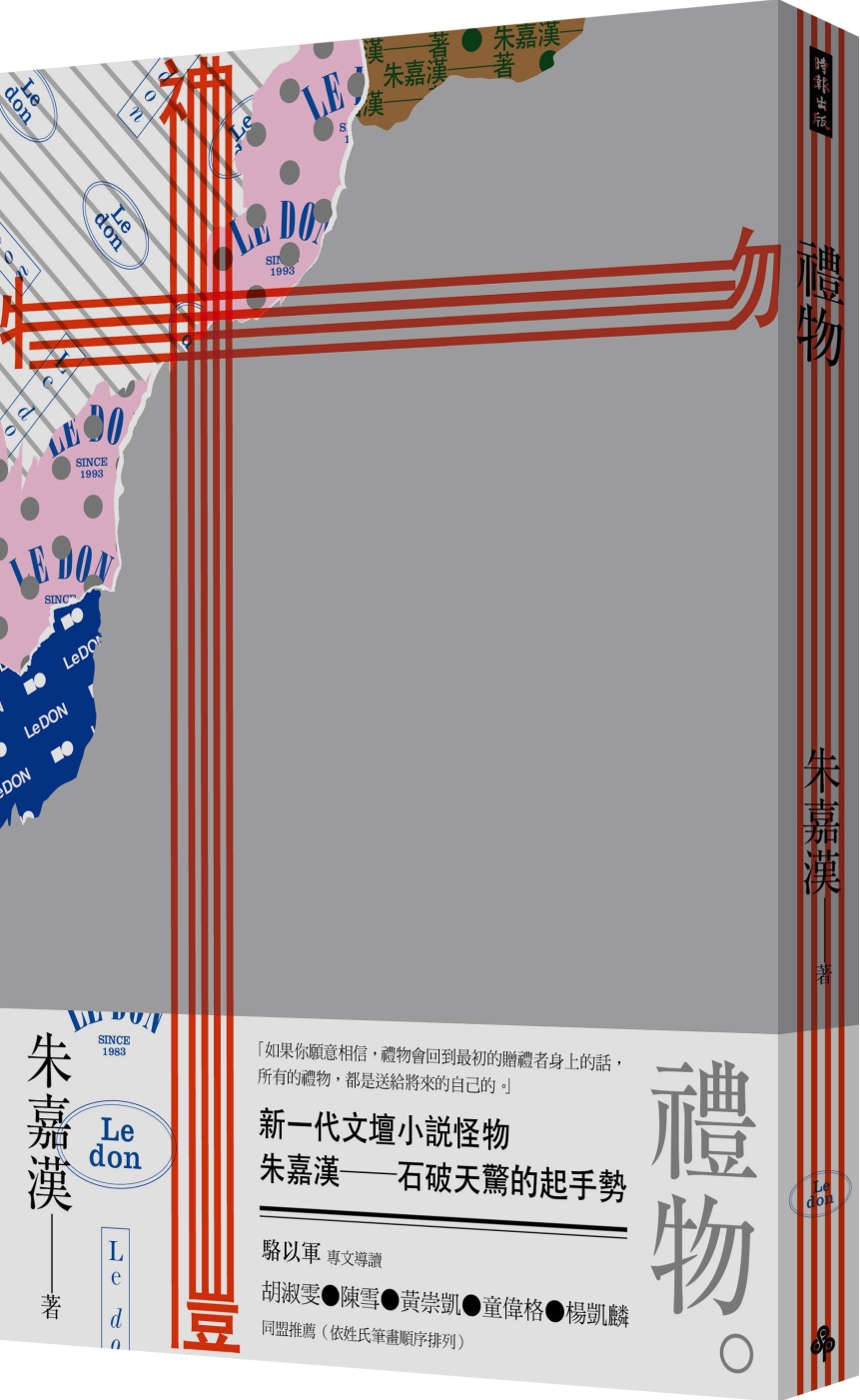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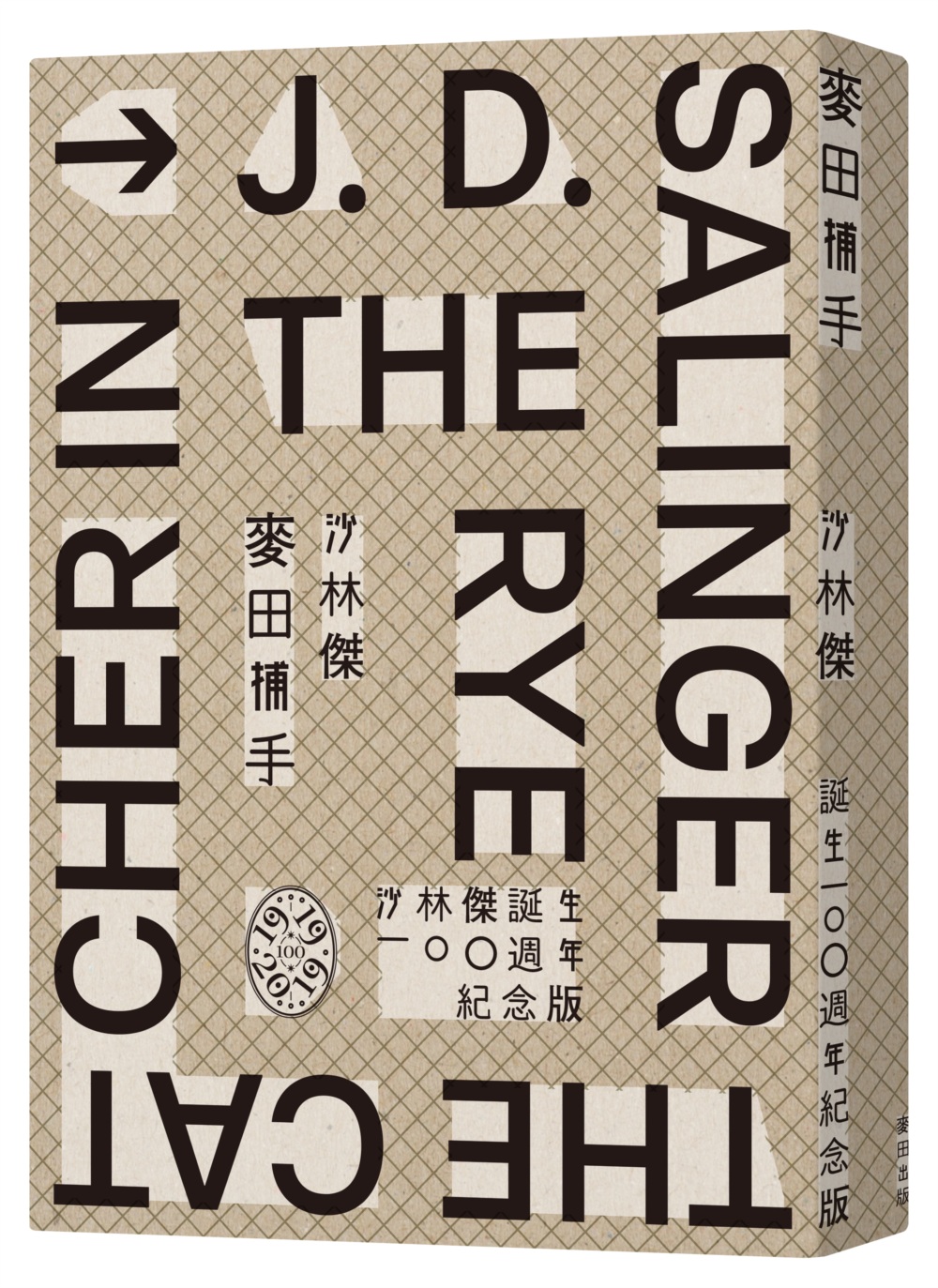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