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是因為書名,讀完林新惠的《瑕疵人型》,關於「人觀(人的觀念)」難免受到一番翻攪。「人之死」的預言早超過半世紀,沙灘上的人之臉遭浪潮抹去後,彷彿散逸在各處,聚合離散,短暫形變難以捕捉,卻無法忽略。
「後人類」一詞並不新鮮,在這本集子裡不難辨認出。然而,林新惠對理論的熟稔,已經預先除去一種大驚小怪的天真(例如覺得自己想出劃時代的小說奇想),而更專注於執行。
不堆砌辭藻(用字偏向智性有效),甚少鋪陳(敘事線明顯可辨),不眷戀古典的人性與人際關係。小說家於幾個元素的拆解、拼湊,抓準在某個崩解的瞬間。
奇妙在於,這份終結並非悲觀地揭示。畢竟早在進入小說前,悲觀與樂觀的框架早已取消。崩解,更像是一種完成,預先設定的目標。例如可做為對照的〈一具〉最後成功製作出的忠誠的夫,與〈剝落〉最後散落的白骨與「我在我不在之處」的觀看,並不是人性或世界的終結,而是永劫的開始。既然如此,便不需迴避終結,如《一千零一夜》為了續命而拚命故事,而是以敘事試探這系統的最具張力的平衡點。崩解,即完成。像是古老的遊戲疊疊樂,過程中的緊湊,在於根基的破壞卻能維持平衡(只做最安全選擇的人不是位高竿玩家),然後將一種極度的知性與感官,匯聚在不能再破壞的那個點上,不需施加任何外力,讓結構自行崩塌,彷彿一切在等待那個崩毀即完成的瞬間。
這樣的小說,不可避免地有展演性。也許因為如此,作者本身的聲音在小說中是內斂的(紀大偉語),壓抑、甚至剔除了表演性。
《瑕疵人型》裡的人物,觀念性極強,連同肉體、器官、記憶、精神等,幾乎直接訴諸於觀念,無需設造擬真假象,而是擬象。如此簡單,擬出人的形象。
諸多的篇章,是沒有名字的男女,只以「他」、「她」,以及「我」代稱(本書的分輯亦依據此)。代名詞取代名詞,在此成為唯一之名。缺乏面孔特徵描寫,亦少有深入的身世設定(除了〈虛掩〉、〈佑佑〉同樣可當對照的兩篇);相對於許多精準的數字(譬如〈Hotel California〉的肋骨計算法),年齡只是有個大概階段(成年、中年);工作則呈現單純的勞動與機械感,而非與個人的認同、價值勾連(唯一的例外〈跳舞的Kuma〉則精準處理了自我認同問題)。
極簡的人物設定,放置在極端的情境,加上語言的去抒情感,讓我想到的不僅是賽伯格這般清楚可指涉的路線,反倒是貝克特的晚期作品。譬如《美好日子》裡卡在沙丘多語女子或《終局》裡的失語與失能(尤其卡在垃圾桶裡回憶的父母)。我相當同意,林新惠在小說裡呈現的「人」的消失,尤其情感、人際關係幾乎可透光的削薄、一扯即破的表象,目的不在否定人性,而是探索人的界線(但絕非人文主義式的,也非藉著冷調的書寫偷渡抒情成分,她這點做得非常徹底)。會想到貝克特,主要是因為語言的緣故。儘管不像劇本裡的人物更依賴言說,《瑕疵人型》的小說人物,給我某種一致的怪異感在於:這些人,無論是沉默或多語,語言都是相當陌生的。簡單來說,主體的意識需要語言結構的建構,然而在這裡,每當角色試著思考,使用語言,反倒讓主體更加迷失。
語言無法用來表述情感與感受,無法用來認識外界與自身,無法推理現況,無法慰藉,尤其,無法溝通。
這些人物,都有相當強烈的獨語感。這些人的活著並不留下多少痕跡,而不存在的物事痕跡卻如此明顯(〈旅館〉、〈虛掩〉),連叫喊都嫌多餘。獨語形塑起強烈的孤寂感,像〈說話〉裡無比懷念發生意外的妻的叨念的男人,找尋不到一個位置。如果語言並非溝通,而是像〈一具〉裡讓人忠貞扮演系統指派的角色的一道道指令,那麼孤寂者的相遇,孤寂者與世界的試圖聯繫,最終只是「孤寂環生孤寂」,是「永恆他者的孤寂」(〈LCL〉)。
這種失語,不光是讓人無從尋得認同,無法進行認識(不需真偽,只能被動接受,選擇永遠是被制定的選項),甚至剝奪了痛感。雖像是小說的操作,刻意在描述中以鈍感取代痛感,消失的手指(〈一具〉)、剝落的血肉(〈剝落〉)、剪成另一個人(〈剪〉)、像是愛撫般摘下自己生命花瓣(〈假花〉)。最明顯書寫的痛,是〈虛掩〉裡對女兒的生理痛無能為力的父親,然而那卻是一個中年喪妻男子,急切想要理解但永遠被隔絕在外的「切身之痛」了。痛關乎死,也關乎生,痛是感受生命存在的最深切感受。在此,稍微僭越的詮釋,這種痛感的剝奪,在於作者並不輕易以既有的語言去表述這些尚未被歸類的痛。
尚未被歸類,尚未有言語可以表述的痛,如同一種尚在等待語言界定的存在狀態。
那麼,這些沒有痛感的身體呢?如同張亦絢所說,這些個體,預先被剝奪了完整的概念。所謂瑕疵,彷彿是出廠設定,不瑕疵,不成人。痛仍然存在。或者說,取消的痛感,召喚出了另外一種痛:體驗不到卻無比渴望的痛。基本上,不難辨認,這是一種更深邃的,對於愛的渴求。
所以,失語並沒有痛的男女,無論怎樣的身分與身體,在小說內都不斷地拆解與被拆解,重組與被重組,欲望著成為自己所不是之人。讓死物成為真人(〈安妮〉),修剪自己成他人(〈剪〉),剝下血肉填補另一個性別的模型(〈剝落〉),不斷被戳針好成為稱職的母體容器(〈電梯〉)。缺陷的人期望完整,期望徹底理解,但真正仿若消弭了一切界線,進入更大的整體後,「才曉得真正的答案不會到來」。這種「全然取消他者與自我的不可能」,正是宣告「我」是無所遁逃的:不管你多虛擬、怎樣裁剪、化身為布偶、進入LCL,我想要不是我,人想要成為非人,即便是這樣極端的情境,仍是不可能。
的確,如同〈Hotel California〉所說的,實在與虛擬的辯證已經過時。《瑕疵人型》除了少數的篇章外,並不被小說的再現系統給框限。這樣做法稍嫌危險部分在於,這些小說允諾的作者思考,可展示並抹去自身思考的痕跡,卻大為限縮作者自身的反思空間(甚至讀者)。即便有,也在敘事美學中必須淡化。例如〈Hotel California〉的敘事者的自我質問,偶見尷尬,且必得回歸循環的迷宮。儘管傳統敘事的反思性經常令人不耐,時有故作姿態與自溺(且令人膩),但往往這樣的反思不是為了追求意義、價值,或是救贖,而是讓作者可以有個迴路,在拋出小說的話語之後,能安然重返自身的語境,並重新整裝至下一回的重啟。
但也許,用林新惠自己的小說話語就能解釋。在密不透風,如同加州旅店那般永遠出不去的情境裡,仍可以在標示的邊界上詢問:「為何不能偏離?」
或更簡單的說,出口在曖昧處,在那虛掩的房門,或是那個義眼流下的人工淚液中。
作者簡介
專長法國文學研究,評論與創作作品散見《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雜誌》、《週刊編集》、《文訊》等。長篇小說《禮物》獲國藝會創作獎助。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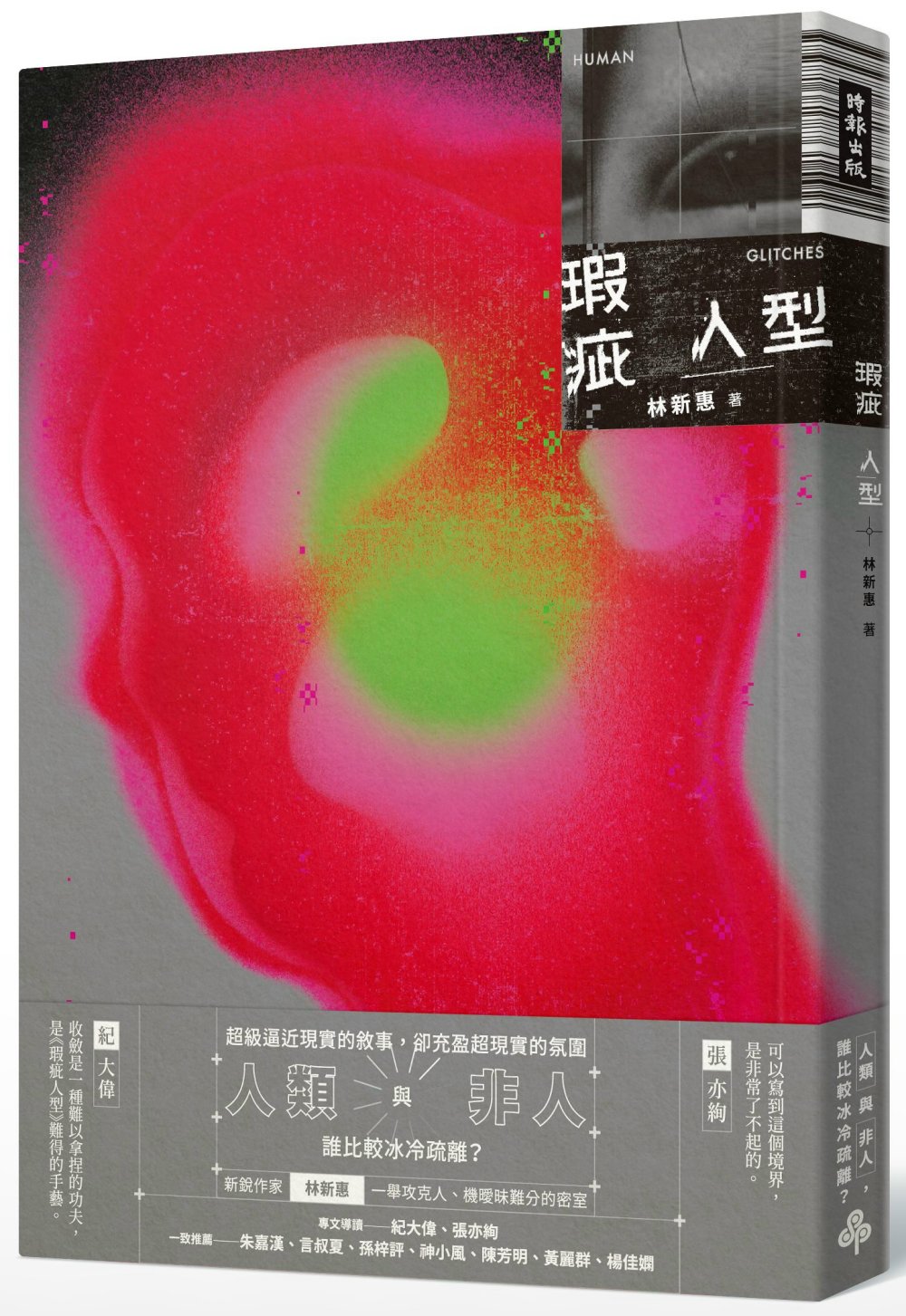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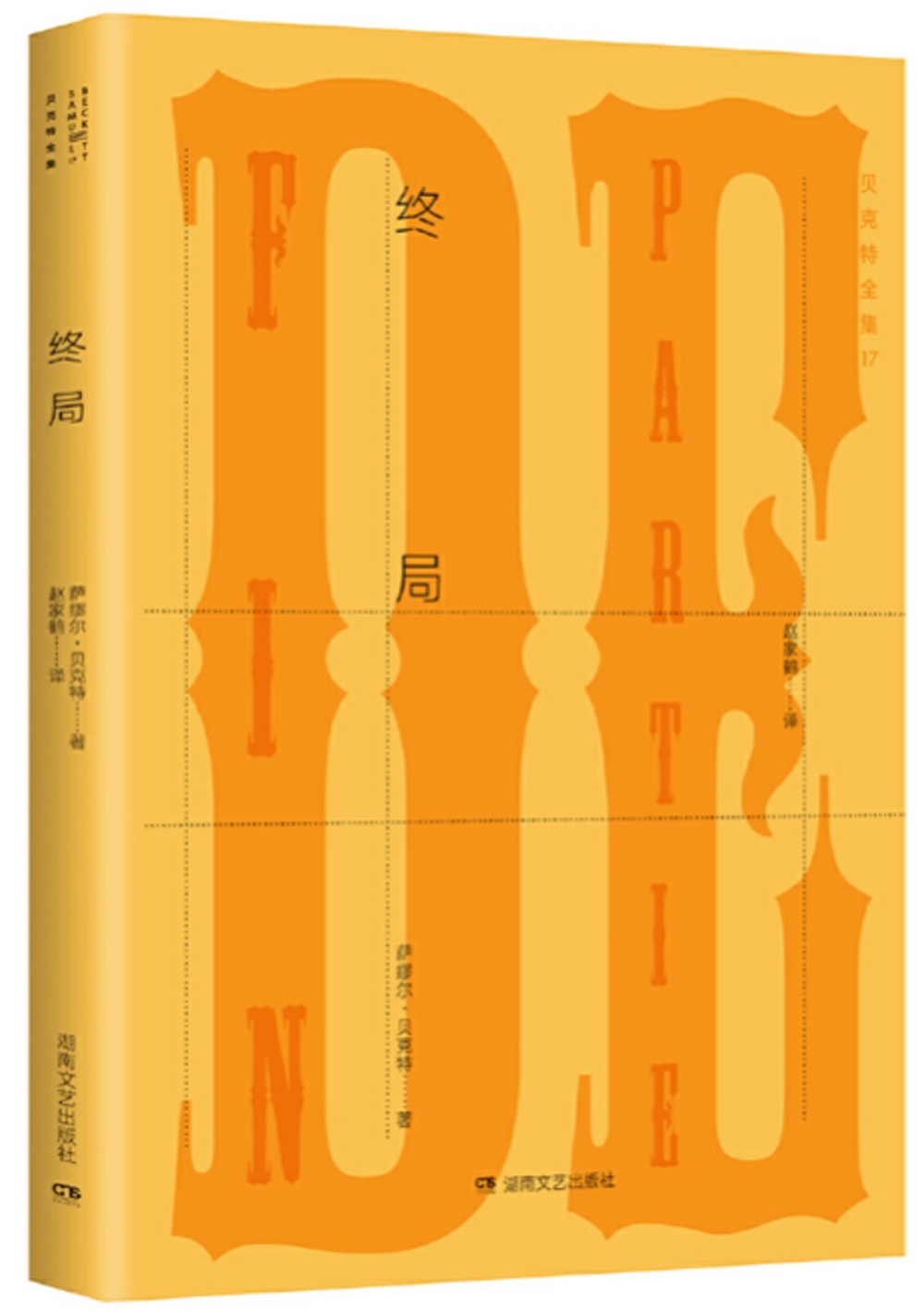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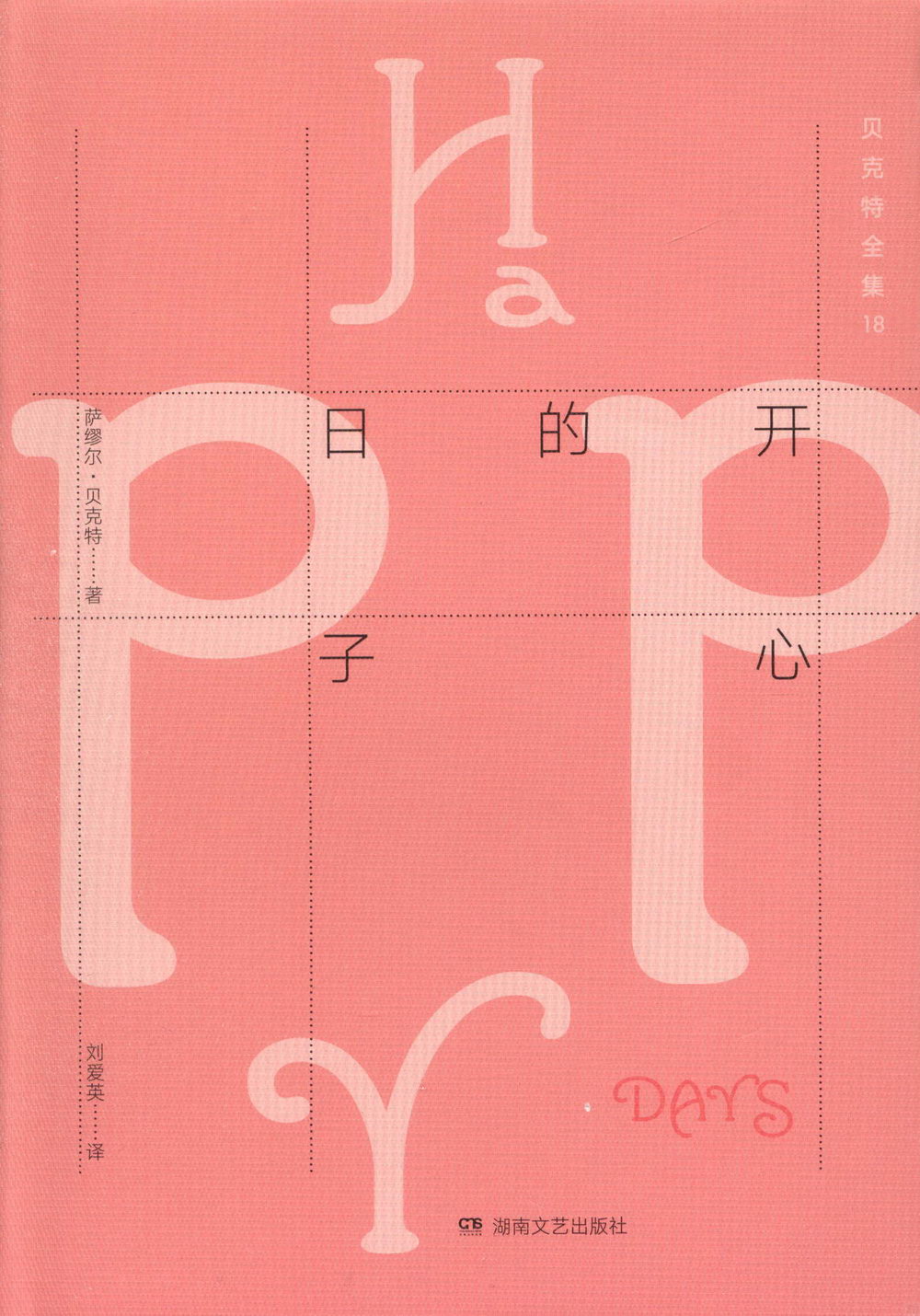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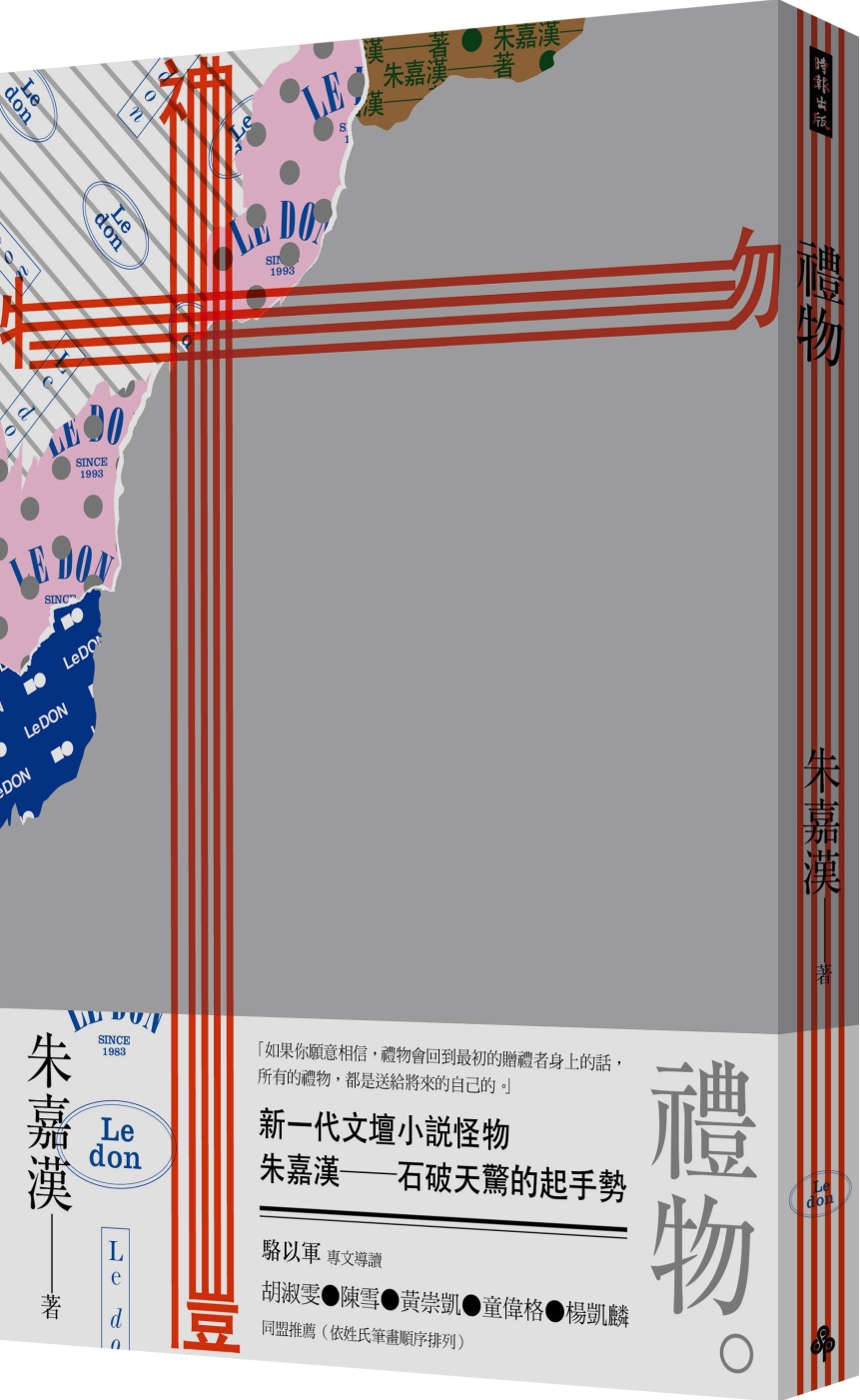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