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嘉漢是典型的斜槓青年,大學念完人類學,前往法國攻讀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班,回臺灣後他教過法語,與太太經營甜點店,並策劃多場引介法國重量級作家的講座(如巴塔耶、卡繆、普魯斯特),還擔任過某網紅粉專小編;目前在北藝大兼任講師,教授「哲思隨筆選讀」課程,也在台師大進修推廣部教文學和寫作。熟稔法國文學的他,在2018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禮物》,便將作家莒哈絲、阿娜依絲.寧、班雅明、布赫迪厄的文風與思考模式,透過四位留法臺灣學生的定期聚會加以展現。
《禮物》出版不到兩年,朱嘉漢又完成最新長篇小說《裡面的裡面》,書中結合史實與虛構,由不同角色進行敘事,帶領讀者從多重面向進入故事核心,主要登場人物有台灣共產黨員「潘欽信」、潘欽信擔任滿洲國通譯的哥哥「潘欽仁」、潘欽信的遺孀「廖盆」、潘家大姐「潘笑」。小說就從潘欽信的逃亡開始,他在日治時期加入共產黨,被殖民政府圍捕取締,出獄後又遇上國民政府遷台,再次被右翼政權盯上,成為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政治受難者,其後,家族成員或許憂心被列為黑名單影響出路,閉口不談這段往事,終成沉默之人。
《裡面的裡面》不僅碰觸台共、滿洲國以及白色恐怖的歷史,也是朱嘉漢的父系家族史的一部分。朱嘉漢說,「長期以來我的家族不談這位台共親戚的事,這個時間長到讓我感覺很奇特。甚至我很疑惑,比如長輩都說我阿公很有教養,是延平中學的英文老師,但這些長輩們的英文很爛,有點『棄絕教養』,這算是我寫作這部小說的私人因素。而這也澈底顯示,歷史的缺塊是絕對有可能的,並且是自然而然、無意識形成的。我的小說就是要指出:遺忘,也是記憶的一種模式。」
當我們身處轉型正義的時代,面對「不要害怕想起來」的普遍號召時,朱嘉漢直指,關於白色恐怖的歲月,有時不是對記憶的壓抑,而是我們真的會忘記,不斷地忘記。在《裡面的裡面》,這個忘記與空白,反倒成為一種「抹去痕跡的痕跡」,也是時間的證據。朱嘉漢在小說中使用三種空間模式:「折疊」、「承接」及「保持透明」來描述三個角色(潘欽信、廖盆以及潘欽仁),同時也展示對記憶的隱喻:
逃亡的潘欽信曾躲藏在大姐潘笑家的閣樓,後又乘船逃往香港,他將自己的生活過得如影子般扁平:「他學會緩緩地讓尿液流出,在龜頭打開的小小縫隙,用尿壺接著不發出聲響。」而寡婦廖盆,以盆為器,她收攏了世間所有祕密:「聚著他人心事,毫無壓力,以至於羞恥的、令人見笑的心事,在寄放的那一刻,也彷彿找到最好的暫時安置。」潘欽仁在滿州國擔任中日之間的通譯,他如此想像自己的存在:「在最好的狀態,以自己的嘴,轉達著大佐的話語給皇帝。他感覺自己是透明的,最好是透明的。他在場,但又不像真的在場。沒有人回應,沒有人發現他在場。」

《裡面的裡面》是朱嘉漢家族史三部曲的第一部,目前他已開始構思第二部母系歷史《外面的外面》,與第三部《邊緣的邊緣》。才剛完成一本小說又馬上開始準備下一本,儼然已是朱嘉漢的寫作模式,多工作業、高產能、不拖延。這種相當令寫作者艷羨的節奏,其來有自。
與太太經營甜點店的期間,他也同時開設文學講座,看似有美食有文學,是個充滿夢想之地,但他苦笑說,「開甜點店是我離文學最遠的時候,當我發現一個月竟看不完一本書,瞬間感到嚴重的精神危機……」後來甜點店因故歇業,他到補習班教法語,也利用零碎時間接案和寫作,《禮物》便是在這個狀態下慢慢完成。而後,他更晉級到一天就能處理翻譯、備課、寫作、家教等工作。
朱嘉漢說,《禮物》跟《裡面的裡面》可以放在一起看,主題的差異性雖然很大,卻是他在差不多時期完成的作品。「《禮物》出版後一個月內我開始寫《裡面的裡面》,七個月完成故事,構思的時間是差不多的。《禮物》對我而言有其必要性,那比較像是我在清點軍火,究竟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而走到《裡面的裡面》就變得樸實很多,我算是用肉搏戰的方式來梳理歷史。」
梳理歷史,是朱嘉漢用心的嘗試,他強調,「家族史是歷史的另一種版本,我相當在意這個版本。因為很多人是憑藉這些記憶活下來的,即便有些可能不是『史實』,但這個虛構的版本,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真實。」
因此,朱嘉漢挪用親人的身世與遺下的手稿資料,用小說表述歷史也可能是一種虛構機制,「我喜歡像俄羅斯娃娃那種一個故事套著另一個故事的方式。比如當我們嘴巴念著『裡面的裡面』,可能會忍不住嘴賤繼續接『的裡面、的裡面』,這就是一種動態思維的呈現。」《裡面的裡面》不同章節的敘事者,正是他所說的「俄羅斯娃娃」:台共潘欽信的「裡面」,也有著象徵國家機器的憲兵的「裡面」、與遺孀廖盆的「裡面」,由此,即能帶出白色恐怖施加在每個人身上的不同作用與意義。「這當中有歷史的曖昧,也有對遺忘的不甘願。」

有別於《禮物》中口若懸河的女性角色,朱嘉漢在《裡面的裡面》安排了兩位女性角色:廖盆與潘笑,卻幾乎讓她們保持沉默,滔滔不絕的剩下男性角色與敘事者。「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女性的歷史本來就是很沉默的,甚至當她們能說的時候,反而寧願選擇不說、保留空白。」小說裡,廖盆經營舶來品事業,一個人扶養四個女兒,也接濟蔣渭水的孫子,甚至許多跟台灣文化協會、台共有關的後代都受過她的照顧,「她基本上是一個『不像寡婦』的寡婦狀態。潘笑跟廖盆是最重要的兩個角色,沒有她們的守護,記憶就沒了。」與其把她們的沉默變成話語,朱嘉漢更想尊重她們的沉默,「要讓沉默有價值,不是虛構一些話語給她們的嘴,而是去描述那個沉默,召喚出她們沉默的形狀。」
朱嘉漢在意歷史,也信仰小說之神。他用小說召喚歷史中被抹消的空白,在寫到原先要命名為「絕後」的尾章時(後來定名〈遠方的信〉),更聽見每個角色都跳出來與他對話。奇蹟的是,朱嘉漢的父親在讀完小說初稿後,告訴他小說中祖父焚書的段落,的確是自己對父親印象深刻的記憶:「父親常焚書,而且技巧很好,從不冒煙。」朱嘉漢聽完驚呼:「齁!為什麼不早點說。這是多麼小說語言的畫面,要燒書又不讓它冒煙,就能知道其中意志之大。」驚呼過後朱嘉漢隨即又回復沉思的表情,「也許是因為被我的小說觸發,才讓我父親想起那段記憶吧,即便可能是虛構的。但無論如何,都像是白色恐怖的一個隱喻,而寫作就提供了召喚這些失存記憶的可能性。」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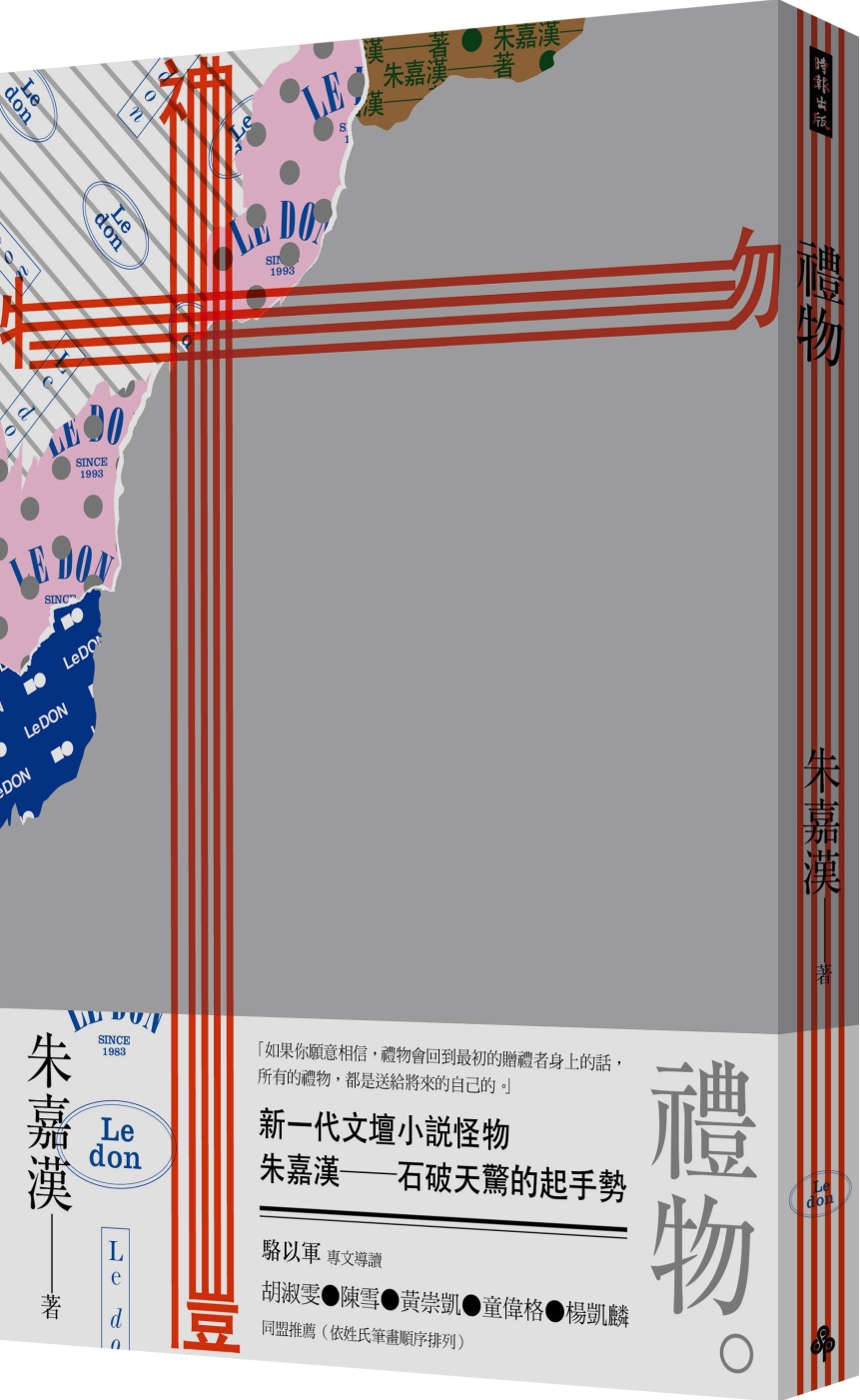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