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2月14日,墨西哥的女權、婦權與性平組織集結起來,走上街頭,展開「情人節起義」,導火線是一名25歲女性英格麗・愛斯卡蜜亞(Ingrid Escamilla)被46歲的丈夫殺死並肢解,而警方竟然將現場照片上傳至社群網路,甚至販售給多家媒體。這一連串行徑勾起了墨西哥女性常年壓抑的憤慨。在墨西哥,每2小時又20分鐘,就有一名女性因「殺女」(femicides)而死。而在遊行當天,參與者在首都國家宮(National Palace)的大門噴上「殺女之國」,有人則受訪表示:「殺女,在墨西哥,不僅是一種常態,甚至是逐漸流行的病態。」殺女為什麼盛行?有論者曰,由於墨西哥長年深陷毒梟戰爭,社會普遍強調陽剛氣概,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女人陷於非常脆弱的處境。然而上述描述流於冰冷,未能提供足夠的景深。
 受到丈夫殺害的女性Ingrid Escamilla(圖/wiki)
受到丈夫殺害的女性Ingrid Escamilla(圖/wiki)
所以我們得借助文學,得透過《為失竊少女祈禱》以及小說主角黛妃.賈西亞.馬丁尼茲的口吻,甚至她的人生,帶領我們深入那個女性並不被視為人的風景與地貌。
黛妃與母親麗塔住在墨西哥南部格瑞羅州(Guerrero)的山區,據麗塔所述,這兒男人出路有二:
一、渡河至美國,並淡忘墨西哥的妻兒與其他,按麗塔的說法,「走入偉大美國的墳場」;
二、成為毒販,背著AK-47步槍,戴著昂貴的太陽眼鏡,從此過著槍殺擄掠的營生。
寥寥數語,即道盡了墨西哥的處境,墨國在地緣上深受美國干擾與影響,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後,墨西哥失去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農業受挫,勞動人口或者外流,或者留在當地,進入黑道與毒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國家情勢給任意切割著。麗塔說:「我們失去了男人,從他們和他們的美國婊子那裡染上愛滋病,我們的女兒遭竊,兒子離家,但是我愛這個國家勝過自己的呼吸。」黛妃也說:「我想起我們那片充滿怒氣的土地,曾經有過真正的聚落,卻遭到毒販的犯罪世界與移居美國的風潮摧毀。我們那片充滿怒氣的土地是破碎的心情,每間小小的家都是灰燼。」
 墨西哥南部的格瑞羅州。(圖/wiki)
墨西哥南部的格瑞羅州。(圖/wiki)
在毒品與槍枝至上的社會,女性,尤其是年輕貌美的女性,淪為資產,可供交換。毒梟們為女孩們建冊,悉心等候她們熟成,女兒的父母們,或遮掩其性別,或千方百計地「醜化」女兒,他們試著家裡挖洞,等到有人來「狩獵」女兒時,把女兒埋進地洞。黛妃與她的玩伴的童年,充滿了疑猜與驚懼。黛妃的父親前往美國並消失了。美豔動人的朋友寶拉被毒梟擄走了一段時日,憑著己力回來,然而心智已退化得無法溝通。艾絲黛芬妮的父親前往美國謀職,並把愛滋病傳給她母親。瑪莉亞的家庭,似乎也掩藏著不可告人的情事。所有我們眼中「戲劇化」的元素,卻是這些女孩的日常,她們對人口綁架、愛滋與槍枝習以為常。
嗣後,黛妃與戀人胡立歐「僥倖」地占用了毒梟的資產,(不意外地,胡立歐也曾面臨兩條路線的抉擇,他選擇前往美國,卻被巡邏衛兵發現而殺了對方,只能回逃墨西哥,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我認為,與胡立歐的美好時光是作者珍妮佛.克萊門鋪排最高妙之處,墨國人民的幸福往往建立在走鋼索上,她安排黛妃也上了鋼索,一如母親麗塔抗拒不了順手牽羊的小確幸,黛妃也決定在不屬於她的財富裡,與情人徹底探索性與愛的歡愉。縱然日子多麽艱辛,黛妃與麗塔,還有其他女性⋯⋯她們仍試圖跟苦難討價還價,她們深諳扭轉命運的不可能,但她們依舊小動作頻頻,把握每一次能為自己作主的權力。
而在最終章,黛妃捲入一起命案,被送進了大牢。如同黛妃的童年,作者再度形塑了幾名立體的女性同夥,差異在於,童年時女孩們往往是純粹的受暴者,而這些女囚,則隱隱傳遞了受暴者轉變為加害者的動態。這些女子都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而她們的罪,都能與她們長期受暴、被利用的經驗,有著千絲萬縷的交集。
《為失竊少女祈禱》組織巧妙,作者織入許多人性的疑難與謎題,環環相扣,每一個設計都精緻且有其必要,閱讀上你屢屢會因事件的鑲嵌、呼應,而逐漸對劇情走向不可自拔。我尤其欣賞裡面每一女性角色,她們面孔多元,在荒蕪中仍懷藏豐沛的欲望與意想,像是麗塔,她尖酸刻薄,認為報復比寬恕更好,然而讀者會在她犀利的言語中,逐漸明白到麗塔反映了墨西哥女性的痛苦:她們承擔著這塊土地上長年暴亂與別離。她們一無所有,政府跟警察尤其不能信任,以及,她們無處可去。而黛妃,她繼承了母親慧黠與微微的狡猾,也有個人的幽默與浪漫,她討喜又迷人,她因應考驗,想辦法在處處侷限中書寫下個人的觀察。這些女人們,偶爾與體制共謀,偶爾背棄規則。讀者不僅看見這些她們所承受的折磨,也知悉了她們的智謀與選擇,為她們祈禱,也莫忘她們的意志。
延伸閱讀
- 從N號房性剝削事件,看韓國性別的不平等
- 江鵝:我因此在性上,看見自己敗棄舊身崩解僵名的可能──讀張亦絢《性意思史》
- 性侵受害者怎能不談論呢?不談,本身就是一種欺騙。──讀李懷瑜《生命暗章》
- 從「女性主義」延伸7個短篇,韓國女作家如何寫出女性的故事?──讀《致賢南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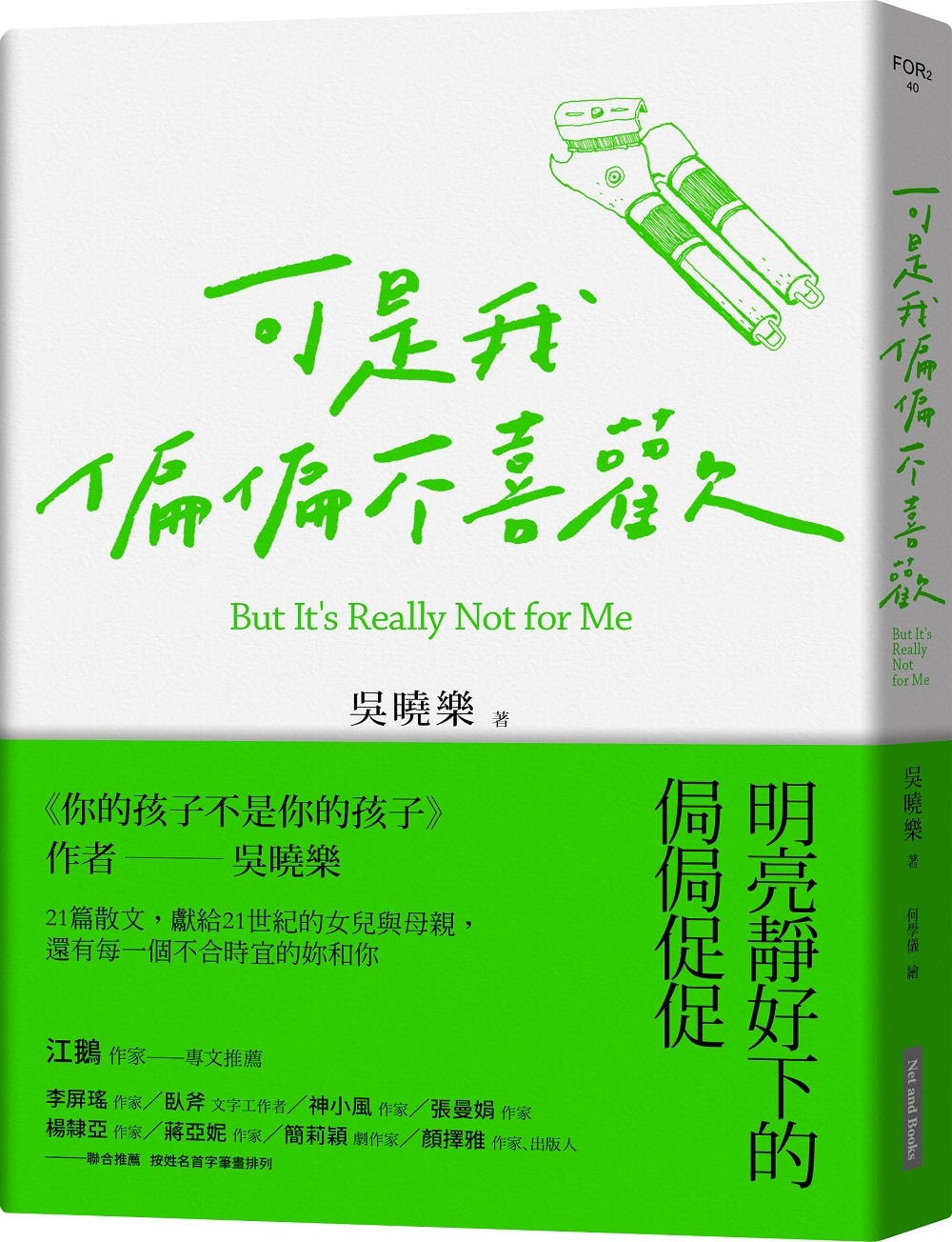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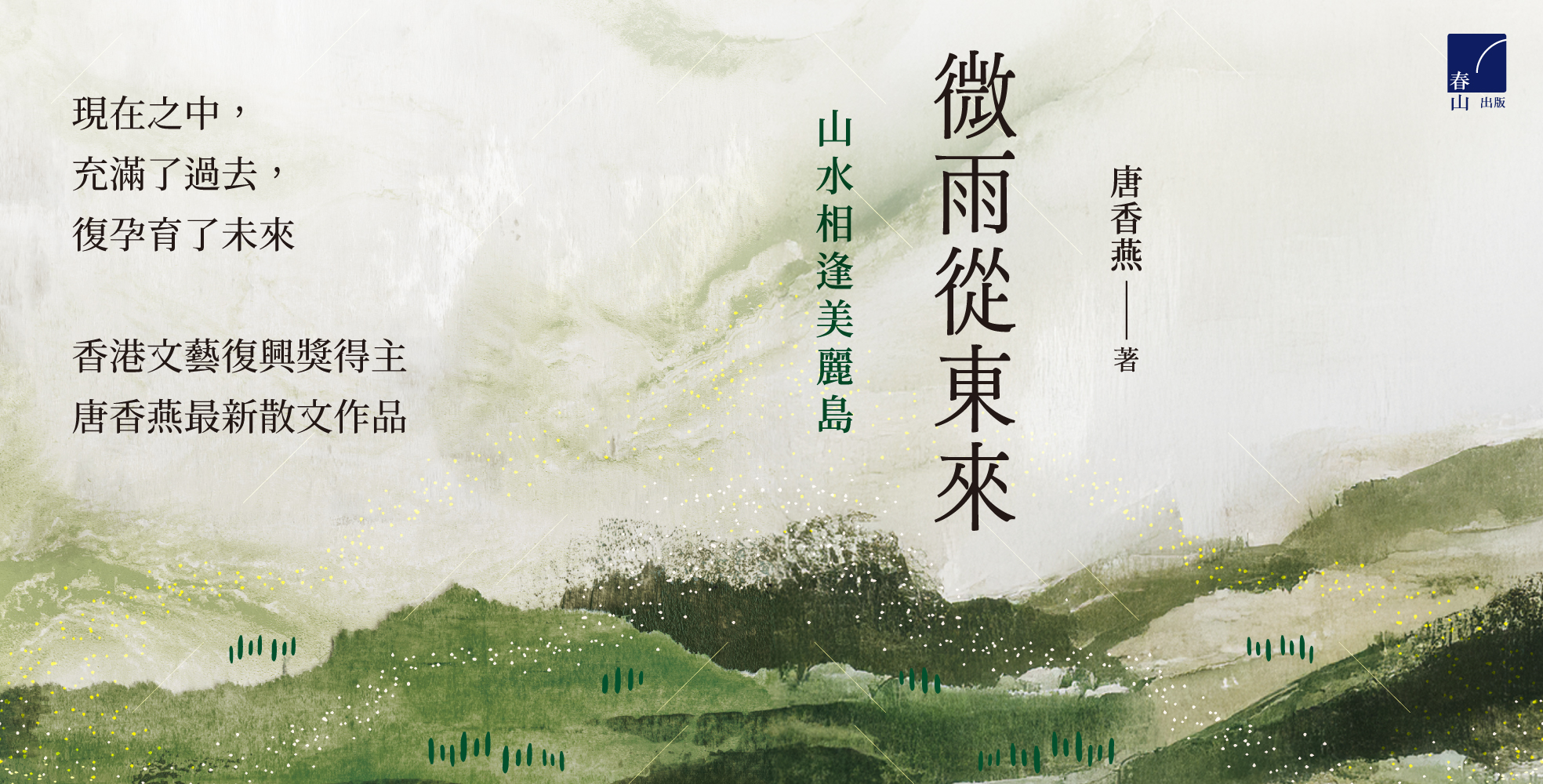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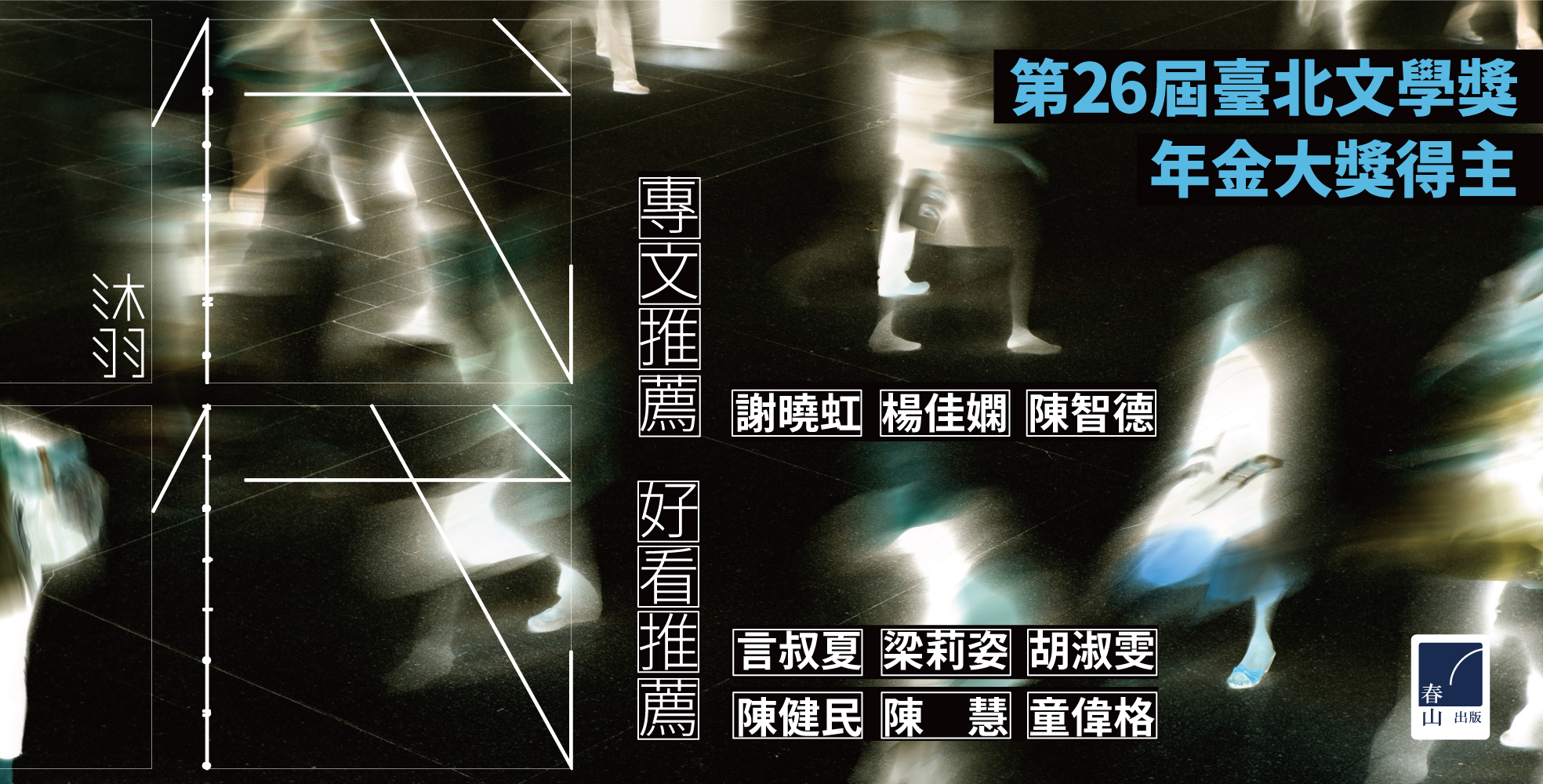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