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懷瑜(Winnie M Li)的《生命暗章》(Dark Chapter)不同於其他翻譯小說之處是:它如此遙遠,卻又如此靠近;如此真實,卻又不斷地在嘗試「不可能」。它盡力維持了一種小說中,難以被實現的絕對平衡與相對。勇敢地去處理自己曾被性侵的往事,但她的勇敢,遠遠不只於性侵受害者的現身,更因她選擇去挑戰我們生命中,「絕對的對與絕對的錯」。
我曾讀過台灣小說家陳思宏在《生命暗章》甫獲2017年英國「非布克獎」(Not the Booker Prize)時分享的文字,他以#MeToo的一員現身,從他的童年召喚出了相近的創傷感,坦然公開自己在2014年奪得林榮三小說首獎的作品,是過往性創傷的遺跡,於是他決定「說出口,寫下來,大聲說,我也是。」李懷瑜是,他也是,或許誰都可能說出那句「我也是(#MeToo)」。正如李懷瑜曾說過的,如果透過她的努力,能夠改變世界一件事,「我想要創造一個世界,在那裡,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可以毫不羞愧地說出真相,而不被世人評判。」

李懷瑜在TED上說:「希望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可以毫不羞愧地說出真相,而不被世人評判。」(圖片來源 / 作者fb)
 《控訴》改編自真實事件,直視「檢討被害人」的司法體系。茱蒂佛斯特因本片奪得1989年第61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控訴》改編自真實事件,直視「檢討被害人」的司法體系。茱蒂佛斯特因本片奪得1989年第61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當我回顧童年,能與鬼故事一樣,讓我蒙住雙眼、懼於想像的事件或新聞,多半涉及惡意。我在16歲時,曾經看過一部老片叫《控訴》(The accused)。茱蒂佛斯特稚嫩的臉,控訴著一段在酒吧的集體性侵案件,它與《生命暗章》都觸及了一個核心,與傷害本身無關,而是受害者在法庭與社會上所面臨的質疑。《控訴》裡的女孩,不斷被提問「妳為什麼一個人去酒吧?」、「妳為何穿得那麼少」、「妳為何與男性搭話?」。一如《生命暗章》裡的薇薇安,因為她總獨自一人登山、旅行、回應其他旅人的交談。16歲看的電影,得到很後來才能從那些驚心的場景裡掙脫,看出一些別的滋味,即使是這世界更深沉、刻薄的滋味。
《生命暗章》裡的加害人強尼,在與薇薇安相遇於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那片幽谷森林時,也是16歲,這也讓作者開始陷入了思考,一個才16歲的少年,「他」為何會做出這樣的事?
哲學裡,有一種顛覆的思維系統,叫做「道德相對主義」。即世間沒有絕對的對錯、絕對的道德真理,即使是救人、殺人、亂丟垃圾,都沒有辦法冠以絕對的對錯,一切的事物都是相對的,就像「太陽光是黑色的」並沒有錯,對於某些視覺障礙者,這就是他們感知的太陽。《生命暗章》的作者李懷瑜,就以她的小說處女作呈現了這樣的相對感知。
小說初始,便以許多段薇薇安與強尼各自的成長經驗起手,一個是成長於「漂旅人」家庭中的弱小男孩,有竊盜前科的哥哥、家暴的父親,生活是四處流浪與嗑藥;一個是18歲進入哈佛,從小對旅行、文化、民俗學有所癡迷的亞裔美國女孩(當然是白領家庭)。以及他們各自的、在交會前所發生的第一次加害成功(強尼,14歲 ,都柏林)、第一次逃脫被害的經驗(薇薇安,19歲,奧伯斯多夫)。
當然,李懷瑜並未試圖替任何人的罪行開脫,她所做的僅僅是努力還原這個世界,以及當中若有對錯,對錯的脈絡。正如作者在繁中版自序裡寫道:「我選擇以這種方式寫作,讓受害者與年輕加害者的經歷交錯呈現,讓大家能夠開始理解此類罪行的根源。」李懷瑜的還原,絕對是最大限度的還原,除了紀錄片鏡頭般還原自己從報案、拍照、身體被侵入採證、上庭將每一個難言的單字重現給陪審團的瞬間;她甚至讓自己之外的角色,一如加害者強尼,有了文學上的悲壯性。比如那場強尼的父親逼他去自首前一晚的歡送會,親友齊聚,遠道而來,他們像一群海盜們為出征舉杯暢飲,所謂的「罪行」與「自首」,也變得如投名狀一般,彷彿是他們成為男人的標誌。甚至強尼的父親還有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說:「『我的強尼,他現在長大了。即使我們不知道之後他會怎樣,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老爸停頓了一下,清清喉嚨。『我們確實知道的是,他將永遠是我們的一員,永遠是史威尼家族的人。』其他人咕噥說著:『Sláinte.』(祝身體健康)。」當她選擇還原,就不只是還原自己或還原他者,她要還原的是「我們」。
而這世界,面對受害者的惡意與質疑,也沒有被李懷瑜選擇性隱蔽。不只是對於受害者的正當性,她沒有遺漏,她更進一步地、極盡可能勇敢的深掘出另一種受害者模樣,一個極可能令人不喜愛的受害者形象。比如薇薇安廣發電子郵件告訴她親密的20位好友,自己遭遇了什麼;比如薇薇安在自述受暴經驗時,她心裡一一閃現的那些他人的念頭:「讓他們看看,妳被強暴時有多悲慘。」、「妳不過是為自己創造了最佳形勢,要我們相信妳是強暴被害人。但事實上,妳是一個全然掌握局勢的女人。」這些想法,危險而不堪,卻是真實世界裡如她一般的受害人,時時遭遇著的。李懷瑜明知道談論、重申、辯證自己的悲慘,尤其是藉由「文學」這樣的階級產物,挾帶著她超高學歷的女性身分,從華人家庭甚至西方世界,都無法避免會引起某種隱晦的獵巫情結。
但是,就像小說中薇薇安所說的:「她怎能不談論呢?她怎能漠視那個星期六下午所發生的嚴重事件?真要這樣的話,這根本是個天大的謊言。」不談,本身就是一種欺騙。李懷瑜不只要談,而且是盡她可能的不溢美、不溢惡,真實地去談,真實到去包含了這世間所有道德的相對可能。於是,她才能夠在得知強尼違反假釋條件消失時,讓薇薇安的心裡生出那句:「他在逃,就和她一樣。」
李懷瑜用親身經歷與近十年的沉澱,寫出這一本小說,她沒有選擇含蓄而幽微的文學筆法,一切的文字都如此清晰與直白。所探討的也並非性侵的錯對與悲慘,惡的度量衡沒有絕對。她只不過是帶領所有讀者與世間之人,一起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構成了怎樣的世界?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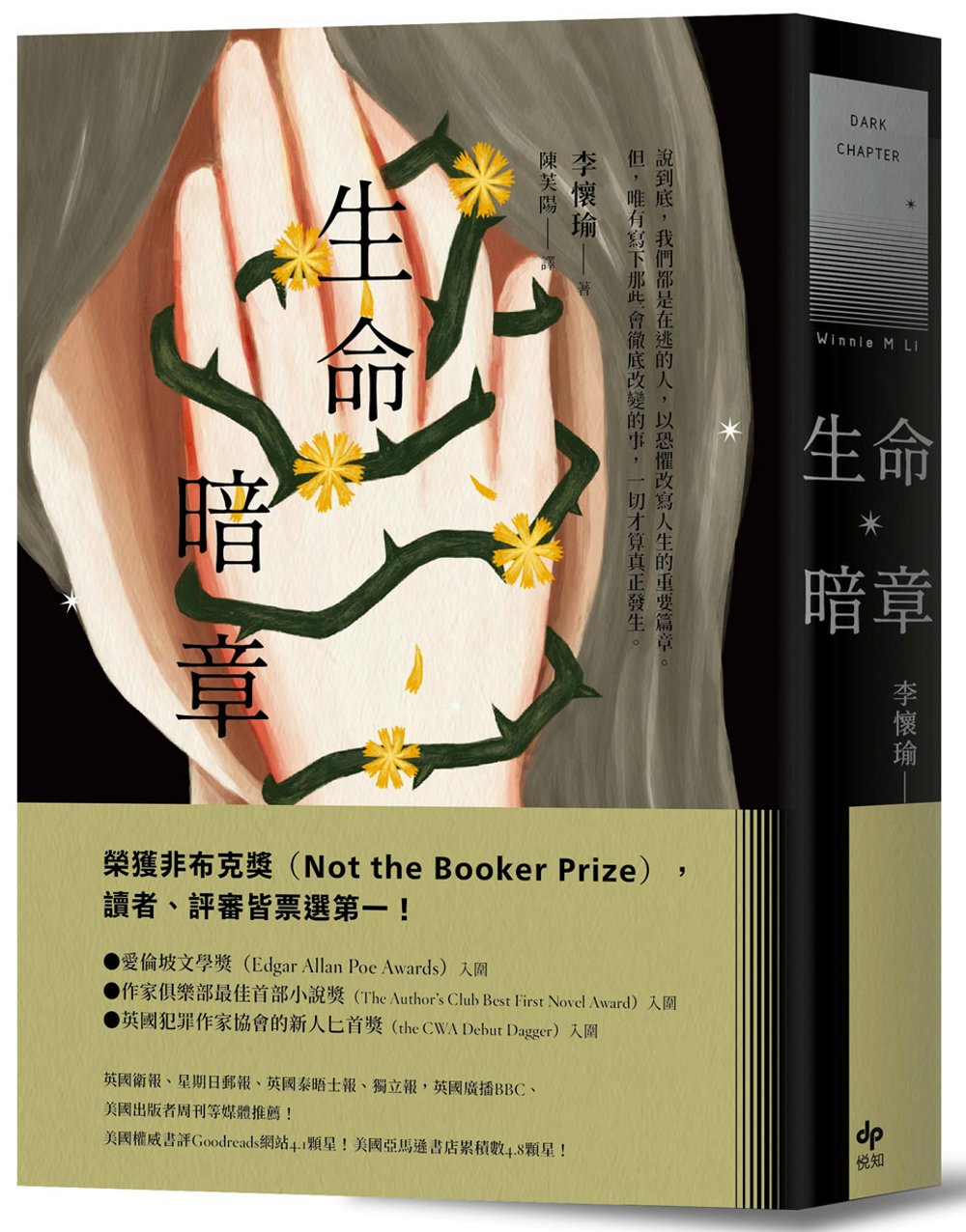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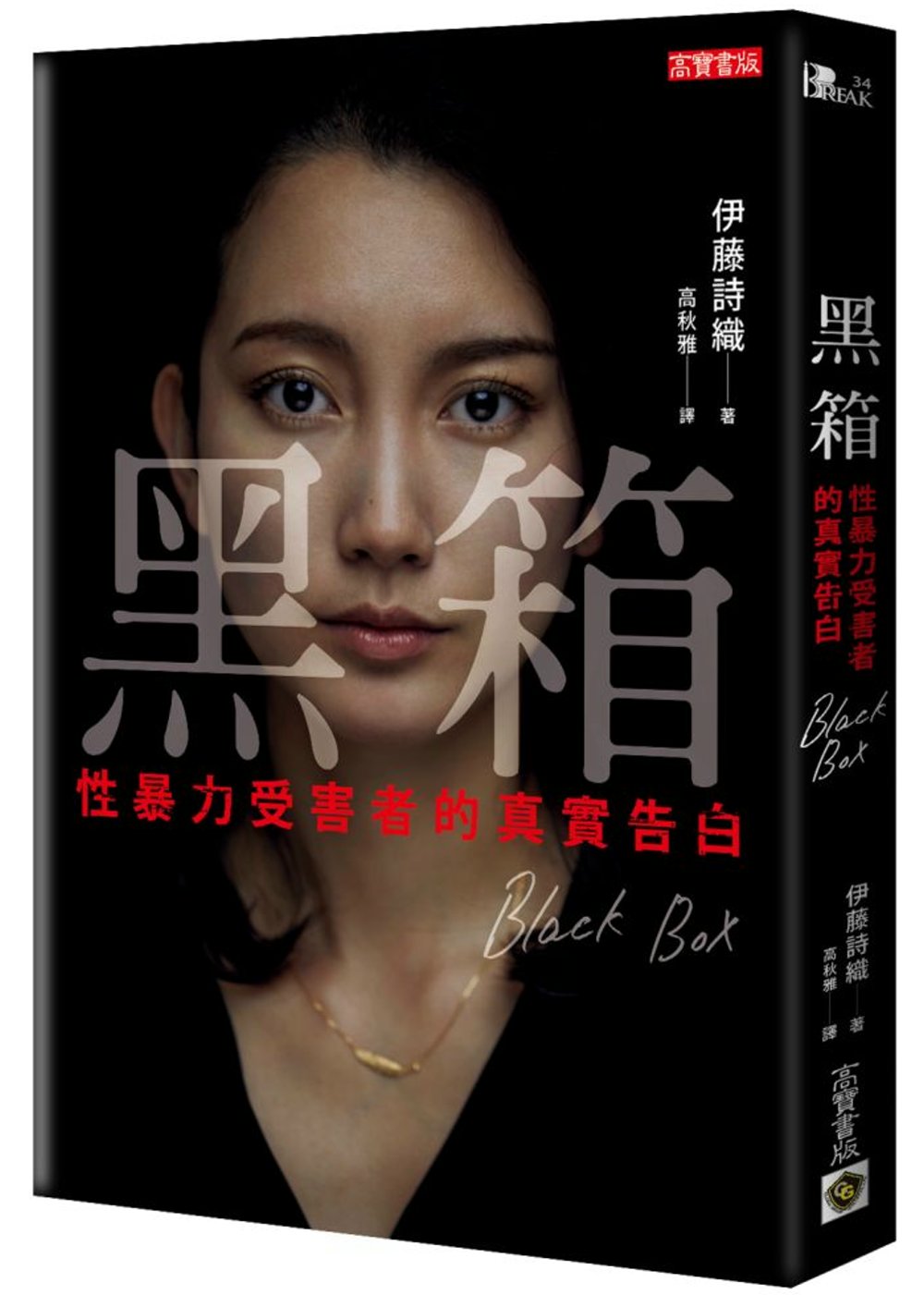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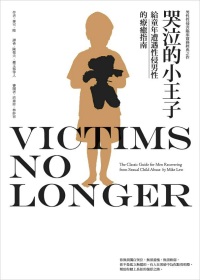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