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年秋天,一個西班牙詩人在古城格拉納達寫下:「所有的玫瑰都是白色,宛似我的憂傷。」他是賈西亞.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桂冠詩人聶魯達的摯友、畫家達利傳說中的情人。這首〈秋天之歌〉,還有另一段落:
如果死亡不過就是死亡,
那詩人會變得如何?
無法記憶的事物又會變得如何?
穿越時空,被移栽到當代韓國小說家金英夏(1968- )的《黑色花》(2003)中,成為開章導言。白玫瑰與黑色花,詩人與小說家,時代與朝代,十多年過去,在新譯版的《黑色花》裡,你更能看清記憶果然是一種技藝。金英夏在《黑色花》藏進了多重時間記憶,從李氏的「朝鮮王朝」(1392-1897)與動蕩不安的近代「大韓帝國」(1897-1910)到朝鮮日據時期(1910-1945);一路到太平洋彼端中美洲的墨西哥革命(1910-1920)。朝鮮的榮光與衰亡,不過是書架上找尋得到的故事,於是他迴身歷史中探看,決定擷取極小一瓣野史擠生出的花。1905年,英籍貨輪「伊爾福特號」滿載1033名朝鮮移民前往墨西哥,這個小說中預言般寫下世界地圖中「一個形狀很像餓癟肚子模樣的國家」。這一群朝鮮移民,滿懷對「天堂之地」的期許,卻掉入了另一個由剝削與仇恨建構的新第三世界。在龍舌蘭田、馬雅人和西班牙語的異鄉中,遺失了自己的語言、血統、文明尊嚴,甚至是味覺。
不只金英夏,從1996年的韓國電影《灰葉劍麻》、2009年宋一坤導演的紀錄片《時間之舞》,再到曾引起我眼球地震,2017年拿下「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肖像類一等獎的韓裔美籍攝影師Michael Vince Kim(作品集:《Aenikkaeng》),他們全都選擇相同一瓣歷史切片,從影像、畫面到文字,試圖還原這一段遺失在中美洲的時間。

電影《灰葉劍麻》、紀錄片《時間之舞》、攝影作品《Aenikkaeng》皆以中美洲韓國移民為題。
時間,當然也是歷史,但金英夏並不甘於只還原歷史。《黑色花》是金英夏的新歷史小說,他在小說中經常發出「作者」的聲音,刻意不帶情感地說明主要人物外的所有事件結局,甚至加以評論。南韓文學評論家徐希遠(或譯南金宇)這樣分析:「他並不想把讀者帶到過去的某一時空,相反地,他只是將過去和現在加以連結。」或許我們再大膽一點,從此處出發,在這個時空與小說的過去時空中,金英夏所強調的過去與逼顯的現在,不過是雙重的「沒有未來」。《黑色花》當然不是史詩,或許帶有一點史詩的可能性,比如主角金二正雖然具有史詩英豪一貫的「反自然性」(contra naturam),一心反抗命運。
但如果史詩的特質,一如美國評論巨擘哈洛.卜倫(Harold Bloom)曾定義的「豪壯」(heroism),史詩性也來自於人對感悟識見的執著不捨。那麼《黑色花》與金二正,不過都只是隱約靠近了史詩的可能。
我們活在沒有神話,也唱不出史詩的年代,金英夏選擇讓神性下降成人性,就像《黑色花》與後作《光之帝國》(2006),都是在特殊的背景時空中尋找個體的普遍性。「普遍」比「豪壯」更接近當代小說家的野心,但那樣的普遍,並不是普通,而是不可思議的神之技。中國作家余華便曾在散文〈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裡,精準狠厲的定義了(可能是)一流小說家們追求的普遍性:「什麼是文學天才?那就是讓讀者在閱讀自己的作品時,從獨特出發,抵達普遍。」
不需要抵達1905年的墨西哥猶加敦半島,即使是活在臺灣的當代島民,都能依靠自身歷史,共感金英夏十多年前召喚的移民故事。當小說裡寫下:「什麼時候個人選擇過國家?很抱歉,一直都是國家選擇我們的啊!」或是,「國家會永遠消失嗎?如果是的話,那又會變得如何?從革命一開始,墨西哥就已經變成沒有國家的地方。」那麼遠也那麼近,於是你便讀懂「國家」是多麼重的兩個字,在擁有國家前,我們甚至必須不斷變換姿態別名,只求它別在誕生前破滅。就像朝鮮成為韓國,漢城變作首爾,中華臺北也是臺灣;小說中的金二正,甚至原本只被隨意取名「長鐵」,還不叫金二正。
黃崇凱曾以日本的「兩個村上」(村上春樹與村上龍),做為金英夏其人其文的縱深比對。但金英夏是站得更出來的下一代寫作者,年少時的張揚不再,這幾年他在實境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裡以「金作家」身分出任常駐嘉賓,經常說出洞悉世情卻無比溫柔的可愛發言。在佛羅倫斯看日出,他說:「其實看百次、千次日出,都不會對我的生活造成影響。可就算和日常無關,當我們看到美好的事情而感動時,就能明白身為人類的意義。」談到學生問起他,寫小說最重要的是什麼?他也能堅定回答:「存檔。」
他更感嘆年輕作家開始寫起自己也不知曉其名的花與人事,但作家應該是告知讀者事物名字的人。《黑色花》便是金英夏盡力靠近萬事萬物真名的作品,他以小說的情節、語言帶領讀者認識宗教、風俗、文化與地理自然。小說最好的一段落在前頭,那千人窩擠渡海的惡臭船艙,有經血、巫偃與疾病,儼然成了「神話中怪物内臟的船艙」,讀時竟有翻看人類學經典《金枝》的錯覺,大道在屎溺。下船出艙後的人生,是脫離子宮的一次新生。縱然小說的後段與前段,存有神力與人力的落差,但他方之國就是來生,那些遠得像夢的就當作一次通靈觀見的前世。「朝鮮人把天空和土地之間稱爲江山,自然無法想像沒有江、沒有山的世界,然而在猶加敦半島,這兩樣東西都付之闕如。」從此,他們只能活在江山的盡頭,成了陷落的一段。
小說的最後,女主角李妍秀並未再見到愛人金二正,而是嫁給了另一個成為當地理髮師的朝鮮移民。千萬傷痕,都留在了過去,連「現在」也即將過去。那處只存於想像的理髮廳,卻與2019年的韓綜《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魔幻重疊,韓國節目將理髮師與明星們全送往西班牙半島,開起真人實境理髮廳。韓語與西班牙語交會、錯身,妝髮精緻對著鏡頭的明星們,是否有人知曉龍舌蘭田野裡漸漸與馬雅人混血的同胞?
不管知與不知,這就是文明的今生、當代人的今生,與一個國家的今生。
作者簡介
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 2017年出版《寫你》, 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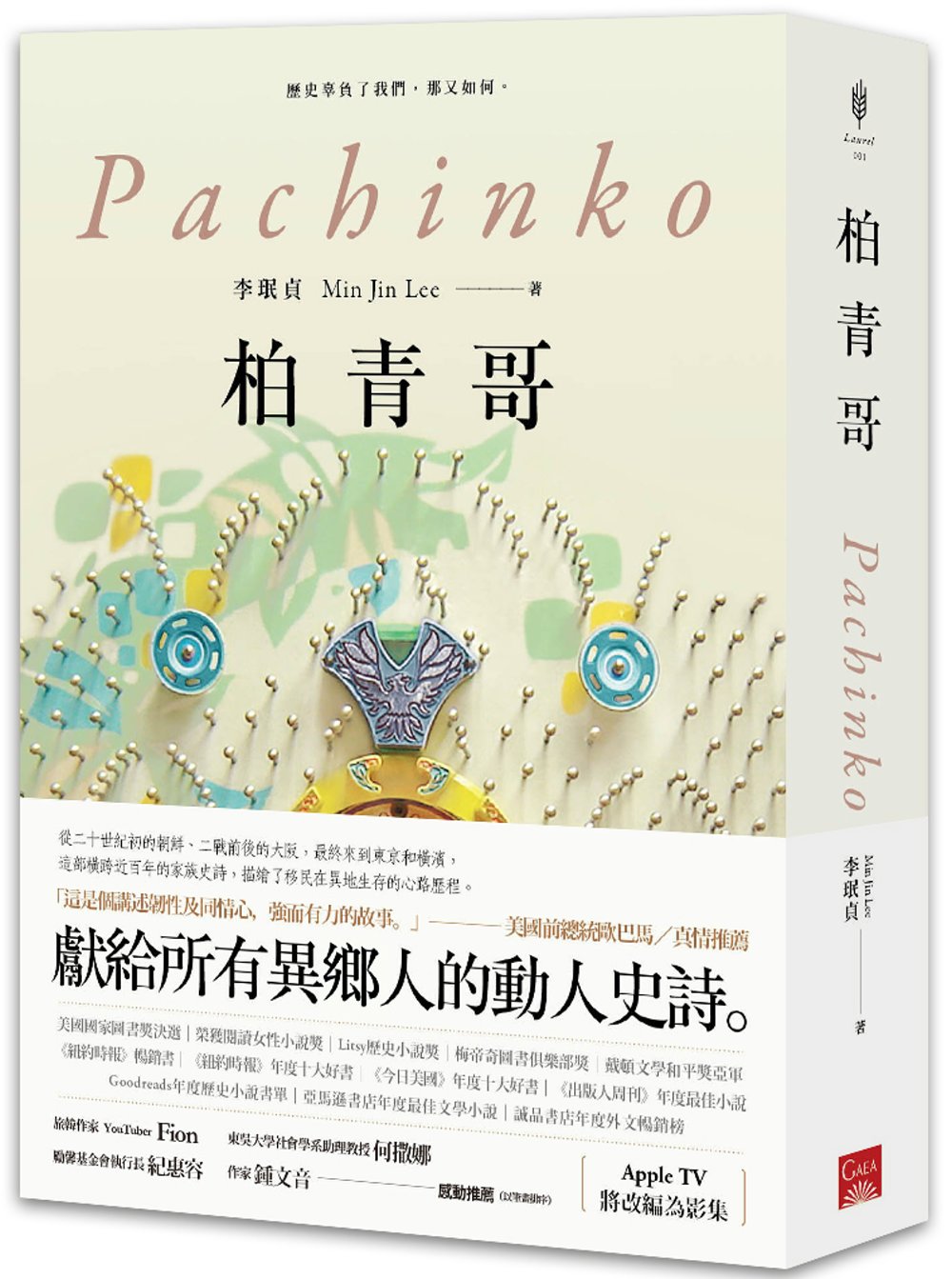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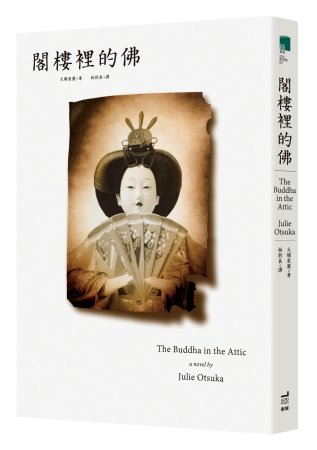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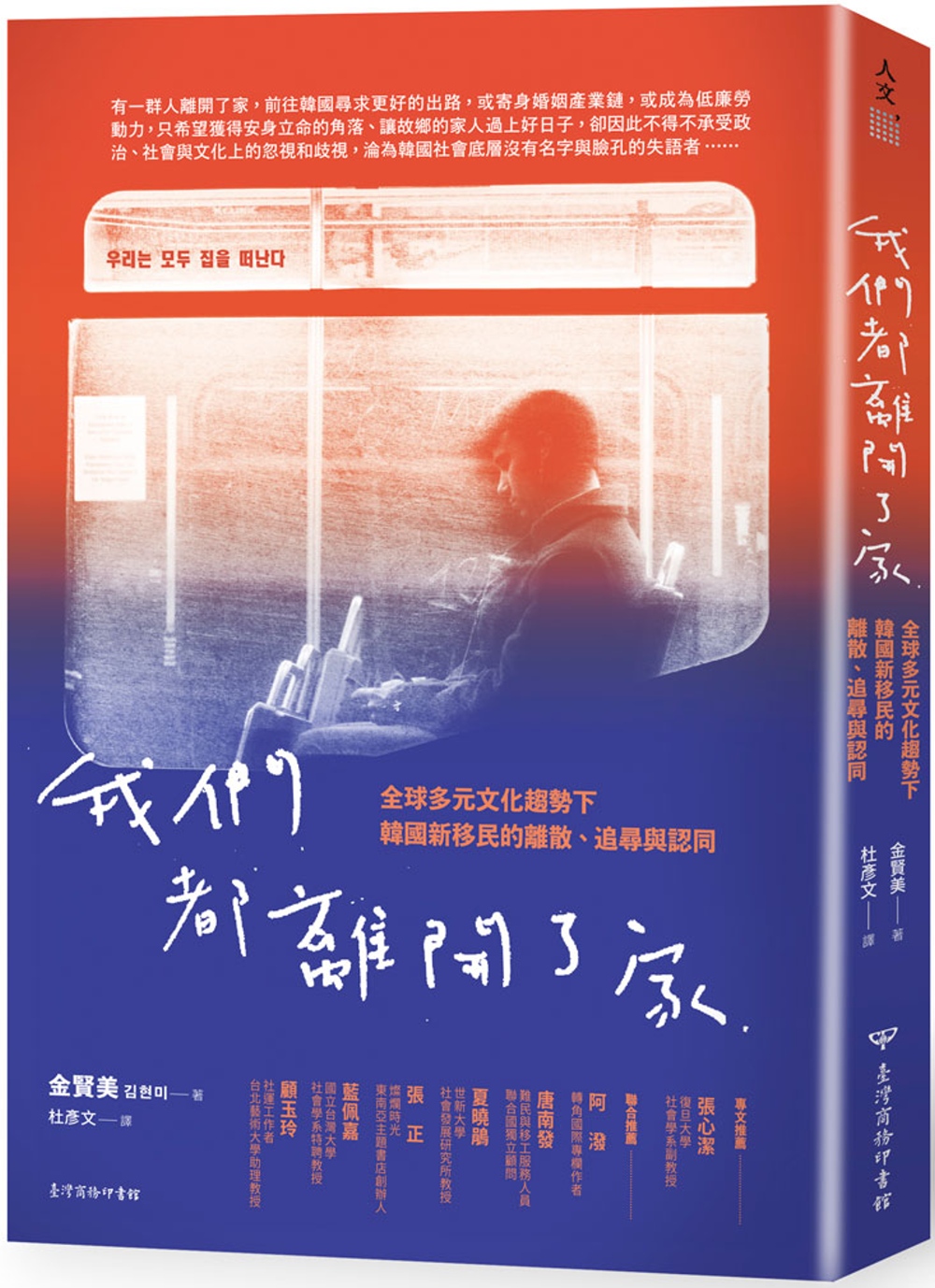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