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遺忘的孩子》作者瑞安儂.納文(Rhiannon Navin,照片取自作者官網)
《被遺忘的孩子》作者瑞安儂.納文(Rhiannon Navin,照片取自作者官網)
近20年來美國槍擊案層出不窮,從 1999 年發生的科倫拜校園槍擊案(13死)、2007 年維吉尼亞科技大學槍擊案(32死)、2012 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27死)、2016 年奧蘭多夜店槍擊案(49死)、2017 年拉斯維加斯演唱會槍擊案(58死),到今年 2018 年二月又在佛羅里達的道格拉斯中學發生造成17死的重大槍擊案。
這些死傷慘重的槍擊案,屢屢在美國引發修改憲法第二修正案──不得侵犯人民擁槍自由權──的聲浪,但在過往曾被殖民的歷史之下,及自詡為一個崇尚民主自由國家的驕傲下,多數美國人相當保衛擁槍自由權。然而,近幾年校園槍擊案比例急速攀升,前段所列的重大槍擊案中,6件就有4件發生在校園;根據《華盛頓日報》報導,自從科倫拜校園槍擊案事件以來,至少有2萬6千名未滿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死於槍殺,占了大規模槍擊案死者人數的10%。沒有投票權的孩子們,是否該成為滿口自由、人權的擁槍人士與政客的犧牲品?這些孩子和他們終日憂心的父母有沒有在政治、選舉之外的選項可以推動對於擁槍權的討論?
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作家瑞安儂.納文(Rhiannon Navin)被她孩子在校學習的「防槍擊演練」所撼動,她以身為人母的細膩與憂慮,寫出這一本貼近現實的小說《被遺忘的孩子》(Only Child),以母親凝視孩子上學背影的牽掛,鋪陳出擁槍自由背後的孩子們與父母的幽微心事,為槍枝問題的討論補上一個文學的角度。
《被遺忘的孩子》描寫一個家庭在一次小學校園槍擊案中痛失長子之後,在同一個學校同樣經歷槍擊案卻幸運活下來、年僅6歲的次子,如何面對失去哥哥的事實,以及父母鎮日以淚洗面、難以走出傷痛的破碎家庭氛圍。作者成功重建了一個6歲學童的聲音及世界,讓小兒子札克成為故事中所有悲傷與希望的中心。英文書名 Only Child 聰明地點出納文隱藏在故事中的叩問:失去哥哥之後,6歲的札克成為家裡唯一的孩子。而更重要的,這些槍擊案的受害者都「只是孩子」(only child),只是孩子的他們成了槍枝問題最無辜的受害者,這樣公平嗎?支持擁槍自由的大人們於心何忍?他們嘎然截斷的人生,該向誰討回公道?
這些問題是《被遺忘的孩子》想問的,但是作者納文卻不準備回答,因為她從不想藉由這本小說介入政治或辯論,她想做的,是某種柔性的提醒;納文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小說中寫到為母內心深處的那些字句。當身為成人的我們對於某些社會問題找不到答案,看看孩子們熟睡時滿足的臉龐,想想孩子們凝視你時信任的雙眼,任何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都有絕對的責任,保護那份滿足與信任。因為他們,只是孩子。
以下是筆者與作者瑞安儂.納文所進行的訪談。
採訪=胡培菱
Q:《被遺忘的孩子》讓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分是,你對年僅6歲的小兒子札克有非常真實而可信的描繪。可否談談你如何抓到描寫札克的竅門?身為三個男孩的媽,寫作過程是否也寫進了你的孩子們所說的話?有用過書中的情境來測試孩子們會如何反應嗎?
瑞安儂:我在寫《被遺忘的孩子》的時候,的確是用關注我三個孩子的行為言語來揣測札克會如何行動或說話。我的兩個雙胞胎在我寫這本書時,年紀跟書中的札克相仿,所以我經常注意並觀察他們的言行來找一些線索:他們現在在想什麼?他們如何處理並表達自己的情緒?我把孩子們說的話寫進書裡很多次。甚至最後在編輯的過程中,我也轉向他們尋求協助。當我的編輯問:「小孩子真的會這樣說話嗎?」我就跑去用德文問他們:「這你們用英文怎麼說?」有時候我猜的一點都沒錯,但是有時候我會根據他們的回答做些改寫。
*筆者按:作者瑞安儂.納文來自德國,在美國結婚生子定居,以英文著作。
Q:當札克躲在哥哥房裡的秘密基地時,為什麼會設定讓他讀《神奇樹屋》?
瑞安儂:《神奇樹屋》套書是我的孩子們最喜歡的書之一。我們整套書從頭到尾讀過兩次,第一次是我大兒子開始學閱讀的時候,後來是兩個雙胞胎也到了閱讀年紀的時候。瑪麗.波.奧斯本創造出一套真的很具有魔法的童書。她的書在我們家引發很多很棒的討論,我的孩子們也從中學習到很多。我一開始寫《被遺忘的孩子》其實沒想到要寫到《神奇樹屋》,那是後來才很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札克開始躲到哥哥的秘密基地,想找方法處理自己的情緒時,我認為閱讀是對他來說最自然的情緒出路,因為書本有時候真的可以讓我們逃避現實。看書時你潛入另一個世界,品嘗他人的生活,然後等你再出來的時候,你很有可能已經學到了一些你之前不知道或從沒考慮過的人生智慧。透過閱讀《神奇樹屋》,札克除了得以暫時逃避他當前很情緒化又很混亂的日常生活,他也從中發現很有價值的學習內容,讓他想把書中所提到的智慧運用到他自己的情況當中。
Q:札克提到我們必須對兇手的家庭深感同情,因為他們也同樣遭遇了失去親人的經歷。讀到這裡,我腦中想到蘇.克雷伯德(Sue Klebold)那本令人心碎的《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告白》一書。當你決定要人性化而非兇魔化故事裡槍擊者的家庭時,有想到這本書嗎?可否分享為什麼你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而這對受害者的家庭來說,又有可能做到多少?
瑞安儂:我知道蘇.克雷伯德的故事,但我還沒有讀過她寫的那本書。我認為寫出一個不要讓善惡對立的故事是很重要的。我想呈現的是,當我們面對這麼悲劇性的狀況,事情從來不是簡單的黑白分明。每當我聽到像大規模槍擊案這種令人難過的事件,我心中第一個想到的永遠都是受害者及他們的家人,他們只是過著每天的生活,但他們的世界卻在一個料想不到、恐怖的瞬間徹底改變了。雖然我的心因為他們的遭遇而心碎,我還是會想到槍擊者的家庭,特別是如果那個槍手是年輕人,像我故事裡的一樣。所以我試圖站在他父母的立場,然後發現我非常同情他們。當受害者的家庭要處理難以言喻的失去;加害者的家庭則必須在失去一個孩子的創傷之外,同時面對他們孩子的行為所帶來的罪惡感與羞愧。社區可以同心協力幫受害者的家庭打氣、支持他們,但是槍手的家庭卻被社區所驅逐,獨自面對他們的悲痛。身為一個母親,我所能想像比我孩子在學校被槍殺更慘的事,就是我孩子去槍殺別人。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告白》作者蘇.克萊伯德在TED的演講。
Q:你在「公共廣播頻道」(NPR)的訪談提到,希望讀者讀完《被遺忘的孩子》後可以感到「希望」。可否談談你心中的這個「希望」是什麼?
瑞安儂:我寫《被遺忘的孩子》是因為我自己的恐懼與憂心,但我同時也是帶著很大的希望在寫這本書。我們必須記得,故事的最後,是年幼的札克用他的真誠、樂觀與執著,帶領著他的家人與他們的社區走向一條同情與原諒的出路,並帶給大家一個可以一起療傷的機會。我們經常認為是我們大人在教導孩子們世界運行的方式,但其實很多時候,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停下來讓孩子來帶領我們會更好。甚至,有些讀者讀了《被遺忘的孩子》之後,被啟發付諸行動來解決持槍問題,以確保他們的孩子、或他們鄰居的孩子、或另一個鎮上的孩子不需要變成另一個札克。
在我的故事裡面,札克找到了一個讓自己與家人向前走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透過愛、憐憫與同情。
Q:在這本談論槍枝暴力與慘劇的小說中,你隻字未提「槍枝管制」,這是一個思考過的決定嗎?
2018年4月時代雜誌封面:「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發起學生,他們是道格拉斯中學槍擊案倖存者。此活動後來並演變成「#Enough! National School Walkout」罷課行動,全美三千校學生、老師和家長一起抗議美國政府對槍枝管制的無做為。
瑞安儂:是的。我希望札克所經歷的一切就可以給我們答案。在美國我們幾乎已經習慣電視新聞經常報導的又一件槍擊案,我們學會了同樣的情緒再循環一回:重創、憤怒、傷慟、無助——然後很快就又回復到日常生活中。
我們經常忘記,這個創傷是多麼持續不斷地、恆長地影響那些被恐怖事件直接影響到的人,還有那些被留下來的人——被害者的社區、家庭及手足。如果我讓讀者從一個孩子的眼中去看那些惡夢及後果,或許可以給他們一些思考的契機。槍枝管制在美國是一個正反意見相當分歧的議題,所以如果我自己站在這裡高喊我個人對於槍枝管制的看法的話,我就已經自動排除了這國家一半的人口。我最想要與之對話的那群人反而會立刻封起耳朵。
Q:身為一個外國人/移民者,妳如何看待美國校園中的槍枝暴力問題?這有沒有改變妳對美國的看法?
瑞安儂:我在德國長大,在德國,槍枝問題整體上——不只是在校園中——從來都不是問題。我搬到美國之後,才發現在這裡槍枝暴力居然這麼氾濫,並且對於槍枝管制的意見居然這麼分歧,這當然讓我非常驚訝,或應該說非常震驚。我還是一直沒辦法了解為什麼這個社會會這樣?在這個國家裡每天有平均 96 個美國人死於槍下,而其中有 7 個是兒童或青少年,如果我們清楚明白這些數字,我們怎麼還能不採取最基本、最根本的安全管制?
Q: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妳如何處理對孩子在公共場所(如學校)中安全問題的焦慮及擔憂(除了把這些焦慮寫成一本超棒的小說之外)?
瑞安儂:老實說,我處理得並不是很好。寫《被遺忘的孩子》這本小說幫助我抒發了情緒,但是很多時候寫這本小說也讓我的情緒起伏相當大。我還是經常夜裡睡不著覺擔憂著孩子們的安全。每次我走進他們的學校,我的心裡就會開始浮現各種「萬一」。萬一有槍手從學校大門進去怎麼辦?為什麼後門開著?萬一有人從那裡闖進去怎麼辦?
五年前那個造成二十個兒童跟六個成人死亡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發生的那天,我一如往常地送我大兒子去上學。他那時是一年級生——跟很多在此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中喪命的幼童一樣年紀——直到那可怕的一天前,我都一直相信他的學校是個安全的地方。但我再也不這樣認為了。每天把我的孩子送去一個我不認為安全的地方,這對一個母親來說是一件很艱難的事 。
Q : 妳希望妳的青少年讀者們可以從這本小說中獲得什麼?
瑞安儂:美國的青少年跟甚至更小的學童都很清楚他們每天所面臨的槍枝暴力問題,他們已經很習慣那些學校規定的「上鎖緊閉演習」,試想在這麼小的年紀就與極端的恐懼共存,這些孩子們問的問題,不是槍擊事件會不會發生在他們學校,而是什麼時候會發生在他們學校。有很多青少年讀者告訴我他們很感謝我寫出這樣的故事。有個女孩告訴我,佛羅里達校園槍擊案發生後,她需要一個空間來安置她內心的悲痛,而我的小說給了她這個空間。我認為這些孩子們可以很輕易與札克產生某種連結,因為他的恐懼與想法跟他們的很像,所以我希望札克最終走出悲傷、走向痊癒的過程,也可以給這些孩子們某種答案。
(本文由親子天下提供)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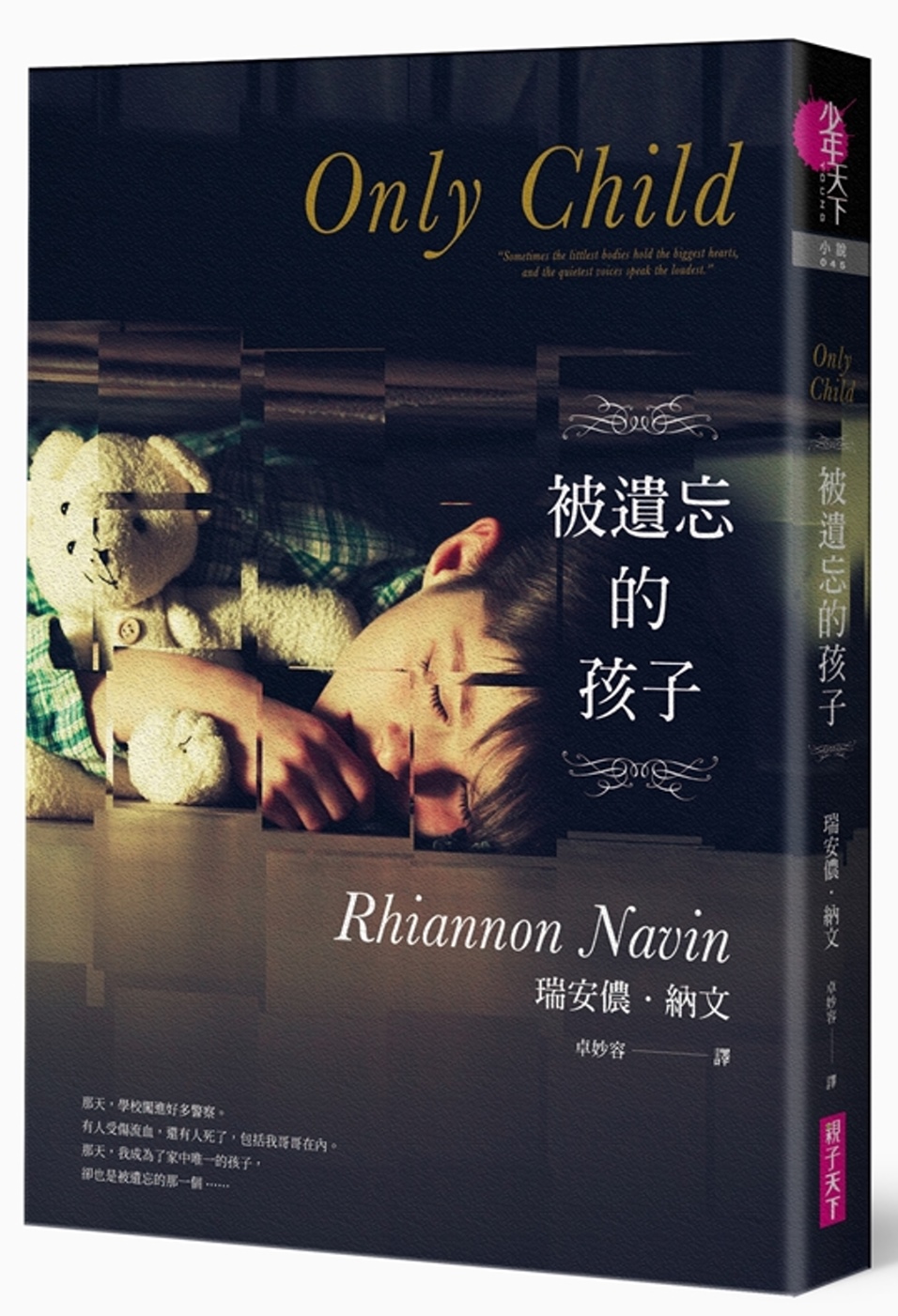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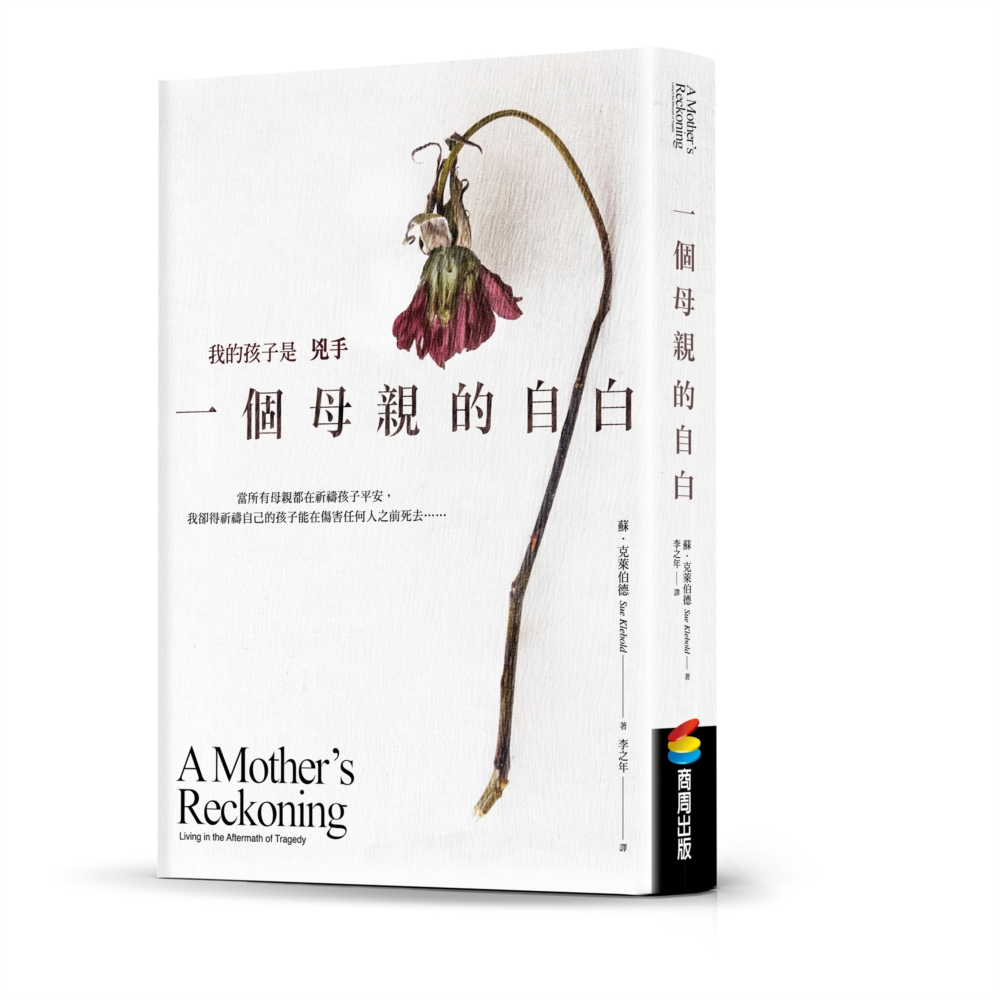
 2018年4月時代雜誌封面:「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發起學生,他們是道格拉斯中學槍擊案倖存者。此活動後來並演變成「
2018年4月時代雜誌封面:「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發起學生,他們是道格拉斯中學槍擊案倖存者。此活動後來並演變成「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