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那國家這麼大,每一段時期,卻只有一張女孩的臉是最幸運的,許多女孩繞過千山萬水去找「她」,這過程中,不惜遺失了自己,只為了更接近了「她」。
那國家這麼大,每一段時期,卻只有一張女孩的臉是最幸運的,許多女孩繞過千山萬水去找「她」,這過程中,不惜遺失了自己,只為了更接近了「她」。
沒人告訴你,回憶像隻禿鷹嗎?拉扯著妳腦海中最濃郁的香甜,在妳以為妳安居在這宿的安穩裡,發覺是充滿水漬味的浮沉。
我不知從何時無法清醒於現實裡,僅有的我被壓縮在夢境裡,從扭曲的縫看著鑰匙孔裡的現實,那裡日曬強烈,失了細節。
在夢境的管轄裡,我是個符合「成功」期待的樣板女人,有著加州陽光的笑容,好像從沒被任何陰影給干擾過,就像個被播放中的投影,雖偶有雜訊,與參差不齊的影像,但不會讓後面的破瓦磚牆出現。有些女人,她的投影可以是整片天空,像個巨大的斗篷落下,包著一個瑟縮的小女孩,說著不知在跟誰求的祈禱,千萬別走漏什麼塌陷的一角。
我夢裡那個叫貝蒂的有個可靠的親戚,以為有人保護著,甚至把那叫「好萊塢」如隔絕城鎮的地方,都從它長久的濕漉漉陰暗處給撈出來,回憶變成一張輕薄又乾掉的紙,上面寫著所有關於那個叫「貝蒂」的女孩的事。她的簡介像是要去超市前的「代辦事項」,幸運地可以只用寥寥數字來寫成幾行,後面的空白可以伴隨著待買的沙拉醬與速食餐後,想起來後再補上。是如此輕巧的人生,像個發泡錠,讓人喝水服下。
 夢裡的我有著加州陽光的笑容,好像從沒被任何陰影給干擾過
夢裡的我有著加州陽光的笑容,好像從沒被任何陰影給干擾過
夢是個什麼?是寄居蟹用來遮掩的殼,也是蝸牛殼上的紋路,一圈一圈的,裡面那些擠壓的殘屑,總忍不住摳擠出來,又卡進妳的指縫裡,就是這麼礙事啊,妳吸著手指,不安地在大太陽下,知道「陽光」一灑下妳又該上場。這裡的太陽是個燈,人們輕薄短小似地擠在光暈裡,個個美得沒有商量餘地,當一個好萊塢的女人,傾銷的美會把妳吃得骨頭不剩,因為妳將榮耀了好萊塢,無論是穿著鍛面的性感致命、被風不斷吹起的裙襬、在樹下勵志的南方閨女、還是拿著盔甲的女戰士,一次又一次的重製,我們總既纖細又堅強、我們仍憤怒到惹人憐愛,那裡的女孩活在男性的夢裡,又活在自己的夢裡,但卻不是同一件事。
這是一個下面極重,如砂石重量的女孩願望作基底,而上面懸了一線陽光當魚線的世界,我進入裡面,一層層鏡子就會把我變成一層層我,我在很多試鏡裡飾演很多種女孩,但沒有一個是深入女人內心世界的角色,那每個就像將醒未醒的夢,一再地在「未完待續」中醒來。我人在哪裡?夢的疲憊像海底的鯨被捕上岸、擱淺著,拍打無力,愈拍打掙扎,細沙愈揉進妳的身體,黏又扎身,這現實被夢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在穆荷蘭大道上,來回進入麗塔與貝蒂的世界,她們的形貌都能那麼清楚地被打撈出來,所有前往的都是未知,只剩下感受可以記取,試鏡中與男星舌吻時,對方的手在臀部的不安分,周遭的女人微笑旁觀著,人們恭維著。我片片段段坐實著我的空虛,那些令我不舒服的,貝蒂都認為是夢想的實現,那細細碎碎刮出我內心痛楚的,她眼中盡有刺眼的陽光可以取代。
 男星的手在臀部的不安分,周遭的女人微笑旁觀著,人們恭維著。
男星的手在臀部的不安分,周遭的女人微笑旁觀著,人們恭維著。
我多麼希望像她一樣,切割對自己身體的意識感,成為這萬花筒的一部分,只要一起轉一直笑,讓騰空一樣的浮水印,她是我的眼淚,笑是她唯一的表情,代表我羨慕的、我鄙視的、我想變成的,都碎碎的如小貝蒂,在一個小桶子裡快轉的亮片。
夢裡的水漬逐漸蔭出來,如我的屍體一樣,麗塔的鮮活身體隔著淋浴間出現,記得那是盛夏的水氣,包圍著再開始,讓人躁動莫名。我這乾枯的存在,所有過期情感都滲進回憶裡,滴答無人收拾的敗絮,人精神枯萎時,肉體的臭氣自己最聞得到,我僅剩的青春尾隨著麗塔的身影,再過一次青春,找尋自己是誰?
結果這裡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我可以是任何女孩,在公路餐廳打工的服務生貝蒂、可以是我慾望的託身麗塔、也可以是某一晚去的夜總會,那個唱得哭花妝的女歌手,至此,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是穆荷蘭大道上的許多女孩,前往好萊塢的各種女生。
或許我原是個公路餐廳的女服務生黛安,到好萊塢後並沒有碰到熱情老夫婦的接待,甚至你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我想逃離的家,我沒有什麼家庭背景,與一個名為卡蜜拉的女子相戀,她後來搭上名導演,旋即背叛了我。我身陷好萊塢性剝削,與習慣這樣生態的環境中,我試鏡被吃豆腐時,有人嘲笑這戲反正也不會開拍,這樣子已好多年,但或許這也不是我,畢竟這樣的人生故事沒有什麼好提。
 我這乾枯的存在,所有過期情感都滲進回憶裡,滴答無人收拾的敗絮
我這乾枯的存在,所有過期情感都滲進回憶裡,滴答無人收拾的敗絮
你不懂,在穆荷蘭大道上,重點已不是我是誰,而是我能成為「誰」。
這樣的我,有一千一萬個我,我們內化了好萊塢的五光十色,我們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自己,我們像量產的「特別」。無論是黛安、貝蒂、卡蜜拉與麗塔,或是其他的女星,我們都沒有真實的面貌,我們也不知道彼此的真假,我們對那些導演與製片來講都是抽象的,因其抽象,我們既被膜拜又被踐踏。沒有與好萊塢相關家世背景的我們,都可以變成同一張臉,誰變成誰都是成立的,只是我黛安是在這臉譜的最外圍,跟拿字卡的一樣,如果不跟著群體變換動作,妳就不接近那個最吃香的「女生」了。
說穿了,好萊塢時興的只有一個「女生」,每隔一段時期認養一個不同類型的「女兒」,這條穆荷蘭大道,是讓後面跟隨的女生都變成那個「女生」。不知道是誰,也不是在演戲,而是那市場價值擺在那裡,我們變成了那個「女生」,不管妳曾成名與否,過期了就是不存在了,除了有限數量的影展、男導指定與人權電影做公關形象,讓它容許了梅莉史翠普、茱莉安摩爾等例外,好萊塢只有一個女孩限定,其他的女孩們,妳成為「她」外,什麼也不是。
電影中誰跟那個誰,還有另外一個誰,都沒有醒來的一天,這條穆荷蘭大道走不完,這是一個很古老的恐怖寓言,有很多女孩的實體消失在他人的抽象裡,自我認知錯亂,大於它是個兇殺案。
《穆荷蘭大道》(Mulholland Drive)是由大衛‧林區(David Lynch)執導的電影,電影在2001年坎城影展首映,大獲好評,當時他與拍攝《隱形特務》的喬伊‧柯安(Joel Coen)共同獲頒影展的最佳導演獎。此片被紐約影評人協會評為年度最佳影片,林區憑影片第二次被提名奧斯卡獎最佳導演。之後隨著大量在網上流傳的關於其真實涵義的詮釋,《穆荷蘭大道》近年來已晉身殿堂級影片,此片並被BBC評選21世紀最佳電影第1名,近期又在台灣上映。林區從未對其涵義作任何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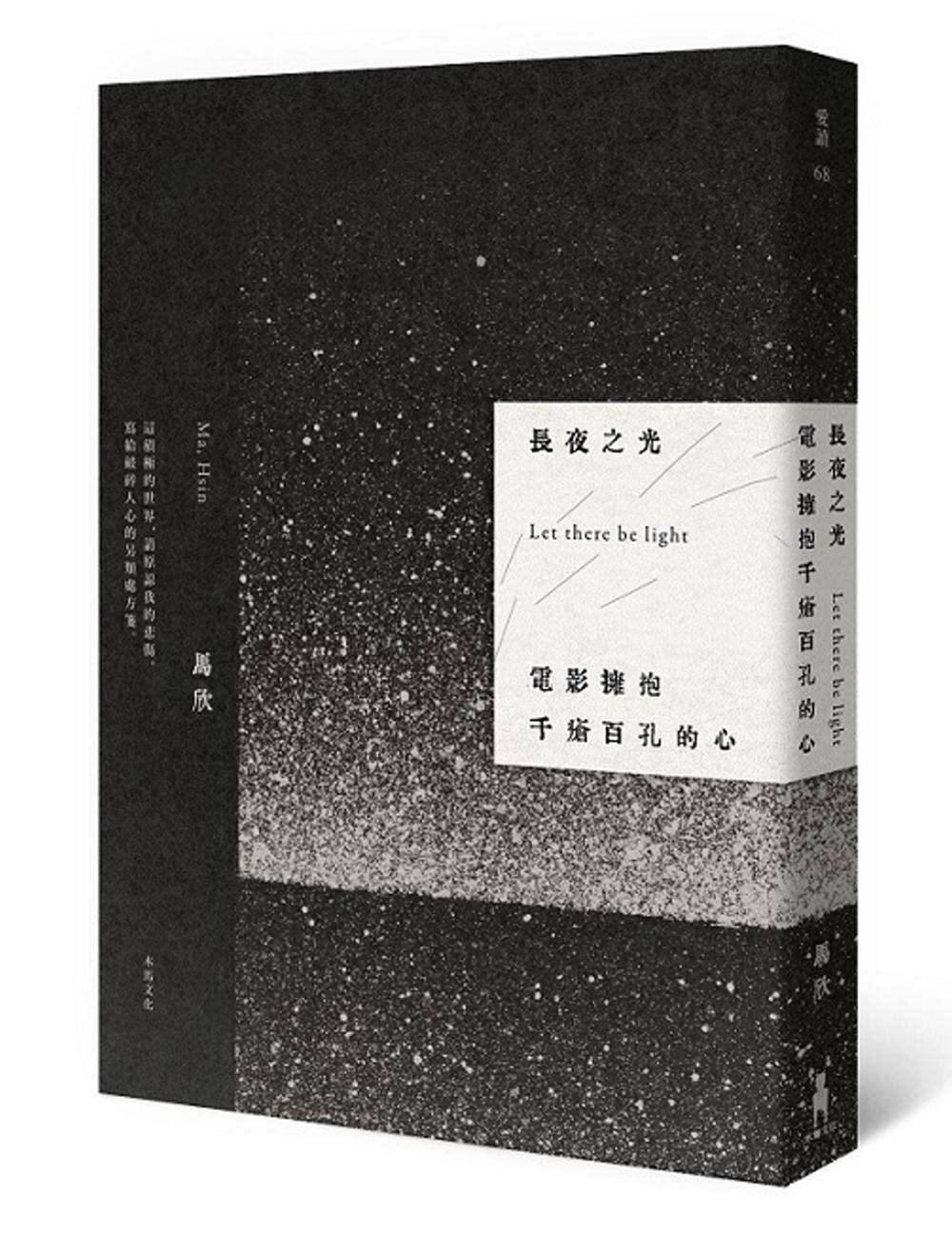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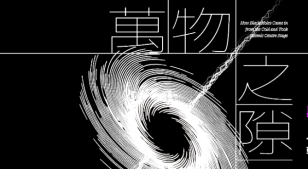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