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一門專門討論「翻譯」的課程,除了邀請夢幻講師村上春樹和學生分享海明威、沙林傑等經典文學翻譯心法,首創逐字逐句演練的互動式教學,成為東大長年的熱門課程,更被譽為「令人興奮的翻譯教室」。
如今,這堂經典翻譯課程實錄首度中文化,將帶領台灣讀者認識何謂最高等級的翻譯,日前更特別邀請柴田元幸先生,於東京接受《翻譯教室》中文版譯者詹慕如採訪,讓我們親炙專業翻譯家是如何同匠人般,於文字大海細細打磨思量,專心致志,只為重現文學作品意境。
訪問者 詹慕如,《翻譯教室》譯者(以下簡稱「詹」)
受訪者 柴田元幸,《翻譯教室》作者(以下簡稱「柴田」)
〔續上篇〕
詹:您在許多著作和訪談中都提到,您非常重視語言的正確性、譯者的語言能力,但是村上先生受訪時被問到自己最缺乏什麼時,他的回答是「語言能力」,村上先生對自己的語言能力好像比較沒有信心。
柴田:村上是憑直覺在學文法,所以難免會有些破綻,但憑直覺能有這樣的正確度也是很了不起。
詹:那麼,您相當注重的語言正確性,跟您在學校任教有關嗎?
柴田:日本的英文教育漸漸從重視讀寫,轉移到重視聽說的方向,有時想想,以前注重讀寫的方向其實也不壞,特別是我自己從事翻譯這一行,更能體會到老式教育帶來的好處。不過會懷念老式教育的,可能只有翻譯這一行的人吧。
詹:現在大家討論翻譯,總會強調外文能力的重要,其實母語能力也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畢竟最後這些都需要化為母語文字來傳達。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一些譯文,很明顯徹底了解原文,但譯文表現上卻還差一口氣。而我們往往很容易把重點擺在如何增進外文能力,老師您身為翻譯家,如何提醒自己精進母語能力?
柴田:很棒的問題。現在大家確實漸漸有「譯者的母語能力很重要」的認知,不過我覺得這樣的認知也存在一些誤解,很多人似乎以為只要語彙豐富、能運用華麗的詞藻,就等同於「母語能力優異」,但我認為這其實沒那麼重要。比方說,我自己鑽研的當代美國文學,受到海明威很大的影響,他的表現手法很簡單,翻譯他的文章如果運用太多華麗詞藻,十之八九會偏移原文的意義,這時候重要的是怎麼運用簡單的字詞表現出真正的意義。
我認為翻譯需要具備的母語能力,是能夠不厭其煩地印證自己寫出來的譯文,是否與原文要傳達的意義相同,那是謹慎講究的功夫。與其說「能力」,在我腦海中那更像一種拿磨砂紙細細打磨的苦功。
----
詹:一般講到一個字或詞是否正確,大家或許直覺以為這是種「一對一」的對應,不過在翻譯的世界裡要追求真正的正確,並沒有那麼容易,要抓出在兩種語言中各自正確的意義,真的是一種很費心的過程。與其追求詞藻上的美,如果能找到這種真正的正確對應,似乎自然而然就能導向漂亮的翻譯。
柴田:一點也沒錯,反過來說,甚至有時候為了呈現出閱讀原文時感受到的趣味,還會進行一些「編輯」。譯者經過推敲,覺得進行某些調整、修正,更能表現出原文的意義。這樣的翻譯,或許從字面上看並不與原文一字一句吻合,若談到傳達的效果,這種譯法絕對比較有效。譯成日文時我最重視的是原文的意境、趣味,在譯文中是否能同等表達,真正該傳達的是這部分才對。
詹:這讓我想到《翻譯教室》當中,哈佛大學日本文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解釋他為何將村上先生的短篇〈青蛙老弟救東京〉篇名英譯為「Super-Frog」,我覺得相當有趣,也很有收穫。他譯的不是字,而是青蛙老弟帶給讀者的新奇和趣味感。
柴田:青蛙老弟救東京、Super-Frog Saves Tokyo,兩句讀起來有類似的韻律感,如果只譯為Frog Saves Tokyo就少了那種韻律感。
詹:我們日譯中的另一個難關,就是和製英文、片假名。日文是新語彙出現得很快的語言,老師對這種新字會有抗拒感嗎?一開始這類新字或許會被認為不正統,有人對於使用這些字帶有抗拒。以台灣來說,很多日文辭彙已逐漸融入日常語言,例如「達人」、「職人」、「人氣」等等,起初這些字詞沒有被翻譯成適當的中文,直接沿用日式漢字進入我們的文化中,現在有些字詞似也約定俗成地被接受。語言是活的,本來就會與時俱進慢慢變化,不過我的用字習慣比較老派,還是會避免這些字,盡量選用中文中原有的方法來表達。
柴田:我自己的原則是,盡量不要用片假名。翻譯是為了不懂英文的讀者所翻,把外來語用片假名來解決,對我來說是譯者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不過有時候也要看語境,確實有些文章的脈絡上,適合用新潮一點的外來語來表現味道,這時候我就會斟酌使用。不過,基本上我認識的新詞也不太多(笑),除了新名詞,有些年輕人的流行語,我也盡量不用,其實應該說就算想用也沒辦法,而我也不會有想用的念頭。因為這些流行語有時候會長久流傳,也可能只是一時流行,萬一退了流行,這些用法後來回頭看反而會覺得落伍。所以年輕人看我的文章或許會覺得我用的日文很老氣,那也沒辦法。
每個人能運用的字彙有限,每次翻譯時如果想不到適當的字詞,我就會找類語辭典,發現一些以前沒用過的字,試著用用看,不過隔天再看稿,經常會覺得只有那個地方跟其他文章格格不入,這就表示自己還沒能自然地運用那個字,還沒能充分消化。所以新字也一樣,對我來說是種不太容易消化的東西。
詹:在日文中另一個特色是主詞的運用。日文常省略主詞,也會在代名詞上運用許多不同的稱呼,例如以「俺、僕、私」來賦予特性,我想這是日文相當特殊的部分。在此,中文可能比較接近英文,種類也不若日文這麼豐富。反過來說,老師您要將英文譯入日文時就,必須要從許多選擇當中去挑選。
柴田:沒錯,其實這部分的工作是很愉快的,比方說英文的 I,在我眼中就不只是一個「單字」,而像是可以牽引出許多可能性的「素材」,在這一個英文的單字裡,其實藏著很多可能的日文。
詹:所以算是在譯者權限中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柴田:對啊。不過從外界看來或許覺得這是一種主觀選擇,但我自己在挑選時,往往會有一種「要用這個字」的直覺,我並不覺得是依照自己喜好擅自決定。
詹:同樣的作品,由不同譯者來翻會有不同的味道,所其中當然還是有容許譯者揮灑的空間,您覺得能容許譯者有多少這樣的自由空間,表現出多少譯者的色彩?
柴田:譯者在翻譯時,不能想著表現出自己的色彩。以我自己來說,因為我看到原文時有了這樣的感受和認知,將自己客觀感受到的東西盡量重現。我不會去衡量自己的主觀跟外界的客觀之間的差距,畢竟我無從得知外界的客觀到底是什麼。
詹:所以譯者色彩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必會呈現的東西,但是您不會、也認為不能刻意表現?
柴田:對,我不會。會這麼譯是因為我讀了有這種感受、我聽到這樣的訊息,所以直覺認為這樣是正確的。
----
詹:您在翻譯時有覺得特別困難或簡單的作品嗎?
柴田:單純從語言難度來看,確實有。像是口語式俚語較多的東西確實比較難;比較充滿理性、調理清晰的文章比較簡單。不過文章好不好譯,跟翻譯過程有不有趣,不見得有直接相關。
詹:您目前的翻譯工作多半可以直接接觸編輯、接洽想翻譯的作品,那麼,一般日本譯者多半如何接觸到工作?
柴田:假如是大學教授、學者,多半像是打工性質,偶爾會有出版社自己上門詢問。久了之後也建立起跟出版社之間的關係,開始可以定期接稿,這應該是最常見的模式。當然也有更熱心的譯者,自己譯好之後去找出版社自薦。
專業譯者通常可能會先上翻譯學校,獲得老師賞識後,以師徒制的方式共同工作,我個人並不太喜歡這種系統。台灣也有這種形式嗎?
詹:在專業譯者當中似乎沒有這種合作模式。
柴田:原來如此,當然後來也會有老師介紹案子給學生的例子。先從跟老師共譯,再慢慢建立自己的地位和知名度。我覺得比較理想的方式是建立起一套國家認證制度,可以客觀判斷一個人的能力。
詹:不過台灣幾年前也曾經討論過要導入翻譯證照制度,後來不了了之,因為要考試就得有標準,但翻譯跟口譯很難訂定一個共通的客觀標準。另外想請問您跟編輯的合作方式,您的譯文也會經過編輯再次修潤嗎?
柴田:在編輯之前還會有校正,檢查原作中與事實相關的錯誤,也會替我修正我的日文錯誤,如果覺得我原先的表達方式太艱澀,也會建議我其他替代方案。當然每個人的工作方式都不一樣,我覺得校正非常重要。不過校正畢竟只是提議,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譯者自己手中,我基本上還是對自己的譯文有決定權。
詹:編輯是帶著最嚴厲眼光、最深沉愛情,認真閱讀譯本的第一位讀者。不只糾錯,也能客觀驗證譯文是否真如譯者所願,呈現出「原作精神」。但編輯和譯者難免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老師也從事編輯工作,您心目中譯者和編輯的理想關係是?
柴田:編輯不見得能讀懂原文,我想或許不見得能夠客觀驗證譯文是否真正重現了「原作精神」。當然,有能讀懂原文並且進行客觀驗證的編輯自然再好不過,不過首先我想編輯如果能夠直覺地閱讀,先告訴譯者他覺得不錯的地方,這很重要,然後再附上充分理由指出他認為不好的部分,這就夠了。要是能再提出替代方案,就更理想了。
詹:您跟村上先生第一次合作,是因為替村上先生校正原稿,我聽了覺得非常羨慕。不管對方是誰,能夠跟同行針對譯文有這樣的腦力激盪和討論,真是過癮啊。
柴田:沒有錯!不管對方是不是村上先生,所有的翻譯都理應這樣做啊!今天只是因為村上先生的翻譯作品很暢銷,所以出版社有這個預算做這件事。偶爾在共譯的作品中,其他譯者也會校閱我的譯稿,這種工作方式我覺得很開心。
詹:您喜歡共譯,還是把書全部翻譯好後再交給另一人審校?有些譯者認為,由其他人審校後的譯文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並不希望這麼做,審校者也該掛名共同譯者,您覺得呢?
柴田:我認為應該盡量避免共譯,因為要維持譯文聲音的一貫性相當困難。但我非常歡迎其他人審校我的譯文。您提到有些譯者認為「由其他人審校後的譯文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並不希望這麼做」,假如有這樣的人,我想他要不是天縱英才的優秀譯者,就是極為傲慢的人,然而多半是後者。
----
詹:您習慣全文快速譯好後再來細調,還是翻譯每一段都字斟字酌,滿意後再譯下一段?
柴田:我會先一口氣譯完,掌握全書感覺之後再重複推敲數次。
詹:跟譯者朋友們聚在一起時,談論的話題還是圍繞在翻譯上嗎?
柴田:去年開始舉辦了「日本翻譯大賞」,藉此機會,翻譯家有機會齊聚一堂,但是平常好像沒什麼機會見面,反而是跟作家相處的機會比較多。
詹:您是指翻譯作品的作家嗎?
柴田:除了翻譯作品的作家之外,我自己還有文藝雜誌主編的工作,也經常因公跟日本作家一起赴美參加活動、朗讀會等等,與其跟翻譯家,反而跟作家之間的來往比較多呢。
※《MONKEY文學文藝誌》是柴田老師近期工作重心
----
詹:著作、研究、教學、編輯、翻譯,這些工作之間的關聯?是否以研究為中心,發展出其他的工作?
柴田:我現在辭去大學專任教授、改為特任教授的方式受聘,所以工作以翻譯和雜誌編輯占了絕大比例。大學的課只剩下一年兩門課,跟年輕人接觸對我來說確實是很好的刺激。至於研究……我好像沒什麼在研究,只是看看自己喜歡的書罷了。要認真做研究,就得讀自己不喜歡的書,比方說要研究某位作家,就得先看完所有之前的相關研究,所有跟那位作家有關的無趣論文,這我實在做不下去。
詹:所以您最喜歡的還是翻譯?
柴田:是啊,還是最喜歡翻譯。
詹:您在很多書中都提到「翻譯的樂趣」,要帶著樂在其中的心情來翻譯。對您來說,翻譯讓您感受到什麼樂趣?
柴田:我不是天才,卻可以透過翻譯貼近天才們的工作,替那些天才們完成他們自己無法辦到的事。
詹:我事前問了一些譯者朋友,假如要訪問一位在這一行耕耘了將近30年的前輩,有什麼問題想問?結果有好幾位都說「想知道前輩如何能堅持努力30年!」您有覺得自己在「堅持努力」嗎?
柴田:沒有啊,對我來說只是覺得好玩才持續下來。而現在我的生活變成以「玩」為中心,可以說相當理想。
詹:您的作品在台灣很少有譯本,這次是首次有譯本問世。身為翻譯家,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現譯本,有什麼感想?
柴田:總而言之是說不盡的感謝。
詹:不會覺得擔心?
柴田:沒有,真的沒有,而且我非常開心。也謝謝您。
詹:假設未來有機會在台灣舉辦類似「翻譯教室」的課程,您願意來參加嗎?
柴田:當然,只要有人邀請我很樂意。
詹:最後請您對將來有志從事翻譯的朋友說一句話。
柴田:替自己塑造一個可以只翻譯自己真心喜愛作品的環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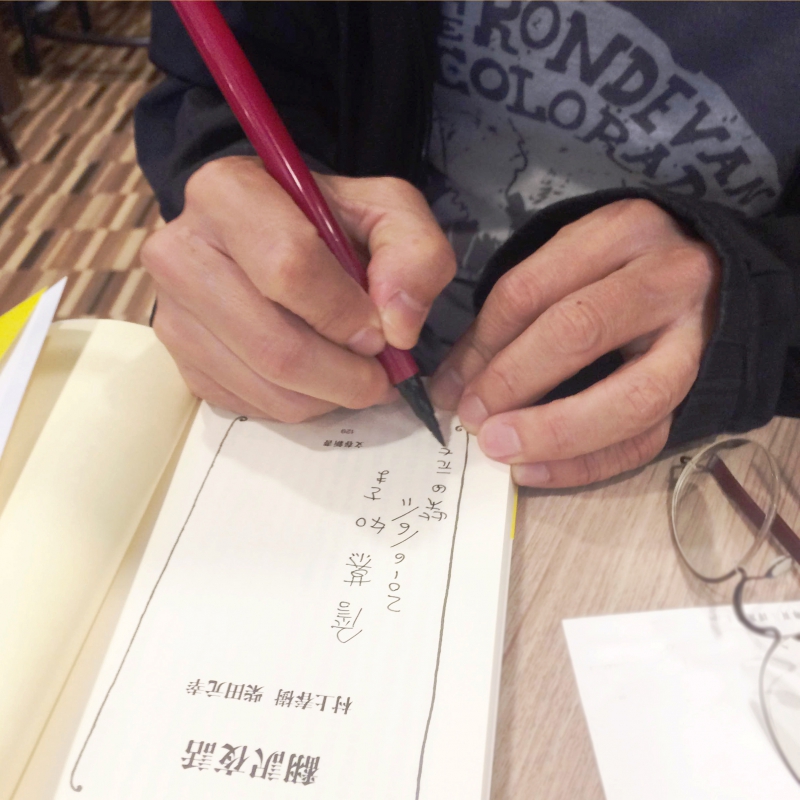 訪談最後,請柴田元幸老師簽書。(攝影/詹慕如)
訪談最後,請柴田元幸老師簽書。(攝影/詹慕如)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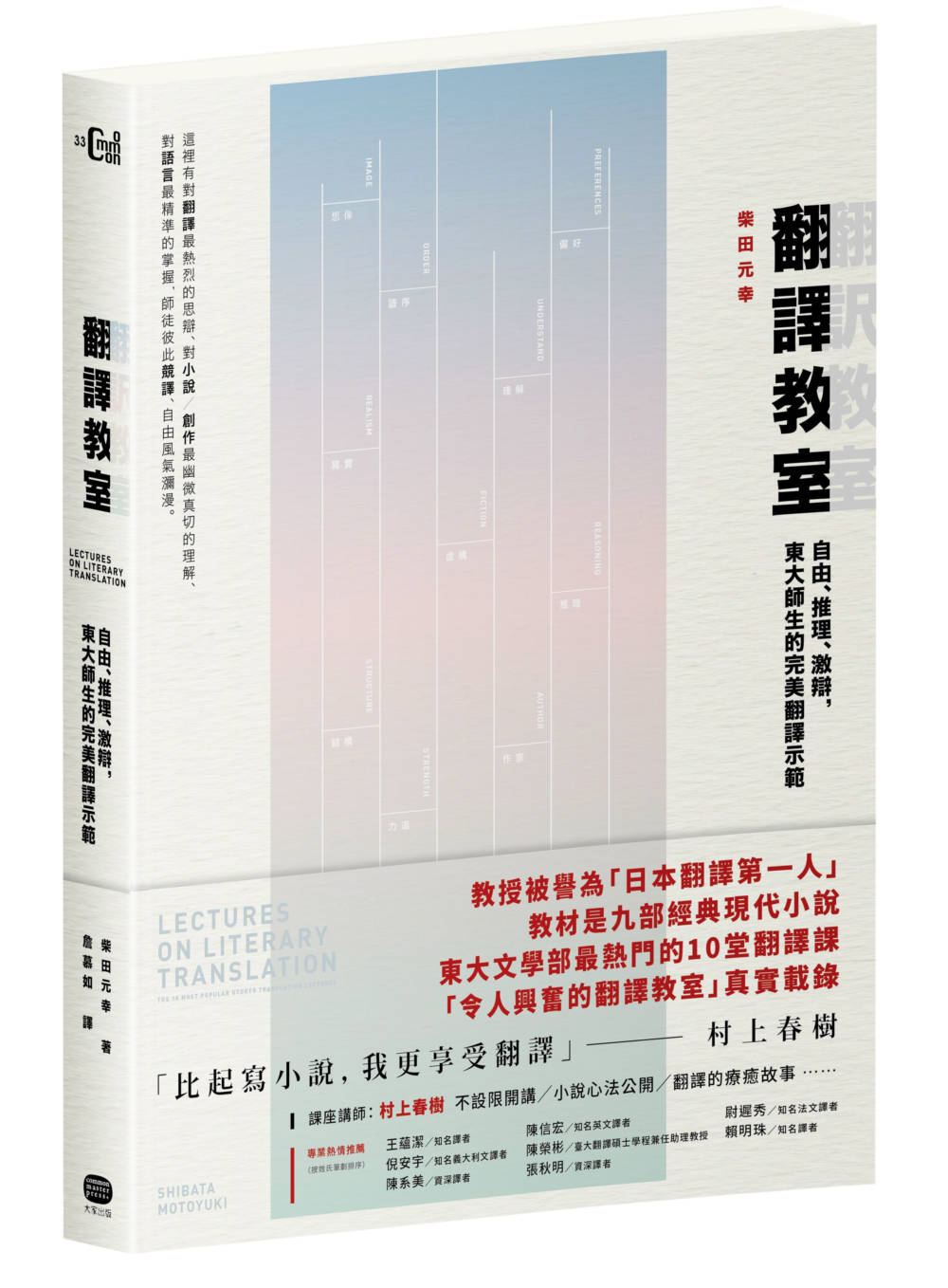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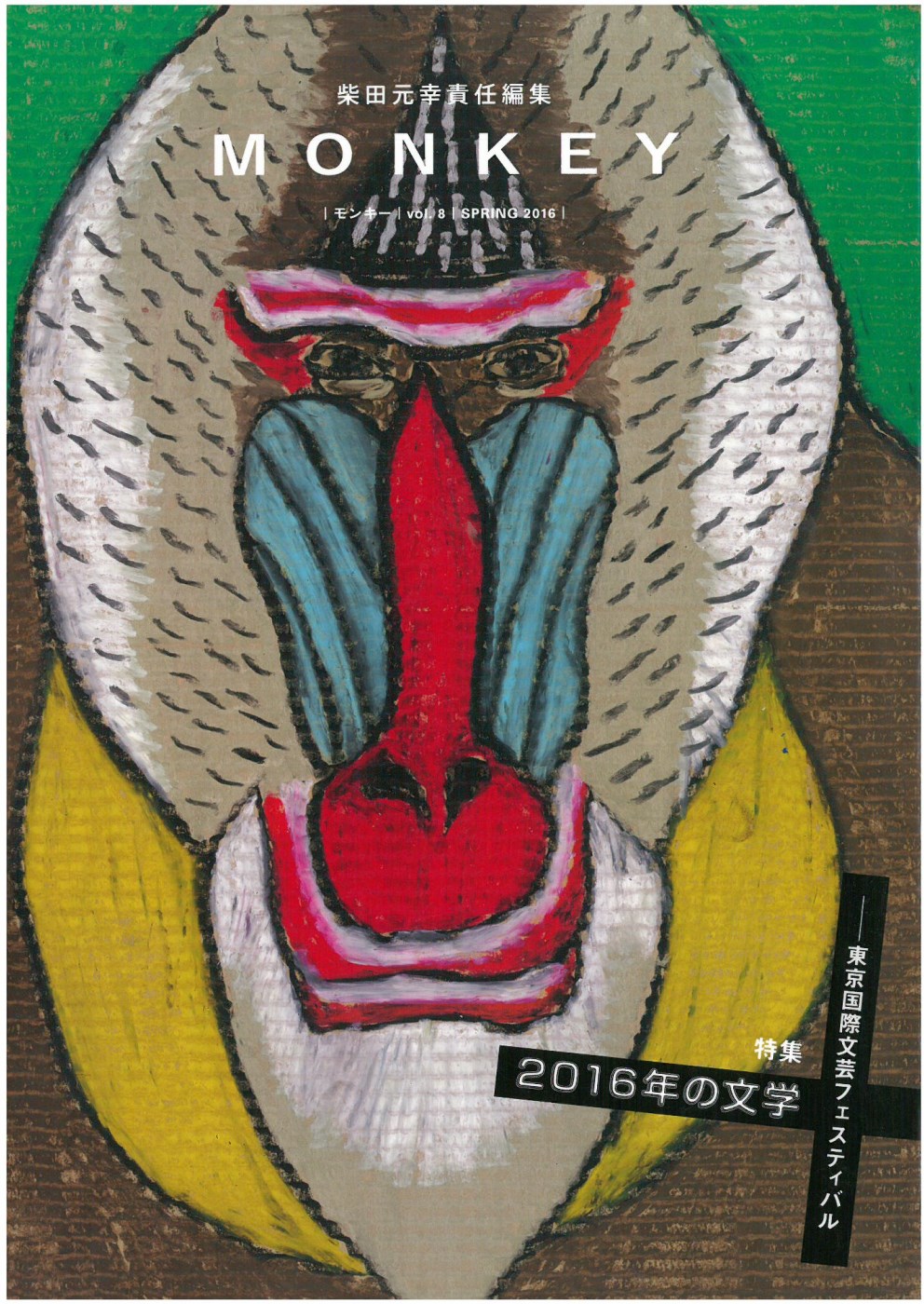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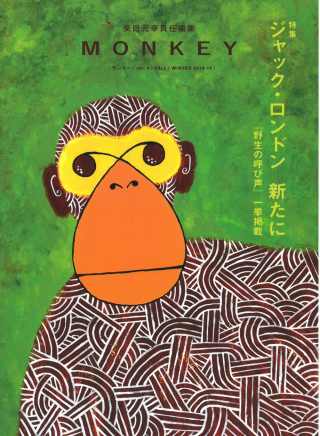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