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慧,於香港97回歸隔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拾香紀》。當時大家不知道她是哪裡冒出的新人,而她憑著《拾香紀》一舉奪得第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之後她陸續寫了二十多部小說,2023年在台灣出版的《弟弟》,亦榮獲台灣文學金典獎。這次,她把《拾香紀》與它的後續故事《焚香紀》結集在台灣推出。
請陳慧向還未認識她的讀者介紹自己,她說,「我從前會說自己在香港出生、長大、受教育,這些只是事實的陳述,但當我來到台灣居住,『我來自香港』這句話好像意義又不一樣了。我每一次說出來,就提醒我是寄居在這邊。」
她大概二十出頭歲進入香港電影圈當編劇,曾參與成龍《A計劃》、陳可辛《甜蜜蜜》、《金枝玉葉》等電影,後來在電台擔任節目監製多年。97前她離開電台,創作了《拾香紀》,之後在香港演藝學院從事編劇教學,五年前(2018)受聘至台北藝術大學教授電影編劇至今。她說,「編劇、廣播、授課有一個共通點,我一直是個說故事的人。」
▌從拾香、焚香到弟弟
《拾香紀》描寫40年代從廣州來到香港的一對年輕夫妻,在香港落地生根,生了十個孩子,最小的女兒叫做連十香。書一開頭就告訴讀者,連十香生於1974,卒於1996。父親連城總是說十香的命最好,那時候他並不知道,這個玲瓏剔透的小女兒,只短短活了22年。
小說就在十香彌留之際展開,娓娓道出這個大家庭充滿人情味、緊扣時代起伏的大小事,彷彿是對香港美好韶華的情深道別。當時很多人問陳慧,為什麼要寫一個死去的女孩?「我現可以說了,因為香港最好的22年已經過去了。1998年在香港出版時我不能說,因為大家還不能接受,但我真的是這樣看。」
 《拾香紀:1974-1996》初版書封
《拾香紀:1974-1996》初版書封她回想寫《焚香紀》的心情,是有些東西她看不清楚,所以當中有很多「要是這樣,那會怎樣?」的設想,包括小說人物去到一個「沒有回歸的香港」的平行時空。而去年決定出版《弟弟》,則是因為經過2019年「反送中」與2020年港版《國安法》等重大事件,她覺得台灣人好像淡忘了雨傘運動,「那是一個有天可能發生在台灣、發生在你家旁邊的事情,很多人卻完全失去了警覺。對我來說,《弟弟》是台灣為香港人出的一本書,雖然是香港人的故事,但我也希望台灣人看懂。」

▌清理,卻沒有處理的事
97回歸前,整個香港沉浸在懷緬回顧的氣氛,當時陳慧替電視台策劃一個香港教育發展史的節目,促使她研究起早期的英殖歷史。她看到英國人化解社會危機的高明手腕,以及建立教育制度、醫療衛生系統、建設公共房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措施。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理解,我真的覺得中國跟西方還是有一個很遠的距離,中國到現在還沒搞懂『政治』兩個字,他們有權力,但不懂政治。英國人是歐洲最早搞懂這一塊的,早就有上下議院,他們把這一塊帶來香港,不過香港只學到一個樣子而已。」
對比回歸後特區政府的表現,她想起2003年香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新增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煽動叛亂以及勾結外國勢力等條例,2020年已通過),「50萬人站出來了,你想想世界上要是哪個城市50萬人上街,整個政權都下台了好不好?然後這個人(特首董建華)可以第二天上班被記者包圍,說句『早晨』(早安)就走了。那時候我看著電視很崩潰欸。」
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她說,「接近120萬人在哪邊,然後一個下午,整個金鐘道就被清掉了,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但真的什麼都沒發生嗎?你可以把它清空,但是你什麼都沒有處理。我相信文學、電影都一樣,action(行動)是從emotion(情緒)而來,你一次又一次把它壓平,那就是一場革命啊,所以我覺得2019是早晚會發生的事。一街都是催淚彈,整個城市像廢墟一樣,你是多不關心住在這裡的人才會這樣?」
▌說療癒之前,先看清自己
陳慧說寫《焚香紀》時彷彿有個意象,「要是真的可以開天眼,我看到的是一個樓房坍塌、化為焦土的香港。」那麼,寫作算是處理它的方式嗎?「我不會說是處理,而是有些東西揮之不去,它好像是一些焦慮,一些悲哀,那些無以名狀的東西,書寫就是一個把它弄清楚的過程。」
她認為故事很重要的存在意義是,它是穿透冷硬現實的出口。「近年有一個字眼我覺得用得太多了,就是『療癒』。無論文學或電影,先不管療不療癒,它把你帶去哪裡,給你另一個角度去看清楚你不能面對的現實。與其說療癒,我更希望它是一種力量,那力量不是我給你的,而是你本來就有,你只是不知道而已。《焚香紀》就是我用故事把你帶到哪邊去,讓你回頭看這個香港、這件事。對,它是焦土又怎麼樣?」
她說她很多學生都不相信,寫作很重要的是「習慣」與「狀態」。她認為一定要每天寫,帶著筆電找個咖啡店就能寫,即使只寫500字,也至少有在動,有在思考。每天寫日記的她,也要求學生寫週記,紀錄自己做了些什麼?這事情對你來說為何重要?「有學生跟我說不知道怎麼寫,我說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要知道自己是誰,要保持清醒,你起碼要知道日子是怎麼過的。」就算狀態很消沉也能寫嗎?她說,「低潮的時候,反而是寫作救了我。」

▌在霧裡、洪荒中的香港
疫情過後,幾年沒見的朋友都問陳慧適應台灣了沒?「我吃得好、住得好,懂得搭車、知道去哪裡玩,這算適應嗎?但我怎麼可能適應,這不是我長大的地方。」事實是,即使回到香港,也只是另一種不適應,陳慧說,「我覺得超過三、四十歲的香港人,他們長大的地方已經不存在了;可是台灣人,你們長大的地方都還在。」
那麼,要如何安於自己餘生都是異鄉人?陳慧解釋,「不是安於,是要知道,要接受。要提醒自己:對,我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談到香港現在的處境,陳慧有一種感覺,「我們是在霧裡面,不知道霧何時散,散掉是不是就會好?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在等什麼。無論在香港、英國、加拿大或台灣的香港人,好像都在等待一種改變。但是從等待到那個東西出現之間,我們連怎麼走都不知道。」她形容香港現在給她一種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感覺。「我們知道要有希望,但是要希望一個什麼呢?『光復香港』是怎樣的一個香港?如何光復?我們找不到 Manual(操作指南),現在就是處於這種狀態。」於是「焚香」既有風煙與焚毁的意象,亦是灰燼之中香煙裊裊的祈求。「你有一個盼望但不知要怎麼扺達,就只能祈禱而已啊。」
陳慧每次陳述無解的現況之後的一句「對,就是這個狀態」,雖然語意像束手無策,輕聲細語中卻有堅強的底氣。她繼續說,「我很 proud of 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是陳慧,我是這個時代的香港人,那個香港很好,也很糟糕。」那麼,像《弟弟》裡的年青一代,也可以以身為香港人為榮嗎?「可以啊!其實是他們改變了『香港人』三個字的意義,讓它超越了土地,讓香港人在哪裡,哪裡就是香港。」

▌「無用」的價值
《焚香紀》有一句這樣寫:
「連城說,沒用也得做呀。明知道沒成效,卻仍堅持去做,為的是什麼?那是態度呀,要讓人看到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呀。半晌,林佳仍幽幽的問,有用嗎?」關於這段話,陳慧說她曾經很喜歡老子的「無用之用,方為大用」,後來想到它最後還是在追求「用」,但她的小說更想說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她說,「那可能就是初心吧。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它不會變成『大用』的,它就是沒有用,那你做不做?就像愛情,愛情就是做一堆沒有用的事情。但因為你愛這個地方嘛,你做不做?」
她認為香港這二十年來,敗壞得最多的是價值觀。「因為中共很快找到香港人的一個弱點,就是一定要賺錢。所以香港人常常問『有沒有用』,這幾年我在台灣也聽見了,像是『要不是可以在那邊做生意,就死定了』之類。政治上也是,他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你的 identity(身分認同)拿走,不會一下子叫你不要當台灣人,而是一點一點的,跟你說你會沒有錢、沒有前途、做不下去。他拿走你的自信,最後你的 identity 就不見了。」
最後,陳慧想跟台灣和香港的讀者說,「好好維護自己的價值觀。要知道有什麼東西是你不能給人家拿走的?想想什麼東西要是要失去了,你就不是你了?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通常最重要的東西,反而不是你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的,它可能是一個你愛的人,或是一種生活形態。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自己好好想一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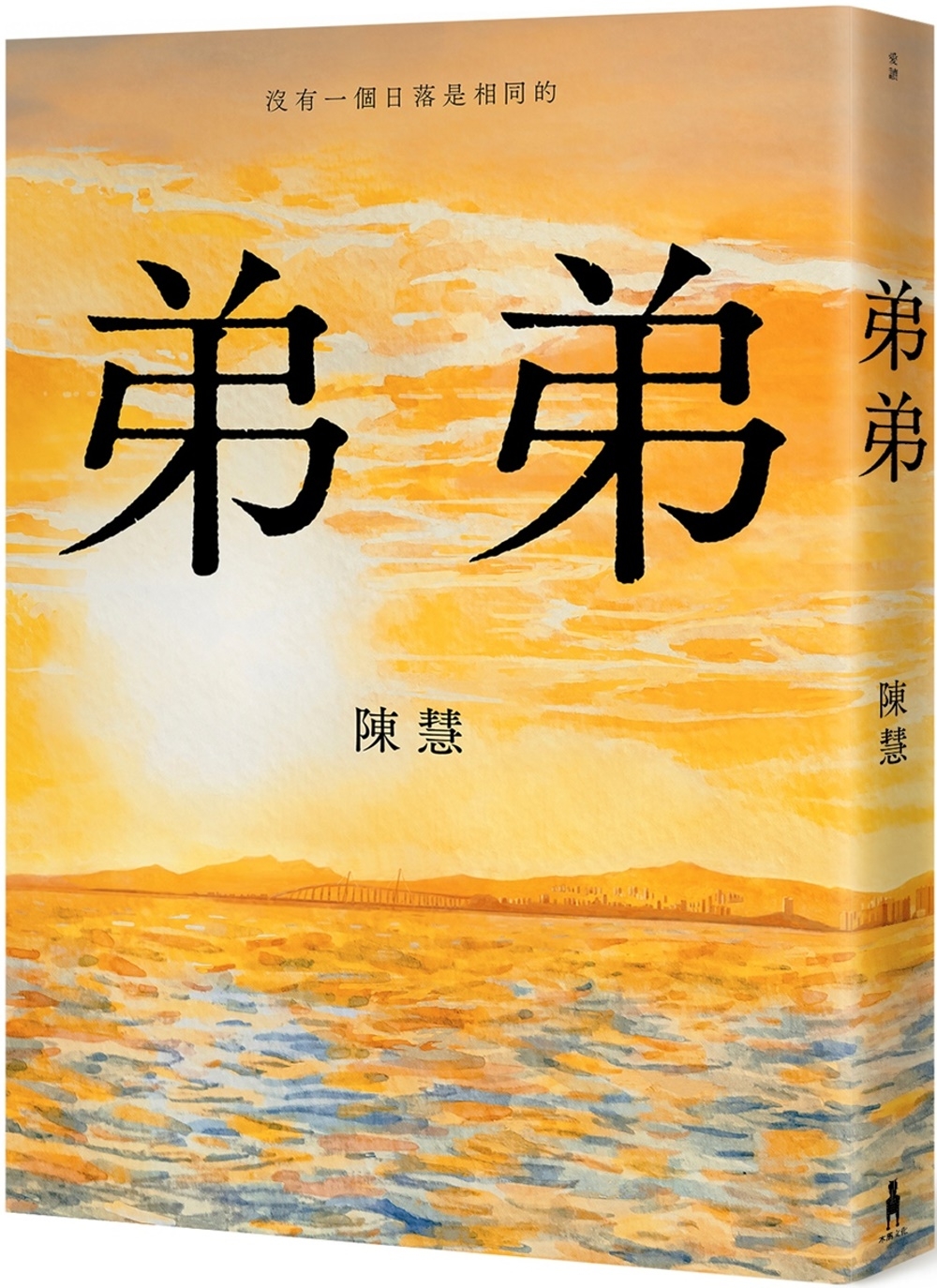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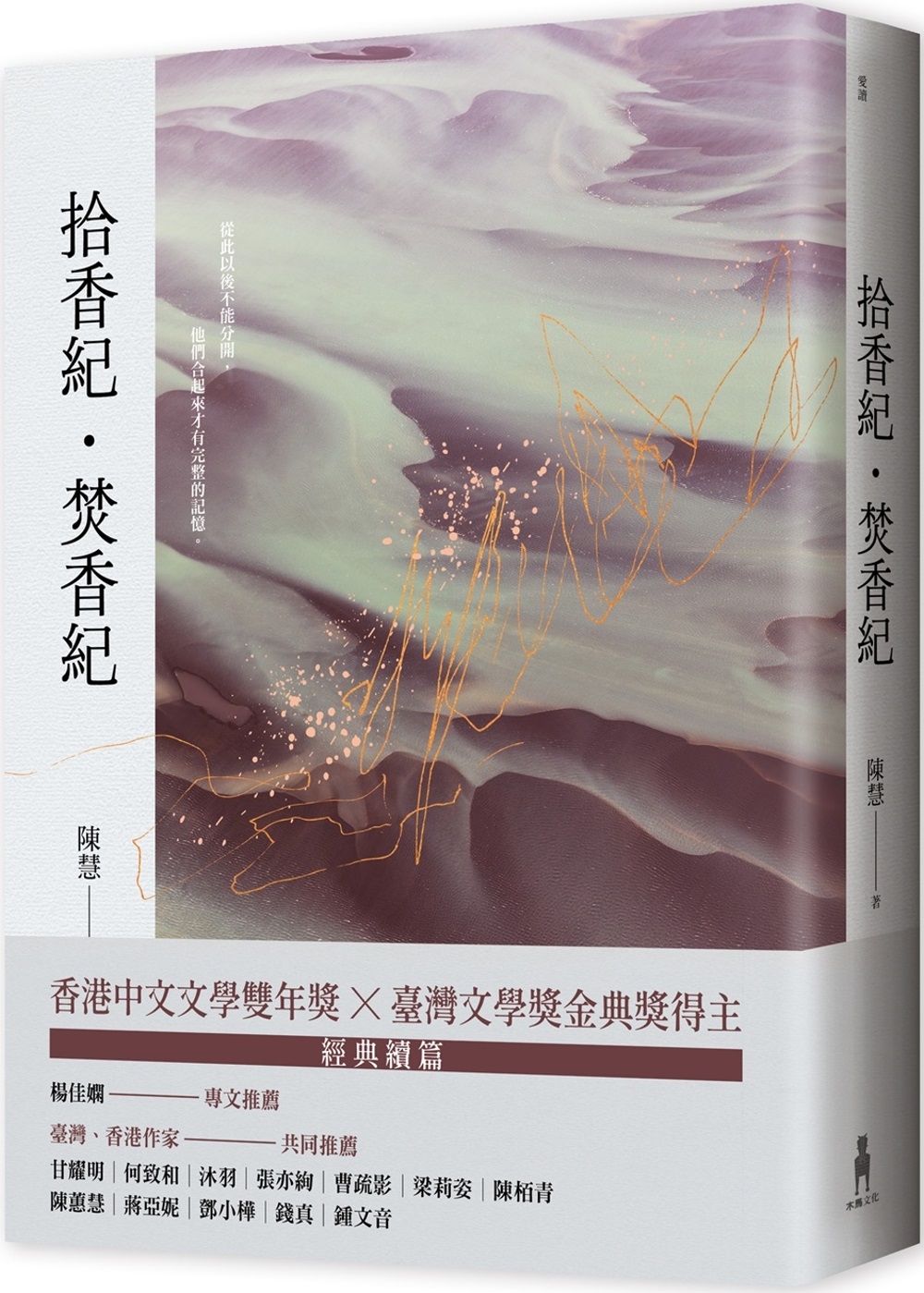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