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個男人》除了勾勒出社會階級的不可動搖,也充滿了寂寥感。(圖/《那個男人》劇照)
《那個男人》除了勾勒出社會階級的不可動搖,也充滿了寂寥感。(圖/《那個男人》劇照)
我發現將作品與事件當魔術方塊看,每次看就會有不同發現。
比方從人心來看那些回憶的流變,或從事件中鑽個小孔來看人性的切面,這對我來講都是生之樂趣,
它不見得會接近真相,但比較接近我人生想追的真理。
如果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說當個「合格的讀者」是重要的,那我們何妨一路當個找答案的人,
在找答案的過程中,它就是你自己的故事了。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電影的開頭與結尾都以人物的背面畫像呼應,一層層的鏡像,很像是Edward Hopper的畫,每個人都之於那個城市空間,形同消失與被遺忘的存在。主角城戶律師野愈來愈將真我消失在人前,也很有可能連自己都忘記了自己原是「那個男人」。
電影的開頭與結尾都以人物的背面畫像呼應,一層層的鏡像,很像是Edward Hopper的畫,每個人都之於那個城市空間,形同消失與被遺忘的存在。主角城戶律師野愈來愈將真我消失在人前,也很有可能連自己都忘記了自己原是「那個男人」。
夾娃娃機裡有很多玩偶,當他們在那樣的機器中時,它們原本叫史萊姆還是蛋黃哥,就已經不重要了,這是電影《那個男人》的核心,如今的社會化對人只是掐頭去尾這麼簡單嗎?
《那個男人》充滿了「指稱」的意味,不設定是哪一位男子,而在於角色們之於外界他者是「什麼」。且掛滿了滿滿的標籤,如耶誕樹讓樹的本質消失的方式。而角色對自己近乎沒有任何表述,或是落於表述也無法傳達的境地。
這不只是我們現在習慣的勢力讓某個人「社會性消失」,而是主角對自己以「消失」來處理他自身的「存在」,一如社區公園的設施,路邊一郵筒這般,讓大眾「視而不見」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是什麼樣的人要讓自己活得像樹葉蟲一般?為何那個社會會有人活得只是一指稱,而非有他真實的名字。
《那個男人》有趣在它充滿了日常性,無論是陰雨中的孤零文具店,還是安藤櫻演的里枝守著的文具櫃台,還是妻夫木聰演的不起眼的律師城戶與他活如精品的妻子、漥田正孝飾演的安靜男子大祐(只有他的畫蘊含了無限語言)。電影中的每一個人都在代言自己的階級似的存在,但內心的聲音則充滿了嗡鳴聲,以此對照著這世界所有的偏見與定論。
這部改編自平野啟一郎的同名小說,這故事的確充滿了大師松本清張的魅力,如一滴水掉進溪水中,看似平靜渺小,卻激起水底下的漩渦,除了勾勒出社會階級的不可動搖,也充滿了寂寥感。
社會有些沉痾的病態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但為何這樣的群體是舞動著卻是寂寞本身?是因他們遵守的價值是否只是啟動了自己可能被排他的恐懼?
有如卡夫卡所寫的《城堡》,裡面許多人只是把體制內化成自己內在,因此成為「城堡」的概念的守門員而不自知(他是A是B都無法大過他本身的階級),這個故事裡面所有的人都如芭比娃娃的娃娃屋(演繹式的幸福從另一個角度很陰森),包括演妻夫木的岳父在餐桌上的言語:「那些外來的人根本不算日本人。」其他家人如芭比娃娃裝飾般地坐著,如同是他們階級的陳列品。
從那幕開始,我感受到原來隱瞞自我的不只是兩個男主角城戶與大祐,而是這電影的所有人都是「那個男人」,每個人都在恪守自己的制度,在其中因被群化了而感到安全,如同會走動的制度代言人,就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意識形態恪守者,他們無論財力大小都以巡視「城堡」的小兵姿態為榮,而忘記了自己是誰,與他的名字除一符號外到底有什麼價值。
這與日本原本信仰的名字如同靈魂的招喚全然不同,他們彷彿都在蛇魔女的眼神下變成了石化人,戲中每個人因恐懼與自身認知不明而成為「那個男人」,讓人想到徐四金的名著《香水》中的最後雜交場面,只要不用為自己的決定付出代價,人們很願意忘記自我。
因此這部電影帶出的是一種後怕情緒,如同《城堡》的K置身於無邊的異境,他出不去是因為那裡是個「時代」,主角城戶在一個大制度下,就如同K一般永遠在叩門。
而電影中的城戶與大祐,前者因為是朝鮮族(始終被當成低人一等的外來者),大祐則因為是殺人犯之子,在階級森嚴的日本始終處境邊緣,雖然被制度排斥,但荒謬的是他們也是制度的信仰者,他們對自我的攻擊不亞於外界。大祐甚至打拳擊賽時有如自殘一般,深怕自己也如父親是這個群化中的變異份子。
只有大祐頂用他人名字後,才能放過自己一馬般,與偶然結識的里枝展開了新的生活,他的人生又重新開機一般,如同騙過所有人地悄然安生著。他像偷來的日子一般珍惜新生,那幸福是這部電影瀝青階級中一股暖流,但也無法讓社會這個石頭巨人往人道方向多走一些。
 大祐頂用他人名字後與偶然結識的里枝展開了新的生活,那幸福是這部電影瀝青階級中一股暖流。(圖/《那個男人》劇照)
大祐頂用他人名字後與偶然結識的里枝展開了新的生活,那幸福是這部電影瀝青階級中一股暖流。(圖/《那個男人》劇照)
因為現代人多半渴望是社會來認可他們,廣告與傳媒的訊息都將社會一元化,而非由個人轉身去看這社會是個培養皿,有時是承載了過期壞水的羊水,誰也不知裡面孕育了什麼?而個人又要如何適應且能接受自己?
電影中的回馬槍放在妻夫木飾演的律師身上,他活得就像表面平靜的漩渦一般,看似衣冠楚楚,其實所穿所用都只是規格化,你從他的包包到他的表情都是規格化過的。這角色很難演,他內在幽閉了膽怯的自我,包括他的婚姻都是他的加固保險,來隱藏他的真實。
 妻夫木飾演的律師看似衣冠楚楚,其實所穿所用都只是規格化,包括他的婚姻都是他的加固保險,來隱藏他的真實。(圖/《那個男人》劇照)
妻夫木飾演的律師看似衣冠楚楚,其實所穿所用都只是規格化,包括他的婚姻都是他的加固保險,來隱藏他的真實。(圖/《那個男人》劇照)
他比大祐必須盜用他人名字才能展開新生還要徹底壓抑,他將自己喬裝成「社會」所有的正確,他就是一個相對於「芭比世界」裡如雞肋的塑膠肯尼,可以是任何人,只要夠正確。而他周圍人對大祐的批評,都如同刺在他身上,讓他更害怕自己身為「社會」的贗品被曝光。
這部電影可以看做一個人被密不透風的體制桎梏,如同趨光的蛾黏在蜘蛛網,也可以遠看整個社會只尊崇某一種「那個男人」的形象,「那個男人」看似開放先進,但實則本質上仍然將「成功標準」這玩具玩弄在掌心,驅使人們同化在不知主宰者是誰的「城堡概念」中。
因此城戶律師在他人抹滅大祐想活下去的努力時,才終於失控顯出怒意。他的人設因大祐案而出現裂痕,但他補強的方式是在某些安全場所徹底拋去了肯尼的樣貌,如同對社會病體的發炎,開始演變出另一種相反「人設」。
說穿了,這社會有如灰姑娘童話,認鞋不認人,你的外貌與舉止都要配合那雙該死的玻璃鞋,它是你的敲門磚,至於灰姑娘叫什麼名根本不重要,童話本質都很黑色幽默。有如安徒生童話的《影子》,本體被吞噬了,或是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與《假面的告白》,你不知最後留下來的哪一個「理想的自我」。
《那個男人》這部心理恐怖片,因為日常仍流洩出來,陽光灑落的公園,孩子的笑容,生命真實的吉光片羽還在,但趁著城戶律師的走入「自我迷宮」中的劇情,帶出了若摘掉名字、稱謂與頭銜,你我究竟是合乎市場導向,但內在中空的洋蔥,還是只是相對於天地的真實?
寫這篇稿子時,我正恰好聽到《2009年月球漫遊》的機械化配樂,而貫穿《那個男人》的電影配樂則是一個音的多樣變奏,表達出內在的質疑與重組,這是加分的配樂(出自台灣樂團Cicada)。將兩部配樂聽完,社會給我們的表象,幾乎有如一舉打破石膏像,也順便一把撕掉《那個男人》深入骨髓的社會集體假面貼紙,內外呼應,痛快!

《那個男人》(A Man)由石川慶執導(《蜜蜂與遠雷》《愚行錄》),妻夫木聰、安藤櫻、窪田正孝主演。故事以一場意外死亡的追尋,叩問人的存在意義,改編芥川賞作家平野啟一郎同名小說,導演石川慶與妻夫木聰再度聯手,與安藤櫻、窪田正孝打破個人身分認同,探究人在不同環境的不同面貌。沉穩定鏡節制冷靜,長鏡頭緩慢推入角色內心,包裹在社會派推理的案件偵查下,各方生命經歷對照日本社會問題,不斷對自我提出質疑。若無法改變背負的過去,要如何展開全新的未來?能將人從現在中解放的,是不是愛?
作者簡介
同時是音樂迷與電影癡,其實背後動機為嗜讀人性。在娛樂線擔任採訪與編輯工作二十多年,持續觀察電影與音樂,近年轉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從事專欄文字筆耕。曾任金曲獎流行類評審、金鐘獎、金馬獎、金音獎評審、中國時報娛樂周報十大國語流行專輯評審、海洋音樂祭評審、AMP音樂推動者大獎評審。樂評、影評與散文書寫散見於各網路、報章刊物,如:《中國時報》娛樂周報、《聯合報》、《GQ》、《VOGUE》、《幼獅文藝》、誠品《提案》、《KKBOX》、博客來OKAPI、娛樂重擊網站與《HINOTER》等,並於「鏡好聽」平台開設Podcast節目《馬欣的療癒暗房》。著有影評集《反派的力量》、《當代寂寞考》、《長夜之光》;雜文集《階級病院》、散文集《邊緣人手記》。最新作品為散文集《看似很美,其實是壞掉的》。
✎作家金句:「人生難免失去,但也讓你有再次擁有的能力。」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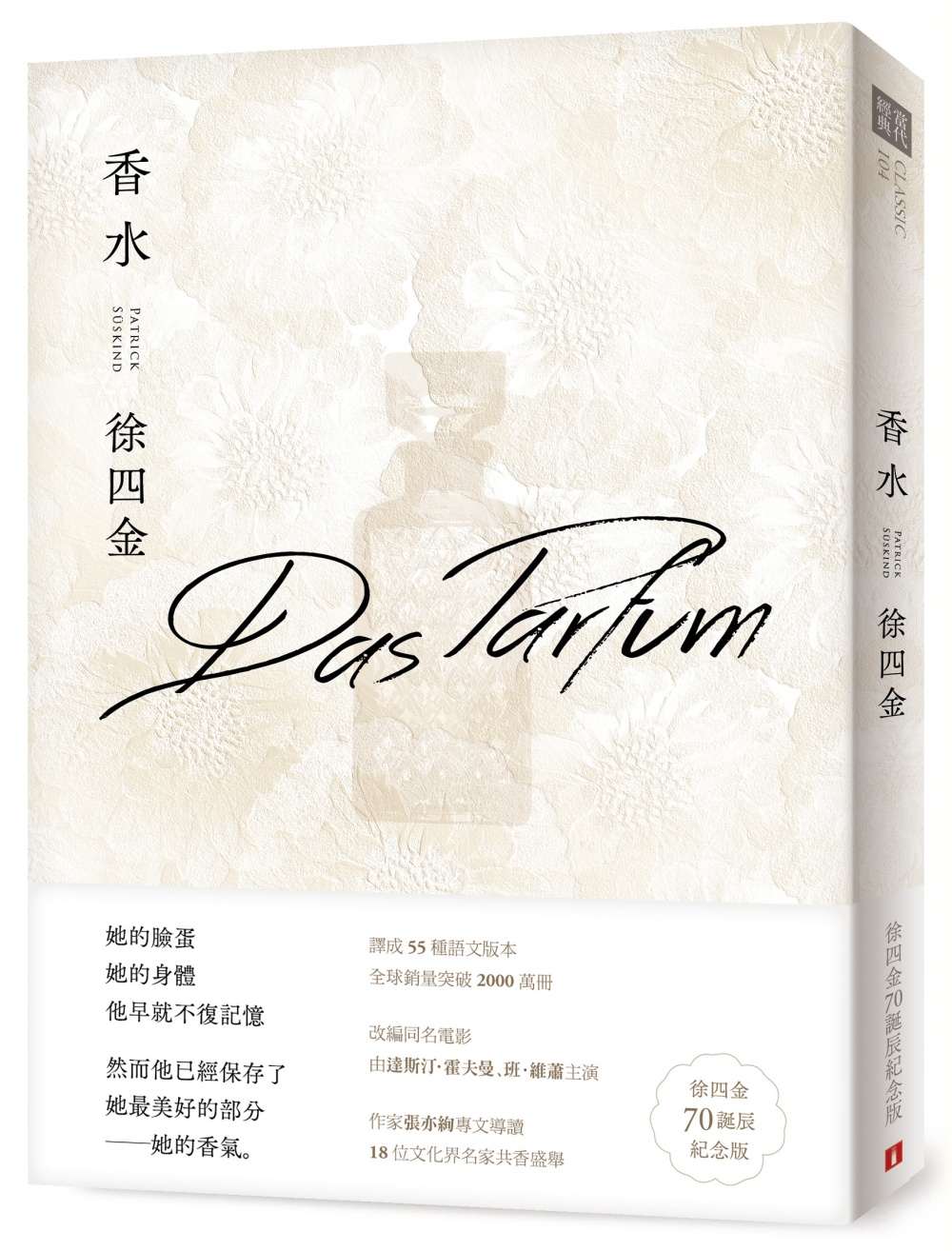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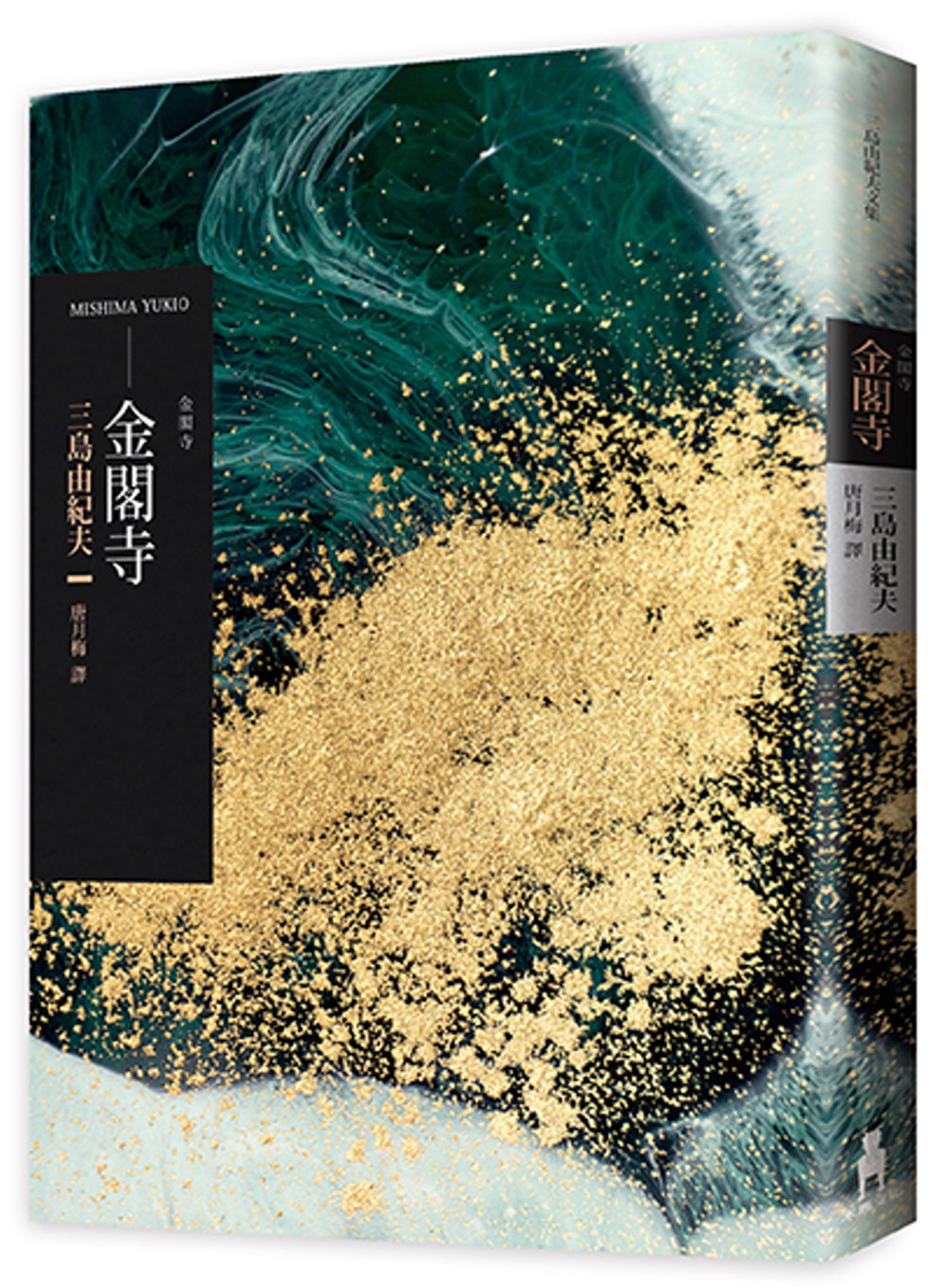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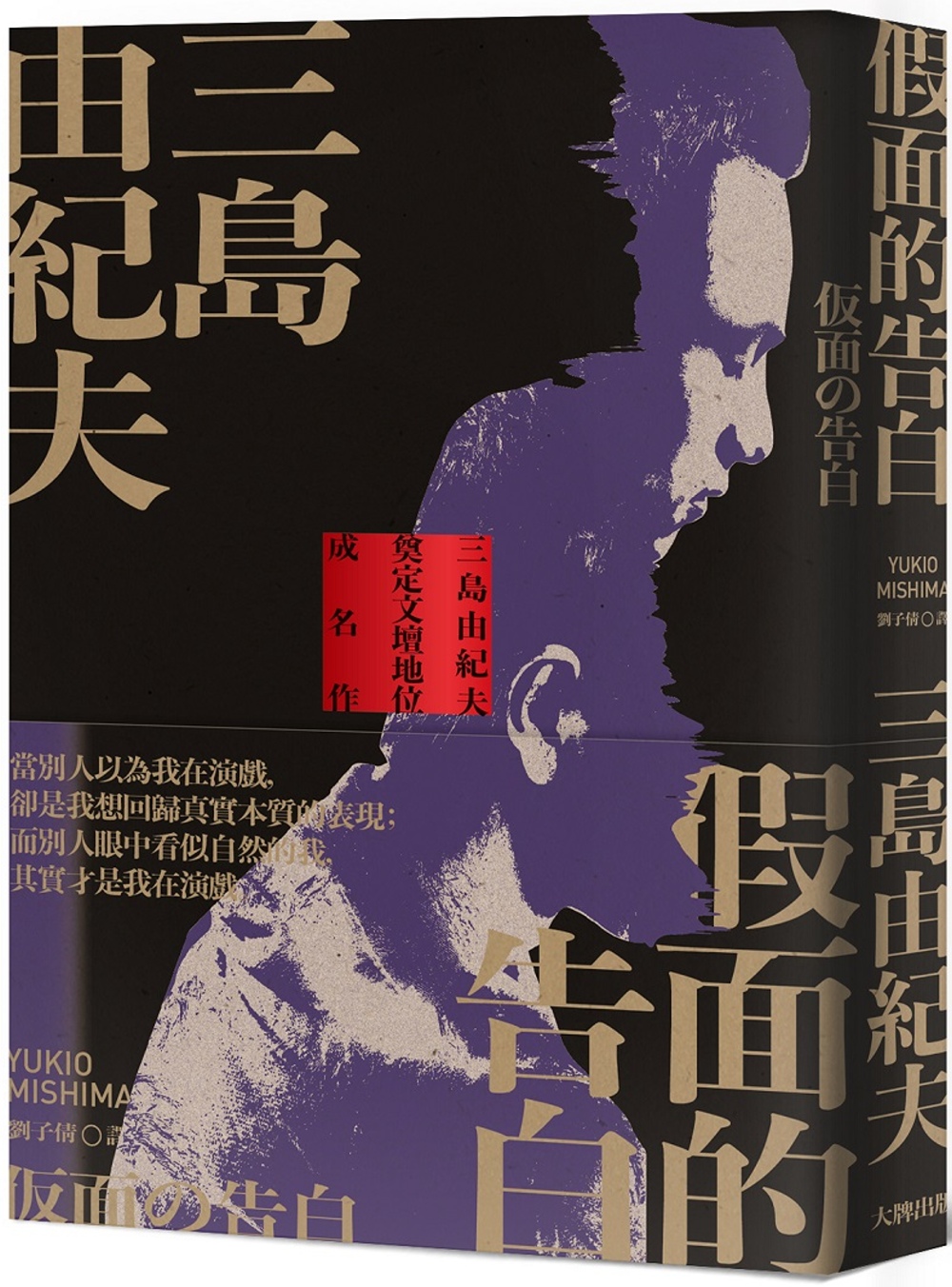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