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書出現兩百多個「fuck」該怎麼翻譯呢?
「fuck」怎麼翻譯?英文國罵的衍生詞多如牛毛,譯者總不能一「幹」打死「fuck」的祖宗八代。三百多頁的文學小說《苦甜曼哈頓》出現兩百多個「幹」,而且出自嬌滴滴的粉領文青之口,那還得了?
《苦甜曼哈頓》的作者一來是藉髒字傳達主角泰絲逆境求生的苦澀,二來是反映美國餐飲業潮男女本色,書寫至為傳神,卻苦了詞庫甚窘的譯者。更難拿捏的是,英文國罵衍生詞的狠勁不如中文三字經,如果照原文宣科是怎麼看怎麼怪。然而,幫作者潤稿並非譯者的本分,原作爆粗口,譯者也該乖乖跟著罵,於是「他媽的」、「狗屁」、「去死啦」、「老子/老娘」、「搞什麼鬼」、「去他的」、「去吃屎」、「操你的」連番上陣代打,乃至於粗俗但不帶髒字的動詞「上(某人)」也加減用,因為譯者的任務是忠實移轉原文讀者的感受給中文讀者,讓F字對原文讀者的效應也延展至譯本。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續集《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也給我類似的試煉,但高頻字不是國罵。翻譯前,我先讀《呼喚我》原文書,然後讀《找到我》,專注在書中人物的情誼、異國場景、故事轉折,倒沒留意到哪些字重複出現。一旦開始敲鍵盤,我在《找到我》一書中找到「smile」90次,假如每次都「微笑」,我到自行校稿的階段一定笑不出來。
此外,「sudden / suddenly」52次、「total / totally」46次、「ironic / irony」25次、「almost」64次、「moment」110次。「perhaps」和「maybe」合計更多,達168次,這還不包括「may」和「might」的110次,譯者能從頭「也許」到尾嗎?即使交替用「或許」、「可能」、「八成」、「大概」、「估計是」、「敢情是」,每一詞也會在《找到我》露臉至少40次。然而,和《呼喚我》相較,這些字頻率之高也大同小異,顯示是作者安德列.艾席蒙慣用語,屬於原著風格的一層,豈容小譯者刪改或敷衍了事?
20世紀初作家D.H.勞倫斯愛用「mechanical」形容「機械式」反應和動作,或許能反映工業化時代的思潮,哪怕《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兒子與情人》裡各有二三十個「機械式」,譯者也只能照著翻譯。同樣的,《唐頓莊園》作者在《往事不曾離去》裡「of course」192次,有時同一頁甚至出現3次,在描寫平民高攀夕陽貴族的故事裡能凸顯作者語氣,我只能跟著一再「當然」,偶爾來個「自然是」、「想當然爾」,不太適合用「廢話」、「想也知道」取代,省得煞風景。
反過來說,作者避用高頻字時,譯者卻可能被迫再三反覆相同的詞。以九一一紀念碑為設想情境的小說《穆罕默德的花園》而言,作者一律以「the names」代表死者名單、以「the buildings」代表世貿大樓、以「the attack」表示九一一,譯者為維持文字精簡,也為避免「那些姓名」、「那幾棟大樓」、「那件攻擊案」滋生誤解,只能義無反顧反芻同樣幾個高頻名詞。
我在翻譯《湯姆歷險記》和《哈克歷險記》期間,和美國友人討論馬克吐溫,多數人想知道我如何翻譯那個「N字」。「N字」中譯通常是「黑鬼」,在現代美國儼然是一個能粉身碎骨的地雷字,但在馬克吐溫的19世紀並無貶義,主張種族平等的他都用了一百多次,因此為折衷起見,我多數以「黑奴」翻譯,只在歧視者的對話中譯為「黑鬼」,希望中譯本讀者能領會這字眼在當今美國讀者內心的違和。「by and by」(未幾)也是19世紀小說的常客,馬爺在兩書裡共使用121次,我能儘量以「後來」、「不久」、「未久」交替用,以免濫用古詞被讀者嫌礙眼。
由於基督教徒忌諱以「上帝」和「天」驚嘆,因此在這方面,擅長寫實當代民風的馬克吐溫自有呈現方言和鄉音的一套,有些角色只喊「地啊」,譯者也必須避免妄用上帝之名,以防讀者聯想起「My God」而悖離馬爺的原意。在《湯姆》和《哈克》裡,以「天」驚嘆的角色唯有社會邊緣人。即使是小遊民哈克,從《湯姆》一書的配角晉級主角,讀了一點書之後也文明了,改喊「他爺爺的」(by Jimminy)。
拉拉雜雜統計了各大作家的高頻字,我回頭看一下,短短不到兩千字的這一篇,「出現」有4次,「高頻」有7次,「讀者」有8次,自己果然也難逃高頻字的盲點。幹。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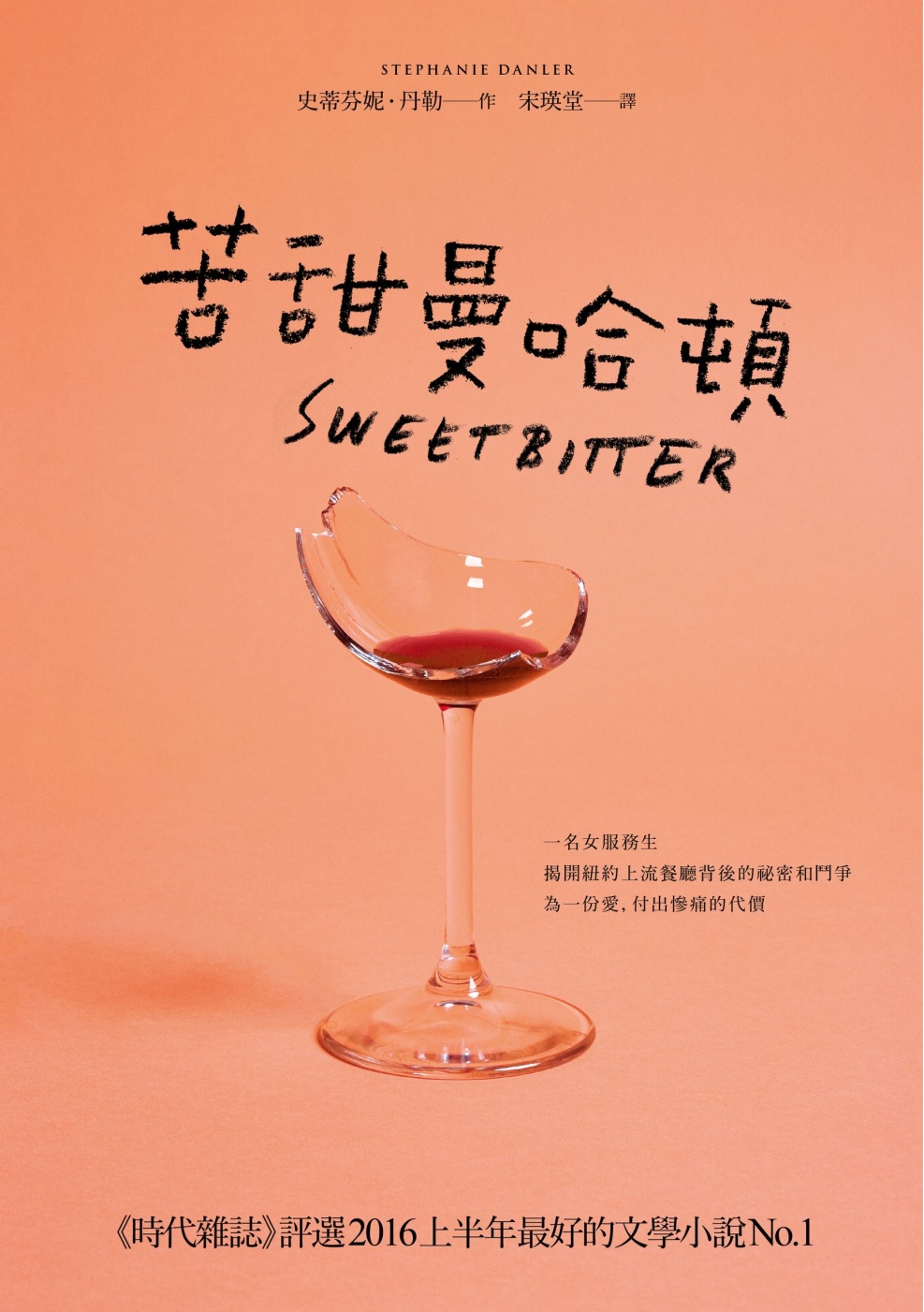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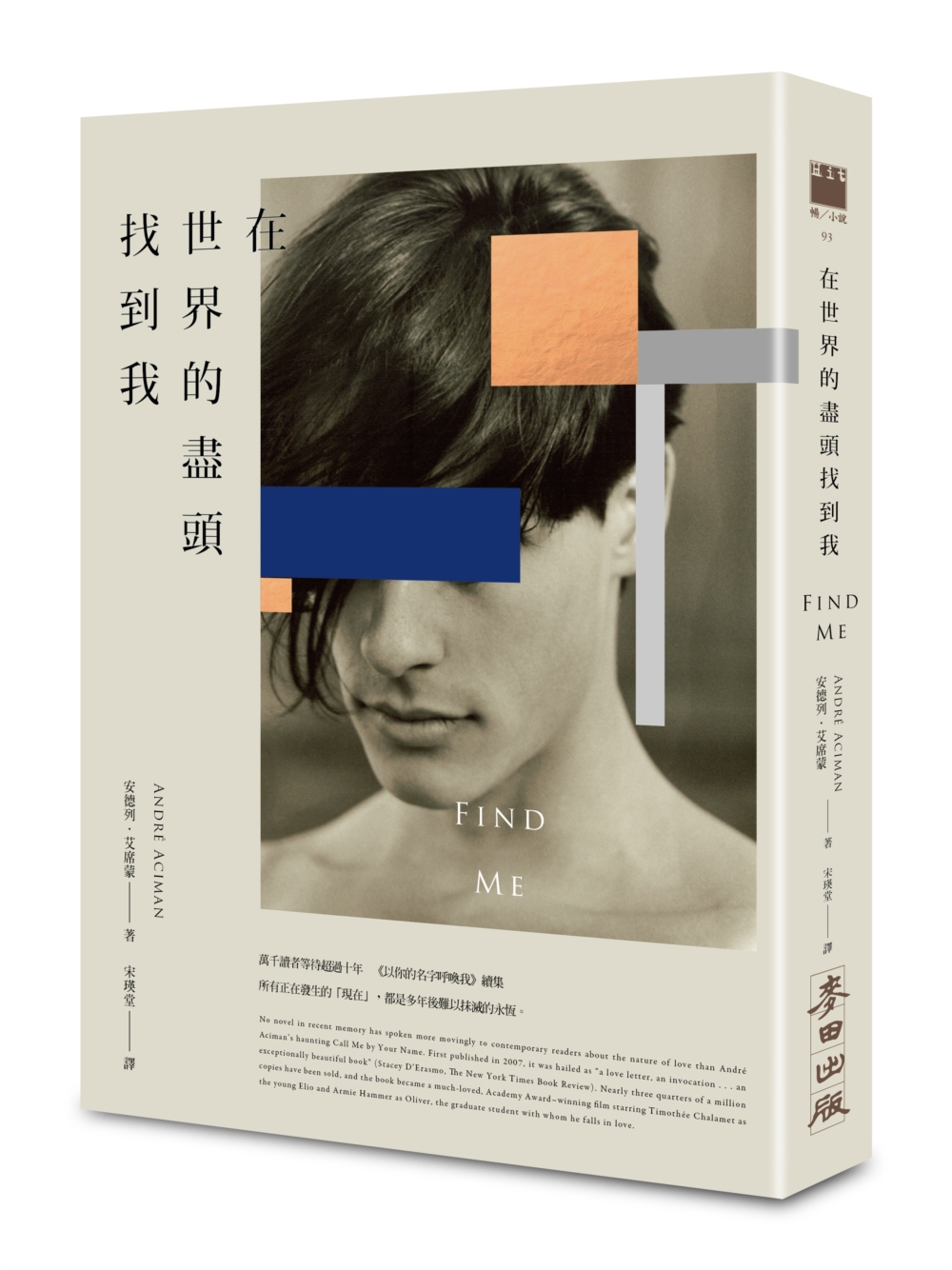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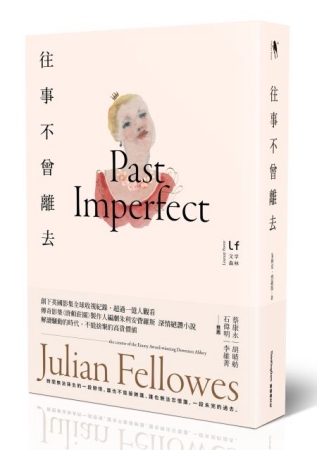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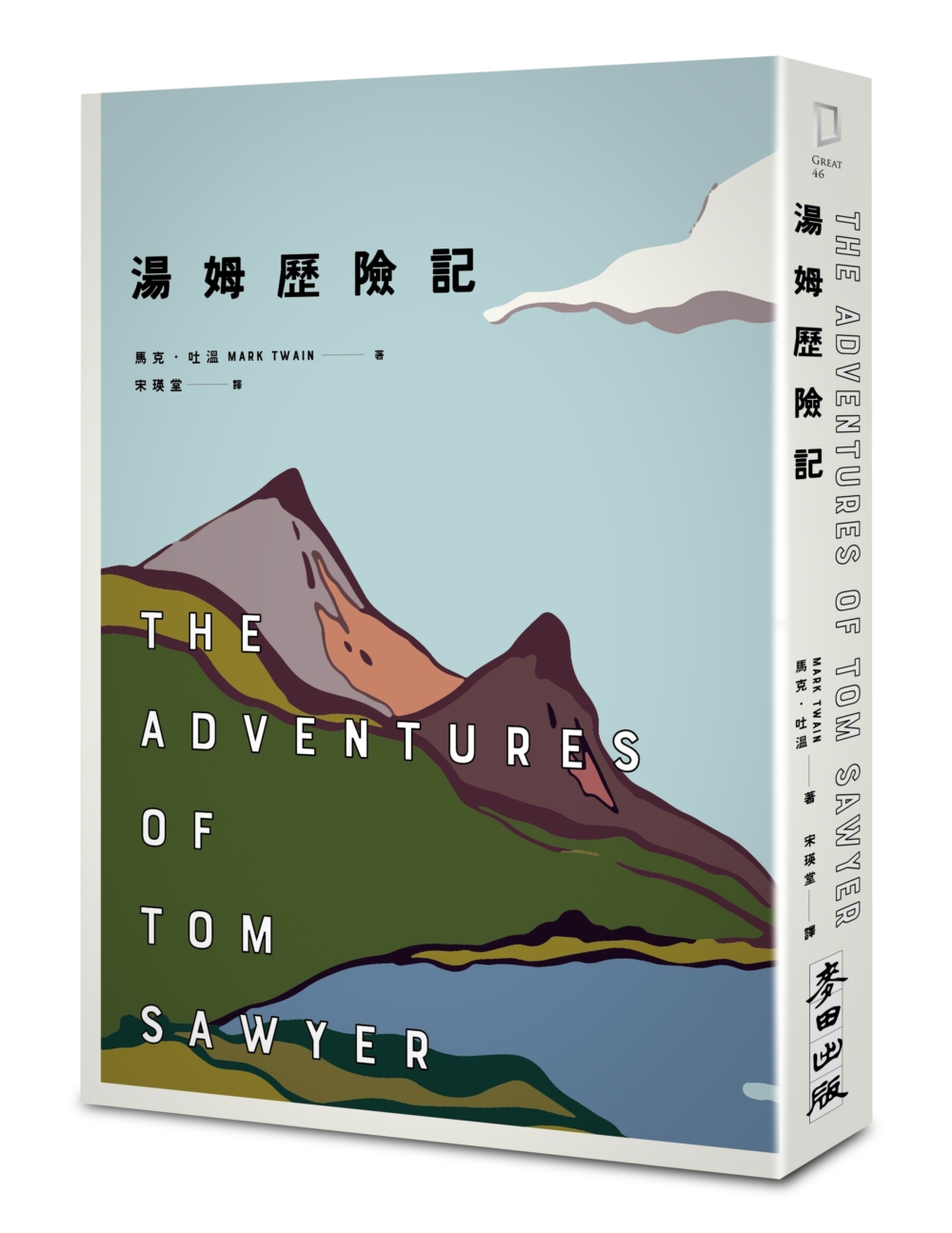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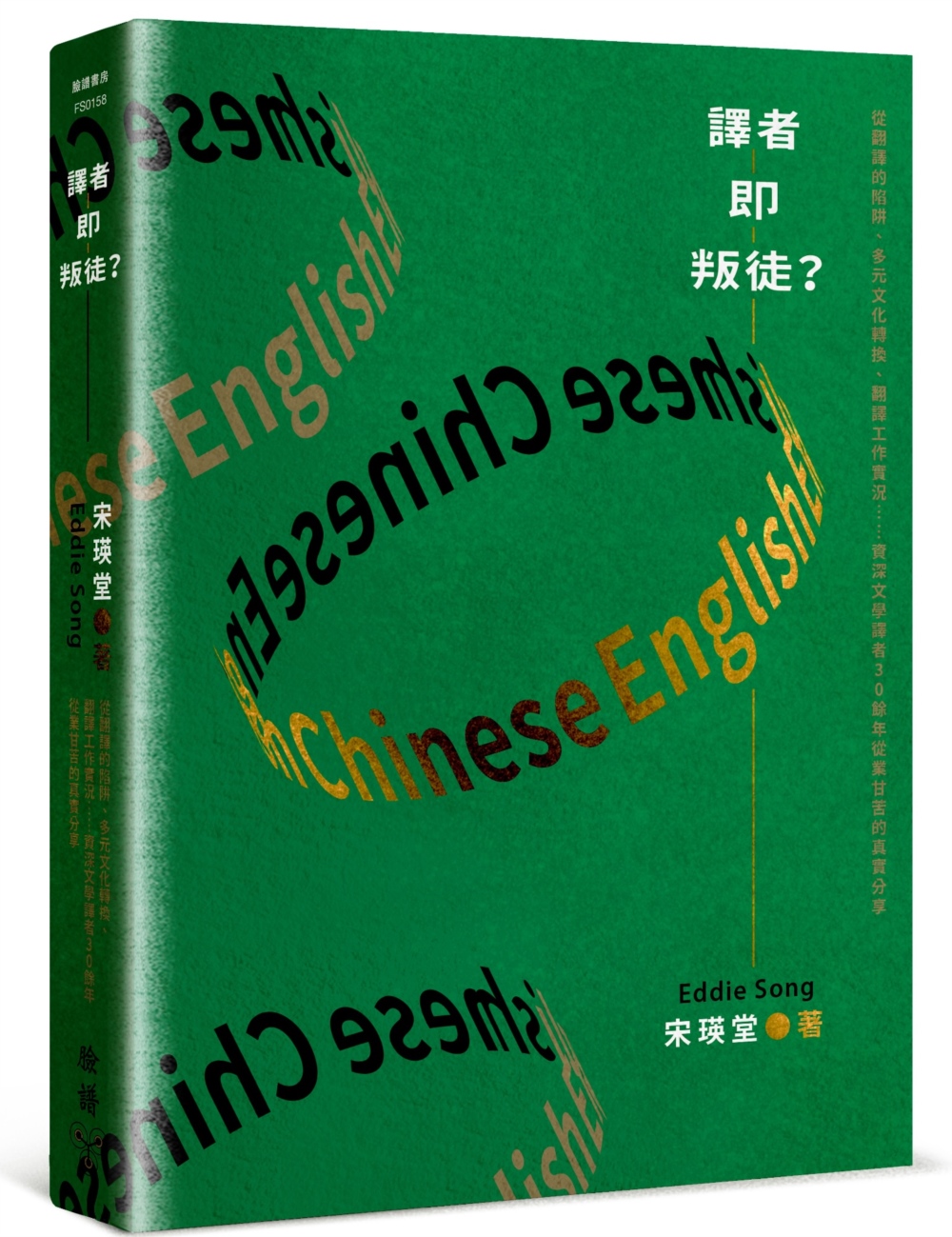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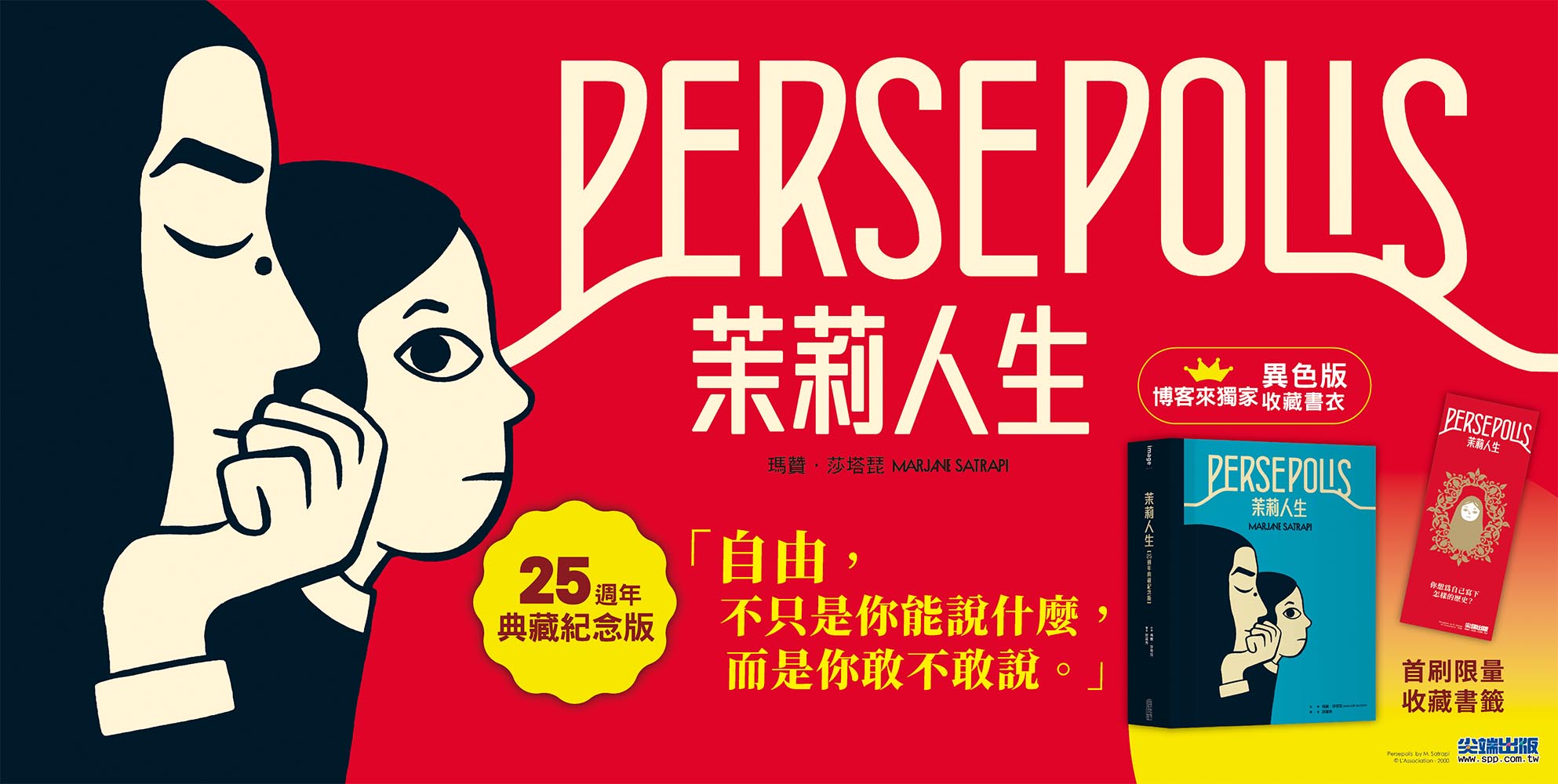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