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本「讀」起來很有意思、儘管「聽」起來並不那麼精彩的書。或許,這也是這本書與那個時代的聲音最為特別的地方。
《我們的搖滾樂》不像書架上那些關於搖滾樂與搖滾樂手的書,你可以一邊讀著一邊按圖索驥,找到一首又一首歌做為原聲帶,跟著字句按下播放鍵。這本書寫的是1950到1980年代,搖滾樂如何在台灣被引進、聆聽、逐漸生長,又如何一再被戒嚴體制打斷的故事。在裡頭,如果要找到屬於那個時代那個島嶼的搖滾歌曲,多少會有些失望。甚至於,當時台上翻唱的曲子,都只有文字記錄,而沒有幾張錄音。幾個少數寫進傳說的時刻,在今天看起來,也難以想像為什麼在那時驚世駭俗。
但是,你還是一頁一頁往下讀了,想著,後來呢? 想著,如果有一天這些不再被阻礙,那西太平洋軍事戒嚴下還被叫做「自由中國」的島嶼,將會有什麼樣的聲音出現?然後在最後一頁想起,那個「後來」,也就是我們身處的現在。
作者熊一蘋是個熱情的說故事者,從當年留下的有限歷史資料中,找出了一個個充滿壓抑與渴望的故事。而這本書更重要的成果,是把這些故事放到時代脈絡下,把我們印象裡的片段畫面——翻版的美國流行金曲黑膠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太保與演唱會、民歌西餐廳裡李雙澤嗆聲胡德夫「你有沒有自己(母語)的歌?」——交織成一段連續的歷史,問道:是什麼樣的結構因素,使得這些成為可能?
這些故事說著,那思想肅殺的年代跟我們以為的非常像,但也有一些不同。體制外的駐台美軍、歸國投資華僑,與體制裡具有軍政背景的外省族群子弟,在堅硬的殼上,打開了各種破口。為了尋找不同的聲音,讓一小部分青年,透過各種管道購得來自美國的唱片,開起電台節目,組成樂團翻唱裡頭的歌,在勞軍名義下,在美軍俱樂部,在外僑消費的夜總會,在打通關節租來的演唱會舞台上,半生不熟,學生玩票一般卻也充滿激情地彈奏,甚至籌劃起出國表演。既關於自由,也關於生意,在中華商場愈來愈多的盜版唱片銷售量裡,人們辦起雜誌,搞起「小美國」似的咖啡廳,討論那叫做「搖與滾」(Rock & Roll)的事物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一切都得自己來。不禁讓人感到有一分熟悉,今天的年輕人,不也是這樣的嗎?只是,在今天組團不用面對的一面也始終在那。在保守、管制的社會氣氛下,「不良少年」開始遭受警察取締,場地被查抄,長髮問題甚至導致演唱會中斷。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被退出聯合國(1971),駐台美軍大幅減員,演出機會減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政府當局,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高舉「流行歌曲藝術化」的淨化口號。
後面的故事,進一步說著處在兩面之間的掙扎,如何使得「熱門音樂」分化轉型,一邊是試圖爭取論述空間的「質樸的搖滾樂」、「自己的歌」、「中國現代民歌」;另一邊,音樂性更強烈,更具有節奏與身體渲染的聲音,則走向幕後,做起流行音樂的錄音伴奏,在報紙上被叫做「歪歌」。在那些年裡,熱門音樂樂團留下的錄音,最後只有幾張翻唱演奏唱片。創作的人們,終究不得不花上太多的時間力氣,去跟審查制度打交道。讀著這些爭取空間的曲折,我們得以解答一些長期的困惑:為什麼聽起來並不衝擊的歌,在那一代人的回憶中有著離經叛道的力量?為什麼答案早在那裡的問題,都要一再地去爭論?
而這些也指向這本書沒有討論、卻隱約點出的另一個成果,帶向了既存唱片與資料無法回答的問題:在清楚可見的政治與思想壓制之外,我們如何測量戒嚴時期未及誕生的創造與想像?
環顧1970年代美軍在亞洲的冷戰前線,西方搖滾樂接枝各地謠曲土壤,在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中長出各種奇異的果實,越南有靈魂歌后Carol Kim,柬埔寨有金嗓子女王Ros Sereysothea,泰國有參加民主學運與游擊隊的左翼民謠樂團Caravan,就連跟台灣更接近的南韓,申重鉉(Shin Jung-hyeon)也在軍事政變夾縫之前用藍調迷幻寫了給朝鮮半島山河的曲子。而在這政權統治未受動搖的島嶼,即使是今天聽來那麼「愛國」的〈龍的傳人〉,都要被新聞局長找去吃飯,建議把歌詞改一改。(接近那些歌謠的,也許只有黃俊雄布袋戲靈光一閃,無心插柳翻唱的大節女跟孝女白瓊出場曲。)
再相較音樂文化產業更為繁榮的歐美與日本,這些中斷與分歧,也使得這個島嶼錯過一次又一次「搖滾樂已死」的時刻。當這十幾二十年裡,搖滾樂在彼處,在戰鬥中不斷自我質疑與蔓生,各種新的聲音嘗試在車庫在地下室展開,既被吸收成為主流的一部分,也改變主流。當1970與80年代,次文化的地下水脈正在各國奔流,台灣卻再一次次被打斷,只有片段的資訊。那些,都要等待解嚴(1987)之後,才能一口氣灌進下一代執著的台灣青年的耳朵和腦袋,然後交錯迸裂補完,長出新的樣子。
本書停在1980年代初期,「民歌」與「歪歌」,在各自積累下重新結合,成為了日後新的開端,像是作者說的「搖滾樂在台灣的部分正式告一段落,接下來,是台灣搖滾樂的故事」。不過,那「日後」並沒有隨著解嚴自然地來到。書中沒有進一步往下說的是,在1980年代之前,面對戒嚴體制,在夾縫中攜手打開微小空間的,新興的商業運作、媒體,以及文化論述、現代主義的悵然、社會運動的關懷,在1990年代新的天地裡,並不再是永遠的盟友。在中斷的時間裡,在沒有地下水的時間裡,更為悅耳的流行音樂已快速在台灣茁壯,音樂產業並沒有給予激進的、實驗的創作留下太多空間。在新聞局沒有了審查制度的時代,還有許多東西將繼續審查著人們的腦袋。
後來,那後來呢?
合上書,想著那個將要來到、也早已到來的時代,作者將尾聲交給羅大佑、丘丘合唱團與客語歌手吳盛智,我突然想起另一首歌,翻到前幾頁的高凌風,打開youtube,按下播放。
 大衛鮑伊Let's Dance專輯
大衛鮑伊Let's Dance專輯
1983年,高凌風翻唱了David Bowie剛發行的《Let's Dance》兩首歌。高並不知道Bowie在這張專輯裡做的事。Bowie用了節奏藍調的吉他,對抗舞曲的節拍,把兩者加在一起,在冰冷的拍子裡形成一種新的聲音。高則把吉他刪去,當作了流行的迪斯可,改寫成春去冬來戀愛惆悵的〈短髮的女孩〉。而在原曲〈China Girl〉裡,Bowie卻是這樣唱著藥物經驗(暱稱China White的芬太尼),嘲諷地唱著西方文化產業霸權的輸出:「小小的中國女孩/我會帶給你電視/我會帶給你藍色的眼睛/我會帶給你一個想要統治世界的男子。」
不過,與此同時,也在這首歌的最後,Bowie讓那女孩開口制止了主唱,「她說:噓...」。

那突然安靜的幾秒裡面,彷彿有什麼正在傳了過來。彷彿說著,在高凌風抽離脈絡的翻唱編曲下,在只是模仿卻不知來由的戲劇性唱腔裡,這個島嶼將在搖擺的節拍中,迎來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巨變,將帶著沒有準備好的自由,面對各種新的夾縫,再一次地,繼續開始自己的搖滾樂。
林易澄
嘉義人。歷史工作者。 曾為《破週報》、《放映週報》、《Gigs》、《號外》等刊物撰稿。
延伸閱讀
- 回不去了,那「黃昏的故鄉」:《歌唱台灣》與台語流行音樂史的世紀創傷
- 傷心有話的台語電影史:張亦絢讀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
- 臺語童星的逆襲!為何臺語片在我們的集體記憶完全消失?──專訪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
- 尋找歷史洪流中那些「被消失」的譯者們──專訪賴慈芸《翻譯偵探事務所》
- 【♫|影像留聲機】陳德政:一個更明亮的夏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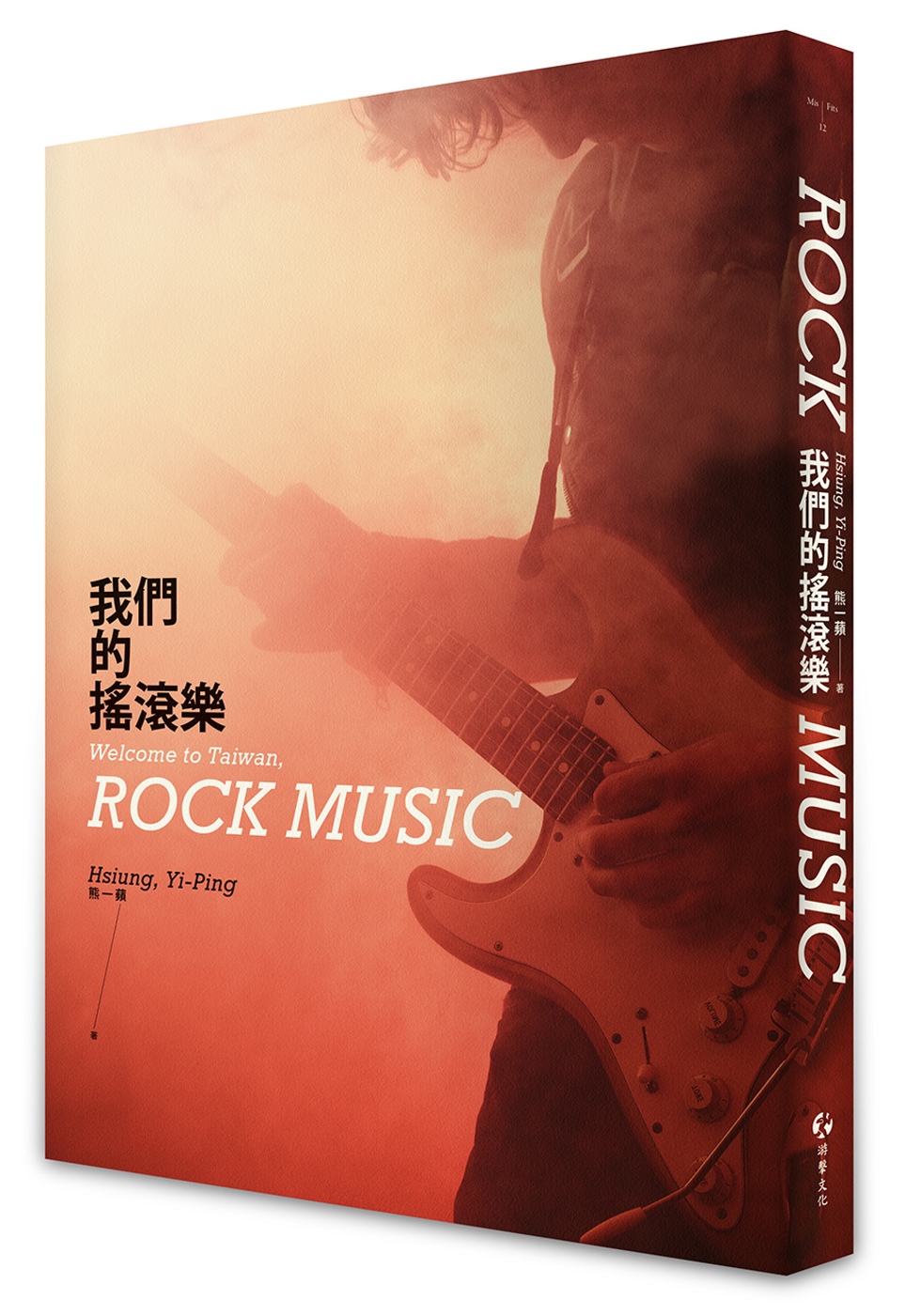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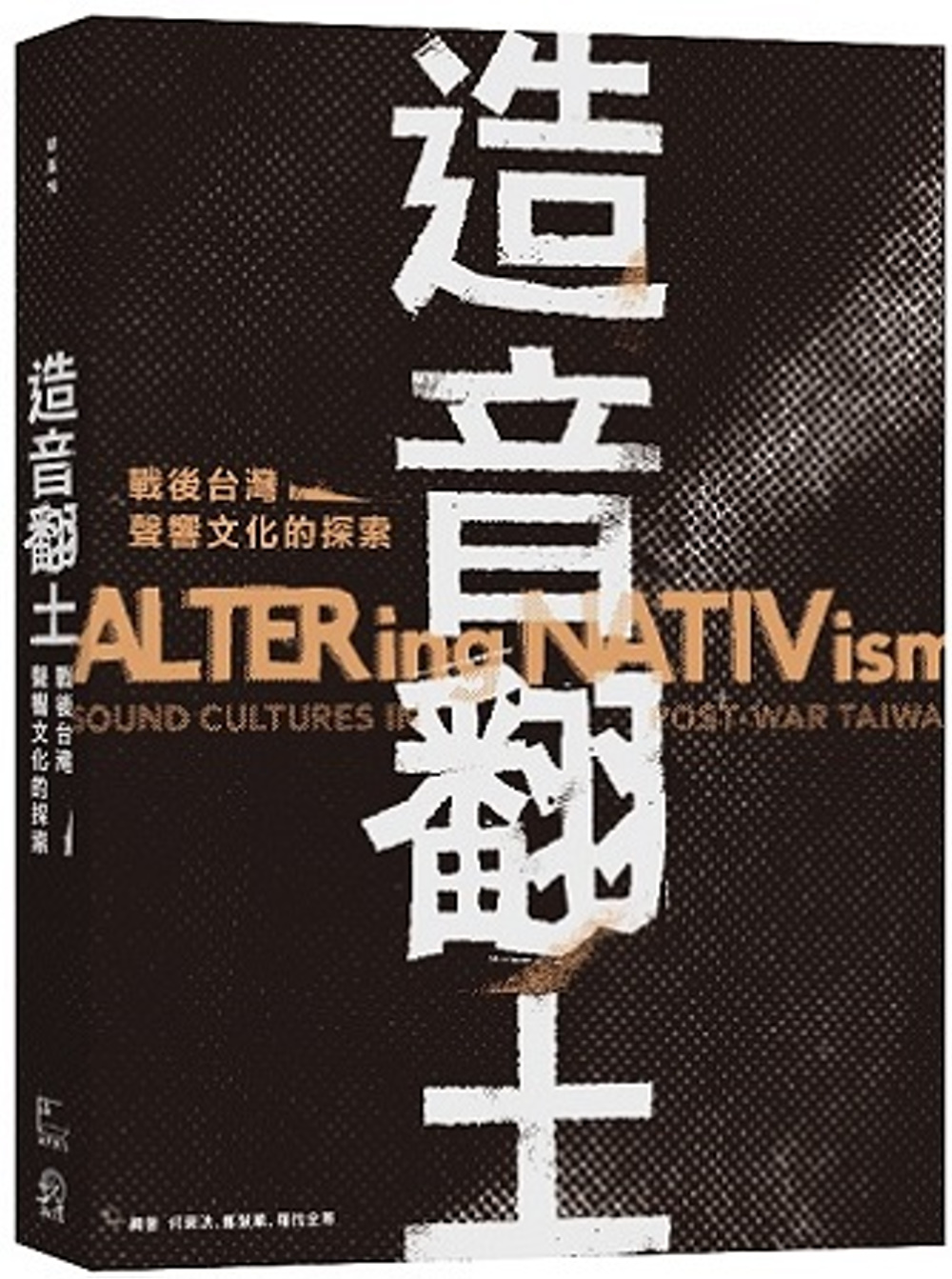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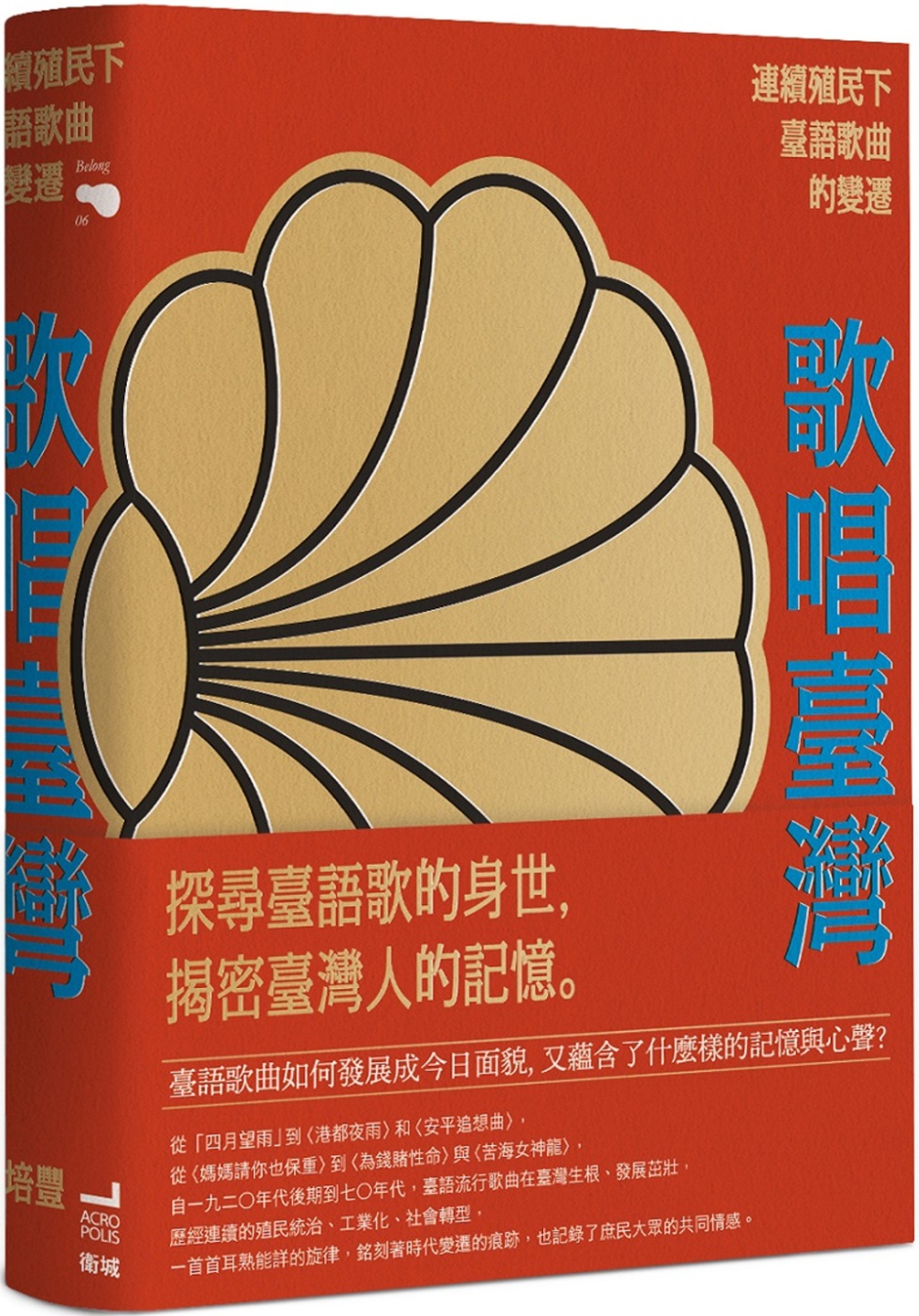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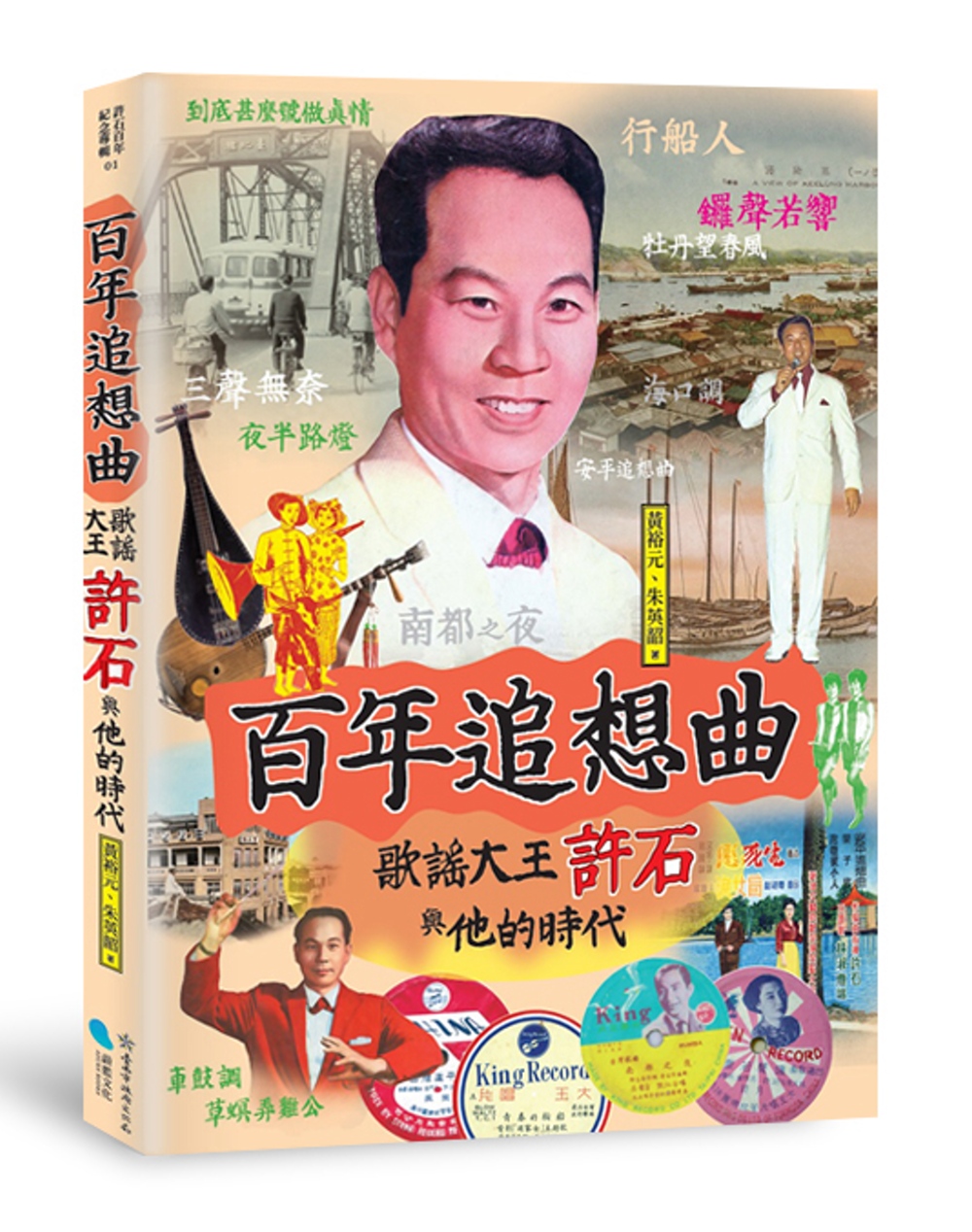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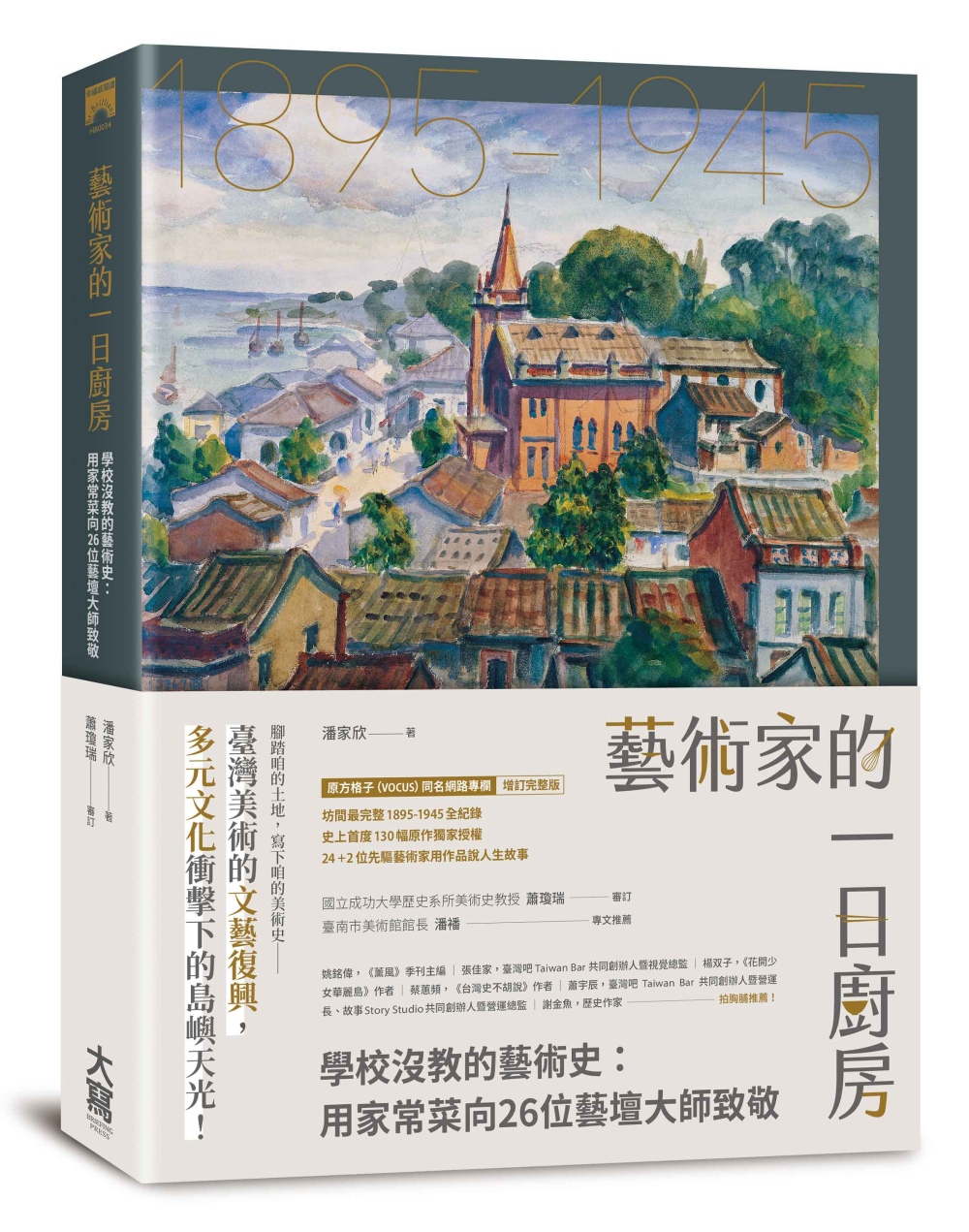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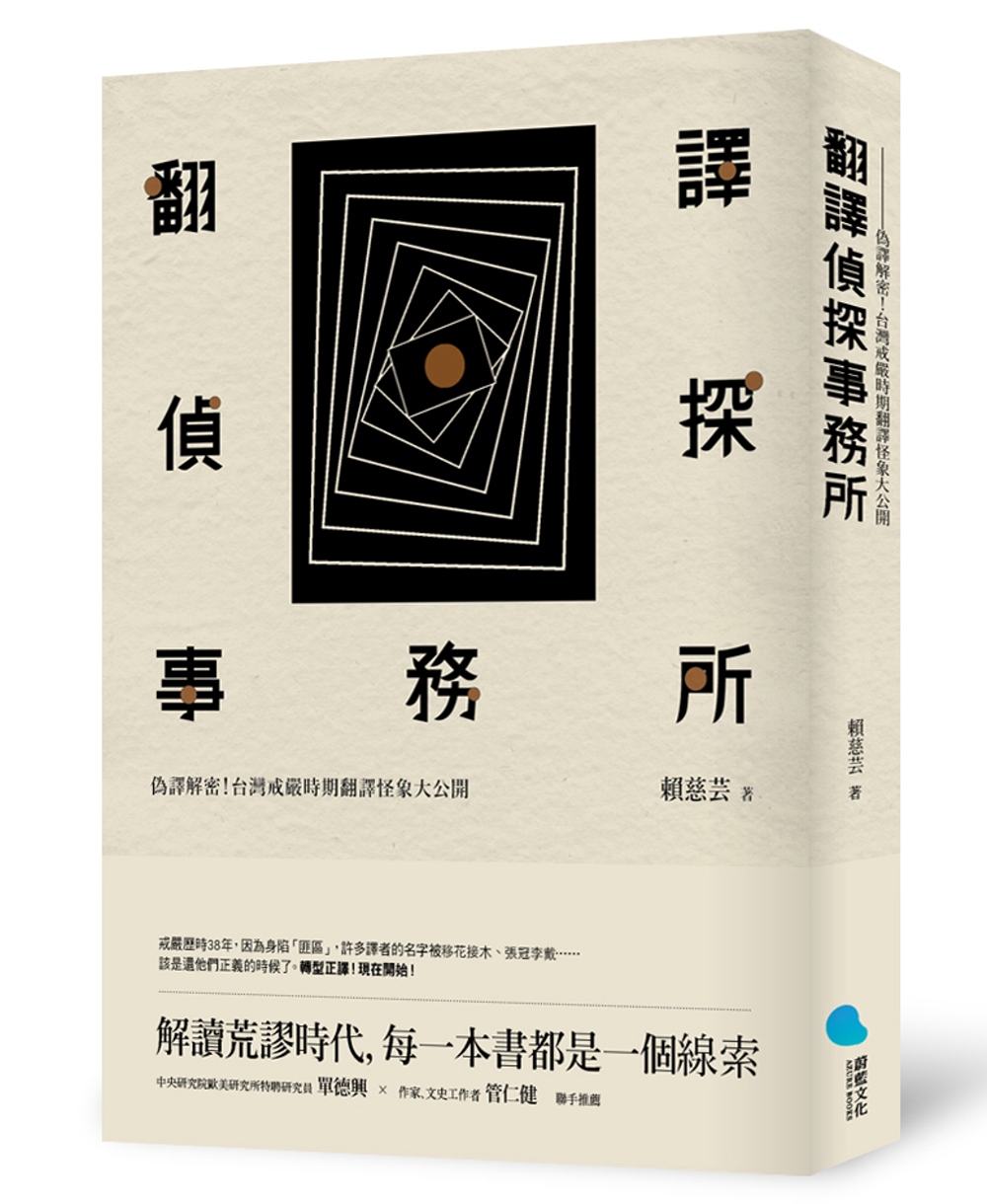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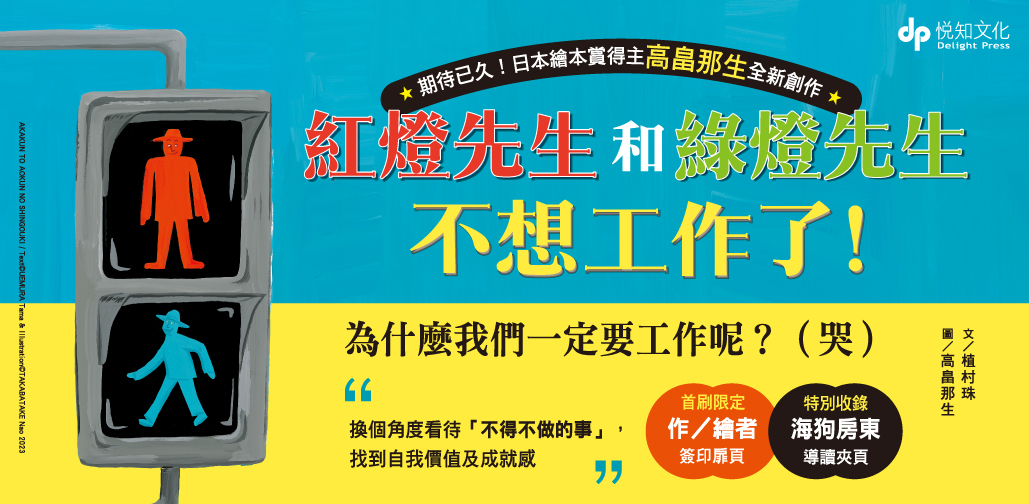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