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念國中的時候,向來勤儉持家、捨不得在任何休閒嗜好上花費的父親,竟然破天荒買了一套「陳芬蘭全集」。說來慚愧,自小講「國語」、聽小虎隊和張雨生長大的我,每次聽見錄音卡帶傳出陳芬蘭那曲調哀戚、情感憂悒的歌聲,不只是感覺極為陌生,多少還有「老爸就是沒讀書才只聽台語歌」的社會性自卑──然而,今日回想,爸爸五音不全地哼哼唱唱〈孤女的願望〉,恐怕那是從宜蘭離家多年的勞工階級,唯一能夠用來思念青春和故鄉的不成曲調。
讀了研究所以後,同溫層多半是個性乖張的文藝青年,我的音樂趣味也從國語流行被同儕「矯正」為台灣獨立音樂。也就在那幾年,我才有點驚訝的發現,那些每每使朋友們激昂不已的搖滾怒吼,比如董事長樂團〈新男性的復仇〉其實致敬的是寶島歌王文夏,或者濁水溪公社〈沾到黑油的肉鯽仔〉借用了布袋戲歌曲〈為錢賭生命〉金句──原來,自詡衝撞體制的現代搖滾,從沒有遺忘我們台灣人最熟悉的傳統小調。
對照我這樣一個中年男性在音樂品味上「認祖歸宗」的個人歷程,那麼,中研院學者陳培豐的新書《歌唱台灣:連續殖民下台語歌曲的變遷》,就不只是一本在眾聲喧嘩中爬梳半世紀台語流行歌曲的唱片博覽會,這本書談的,更是「台語歌曲」這種曼妙的聲音藝術,在經濟壓迫和殖民宰制之下妾身未明的社會位置。
陳培豐的學者生涯有些傳奇,他中年才留學日本,師事政治學大師若林正丈。但他年輕時在流行音樂界工作多年,不只寫詞作曲,甚至在1980年代發行過個人專輯。不過投身學術後,陳培豐主要研究領域是國家語言政策與台灣人身分認同,例如上一本著作《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但是這本新書《歌唱台灣》卻重拾人類文明中言不盡意的曲曲折折──喜愛音樂的人都知道,有些情懷和眷戀,文字語言其實沒有辦法真正傳達。
當然了,《歌唱台灣》首先仍是一本縱橫半世紀的台語流行音樂史。本書按照時序,介紹了1930年代開始萌芽的歌仔調愛情戀歌、1950年代聚焦於「港邊惜別」與「失落望鄉」的東洋風情演歌、然後是1970年代隨著史艷文藏鏡人一同驚動萬教,快速在新興電視媒體上竄紅的布袋戲歌曲。
然而,本書的精采之處卻遠遠超過一本單純的「流行音樂史」。
在膾炙人口的台語歌謠背後,日本總督府和國民黨政戰都曾經在「台灣人唱什麼歌」這件事情上暗暗角力;同時在二戰結束後經濟轉型和農業衰敗背景下,台語流行歌曲更幾乎等同於本省農村男女前往大都市辛苦打拚的勞工奮鬥史詩。
《歌唱台灣》一邊講述〈孤戀花〉、〈收酒矸〉等名曲的軼聞掌故,同時也破譯本土流行音樂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構成,可謂摸蜊仔兼洗褲:若真要解明「流行音樂的故事」就得並肩於我們島嶼曾經走過的蜿蜒長路。
儘管今日一般聽眾對台語流行樂的粗略印象,多半連結於日本演歌、善用轉音/顫音技巧的黏膩唱腔、訴說著底層庶民的悲歡合離等等。然而《歌唱台灣》告訴我們,歷史現場從來不是「本省人就是親日皇民」這種禁不起事實檢驗的想當然爾。
1930年代,隨著以留聲機為代表的所謂「聲音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台灣登陸,在當時為數不多的都市地區中,追求「摩登」聽覺體驗、開始收聽流行歌曲的弄潮男女們,仍然保留了純正的台灣品味。儘管需要借用日本唱片工業的技術與器材,但是台灣最早的「流行音樂產業」,其主流仍是漢詩傳統中的「閨怨」歌曲,充滿女性氣質的〈心酸酸〉、〈雙雁影〉、〈望春風〉等名作,在街頭巷尾傳唱一時。
在歌詞方面,這些作品內容多取自古典詩詞與歌仔戲曲;而在演唱方面,最早的台語流行脫胎自歌仔戲的顆粒狀唱腔。限於當時社會氣氛,好人家女兒並不會投身娛樂產業,多數流行歌手出身於養女、藝旦、伶人,這樣的性別與階層也讓她們沒有機會去日本留學接受西洋聲樂訓練──換句話說,一直到日本從台灣離開為止,台語流行歌曲幾乎沒有受到「殖民母國」的影響,依舊保持了古典漢文化本色。
儘管如此,為何在二戰結束後,「傳統的」台語歌曲卻沒有與「中國」流行歌曲有進一步融合呢?
因為早年「國語」流行歌起源於燈紅酒綠的上海與香江都會,那種旖旎富貴的情調,其實與戰後初期台灣人的兩種主要經驗格格不入:
第一、是讓所有島民大失所望的二二八悲劇、白色恐怖等政治災難;
第二、是倉促實施的「農地改革」,以及隨後犧牲農村社會安定來換取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
對於當時主要仍停留在農村轉型前夕狀態的多數本省住民來說,自身生命經驗和國民黨權貴偏愛的「海派歌曲」,實在沒有任何交集。
1950、1960年代,儘管那是台灣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但這時政府也刻意壓抑糧價、徵收多重稅賦、誘導農村人口外移,當時六成以上的農業人口必須承受的是,傳統農村面臨急速衰敗的嚴酷過程。這也是為什麼彼時大受歡迎的〈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望你早歸〉等經典歌曲,如此訴說自己與故土的距離:「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
事實上,這些台語名曲多數翻唱、改編自日本當時的「望鄉演歌」。這類演歌作品洋溢著「離鄉奮鬥」、「漂泊無依」的寫實感嘆,原本講的是日本鄉村青年遷移至東京大阪都會的種種愁思。然而這樣沉鬱飽滿的情感,卻對政治上疏離、居住上漂泊、經濟上承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台灣人來說,是比什麼都更加契合自身經驗的「聲音表情」。所以,今日台語流行歌曲在主題上偏愛「歹命人」、「![]() 迌人」,並嫻熟運用悲涼演歌唱腔,這些美學特徵都來自20世紀中期我們對於數種日本演歌傳統的「改造」──經過殖民50年都沒有接受「日本音樂」的台灣人,卻因為威權統治下的政經壓迫,而被一度拒絕的日本情調所深深打動。《歌唱台灣》將彼時這段複雜的文化變遷稱為:台語流行歌曲的「自我日本化」。
迌人」,並嫻熟運用悲涼演歌唱腔,這些美學特徵都來自20世紀中期我們對於數種日本演歌傳統的「改造」──經過殖民50年都沒有接受「日本音樂」的台灣人,卻因為威權統治下的政經壓迫,而被一度拒絕的日本情調所深深打動。《歌唱台灣》將彼時這段複雜的文化變遷稱為:台語流行歌曲的「自我日本化」。
如果是熟悉社會科學、文化研究的讀者,讀畢《歌唱台灣》大概還會聯想到,儘管當代歷史學家多半認為,所謂「國家文化」、「民族傳統」一般來說乃是現代民族國家有意識「發明」的人造產物,然而,《歌唱台灣》卻在台語歌曲的世紀風華中找到另一條解釋路徑──日治時代的普羅大眾,選擇了抗拒東洋風尚的「歌仔調」,然後又在威權統治年代,援用「演歌元素」來區隔於黨國主流文化、同時表達勞動和遷移的自身遭遇。或許可以說,這兩次「拒絕」都代表了台語的「流行歌曲系譜」其實與官方建構逆向而行,甚至自然而然從民間社會生成。這也說明了,為何「台灣的聲音記憶」如此獨特、既非中原也不是東洋的深層因素。
除此之外,《歌唱台灣》還深入剖析音樂史上的許多公案,包括〈補破網〉、〈思念故鄉〉等名曲遭到特務機構的介入修訂、許常惠的民歌採集運動對於日本音樂要素的刻意省略、〈苦海女神龍〉這類知名布袋戲角色主題曲如何透過身體殘缺與人生顛簸所營造的「邊緣形象」……百年台語歌曲所折射出的,不外乎草根底層的生涯百態。
姑且再回到我自己的生命經驗──儘管中學時少年無知,對於號稱「台灣美空雲雀」的陳芬蘭暗暗輕蔑,但隨著歲月流逝、人事漸長,如今我最喜歡的歌手,常駐於Youtube或Spotify播放列的「年度最愛歌手」,不知不覺已然變成了少年時完全沒有能力欣賞的蔡振南、陳明章。
「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蹽溪過嶺」,不知為何,我竟想起了謝銘祐的當代台語歌曲〈路〉。一邊讀著《歌唱台灣》,一邊按圖索驥在網路上尋找這些有些熟悉也不無陌生的「懷念台語老歌」的同時,真不免胸口鄉愁氾濫:原來呀,那種苦澀悲涼的況味,始終來自於命運多舛島嶼的百年滄桑。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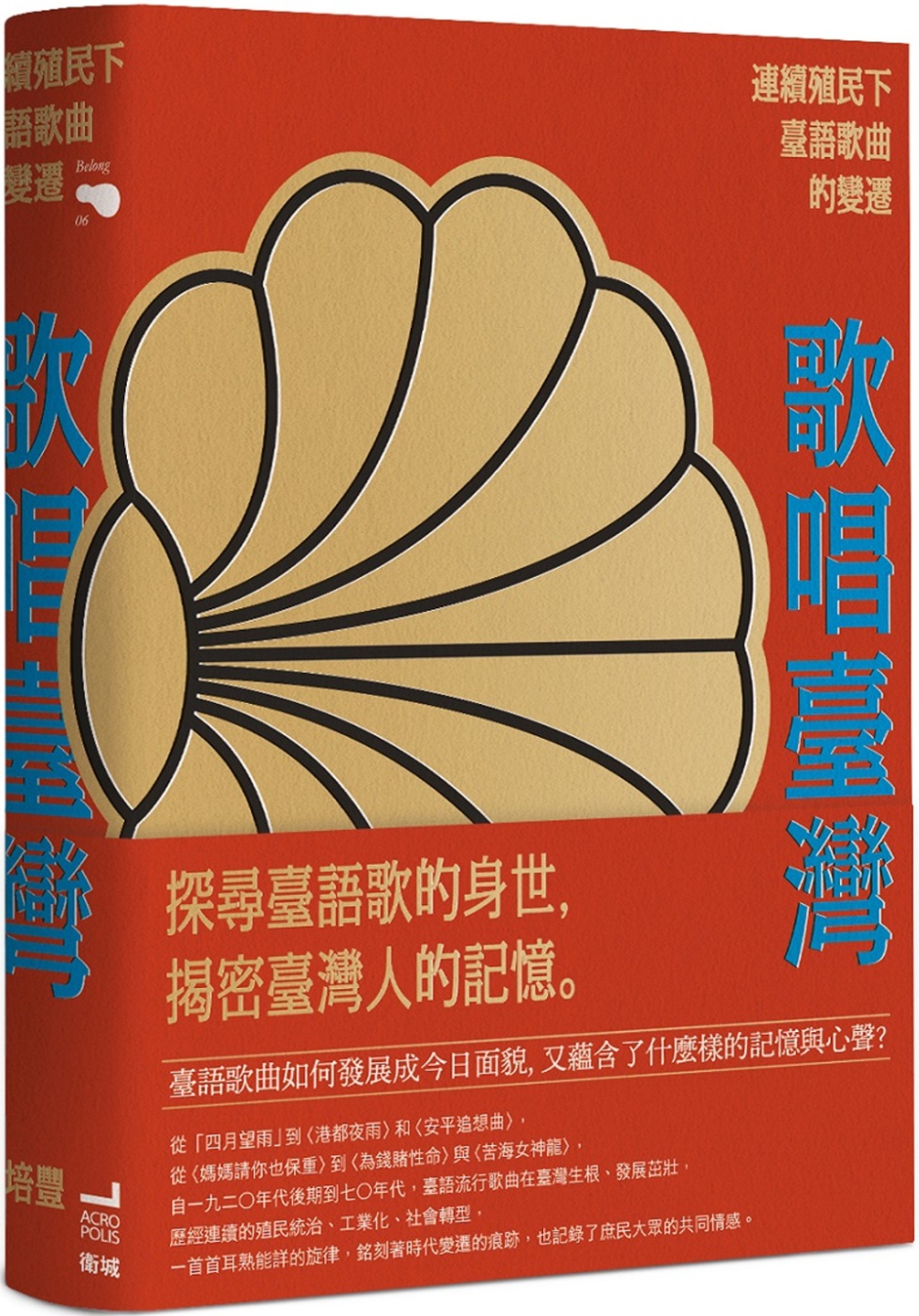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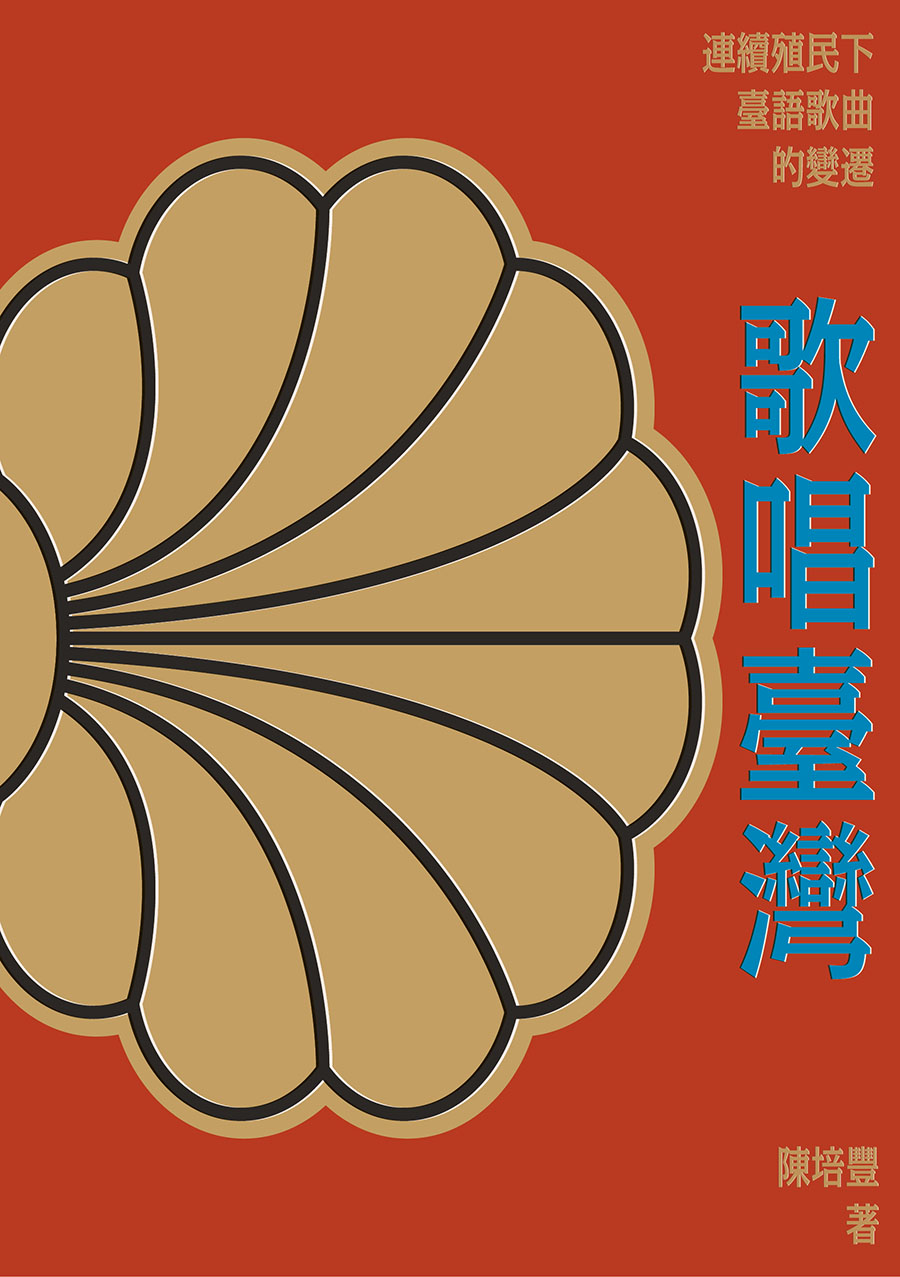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