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本詩集《灰矮星》就令人驚豔的年輕詩人柏森,以第二本詩集《原光》榮獲第十屆楊牧詩獎;不禁讓人好奇,柏森這樣一個靈動聰慧、敏銳早熟、優雅冷靜的創作者,能夠透過文字定義一切,解釋萬物,指出「生與聲」之所在的詩人,卻仍舊對這個世界感到疑惑、罣礙、掛懷,甚至,忍不住提出的問句,會是什麼?
《原光》一書中,如何問問題,問了哪些問題,就成了我在黑暗中,摸索這本詩集的指引。
序詩中,「並延遲著,攸關消亡與遺忘,當我們睡去/是不是僅為被喚醒?」開篇這首,寫〈墓碑前,小號的吹奏〉旋即出現一個問題,嘗試談論人的狀態之所以存在,究竟哪一步更接近目的?
輯一名為「淨沐之水」。在第一首〈散策〉裡,詩人反著問「怎麼暫留,世界的真實?」在這個問句出現的前一段末尾,即便提到「沒有穿透」,並不一定就能肯定:假若充分穿透,將保證充分暫留,面對世界的真實,依然要打上一個問號。
「馬兒不在草原,你可嘗凝視
在幽靜之時
馬兒也回到草原」——〈談及消逝〉p.61
〈野火〉中,詩人問:「分神了什麼?」且後續被問道:「什麼是模糊?」看似丟給「命運」或交付「集體」去回答的字裡行間,含蓄且壓抑地,藏不住詩人關心的社會時事,乃至過往歷史。
〈鄉愁〉裡,詩人想:「這/就是此外了吧?」同時間,彷彿塔可夫斯基也問道:「看到那雪了呢?」詩人又問:「去北方?」然而,北方有諸多意象,譬如詩人寫「北方如我」。
「遠離冥思卻所在肉身
於是他想,北方以外的雪
又如何生長」——〈鄉愁〉p.85
〈日落大道〉中,詩人寫「在盲目時代中/永恆要比一隻蜉蝣虛無?炙熱的晚霞」,近乎邀請讀者一起點開David Bowei的音樂,進入〈Heroes〉,保持面對提問的態度。
「夕霧停留在你眼裏
該談論嗎
這逐漸暖熱的」——〈小華爾滋〉行板3/4 p.101
輯二名為唸禱。有些問句,即便明顯沒有要求答案,只是懸念地存在著,或純粹在問句形成的瞬間,同時也成為了毫無疑問的答案。例如〈平行故事〉裡的結尾:「飽滿的城市啊,也在失眠的光線裡逐漸起霧了嗎。」詩人給出的是明確的句號,比起認真的提問,更接近一種嘆息般的語氣。
令人著迷的尤其是這首〈視線盲區〉,充分展演詩人俏皮且熟稔於哲思般的文字遊戲:「你再問一次自己,你喜歡你的左邊/也剛好是他的左邊嗎?」
「以素簡的方式釀作今日,你問我:
什麼還是時間?並蜷起空白的順時針。」——〈和可衡量與不可衡量的摩挲時態〉p.114
書中每一輯的最後,都會有一張圖像與簡短的字句,彷彿可以看成是濃縮在這輯裡,閱讀過程中,對於升起的任何疑問,作為參考答案,或註解之感。
輯三名為人子安躺於床。比起詩人的主動探問,有不少時候,詩人紀錄自身被問的問題,同讀者一起望向那些問句,彷彿落地前的靜止瞬間。例如〈談論空白時所忽略的移動性〉中,詩人寫「你問:/還有什麼是正常的?」或在〈吃茶〉裡,詩人寫「他問起/要不要泡茶了,又一次/為我沏下日子」。
輯三最特別的是,在整輯的結尾,增添一份備忘〈詩歌盡頭〉,可視為詩人之所以寫詩的註腳。
「然而試驗意志不也是試驗
我們的真實性?敢於生活的信念
為了認識自己」——〈詩歌盡頭〉p.158-159
輯四名為使徒的琴座。透過幾位重要影響詩人養成的作曲家與演奏家,難得看見詩人滿溢的情感,例如〈夜曲〉,詩人寫:「親愛的布莉姬,夜為何如此難眠」,或「要不是記得你的名/我們哪裡有愛情」。
「然後他問起:『你是熱愛生活
用什麼樣的味蕾
去理解它們的顏色?』」——〈聯覺練習〉p.171
若以琴弦來理解這本詩集的精緻與輕巧,詩人給出的纖細感,連字裡行間的空氣不震動時,都是一種極致震動的狀態。曾近距離聽過柏森彈琴演奏的我,且在詩中感受這位詩人的心弦,比起鋼弦,更接近絲弦。譬若詩人寫:「我可否再擁有仁慈?當雨濺過花瓣,/童年尚未離去」
除了提問,詩人也不乏在拋出問題的同時,立刻回以解答,如〈印象〉中,詩人問:「浪漫,何以崇高?因為有了愛的能力」
最後一輯,名為原光的輯五,亦是與詩集《原光》同名。
「已是夜晚
深邃將我們包圍,你可聽見?
細碎言談描述著」——〈復活〉p.230
當我一路尋索著詩集中的問句,像暗夜中指路的小石子,才在詩人的後記中,確認這僅是其中一種讀法。伴隨讀詩時播放著拉赫曼尼諾夫,一邊想著,往後必然會再找時間聽馬勒,重讀一次,相當於詩人透過曲目,提供無數條重返文字世界的路徑,並因此立體文字的感受性。
然而,如同詩人提到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探討「什麼使我們思考」,也是我讀這本詩集時,不一定跟著詩人思考其疑惑的問句,而是因自身從文字中接收的刺激,長出自己的其他疑問。值得我們一起在面對時間之時,保持各自探問的姿態,也許,光是思考,就足以使人驚奇。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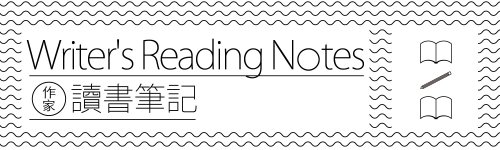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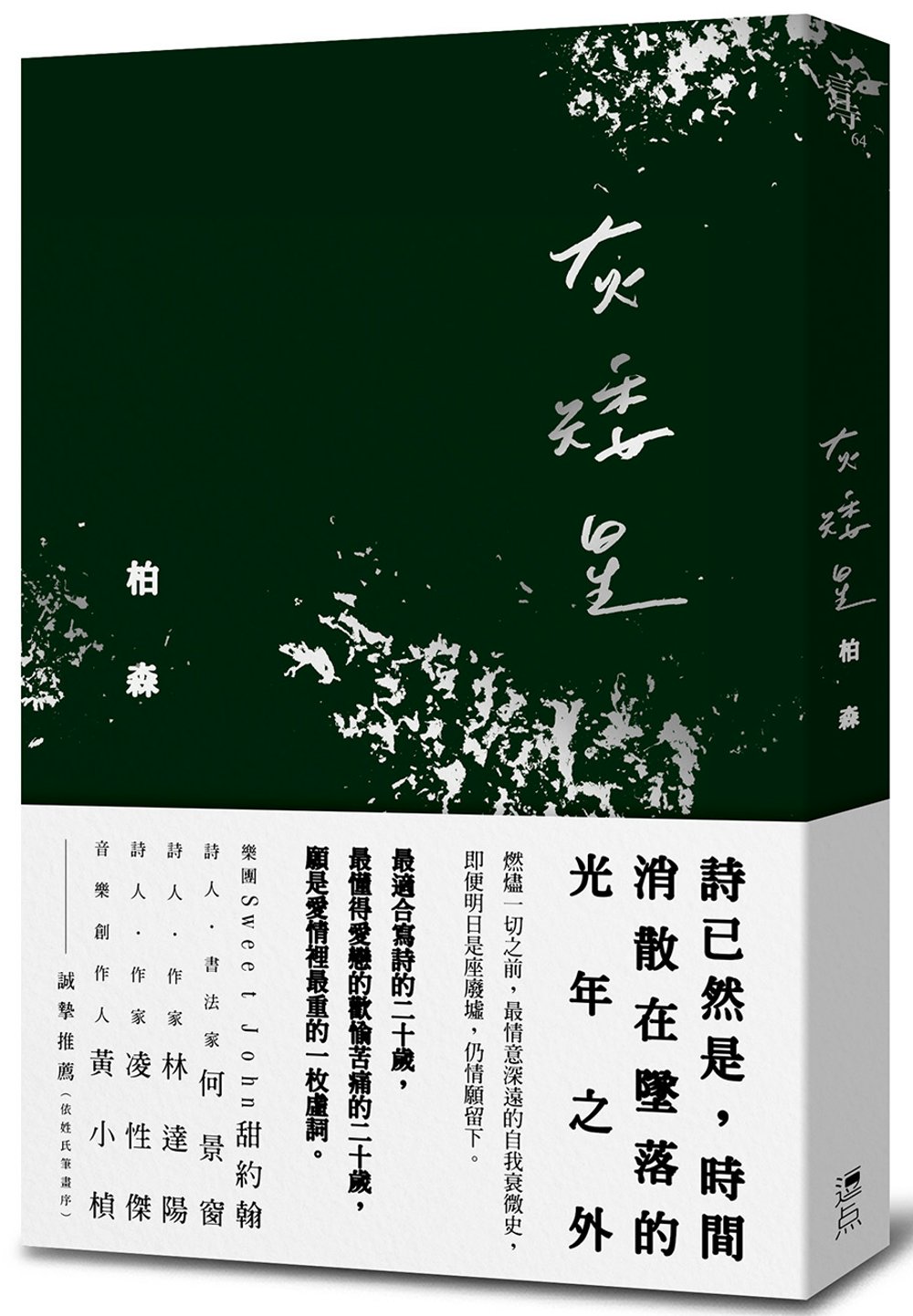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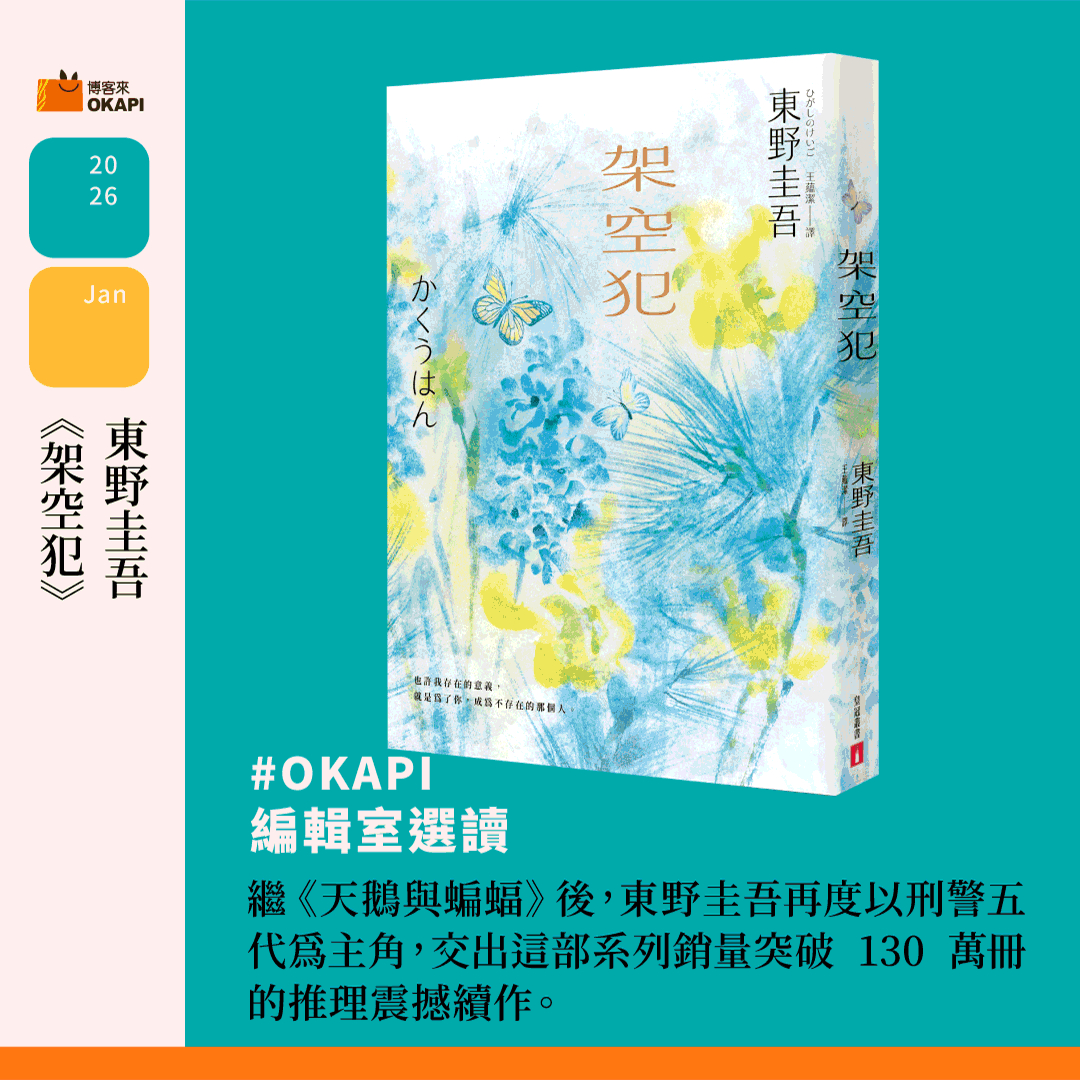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