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當代重要作家,電影導演,編劇艾希克.維雅(1968-)(圖片來源 / wiki)
艾希克.維雅(Éric Vuillard)在2017年以《2月20的祕密會議》獲得法國龔固爾獎之前,每本作品的發表,皆揭露歷史不為人知的片段,且重整對過去的認知,大受好評外,也屢屢獲獎。他在少年時代便隨著家庭旅居各地,加上社會學的訓練,對於所有的權力與詮釋語言(法西斯、殖民、資本主義)保持警覺性。
在他身上看得到過往如雨果、左拉等偉大作家透過寫作控訴社會不公的身影。然而維雅對於歷史的挖掘不僅深入,對於敘事的效果以及真理遊戲亦有所警覺。他專注的「敘事(récit)」一方面承接西方傳統,一方面另闢蹊徑,以獨特的材料與精密控制的敘述手法,創造出特殊的文學語言,除了令讀者震撼,同時令人不得不去面對歷史的陰暗面。
本回的遠距離筆談,維雅不僅深入談論他的文學養分與養成、他對文學與作家的定義及任務承擔,也充分展現其文學與歷史涉獵的廣度與犀利。更重要的,是他選擇「非虛構敘事」的文學理由。
Q:您青少年的時候,便旅行許多地方(西班牙、葡萄牙、非洲等)。能談談少年經歷對於您文學上的養分嗎?
A:我的口袋裡總是有一本華特.惠特曼的《草葉集》。適合旅行時隨身攜帶。惠特曼貼近真實的生活而寫。他本人對於現實充滿熱情的眼光和看法激發了他的詩意。讀著他的文字,語言就不再專屬於教師和其他握有語言詮釋權的人,而是屬於所有人。然後就像大多數青少年一樣,我嚮往他那毫不屈從的人生。
Q:您曾讀過哲學與人類學,且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指導下獲得碩士學位。這些社會與人文科學的訓練,對您的寫作有何影響?
A:在《2月20的祕密會議》最後的其中一章,我引用了一則奧地利報紙刊登的訃告,這則訃告讓讀者知道有4起自殺事件,那些都是剛結束自己生命的猶太人。時間是1938年3月12日,德奧合併的同一天,奧地利正要併入納粹德國。這4起自殺事件的訃告,都以一貫的說法做結論:「動機不明」。可是1938年3月12日,一個猶太人竟在維也納自殺,我們應該要去了解其中的動機。
我立刻想到涂爾幹那本著名的《自殺論》,這本社會學經典是關於自殺的社會學研究。涂爾幹選擇研究這個人們過分習慣將自殺歸結為個體、私人動機的現象。他結合統計學,奠定一種研究類型並證明:自殺也是一個可詳加分析的社會現象。因此,這4起自殺,這些訃告所公開的事件,就不能當作「個體的悲劇」來看待,導致家庭主婦海倫.庫訥(Hélène Kuhner)或作家卡爾.施萊辛格(Karl Schlesinger)自殺的並非內心不安,而是納粹進入奧地利的事實。這些自殺事件不是因為個人的危機,而是因為他人的罪行。
為了更理解這項罪行,我就需要把它寫出來。我必須說故事。為了瞭解它,就必須花幾個小時成為海倫.庫訥以及卡爾.施萊辛格。某種意義上而言,這項能力是很文學的。老舍的《駱駝祥子》裡,敘述者非常忠實地呈現祥子。在此之前,我們從未感覺自己是這樣地貼近這個拉人力車、工作繁重、希望落空、日常生活艱苦的竊賊。這個徹底的觀察能讓人有深刻的認識,並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去比較,換句話說,把一種真正的關聯和普世共相等同看待。頓時間,我們都是拉車伕祥子,花幾個小時變成他人能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了確實掌握1920年代中國的社會境況,就必須花兩百頁的文字化為一個流徙的農民、一個脆弱的工人。藉由文學所產生的這個身分也算一種主體認識的形式。
Q:您是如何、又為何成為一名作家呢?
A:文學裡存在一種了解人情世故的許諾,揭示世界的真相。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敏於察覺這份許諾。
Q:那麼,您如何找到並發展出自己的風格?您覺得自己與同代的作家有哪些不同呢?以及,您喜歡哪些作家?
A:談自己、談個人的風格總是令人棘手。一般而言,書寫的方式有兩種、這兩種隱含的概念分別占據著文學史。實際上,有兩種寫小說和寫故事的方式。我們可以像阿嘉莎.克莉絲蒂那樣寫小說。在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裡,13名角色登上一節火車車廂,作者說,這節車廂就是所謂世界的縮影。但那卻是個沒有藍領工人、沒有白領上班族、沒有流浪漢,一個只有伯爵夫人和帽子箱的世界,因為那是一個封閉且透過文學淨化的世界。一旦案件解決,也就不再有任何不快、任何反常。沒有留下待解的謎團。世界收進西裝口袋巾內。東方快車又能夠再次啟程。
相反地,一股產生自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那樣一本小說的力量,就在於即便把書本闔上,故事並沒有因此結束。尚萬強徹底死了,珂賽特結了婚、擺脫困境,但是小說深刻講述的故事並沒有結束,社會不平等的故事並沒有結束。這點不僅在於敘事,同樣也觸及風格、書寫方式。我們不用同一種方式書寫,寫一本不可能有結局的書,寫一本將會在以後,具體來說,由所有人類共同完成的書。我們永遠沒有恰當的語言去談世界的苦難。風格就是,在語言中,一種把「談論人類具體苦難的不可能性」和「讓尚未實現之許諾產生廣泛回響的可能性」連結起來的主觀方式。這就是我試圖要做的事。
Q:您的作品經常描寫確切的日期:像是7月14日、1885年(《剛果》)、1933年2月20日(《2月20的祕密會議》),或是1524年(去年的新作《窮人之戰》〔La Guerre des pauvres〕)。這些日期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A:日期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做之決策、應負之責任而留下的痕跡。它是事件的痕跡。
1933年2月20日標誌了威瑪共和的消亡。那是史無前例的災難開端。那也是暗藏祕密的日子,有關一場在日後紐倫堡審判的法官們認定為陰謀策畫的祕密會議,畢竟,當時會議在舉行之前沒有人知曉。
相反地,占領巴士底監獄卻是在光天化日下發生的集體事件,一場人民暴動。7月14日是我們法國其中一個誕生日。巴黎城區的市民們形成政治主體,這個主體透過巴士底監獄的攻占而顯現,那是我們所謂的人民。
而在這兩個情況裡,都關乎一則事件,關乎某種脫離常規的事物,即便涉及一個群體,歸根究底都屬於個人的決斷。我覺得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一小部分的人能夠決定絕大多數人的命運,強調他們的個人責任絕非毫無意義。
Q:您如何定義自己的作品?您完成一種特殊的文類,例如《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我注意到它融合了散文、歷史書寫與隨筆。您在書裡頭宣稱「決定不使用虛構」,這本書仍然獲得極高的評價,得了過往幾乎都是虛構小說囊括的龔固爾獎。您是如何想的呢?
A:《2月20的祕密會議》不是一本虛構小說,它是一則歷史敘事(récit)。對話都來自真實人物的記憶,景物描述試圖忠於原址。沒有任何杜撰的曲折劇情,沒有任何憑空想像的內省。在一個全球社會不平等日趨惡化、自由不斷更加縮限的時代,我相信,沒有哪個人比起那些實際掌權統治的人物更令人憂心、沒有一種人格比起那些真正的受害者更感人、沒有什麼曲折情節比起真實的故事更讓人激動。
Q:您的書通常以歷史為主題。對您來說,假如作家與歷史學家書寫同樣的主題,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A:世上沒有未經編排的故事,也沒有不需記載的科學。寫作的藝術,風格其自身就是對照類比的藝術,知識就像小說的元素般,需要加以安排陳設。就這方面來說,歷史和文學是非常相似的,因為最終所有的真相都與事實的安排呈現有關。一切藝術和科學自始至終都是一種摘要、一種統合。
這就是為什麼文學不停努力擺脫那些抽象和人工的形式,我們尋找最能喚起回憶、以及最能還原真實的方式。在魯迅的《阿Q正傳》裡,敘事者從表明想為他的人物(這個卑微人民的典型代表)立傳所遭遇的困難開始講起,以諷刺的方式詳細檢視自傳體裁的各種不同變形。於是魯迅帶著幽默貶損自己將要安排故事的方式,以便喚起受文學所忽略的人民樣貌。那一直是在寫作中,關乎我們世界的定義:誰比較重要而誰又次之?誰支配我們而誰又解放我們?
Q:對您來說,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為何?
A:當黃春明開始寫關於台灣和台灣人的小說,他採取寫實主義的立場,其小說源自他所生活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小說讓我們感興趣、讓我們感動。那是許多作家的名字讓人聯想起一起事件、一個案件的理由,而不只是想到一個寫作的人。維克多.雨果,讓人想到流亡生活、反對政變奪權的共和國。托爾斯泰,社會平等、正義、反對舊制度。老舍,反對世襲制度、人民的真實生活。
他們的名字都同時代表一個獨特的主體、一件作品,但他們也都倚靠著一個群體。才沒有什麼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更沒有什麼作家與其餘所有人的分別。文學是一種集體行動,它無法自外於集體生活的變化興衰。
Q:您對台灣的認識為何?對於台灣的文學有怎樣的想法嗎?
A:蘋果的營收達到2560億美元,而台灣的國內生產所得是6000億美元。台灣並非像開曼群島一樣是有名無實的政府,島上有2300萬居民;GDP並不是台灣流動的資金收入,它是一年之中所有台灣人主動貢獻的勞動成果。這點對於世界上大部分GDP剛好相近於那些最龐大企業之營收的國家來說,也是如此。這樣的資源分配令人擔憂,而且這不是小說的想像,這是事實。工業界、金融界裡存在如此普遍的不對等現象,各國人民卻只能破壞民主程序,摧毀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躲在虛構想像中的文學完全是不切實際的。
Q:最後,能否跟我們透露關於下一本新書的事?
A:我在寫一本關於法國殖民時期越南的書,由環繞著許多片段、在各種不同階層發生的故事所構成。我在書中講述強迫種植橡膠樹的苦力勞動,然後是米其林、沃爾姆銀行和一間礦業公司的董事會會談,以及一場國會會議。在這些段落裡,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同樣的角色、同一名國會議員出席數個董事會,我們會感受到私人利益直接左右著國會裡的討論。很遺憾地,這個慣例並不僅屬於過去,而是仍存於現在。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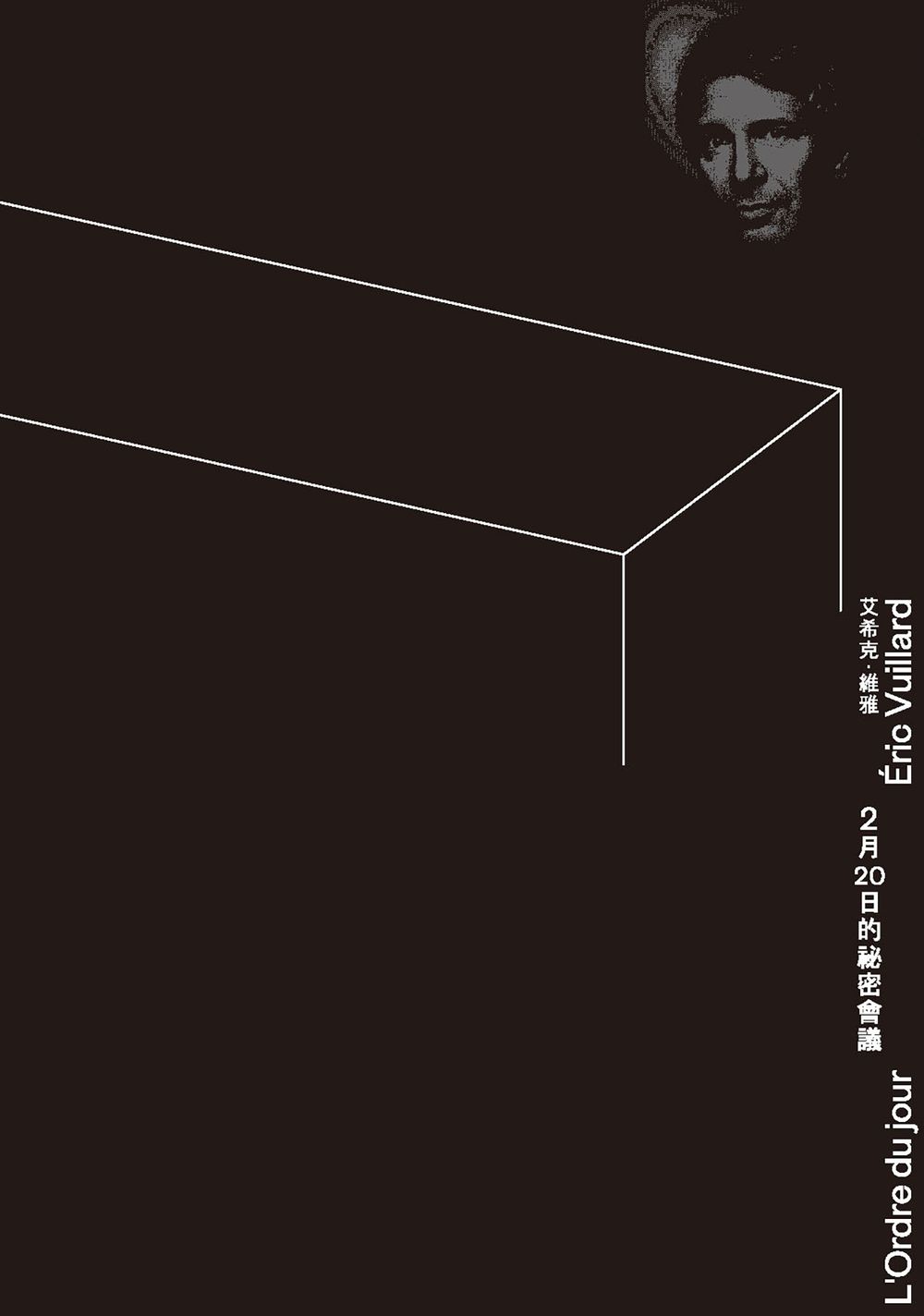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