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電影散場後,它會在你的記憶裡繼續演下去。
有時只是一幕景色、有時是個角色的身影。
看似人走茶涼的一幕,卻讓你也活了進去的燈火未滅、溫度仍在,角色隨時可以回來,你總感到似曾相識。
如《新天堂樂園》膠捲中的一格,記錄了太多意在言外。
為什麼?因為它照亮了你人生中的一瞬之光,相信它是永恆,而你的心仍有星火不滅。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在「果陀將來」的傳說已在隊伍中失靈後,後面世代的人開始起身離開,人們開始在失控的動物園秩序中,去找一個像《大象席地而坐》中「大象」相對真實的存在,不管牠是否存在,至少自己靠近了自我的招喚,而非已經斷訊的「果陀」。
在「果陀將來」的傳說已在隊伍中失靈後,後面世代的人開始起身離開,人們開始在失控的動物園秩序中,去找一個像《大象席地而坐》中「大象」相對真實的存在,不管牠是否存在,至少自己靠近了自我的招喚,而非已經斷訊的「果陀」。
世代和諧相處或許是該有的事,但在時代的前方,無論哪一代,你終要獨自面對自己的斷崖。尤其是活在他人價值中,最終仍要面臨那時代濃霧中的絮語散去。
這部電影看似在講一個三線小城會發生的故事。主角們分別是沒有財力可養老的初老人,還無法飛就被打擊的雛鳥年輕人,還有活得莫名所以的中年人。他們彼此熟也不熟地都在一個人生的關卡處,且看似無解地決定當下「出發」。
他們看似在一個世界盡頭之處,不是地圖上的盡頭,而是集體沒有出口的狀態。路都是通的,但看不清楚盡頭,我們或許跟《大象席地而坐》劇情一樣,幾代人都曾坐在同一個車廂裡,四周是忽明忽滅,但面對的盡頭是不一樣的。
而也如電影後半,以俯角來看,他們這群人總在城中無目的的亂竄,將小城走成一個籠子。以平視角來看,他們最後能否去哪裡也不是重點,只是人活著必須往前走,那可能只是一個宣示性的行為,即便時間軸拉遠來看,自己也可能是原地打轉,那都是遙遠的後話,但當下必須前方有路。
這讓人想起《四百擊》裡最後一幕,天高地闊的無形牢籠,由海岸線來代替,小男孩可以找到出口嗎?對照扎維耶多藍執導的《親愛媽咪》後半一幕小男孩轉身往醫院走廊盡頭飛奔,看似是有限的屋體,他決心跑出一種「無限的寬廣」,都在昭告一種生命態度。自由相關於他人時不太可能,只有對於自我而言,那可以是種追求,人的腦子可以被拘束,只有心會在體內亂竄與振翅著,像生命放棄前不斷的絮語。
也因此,希區考克的《鳥》訴諸的心靈恐懼,是主角們無法面對家庭溝通問題而坐立難安,那累積在電線杆上的鳥群愈來愈多,進而被「失序」所淹沒。那是一種心靈的混亂,打破工整社區的被淹沒,每個過度渴望秩序的人,內心都有骨牌一推就倒的恐懼想像。
 (左)《四百擊》由海岸線代替天高地闊的無形牢籠,小男孩可以找到出口嗎?/(右)希區考克的《鳥》訴諸的心靈恐懼,是主角們無法面對家庭溝通問題而坐立難安。
(左)《四百擊》由海岸線代替天高地闊的無形牢籠,小男孩可以找到出口嗎?/(右)希區考克的《鳥》訴諸的心靈恐懼,是主角們無法面對家庭溝通問題而坐立難安。
這三部電影正好反映了三個世代不同的追求。《鳥》是一種以財富堆積出來的「安全」,鳥群總在髮型工整的人頭上盤旋,像是想像著高頻的吶喊,預告渴望秩序的人本身隱藏的歇斯底里。而描述下一代的《四百擊》與《親愛媽咪》在沒有階級保障下,秩序是不存在的,殘酷真相是淹過來的,他們潛意識就想逃出這立基於恐懼的「城堡」(卡夫卡筆下的恐懼迷宮),每一世代因為優劣勢不同,「逃生口」原本就不同。
而《大象席地而坐》最後一幕,則是回應了以上這些名片的心靈風景。三代下車後仍離大象所在地遠得很,都在看不清前方公路的「middle of nowhere」,卻都聽到大象的叫聲,距離遠到不可能聽到,只可能是自己內心希望的叫聲,一頭平常不會出聲的大象,如生命沉睡中的叫喚,因其飄渺所以如在「密室」迴盪那般真切。

 《大象席地而坐》最後一幕,三代下車後仍離大象所在地遠得很,卻都聽到大象的叫聲。
《大象席地而坐》最後一幕,三代下車後仍離大象所在地遠得很,卻都聽到大象的叫聲。
這裡的「大象」可以與《等待果陀》中的「果陀」世代對話,人們排了又排,無論等了幾代,都在等那個「應許」,「果陀」可以是經濟的保障、或是一個國家的國名、或是群體共同的信仰,但因為前後像隔水傳話,沒人知道那「果陀」具體又該是什麼,連前面是什麼人答應你有「果陀」的都不知道。於是有一天當有人告訴你「果陀」不來了,「果陀」不存在時,後面的人都失控與暴怒,這時只要有人再把「果陀」不論死活拿來再講就有用,因為人可以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麼,但「等待」不能落空。
等太久了,「果陀」是什麼變得更模糊,重點是它必須在來的路上,這是老一代如今這樣失落的原因,不只是因為被弒父權,而是有人告訴他們白等了。
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則劃下一個斷代史,故事中的人太邊緣,愈來愈多人是沒有「果陀」可以等的,有一票人是沒人稀罕騙他們有「果陀」了,因他們如《小偷家族》被打出階級想像之外。他們必須有「起身」的覺悟,或是像戲中「大象」以極不合理的坐姿不服從。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大象」跟「果陀」都是具象也是抽象的,一是牠的存在是口傳的,戲中誰也沒看見過這頭動物園的大象,二是那裡的氣候根本不適合那頭大象,三是牠根本不用現身,牠的具象不是重點,而是牠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承受那樣重量的席地而坐。「牠」的消極是積極的,也近乎是一種抒情的存在。
一隻不可能存在在那裡的動物,以不可能的方式為人們提供另一種生存的想像,人們想起身找牠,想找到如此積極的消極,找到如此無聲的巨大存在,以一個活生生的動物來對照人才是活在失控的動物園秩序裡。

人們近來常說世代鴻溝與撕裂,其實無異於一群人原本都在等待果陀,後來有人發現這時代的「果陀」已被改寫,前方的等待只是等待的本身,於是後面的人陸續起身離開了。前方的人因此非常生氣,因以前他們聽到的也是語焉不詳的傳話而已。
人們開始在失控的秩序(動物園秩序)中,去找一個相對真實的存在,不管牠是否存在,至少自己靠近了自我的招喚。那個午夜,那台夜間巴士,那群下車的老中少,都在四處是路也都不是的地方,聽到了自己心頭的大象嘶鳴。那一聲,是自己長久沒聽太過陌生的心底聲音,而不是來自前方果陀的傳說。如今的老中青三代就在這樣的路口,面對「果陀」的歸零,「大象」得自救的現實。

《大象席地而坐》由已故導演胡波執導的唯一一部長篇電影作品,由章宇、彭昱暢、王玉雯、李從喜等主演,於2018年2月16日在德國柏林電影節首映,同年11月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故事描述四個無名小卒,坐長途巴士,為去一頭坐在地上不動的大象。電影中的一段:「你知道滿洲里嗎?滿洲里的動物園裡有一頭大象,牠他媽的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牠,也可能牠就喜歡坐在那,然後所有人就跑過去,抱著欄杆看,但有人扔什麼吃的過去,牠也不理。」這段是帶出故事的引子。此片原著小說《大裂》亦獲得高度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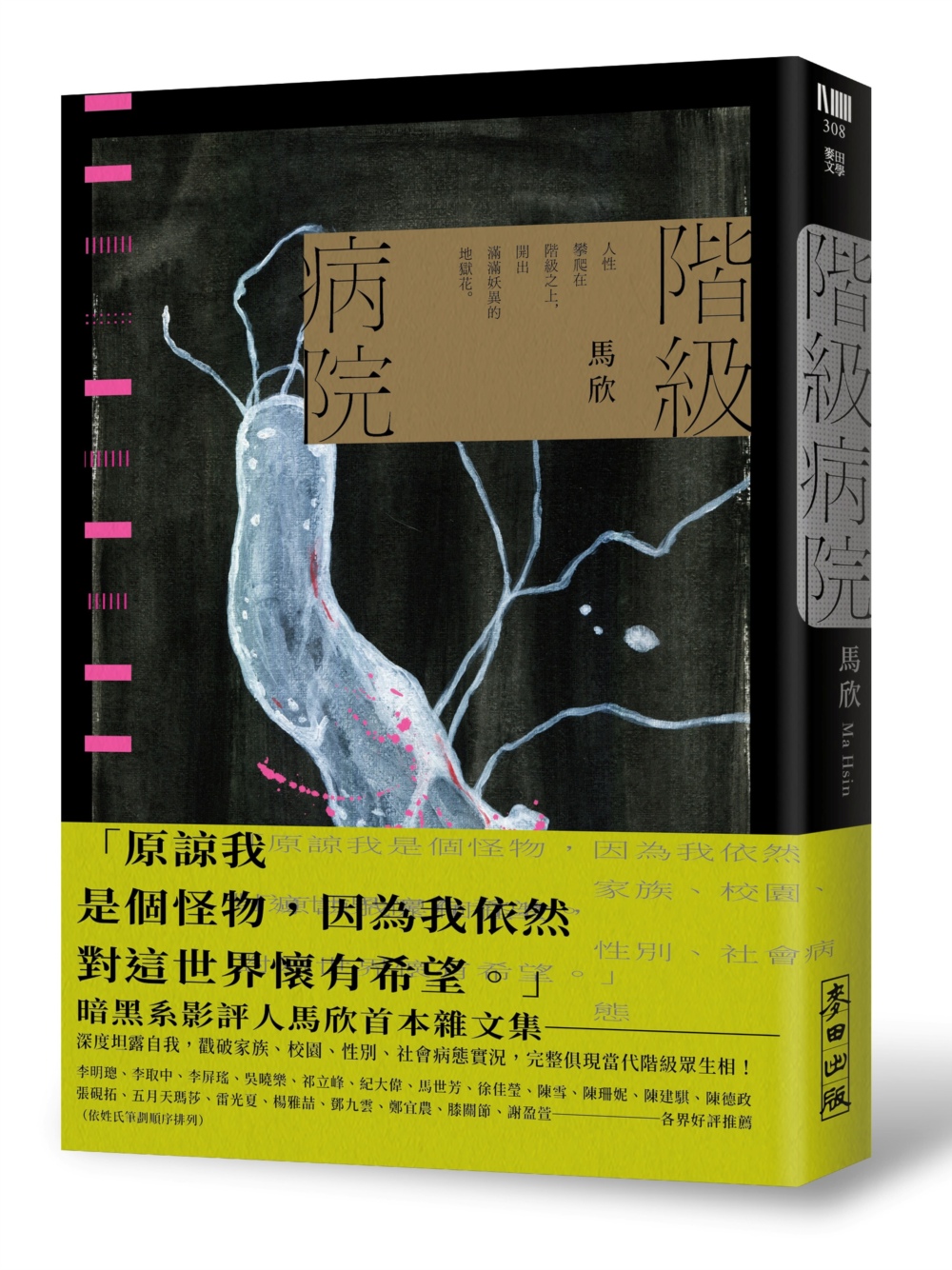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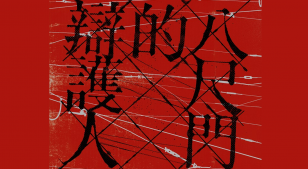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