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世界啊!我沒有什麼本錢跟你齜牙裂嘴的搏鬥,
但我仍有一支筆來當小刀,以為陰暗可以被我劃出一道一道縫隙來。讓那裡透出來稀微的光,能刺眼出我久違的眼淚。
一起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吧!
它被我們搞壞了,但我們仍有傾斜看它的角度,一眼認出它曾經的美好,於是抱得滿懷,即使即將失去。
這就是電影存在的理由,紀念我們所有可能失去的美好,還有我們曾經被拍下的純真。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小偷這一家人每一頓飯桌時光都顯得珍貴,是這群人的價值都被踩踏後,唯一能保持尊嚴與笑容的夢境之地,讓你體會愛發生的當下,原來是長這樣的,唯獨在對方眼中,你沒有被評估價值的必要,愛是這麼平常又這麼奢侈……
小偷這一家人每一頓飯桌時光都顯得珍貴,是這群人的價值都被踩踏後,唯一能保持尊嚴與笑容的夢境之地,讓你體會愛發生的當下,原來是長這樣的,唯獨在對方眼中,你沒有被評估價值的必要,愛是這麼平常又這麼奢侈……
東京,承載了二十年亞洲人的夢想,曾是個幻夢之都,但泡沫經濟與少子化多年後,東京的夢像水一樣,讓許多人無法扎根。「家」的泡影愈來愈多,那裡面沉浮的人與事,流向了「小偷家族」這個故事,讓載浮載沉的人們,有了愛的佐證。
這不是關乎有無快樂結局的故事,每個人生的結局都是殘壘,是你是否又一次被故事接住。是枝裕和的電影有浮力,輕緩如河流,能接住所有的畸零人。
片中兩個孩子的遭遇是推動這故事的齒輪,起先是像小偷的爸爸帶著兒子樣的少年,在超市行竊,讓你不禁為那男孩擔心。
片中蟬聲大作,兩人衣衫滿是汗水濕了又乾的細節,是擰不乾的勞苦人生,正在戲院吹冷氣的我們,無法置啄又感疑慮。之後一小女孩滿身傷痕的出現在這個家庭裡,這一「家」明顯沒有血緣關係,是靠年金與行竊、打零工過活的組合,一開始他們並不想收容她,沒報戶口的他們禁不起任何風險。但當他們送女孩回家的路上,聽到她父母的對話,在暗巷裡格外清楚,小孩明顯受虐,母親並不想找回孩子,這對小偷男女遲疑了,儘管身為宵小之徒,但不捨這女孩再受虐。
 看似爸爸的人,在超市裡教男孩行竊。這故事裡多是被社會拋棄的畸零人。
看似爸爸的人,在超市裡教男孩行竊。這故事裡多是被社會拋棄的畸零人。
我們是這麼清楚這幾年亞洲的家庭起了什麼變化,光看新聞就知有多少意外生子的男女,孩子像拖累他們青春的存在,就如安藤櫻飾演的角色最後審問她的社福員:「是否生了孩子就代表能當一個母親?」這問題一如歌詞散失在風裡,因為我們看到家庭力量散失的案例一樁樁,在這社會氣氛快轉如渦輪馬達時,「家」的意義正被翻攪得難以找回它的抓地力。
但「家」卻在這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身上見真章,極諷刺又極溫柔的,原本只是一群自顧不暇的人的組合,必須互相幫助苟延殘喘,如果以舊時代的眼光來看,這「家」糟透了,但從現代各種實在的已陷落的眼光來看,這家竟然找回了愛,在不符合現代人「愛」的條件下,愛自然的在這群畸零人身上發生了。
現代人的家庭很像經濟單位,家長以財力蓋出銅牆鐵壁,保障小孩的安全與受教權,以後沿襲父母在經濟體的位置。但「小偷先生」他們家頂多是個破木屋,一群沒有戶口身分的人,寄居在老太太的家,靠著她的年金過日,朝不保夕的,但他們卻好像可以天長地久地彼此愛著。
這家的大人都有種酸鄙氣,被窮鬼纏了身的人,但這故事是因為這樣才動人,因為他們本來才是最該自私的一群人啊,你不會去管他們今日為何到達這田地,不論是安藤櫻隨時可能不被延聘的女工、少女從事的情色制服業、老太太定期去情感勒索某家庭,之後舔算著三萬日元的神情,明明像爸爸的人卻教著孩子行竊技巧,是枝裕和的鏡頭並沒有避開他們鄙賤的一面,讓這一切是這麼自然,每天光是「活著」就用盡全力,僅剩的力氣就是坐在那間破屋子裡吃飯。
於是那飯桌顯得多麼珍貴,是這群人被踩踏後,唯一能保持尊嚴與笑容的夢境之地。這一群人共同做一個夢,像家人一樣的一起用餐,老太太用口水抹去小女孩傷口也好、彼此玩笑話地嫌棄也好、大口吃著沒有存糧的今日限定,就是這麼的底層,奢侈得只有今天的餐桌,他們吃的,為何跟我們吃的感覺不一樣呢?
 一群沒有戶口身分的人朝不保夕的,但卻好像可以天長地久地彼此愛著。
一群沒有戶口身分的人朝不保夕的,但卻好像可以天長地久地彼此愛著。
我們有多久沒有只剩下「生活」這件事?我們有的好像很多,多到忘記了我們的失去,他們每頓偷到什麼吃什麼,每個人該哭的時候,聚在一起都讓對方笑了。
原來被導演拍出來的是「時光」,每個發生在那破屋子的影像儘管是流動的,但同時是定格的回憶。讓你體會到愛發生的當下,原來是長這樣的。對他們來講,未來是威脅,每個可以跟彼此相處的今日,都像偷來的美好。無論是老太太多給女孩一個麻糬、小男孩終於認了小女生當妹妹、一段吃完冷麵的有氣無力做愛、偽爸爸見孩子回來趕快穿上褲子,為孩子擦乾頭髮的日常,愛這麼平常又這麼奢侈。
我們常提到貧富差距,階級出現巨大落差,但很少看過這樣抒情的拍這件事。是那麼絕望的一群人,未來被砍掉的一群人,過老、技能沒跟上社會、被親生家人凌虐、被拋棄,一群被階級丟掉的人,每天看他們老的中年的,光是賺到這周能活的,就窮其體力,身為觀眾的你也在為他們倒數過日子,因為他們是死命抱著「餐桌上幸福」不肯放的,那不肯放的力氣,讓你知道外界社會是用多大的力氣讓所有家庭看似正常又正確,家變得是用未來來綁架的「單位」,光是這份拉扯與期待,就足以讓人類整個家庭觀四分五裂。
家庭並不是為了社會服務,不是為了個人產值服務,家庭是因為要讓人體驗到愛而存在,這次是枝裕和在《第三次殺人》拍出困苦人沒話語權後,又再次把階級之病揪出來,人們對家的制式期待,讓我們失去了愛的本能,因愛就是這麼野生地反抗純粹階級這件事。
 家庭並不是為了社會服務,不是為了個人產值服務,家庭是因為要讓人體驗到愛而存在。
家庭並不是為了社會服務,不是為了個人產值服務,家庭是因為要讓人體驗到愛而存在。
這部電影不是要為偷竊或哪種教育方式來開脫,是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家」是什麼,在外界價值觀都被改寫,人被貶值的當下,為何家是浮木?是因為唯獨它有力量站在階級之外。個人會被階級輾壓,但家是為了證明愛,唯一剩下的僅存存在,未來絕對會是一個階級差距更大的時代,人能抓住的,是不見得跟你有血緣家人,是在你失去數據價值時,在他眼中,你有不需要被評估的價值,這是跟現代「家庭」走向正好相反的。
最後的餘韻也牽動在兩個孩子身上,當那男孩在巴士上轉頭無聲地喊著:「爸爸。」當那小女孩在陽台上擁抱滿滿寂寞的眼神,他們可能在世人眼中最正確的地方,但愛沒有在他們的身邊。
我看的那場放映完畢時,雖不是試映會,卻有人忍不住鼓掌致敬,而我則熱淚盈眶。未來會有很多被階級改寫的價值,但請不要讓它改寫愛。是枝裕和這部電影是個晚禱,也是個最不捨放手的心願。


《小偷家族》(Shoplifters)本片獲71屆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由日本奧斯卡最佳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由Lily Franky、樹木希林等「是枝組」班底再度合作,描述一個生活在東京底層的家庭,倚靠年金、微薄薪水和偷竊過活。是繼1997年今村昌平執導的《鰻魚》之後,日本暌違21年再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肯定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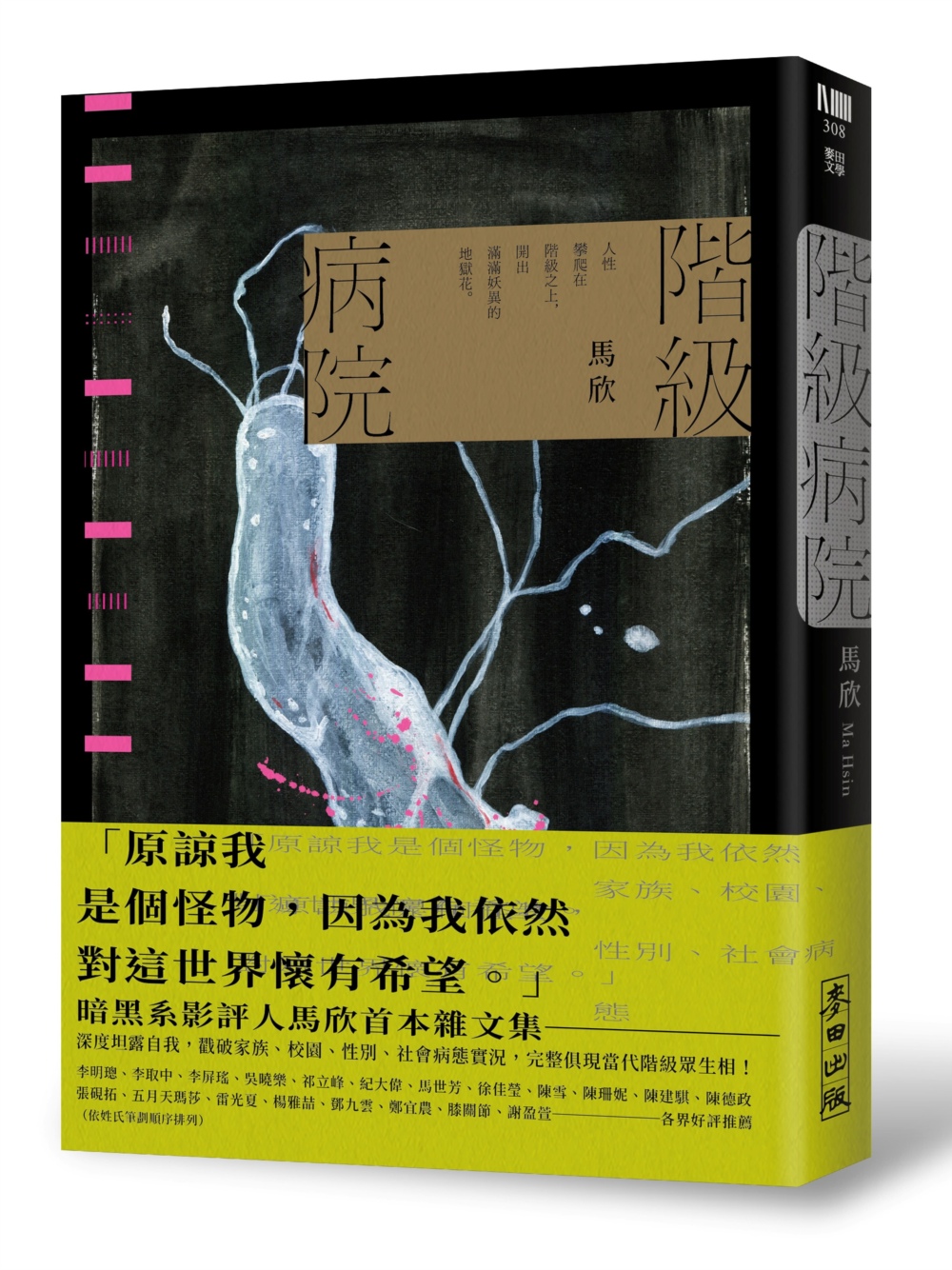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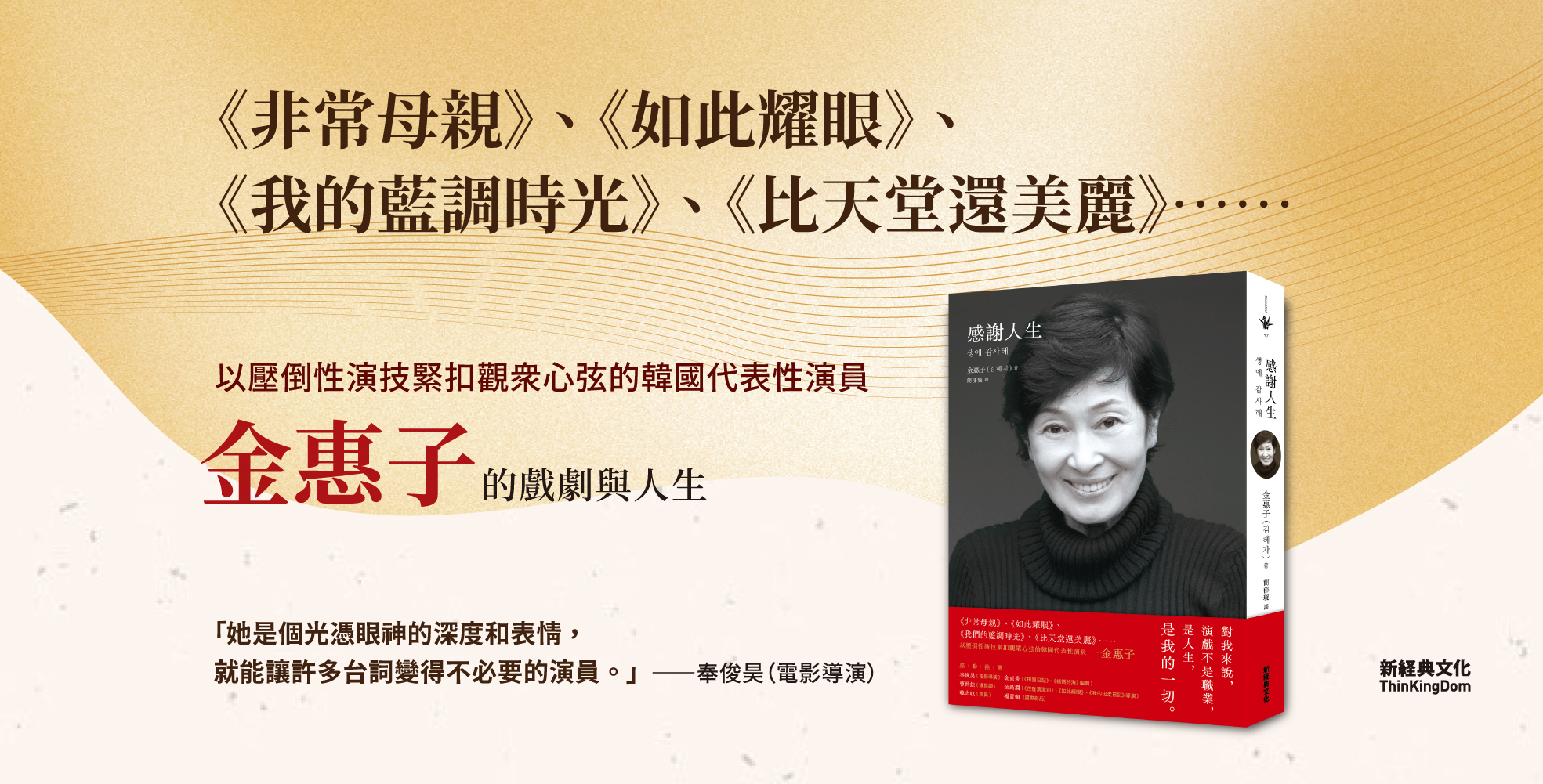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