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質探勘的領域,有所謂的「反射震測法」(Reflection Seismic Method),利用爆炸所產生的高頻震波來測知肉眼看不透的地層樣貌。震波在不同質地岩層的傳遞速度、折射、反射都會有所不同,透過接收、分析這些震動訊號,從地表下數公尺的恐龍化石到地下數千公尺的油礦,都可以準確描繪。《終點往往在他方:傳奇音樂家布列茲與神經科學家的跨域對談,關於音樂、創作與美未曾停歇的追尋》讓我想到這門地球物理的技術。
 透過反射震動訊號,能準確描繪地表下數公尺的恐龍化石到地下數千公尺的油礦。(圖/wiki)
透過反射震動訊號,能準確描繪地表下數公尺的恐龍化石到地下數千公尺的油礦。(圖/wiki)
藝術家──以這本書來說,把範圍縮小到作曲家──如何進行創作?作曲家在創作的時候,大腦是如何在運作?寫規範森嚴的賦格對位,和進行即興演奏的時候,大腦的活動方式會有所不同嗎?人在聽到不同的音樂時,大腦發生了什麼事,以至於我們會有欣喜、感動、悲傷、興奮、厭惡等不同的反應?
貝多芬曾說,「發乎於心,或可再入於心」,從「心」到「心」的抽象旅程,迷惑了無數想一探究竟的人。人的創造思維與美感感知,是最為難解的奧祕;令人沮喪的是,它就發生在頭皮下數寸之處,卻比數千公尺的地層還難探勘。
但是,腦神經科學近年來的迅猛發展,逐漸揭開了大腦運作的神祕面紗,也因此,這本神經科學家尚-皮耶.熊哲(Jean-Pierre Changeux)與20世紀大作曲家布列茲(Pierre Boulez)的對談格外令人期待。熊哲的研究領域包括異構蛋白質、神經系統認知功能的早期發展,他在1982年就獲得沃爾夫醫學獎,去年獲頒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學術地位崇高;而布列茲無論就其音樂創作或指揮,在20世紀的現代音樂都占有一席之地。加上作曲家馬努利(Philippe Manoury)也加入談話的行列,總是比兩個人談更熱鬧,而且高度、廣度兼備。
 左起:神經科學家尚-皮耶.熊哲、作曲家布列茲、作曲家馬努利。
左起:神經科學家尚-皮耶.熊哲、作曲家布列茲、作曲家馬努利。
(圖片來源 / wiki、AllMusic、Philippe Manoury官網)
《終點往往在他方》把這些談話的素材組織成七章,從美學的提問「音樂是什麼?」到音樂的創造與感知,再回到音樂教育、甚至音樂與道德的話題。或許是為了方便讀者掌握對談重點,每一章裡頭又設了更明確的小標,像是「音樂與語言」、「藝術作品與商業價值」。
但是,如此清晰的架構其實是一種錯覺,讀者若是被這些小標引發興趣而去閱讀,往往不見得會讀到回應。因為這三人的對談是發散而非聚焦,而且常常是平行而錯位的。神經科學家熊哲有興趣了解作曲家布列茲與馬努利在想什麼,但是布、馬二人對於神經科學如何解開大腦的奧祕卻不感好奇。回到「反射震測法」比喻,震波乘載了探勘地層的任務,但是地層並無意了解震波。
在這所謂「對談」中,熊哲時常放下科學家的身分,用哲學、美學的口吻提問,但這並非熊哲所長,所以往往東放一槍,西放一槍,沒辦法做有效的追問。在「人聲音樂與劇場藝術」一節,熊哲以獼猴可以發出跟人類一樣豐富的聲音、黑猩猩可以用聲音「交談」開始他的提問,但他真正要問布列茲的是:「他如何安排人聲或聲樂的位置?」獼猴或黑猩猩都只是虛晃一招而已。
結果,布列茲對獼猴或黑猩猩都不感興趣,事實上,他根本不太想回應這個提問,說他沒有以人聲做為編排的核心,而且他上次使用人聲是在1970年。熊哲並沒有追問布列茲為何不用人聲,或是他以前是如何使用人聲的,而是鼻子摸摸,換個話題,問布列茲「為何不寫歌劇、卻指揮了不少歌劇?」結果布列茲說他只有指揮過幾齣歌劇而已。書中類似這種「對談」,出現的頻率很高。
熊哲談到自己的專業時,即使興高采烈,布列茲也常以冷水伺候。熊哲在「音樂與語言」一節提到,俄國作曲家舍巴林(Vissarion Shebalin) 因中風喪失語言能力,不能說話,也不瞭解別人說的話。但是舍巴林在這種狀況下仍然完成了《第五號交響曲》。熊哲想知道布列茲對此有何看法,布列茲直接說他不認識舍巴林,所以無法評論。
有一種對談,像高手過招,問得高明,答得巧妙,問答之間就很精彩。《終點往往在他方》不屬此類,它展現了一種「賦格式」的趣味──賦格的本意是「遁逃」──讀者會看到布列茲如何逃避、漠視、否定種種提問。如果一本書通篇是這種不給力的「對談」,讀者該如何自處呢?它的價值在於「反射震測法」,從布列茲對於震波(熊哲)的反應,而得知他如何看待與藝術相關的種種話題。以此而言,三位各有專精的作曲家、科學家提供了豐富的看法,可讓讀者慢慢玩味。
(本文由臉譜出版提供。原標題為:遁逃的藝術,「賦格式」的對談 )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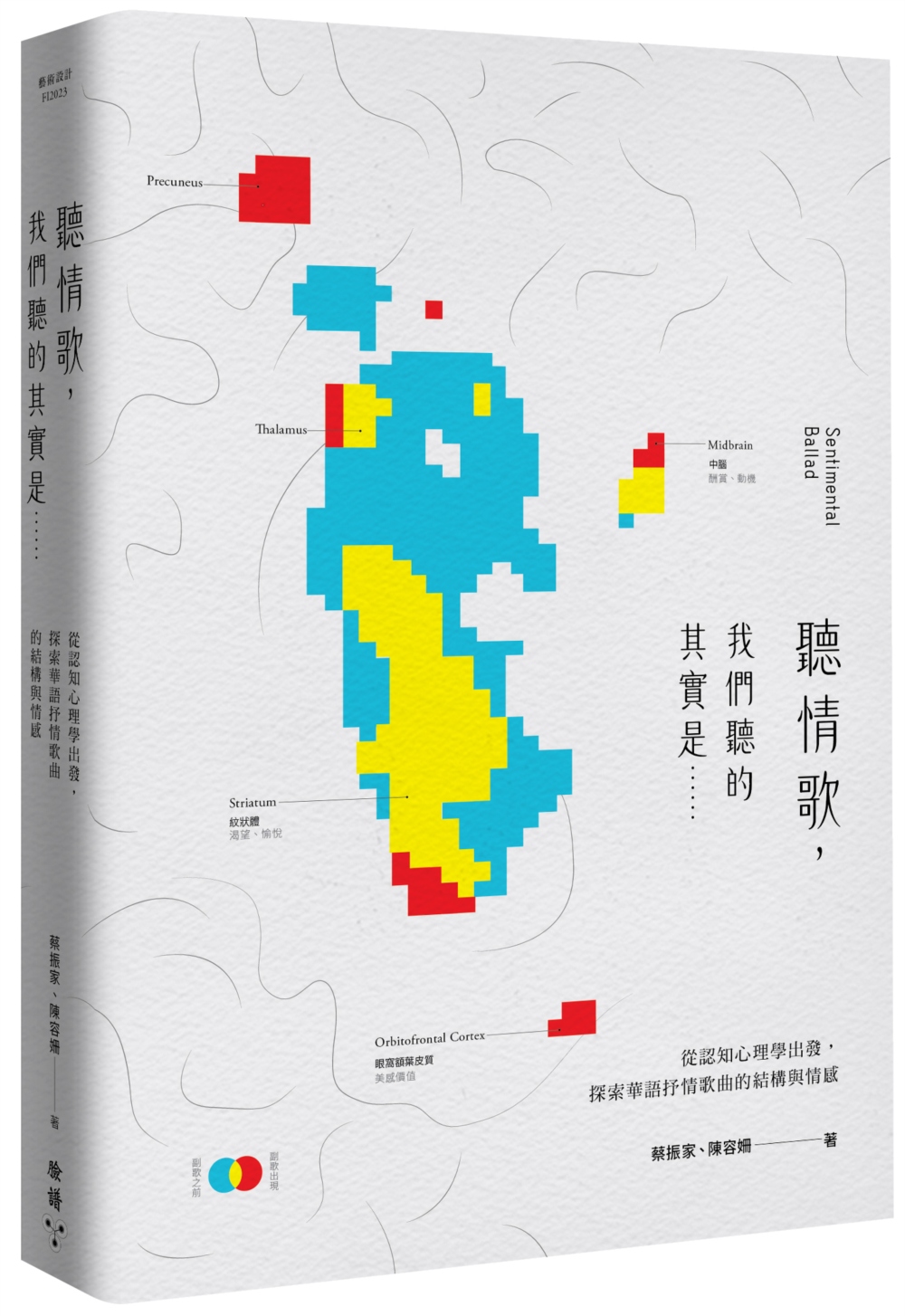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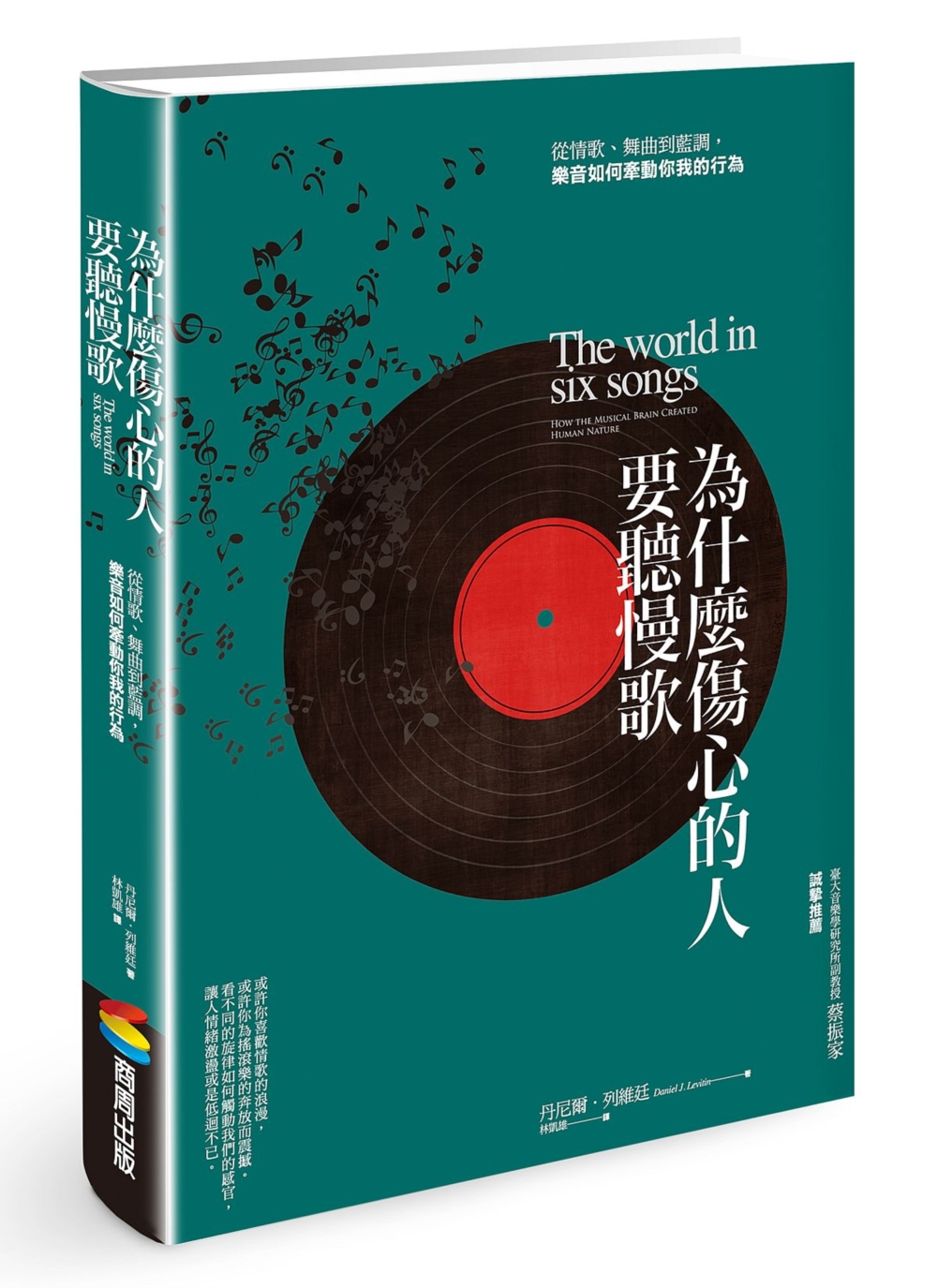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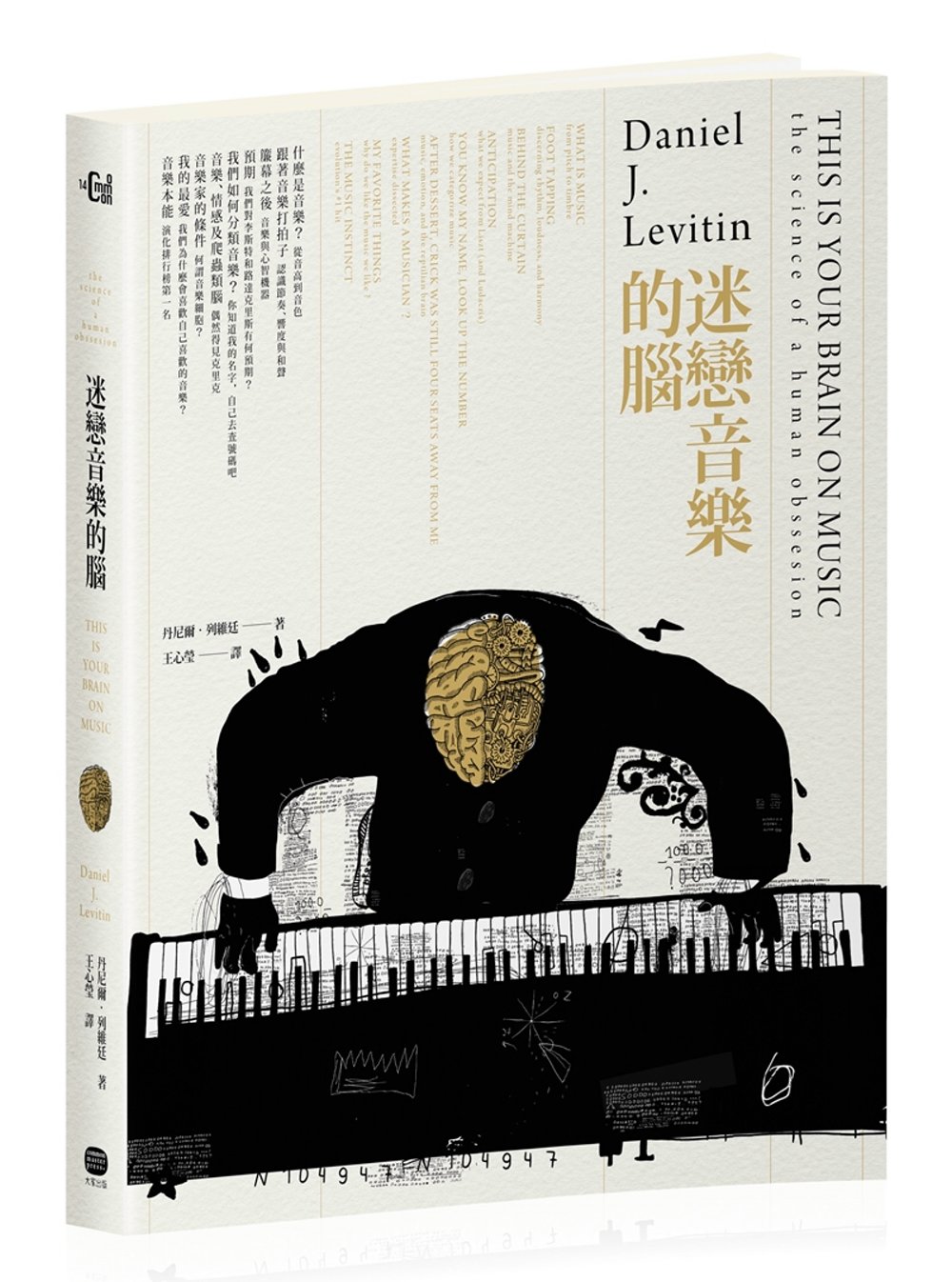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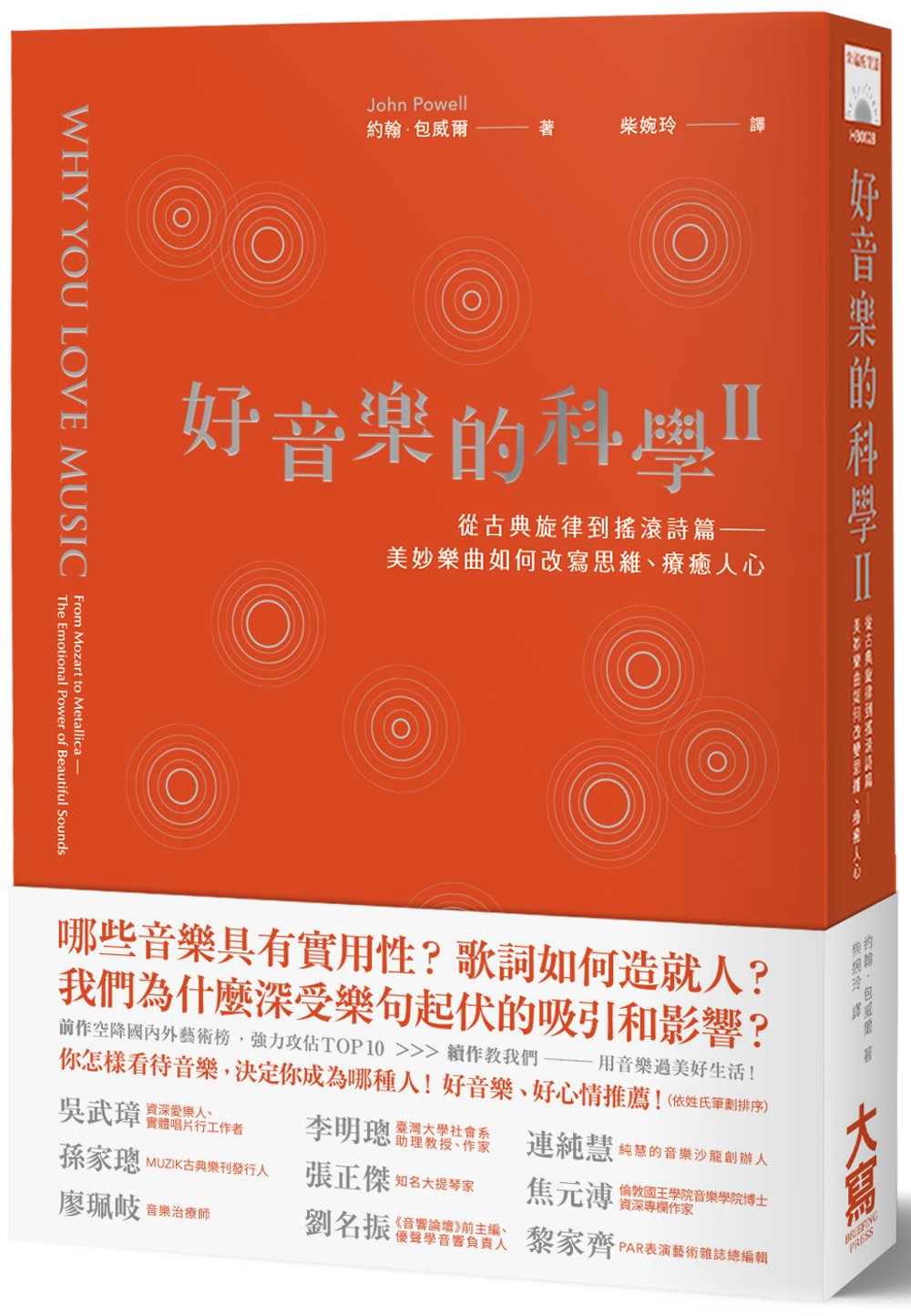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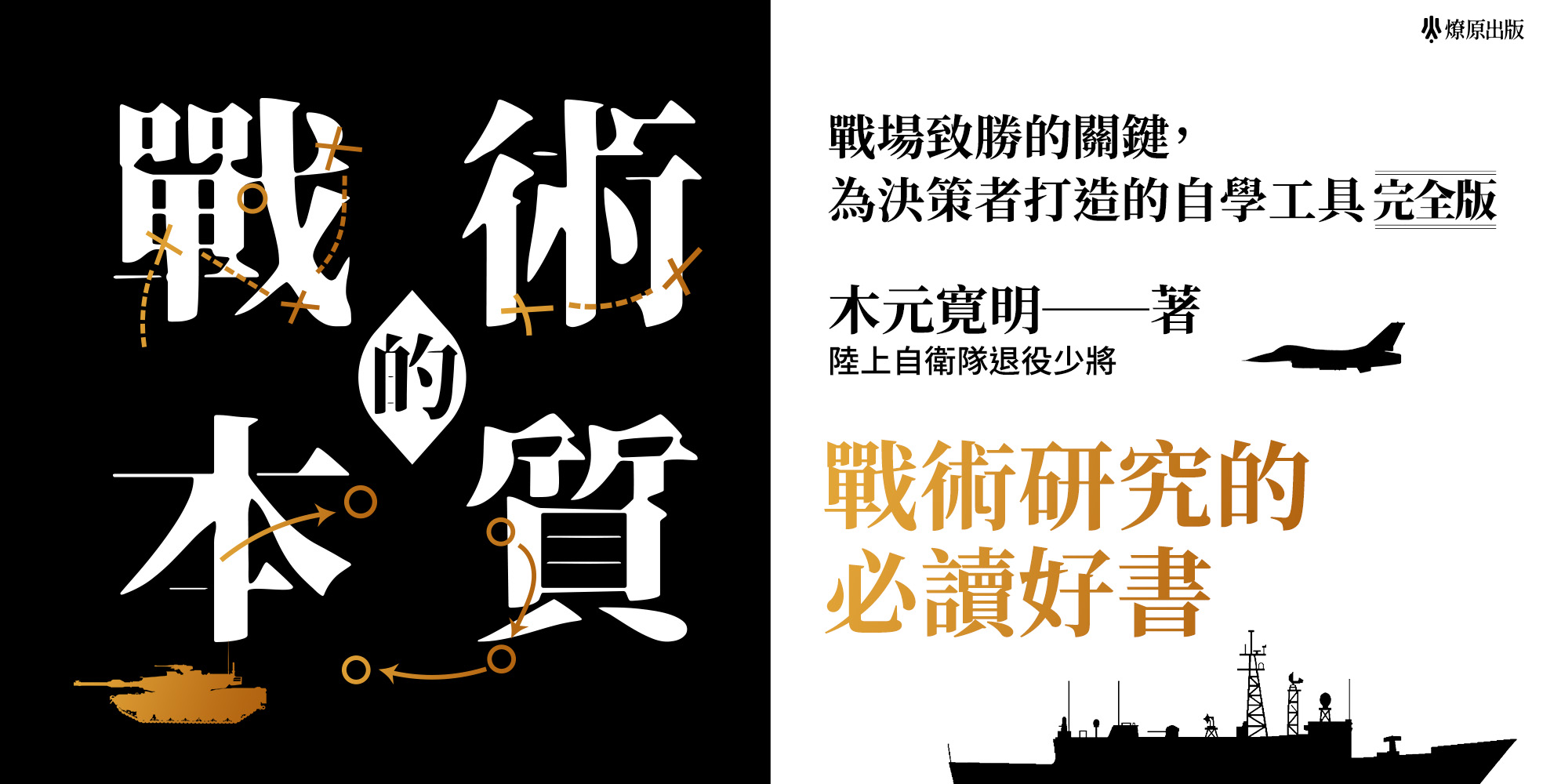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