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柏林影展,我負責口譯中國電影《漫游》的觀眾對談。導演祝新來自杭州,說話跟他的電影一致,如詩飄忽,翻譯難度頗高。我自評幾場翻譯都安全過關,但有一場觀眾對談,祝新說:「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腦中想的是When I was a kid,但,我口中竟然說出When I was a cat。
天。
 是貓又怎麼了嗎?(設計對白)Photo by Max Baskakov on Unsplash
是貓又怎麼了嗎?(設計對白)Photo by Max Baskakov on Unsplash
我馬上糾正自己,但台下幾百位觀眾已經哄堂大笑。其實我也很想笑,腦中出現了許多貓臉,尤其是大學同學的小貓跳跳虎,但譯者不能三八啊,我必須馬上消滅狂笑的欲望,驅趕腦中的跳跳虎,一臉正經,繼續翻譯導演的詩句。
譯者當然怕犯錯,筆譯可修正、校稿,但口譯一說出口,發現自己說錯了,腦中馬上想起黃乙玲的台語金曲《水潑落地歹收回》:「水潑落地、水潑落地歹收回,何必今日才想要反悔…. 啊無必要回頭、無必要回頭,倒返來相找。」當下沒時間拿起麥克風哭腔大唱黃乙玲,也不可能有機會反悔,口譯不能停止,無必要回頭,繼續翻譯就是了。
國際影展觀眾對談開放給觀眾舉手提問,各國觀眾說英文,有各自的口音,譯者必須排除口音障礙,把提問翻譯給導演聽,否則問答無法成立。有些口音是天線壞掉的收音機,收訊不良,但大致聽得懂。有些口音是濃霧,譯者在腦中拿起大電風扇吹,盡力吹散大霧,抓取關鍵字。有些口音根本是沸騰稀飯,濃稠燙口,聽完我一臉呆滯,耳朵無法消化稀飯,一嘴燙,完全無法翻譯。多年前賈樟柯來柏林參加電影論壇,我在他耳邊口譯,有一位說法文的非洲導演用英文發表想法,口音如獅,把我咬得遍體鱗傷,我真的沒聽懂,只好在賈樟柯的耳邊坦承:「導演,我真的,沒聽懂,對不起。」
學英文時,我努力模仿「北美口音」,想要變成美國人。但,到底什麼是「北美口音」呢?美國、加拿大各地有各自的口音,光是一個大城市就會有不同的口音,我們當年都會嘲笑「臺灣腔英文」,長大了才發現,我是臺灣人啊,講「臺灣腔英文」,就是在語言標註自己的出身,臺腔不可恥,無需戮力消弭。後來學德文,我就不追求所謂的「無口音」(akzentfrei),不是說不用努力學發音,而是,語言溝通首重善意,只要有善意、些許耐心,「不標準」、「有口音」,都是可跨過的柵欄。口音標示自己的出身、階級,我就是臺灣彰化永靖出身的農家子弟,我知道我是誰,不用掩飾了。
所以口譯要跨過口音柵欄,首先就是要放棄所謂的「標準口音」,尊重各地的口腔,善意傾聽,試圖在迷障裡捕獲關鍵字句。不傲慢,訓練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站在講者的位置去思考語言的脈絡,往往就很有機會走出迷宮。
比口音可怕的,就是數字。英文數字與中文數字說法真的差別很大,一萬是10 thousand,一千萬是10 million,一億是100 million,在德文裡也差不多。但德文的數字其實比英文複雜,例如34,是先說4,然後再加30。除此之外還有分數,四分之三英文是three quarters,德文是drei viertel。數字道理清楚之後,筆譯遇到一組數字,可以慢慢盤算,但口譯就需要即時性,要是遇到講者說出:「在這個圖表上,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分之二的機會,可以讓我們取得九億六千七百三十二萬的營利,讓我們的業績有6.79%的成長率。」譯者腦中此刻會響起警報,鈴聲大作,輕微症狀是缺氧口吃,嚴重者甚至昏厥,心臟有一塊肌肉僵硬,永遠崩毀。
我有一次在同步口譯的研討會場合,遇到超愛講數字的教授。現場有日文、韓文、中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口譯,教授在台上講了30頁簡報,每一頁都有分數、百分率、神祕的一大串數字,我本來以為只有我口吐白沫,但之後發現所有譯者都已經發瘋,有菸癮的點燃三根香菸,沒菸癮的把研討會的蛋糕全部吃光光,我直接拿起砂糖包往嘴裡倒,吃糖解苦啊。我高中畢業最開心的就是這輩子再也不用學數學,哪知身為口譯,竟然還是會遇到算數。例如這次的柏林影展,有觀眾問導演:「電影預算多少?」導演說了人民幣,以及歐元對人民幣的幣值,請我算成歐元給觀眾聽。要死。親愛的導演,我要怎麼跟你說,我高中三年,數學從沒超過40分啊!我大學聯考,數學是13分,而且我完全不知道那13分怎麼來的,因為我一題都不會。
數字殺人,縮寫也有砍人的力道。在商業翻譯的場合,口譯一定會遇到很多縮寫,例如:R and 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是研發部門,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是關鍵績效指標,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是獨特賣點,無論使用哪個語言,講者通常只會說英文的縮寫,所以譯者其實也只要跟著複誦那些縮寫,就能搭起翻譯的橋樑。但,譯者要是完全不知道這些縮寫的意義,跟著複誦,說出來都是虛的。我真的時常遇到一大堆我完全沒聽過的縮寫,事先要做很多準備,先把各種可能的縮寫都查清楚,依照字母順序製表,以免到時完全聽不懂。
縮寫真的很磨人,但人類真的很愛縮寫,日常語言裡就很常見。我有德國朋友在台灣學中文時,就被許多臺灣獨有的縮寫搞瘋。例如,手搖茶攤常聽到:「大奶綠去冰少糖」,咖啡館則常說:「大熱拿、大卡布」,德國朋友一聽到「大奶」就輸了。學外語,縮寫真的是個門檻,縮了之後不見全貌,很難猜測。
口譯時遇見沒聽過的縮寫,譯者真的會慌張,尤其當講者不斷說那神祕的縮寫,只能先硬著頭皮跟著複誦,有空檔立刻上網查詢。
但還是會遇到必須翻譯縮寫全意的時候,我就曾經因為翻錯縮寫,「害」了一位臺灣女生好友。
好友來我柏林家小住,打開交友APP,立即湧進百封訊息,極為搶手。朋友忙著回訊息,一直不斷請我翻譯,我才發現,網路約會的世界,不管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縮寫,英文很複雜,德文也可怕,不查清楚,真的會誤會對方的意思。例如「dtf」是down to f__k(拜託這個我不用翻譯吧,反正就是找砲友啦),「ild」是ich liebe dich,我愛你,朋友一直叫我幫忙翻譯,我只能請問網路大神。
有天我正在趕稿,朋友來問,對方說他是BBC哩!我馬上大喊:「啊,這不用查啊!英國廣播公司,親愛的,快去約會!英國廣播公司!說不定是迷人的主播!」快速打發朋友出門,專心寫稿。
朋友回來之後,打了我後腦杓:「你不是說你是譯者嗎?亂翻譯!你很過分!你這個大賤人,你故意的對不對?」
嗯。
當天我學到一個全新的縮寫。
BBC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是。Big Black Cock。
作者簡介
得過一些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九歌年度小說獎等。
演過一些電影:《曖昧》(Ghosted,2009)、《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2013)。
寫過幾本書:《指甲長花的世代》、《營火鬼道》、《態度》、《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去過敏的三種方法》、《第九個身體》。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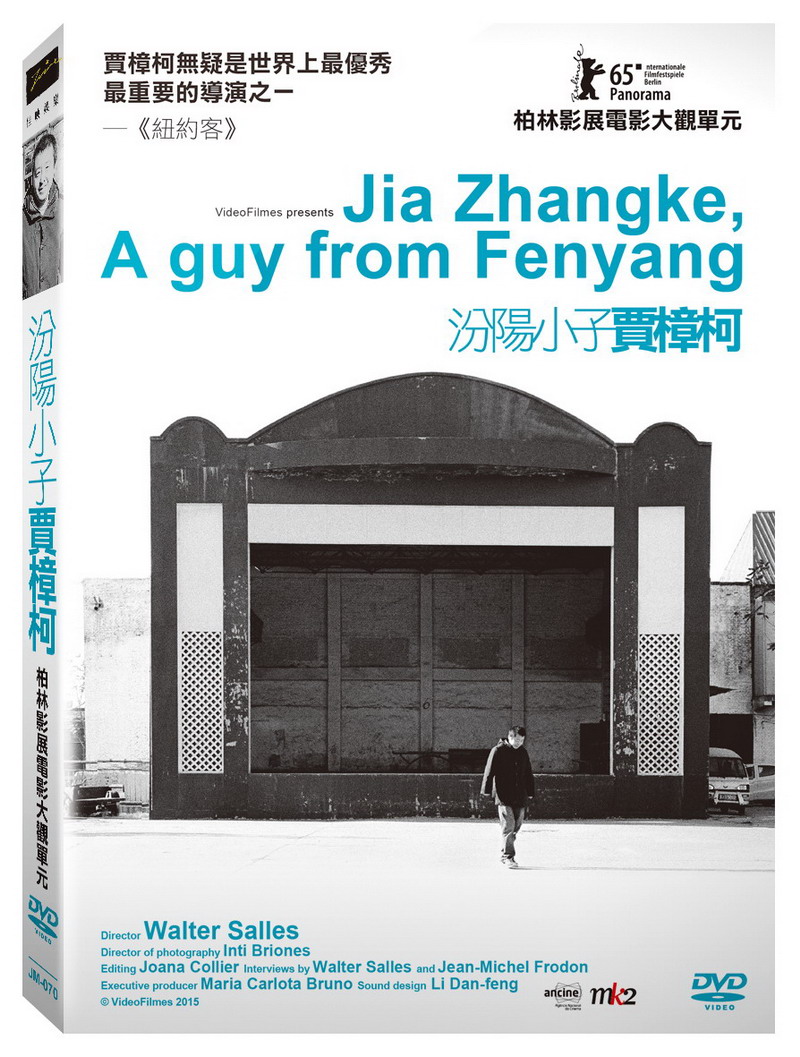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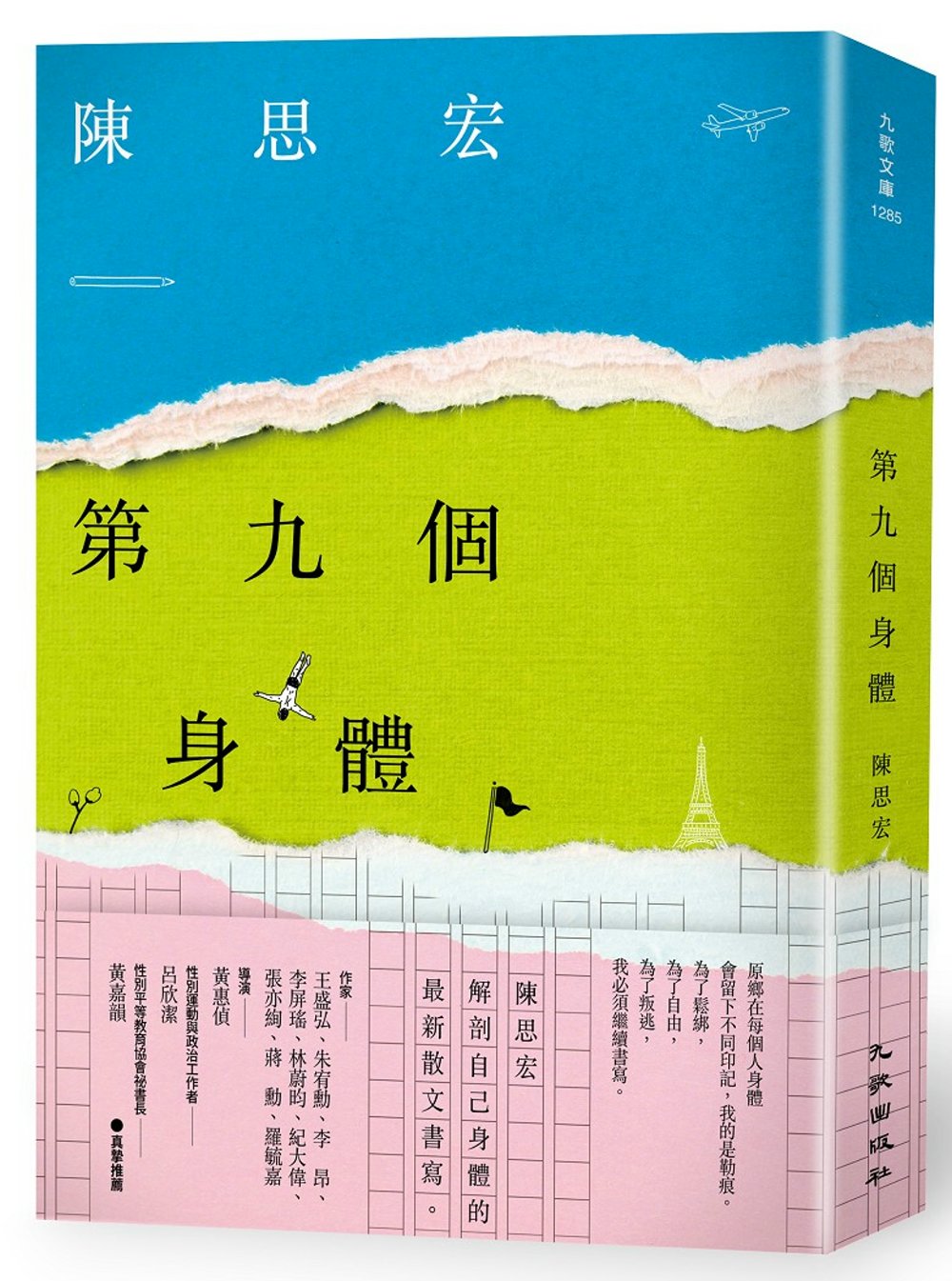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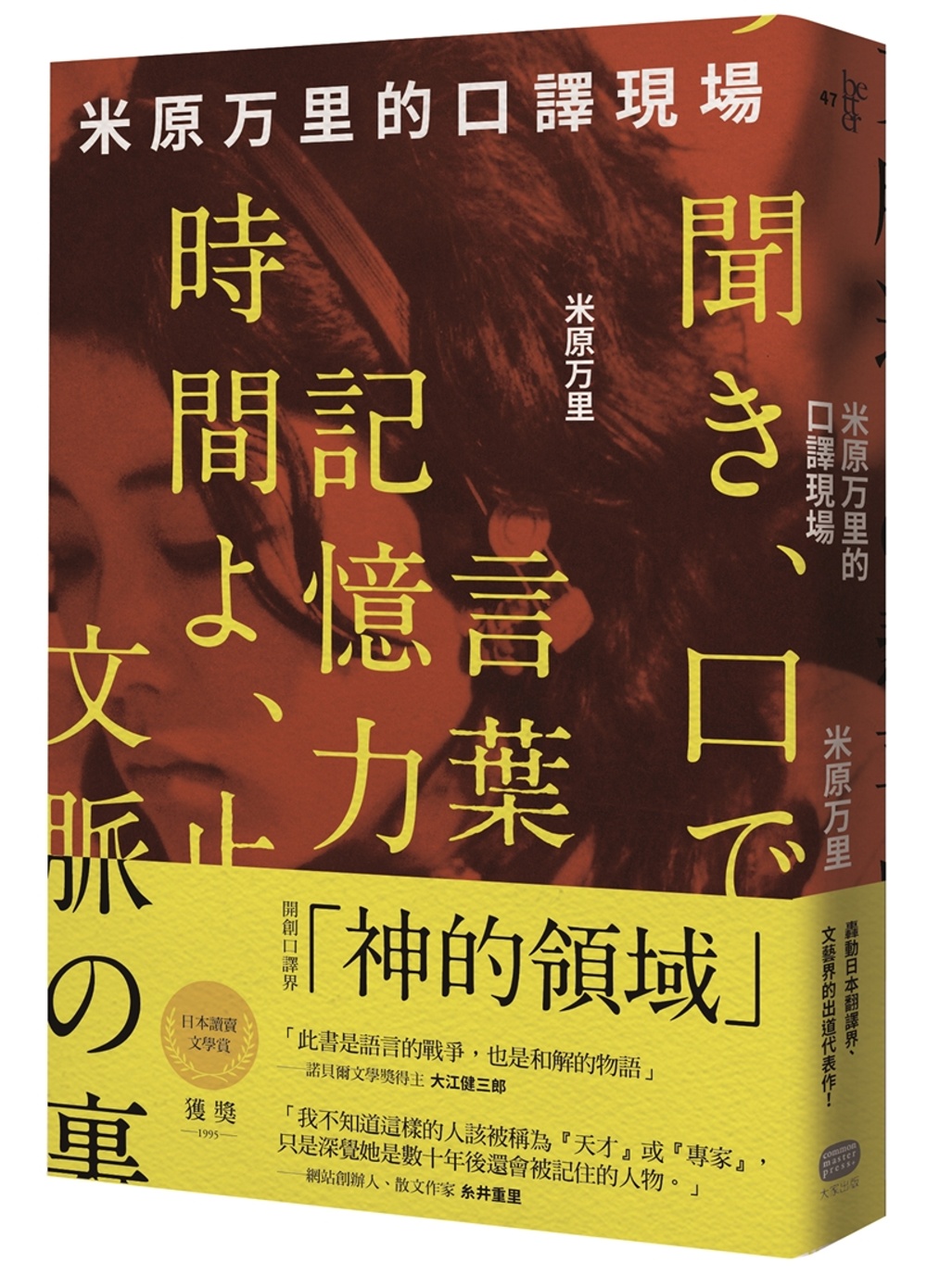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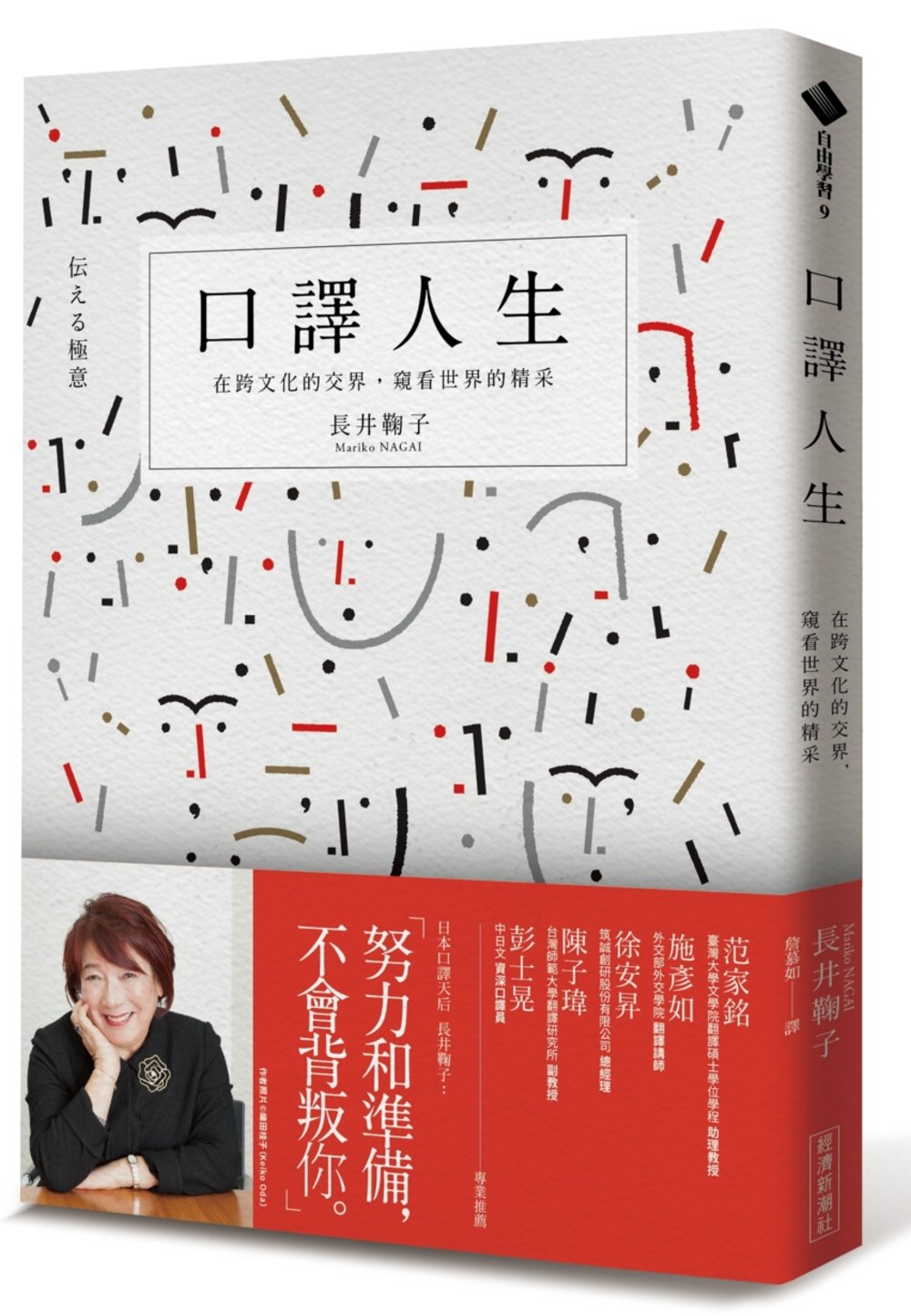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