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圍坐一桌等張惠菁。仔細想想這場景頗寫實──不只我們,整個文壇與讀者們等她好久了。
但在張惠菁的時間感中,可能並不存在什麼片段是停滯的,只是旁人不知曉罷了。採訪那天是個季節錯置般的燠熱冬日,她頻頻把前年說成去年,然後笑著更正,剛越過的那一年,顯然在她頗為漫長。新作《比霧更深的地方》姍姍來遲,三稜鏡般透析出她生活中的閱讀系譜,系譜蔓延出的思索網絡,最終張羅結網打撈上來的,仍不啻對自我如何安居於世的叩問及迴音。
寫作是張惠菁隨身攜帶的一件行李,漂流過中國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十年過去,她想著換大環境換生活方式吧,但回到台北不似橫渡海峽那般直截了當,移動的人發現,停在哪個地方,首當其衝皆是生活的斷裂與抵抗,「《比霧更深的地方》一半是在中國時寫的,一半是回到台灣之後寫的,在這兩個地方,我好像都一直在寫作中努力尋找連結。」家鄉的步履疾行不停,巷口冒出新裝潢店家,天橋和忠孝東路車道消失無蹤。「即使像我們每天生活的此地,你也會不斷發現改變,那改變也包括自己,以至你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你的家鄉跟更大的世界,這都是變化。但不見得是陌生感,比較像重新發現的過程。」
這不是張惠菁第一次感受到異質。台灣的眾多海外學子,她也曾是其中一人。一路順理成章的遠赴愛丁堡攻讀歷史,她卻形容當時的自己很「無知」,「有人出國只是想去看外面世界,有人一心想拿學位,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你通常沒有意識到,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其實還有一個『認識自我』的過程更激烈的同步發生,你甚至可能因此迷失。」論文寫到一半,為何而讀的困惑逼得她答不上來又放不了懷,寫小說成了逃生口,歷史研究者張惠菁與作家張惠菁從此走上歧路,不再回頭。

「你終究要去回頭檢驗人生立下的目標,沒辦法對自己說謊。」現在的她,對當年的自己如此註解。但你若想誠實勇敢,神必然賜予阻礙──例如說,張惠菁的工作履歷多了些不尋常的資歷,最大椿的故宮南院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很多人說你是作家,為什麼會去做這樣的工作?蓋故宮南部分院,我知道自己有困難,但那時候被這理想吸引,能為台灣增加一座亞洲博物館,為何不做呢?」
年少時的理想胸懷如跫音迴盪,這廂我們還在躊躇能不能問,那廂她已經走過自己心底海嘯,平靜得彷彿只是經歷昨夜那陣濕了又乾的雨,「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我經常被那些未知吸引,想實現尚未存在這世界上的東西,比如一座博物館或一本書。說起來,故宮那經歷大家都覺得是個劫難,但難道預先知道那劫難,就不去做了嗎?」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那是應該做的事。我告訴自己,既然一直被這未知吸引,就不要在過程中回頭懊悔,要去面對、去找到路。」歷劫的人正因有了歷劫的生命經驗,更看得到劫難之無可迴避。藉用她在《你不相信的事》裡的形容:「無論那是什麼,我們始終是手無寸鐵的進入,再遍體鱗傷地出來。」
孤獨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面對生命困境不得不單打獨鬥的覺悟,也有一種是被策動著孤身上路的追尋。張惠菁提起在上海時,三不五時會邀請同事在周末時到住處喝酒聊天,觥籌交錯間自己就默默人間蒸發,賓客也漸漸對這不時搞失蹤的主人習以為常,講起這段軼事,她邊描繪歷歷邊笑個不停,「有時候對話題不感興趣了,我就會自顧自躲到沙發背後看書,我同事跟我抱怨時我笑壞了。其實我經常很想參與,但最終還是要退到房間裡,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我覺得孤獨不會不好,甚至就是因為有那孤獨,才得以走得更遠更深。」

《比霧更深的地方》裡談了《西遊記》、《封神演義》、《左傳》,是在孤獨中長途跋涉的閱讀,閱讀也深刻地回應了她的孤獨,「譬如某天我翻開書,讀到《左傳》〈鄭伯克段於鄢〉,想著:啊,原來千百年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那一刻你讀到作者的心,懂得這種感情了。」一瞬間她有點被湧上的情緒哽住,「《左傳》被寫下的千百年來,你不知道它對誰產生過意義,它從沒給你實際的酬賞,你也不會因此中樂透,可是在那當下你得到了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安慰,那就很足夠。」
張惠菁坦言,從前寫作仍偏向為自己而寫的位置,近年的幾場導讀會與活動,讓她開始認識某些面孔,「讀者是誰」才開始稍稍具體,「那樣的場合裡,我不是談自己而是談書談文學,讀者來參與、討論,我覺得這樣挺好。」她微微側身,浮現不擅受注目的靦腆,「我確實在《比霧更深的地方》裡沒有想談那麼多自己的事。沒必要看著我啊,我覺得應該是我跟我的讀者,我們一起看這個世界。」
「《西遊記》一行人取經,歷經劫難,你說最後得到什麼?其實就是智慧,有跨越事情的能力,那也是我很嚮往的。」取經求道路難,但更難的是願意回來,持續而重複地與世界打照面,「世間萬物都在不斷變化,修心讓你眼睛看到變化,不致被擊垮,但變化本身仍讓我覺得充滿魅力。以前碰到不理解或壓迫你的事,譬如說官司,會很想躲起來,可是現在知道,做為一隻小魚,你得游出去。也許我的角色就是去理解、去睜開眼睛看,行有餘力的話寫出來或講給他人聽。」

書名也如同所有活著的故事與象徵,渴望召喚更多可能性,拒絕被完全的定義,「我們考慮了很久,很多人覺得『比霧更深的地方』太詩情畫意,但對我而言不是,那是一種尋找,走向更深處努力,我想刻意保留那模糊性,也是因為我相信除了非黑即白的標籤式論述之外,存在著一種允許比較多模糊空間的思考。」她提起書中輯二〈在時空的座標裡看見美〉,收錄與藝術史學者施靜菲長達1萬7千字的對談,是她回台後重新尋求連結跟安頓的軌跡,「這段期間我不斷跟朋友進行著這樣的對話,那些內容是我們的困惑與共同思考的事。你問我最近忙什麼,其實就是透過閱讀、透過藝術或跟人接觸尋找連結感。」
現在的生活呢?不再棲居於某個頭銜之下,她策展、擔任出版社顧問、與作家對談、為讀者導讀……架橋的工作意外地適合她。「我還蠻喜歡的,但每天都擔心會不會答應太多事了。」她笑著說,有點調皮地瞄向旁邊同事。對她來說,關鍵在於創造連結,是否以出書形式,倒不那麼重要。
在勒瑰恩《地海故事集》裡,年輕的學生彌卓問:「森林有多遠?」魔法技藝師傅萸燼告訴他:「心有多遠,它就有多遠。」霧的深處是未知或不可知,是絕景或絕境,你必須放下所有已知的技藝與路徑,親身一步步靠近。
訪談後,張惠菁接過側背袋,鼓脹的袋子看起來沉重極了,但她從容背上身像穿戴起一朵雲般自若,我們忍不住對袋子裡裝了什麼感到好奇,但又寧願保留著那麼一點有什麼尚未被揭開的神祕。來日方長,同為迷霧世代,相伴而行,旅途上總有機會聽她再說更多。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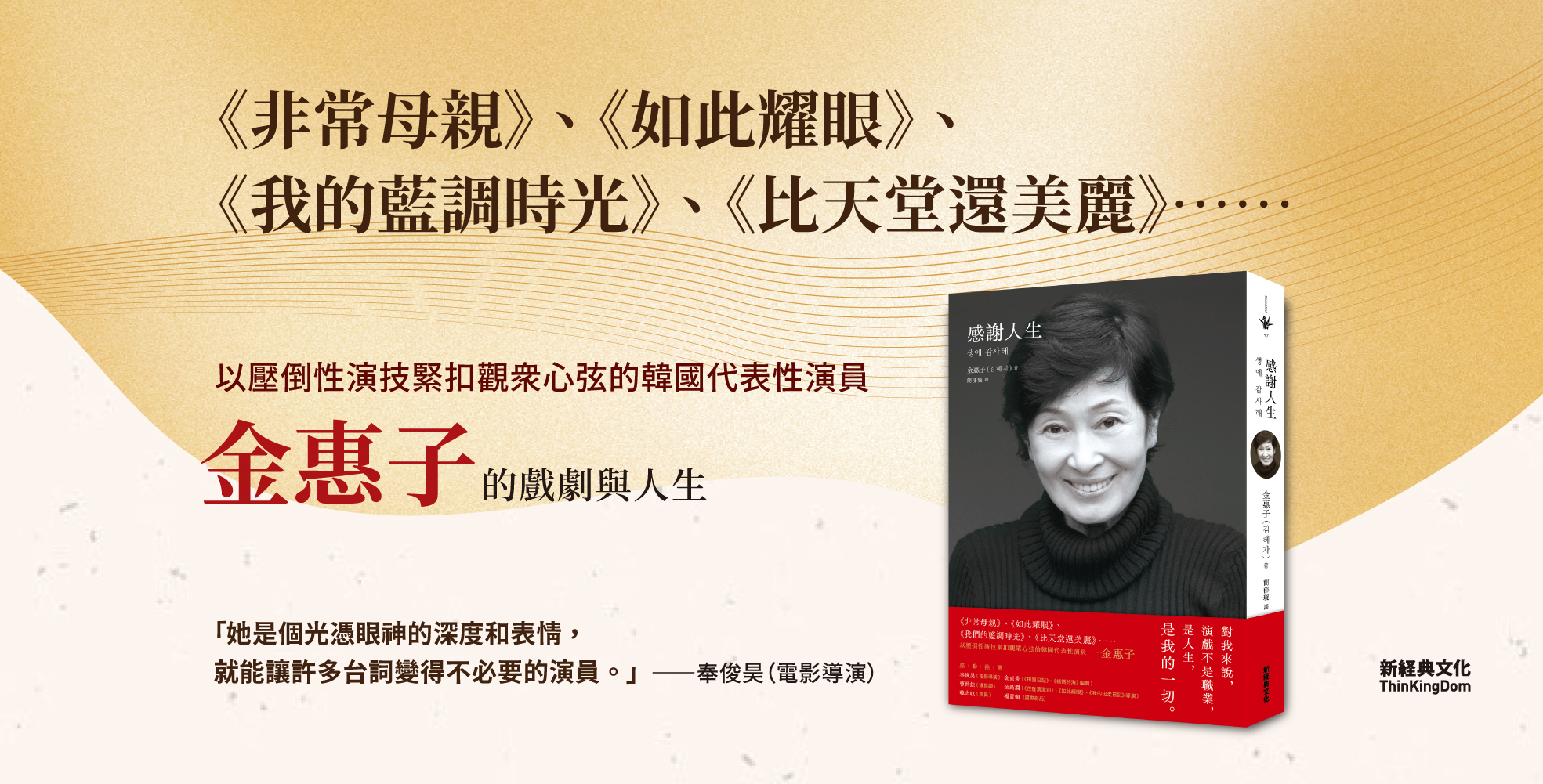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