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睽違五年,言叔夏端出第二本散文作品《沒有的生活》。承接《白馬走過天亮》,言叔夏的文字氣質依舊憂鬱靈動,不只是文字而已,皮膚白皙的她,談話節奏不疾不徐,看上去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我身旁喜愛言叔夏作品的讀者朋友,說她是散文界仙女,也有人說像是古墓派的小龍女。
《白馬走過天亮》裡的90年代質感仍保留延續於《沒有的生活》。倘若以讀者與訪者的位置,我難免想像過「白馬」代表什麼隱喻?在這個世界上試圖尋找走過天亮的白馬,是找不到的。這是言叔夏所創造出來的隱喻意象。白馬或許是時間的純真、潔淨,也或許是創作者與塵世間保持距離的一種質地。也因此,白馬少見,白馬不一樣,身為一匹白馬難免孤獨。
白馬的生活
言叔夏在《白馬走過天亮》曾告訴我們許多孤獨的故事,包括獨居於地下室的租屋、老電影、長長的90年代,這些記憶的殘餘彷彿以某種形式延續至第二本創作。回顧《白馬走過天亮》的散文有三個分輯:輯一「霧路」、輯二「無風帶」、輯三「光年」,可以看出白馬上路,行旅穿越,最後抵達遙遠他方的軌跡。
來到《沒有的生活》,同樣分為三輯:輯一「地平線」、輯二「某城的影子」、輯三「天黑以前」。在第一本書的最終,光年記憶以外,言叔夏這次要從地平線開始談起。地平線是需要眺望才能見到的遠方,也代表著保持某種距離的觀看。「地平線」裡,仍有許多九零年代感的故事。包括FB、IG等社交網絡工具出現以前曾經被大量使用的BBS,例如〈從前從前有個KKman〉,或談及蔡明亮電影的〈「你那邊幾點?」〉她寫:「幾年沒再看過蔡明亮的電影。我以為我的『蔡明亮時間』早已停了,停在大世紀戲院拆掉的那幾年,停在淡水線仍筆直地穿越古亭、公館,抵達城南時的鏡面。那筆直裡有一種儼然,像上世紀地層的某種沉積。」
談及90年代記憶,言叔夏說:「90年代是個電影跟音樂都很豐富的一個時代。舉例來說,我高中時期必須搭車去比較遠的地方讀中學,就是〈白馬走過天亮〉裡面的那台校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校車上會有人突然拍拍你的肩膀,轉頭看,有一卷錄音帶從後面傳過來。許多學生會在書包裡面準備一卷卡帶,一個接一個,從後面把音樂傳給司機。如今想起來很不可思議,也很復古,音樂竟然是摸得到的,甚至你可以用手把它傳遞下去。」

言叔夏說:「不管是BBS、MSN、FB,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時候。現在的網路像自來水,打開就會自然流出來。我意識到的網路是有點儀式性的,比方說BBS ,我某個時間才會上網,發現上站人數很少,只有6個人。那時候人與人的關係很簡單,甚至BBS站臺還會問使用者一些問題,例如:你認為網路跟現實哪個比較真實?如今看這個問題,卻覺得非常古典,甚至是一個抒情的發問。」

以密碼記憶城市
白馬帶著我們走過90年代又回頭凝望。在時間的移動之中,她也以陌生化的眼睛去看待城市。在書寫裡將台北稱呼為「某城」,提到這種陌生化,她認為所謂的某城是許多城市的疊影,不一定只指台北,更像印章一樣,一個印著一個,「漸漸地,看不清楚第一個印章的形狀。於是,某城既是台北,可能也不是台北。」言叔夏說。
聊到成長的家鄉高雄、大學時期的花蓮、碩博士班時期的台北,至今教書定居的台中。這些移動在心情上的感受又是如何?她以代號、密碼來為城市命名:「比起台北的〈某城〉,我搬到台中,暫時稱這裡為「C城」。用一種密碼的方式跟它建立關係。也許未來的某天,我才能在文字裡讓台中這個詞真正降落。」
融入城市需要用緩緩降落的方式,情感關係或許如是。言叔夏在《白馬走過天亮》裡〈月亮一宮人〉曾寫及對母親的恨意,但這份情感在《沒有的生活》似乎不再見到。〈野菇之秋〉裡,母親說:「不要在貓的面前換衣服,誰知道貓看到什麼。」聊到母親與貓的話題,言叔夏表示自己的家鄉位於高雄林園,相較於都會城市而言,屬於比較鄉村的地區,「我媽沒有寵物的概念,所以在她的感受裡動物會有一種神祕性吧。」此外,聊到旅行與出遊,母親也曾用閩南語說:「人親像鳥仔在飛。」或是「天黑了,如果現在還不回家的話,路會湧起來,撲天。」言叔夏說:「聽起來很像上個世紀的語言吧,但對我母親那一輩的人,距離是如此真實的事情。『湧』這個字,洶湧的,眼前的路好像瞬間變成海,會從你的周圍漲高,很浩大。」言叔夏描述她與母親的這些對話,聽起來好像馬奎斯的小說。
「母親與南方,可能是我生命裡很重要的記憶,我既不能回去,但又變成是我隨時攜帶的。」她說。
從高雄到花蓮,花蓮到台北,台北到台中,不知道作家的下一站將會前往哪些地方呢?可以確定的是,從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到《沒有的生活》,言叔夏從90年代主題出發,為讀者保留了更大的故事想像空間,那個在C城駕著車,一名為了聽完廣播電台正播放陳昇的歌,最終沒有抵達目的地的女作家。
言叔夏說:「這個『沒有』並不是指空空如也、一無所有,更像是一種辯證題。」
在這樣的散文質地裡,故事還在時間裡行走,正走進另一個沒有的時間。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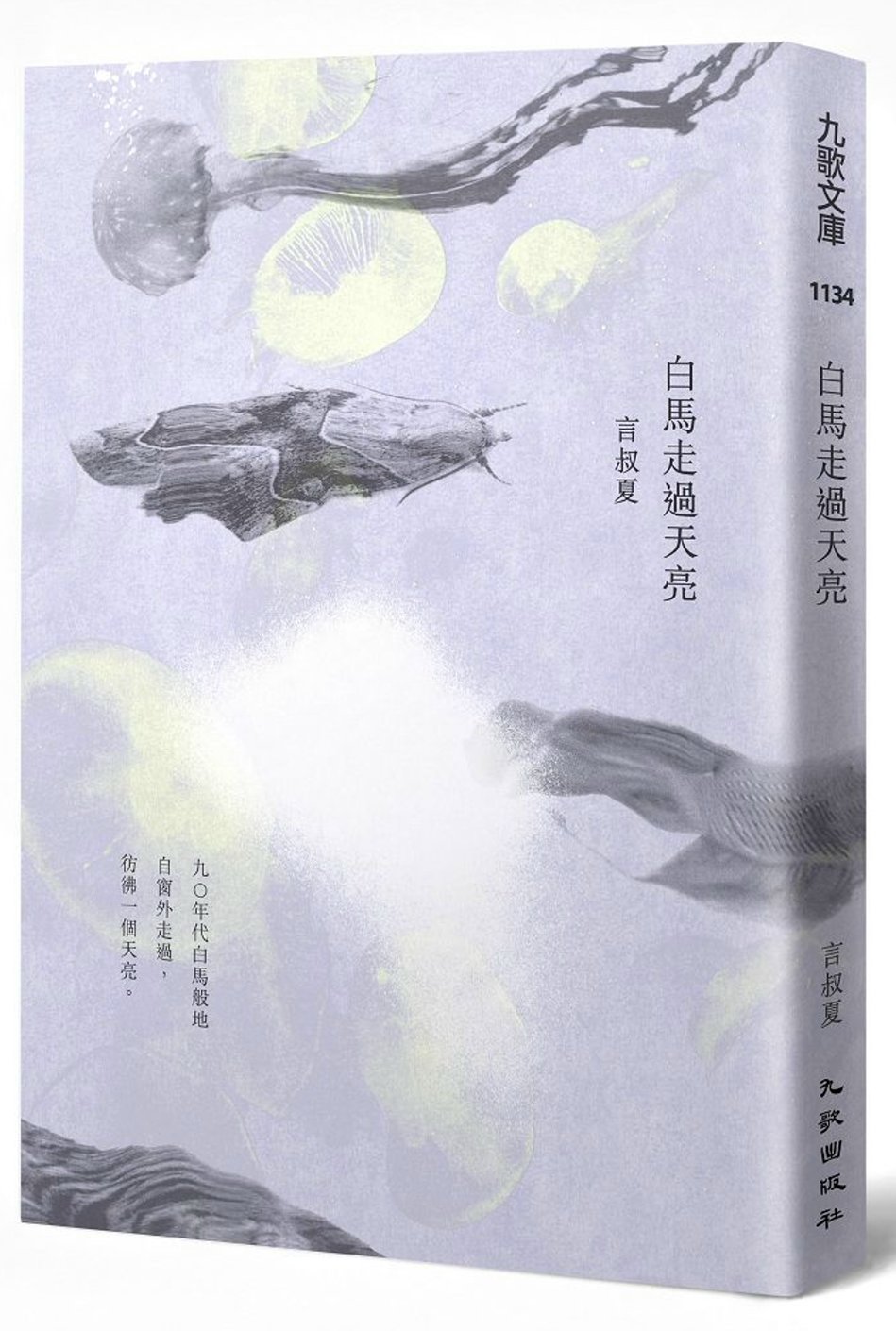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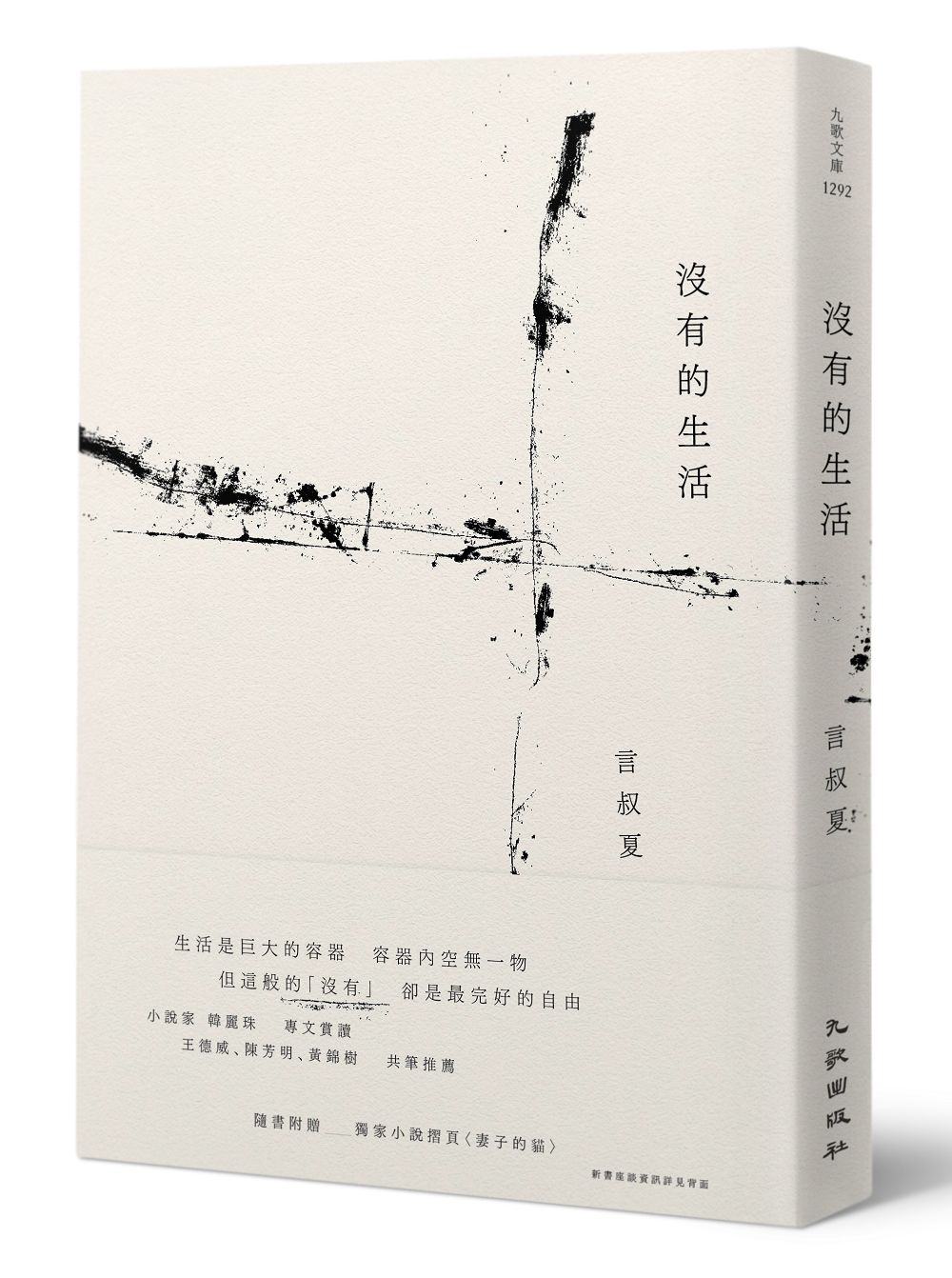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