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如果我的腦子是個小房子,目前正感覺有一處起火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房間,警報鈴一直響,灑水系統失靈中,到底是哪一個門後面有火舌?我走不出去我的走廊。是被什麼黏住了?夢的腹地總有沾粘性,而我潛意識的警鈴,為何跟我現在正嗅聞到的鳥語花香一點都不一樣?「兔子,快跑啊!」驟然醒來,我女友正沐在陽光中笑著看著我,我在這裡的哪一次是真的醒過來?
如果我的腦子是個小房子,目前正感覺有一處起火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房間,警報鈴一直響,灑水系統失靈中,到底是哪一個門後面有火舌?我走不出去我的走廊。是被什麼黏住了?夢的腹地總有沾粘性,而我潛意識的警鈴,為何跟我現在正嗅聞到的鳥語花香一點都不一樣?「兔子,快跑啊!」驟然醒來,我女友正沐在陽光中笑著看著我,我在這裡的哪一次是真的醒過來?
「兔子,快跑啊,兔子!」
跑去哪裡?前方還有灌木叢與果子香的味道,現在是快近夏天了吧?空氣中有甜味,好像聞到有人家要煮早餐了,是濃甜的鬆餅味,而我正要跑去哪裡?跑去雜草比人高,或是與這一切不同的生猛茂盛裡,讓人或獵犬都聞不到我氣味之處?
而我通常就這樣醒過來了。
醒來多時後,腦子裡還滯留著這段音樂,像跳針一樣反覆播著,我人正在一處陽光明媚的花園中喝茶,但那段歌詞像有人在跟我耳語著:「快跑啊、兔子。」是在叫誰?
如果我的腦子是個小房子,目前正感覺有一處起火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房間,警報鈴一直饗,伴著剛剛那段歌詞,灑水系統失靈中,我人還在走道中穿梭,到底是哪一個門後面有火舌?我這屋子的印象怎也跳針似的,我走不出去我的走廊。
自從跟女友蘿絲來到這小鎮後,我日漸以睡眠的狀態清醒活動著,同時也以清醒的狀態睡著,眼前這一切,像夢一樣紮實,卻不太像真實人生能轉個彎就離去。
是被什麼黏住了?夢的腹地總有沾粘性,而我潛意識的警鈴,為何跟我現在正嗅聞到的溫馨一點都不一樣?
無疑的,蘿絲父母是客氣又健談的,好像按一個按鈕,他們就會穿著他們喀什米爾羊毛衫擁抱你,那不禁髒的穿著、看來不宜隨便放置的瓷盤、那得隨時保持隙縫中沒灰塵的高級沙發、那過分乾淨的腳踏墊,包括他們家的女傭,都如此雍容,彷彿灰塵與油膩從來不存在於這家庭一樣。只有我跟她女兒是屬違和樣貌的,我們穿著粗布棉衫,即使企圖燙平了衣角,仍散發著等著想去郊區烤肉的輕鬆散漫,是怎麼回事的不對勁,這個家跟他女兒蘿絲看似是相互失去線索的存在,但他們仍看起來很親暱。
 蘿絲父母是客氣又健談的,好像按一個按鈕,他們就會穿著他們喀什米爾羊毛衫擁抱你。
蘿絲父母是客氣又健談的,好像按一個按鈕,他們就會穿著他們喀什米爾羊毛衫擁抱你。
這裡是有「什麼」一塵不染地叫人發毛嗎?
讓我聯想起我小時候曾看過一種女孩的玩具,它叫「莉卡娃娃」,是同學家的玩具,聽說是從日本帶來的,跟芭比娃娃有點像,它有自己的茶壺、杯碗、美好的少女氛圍房間、跟芭比都有好多套外出服與包包、它有它的購物與公主組合,讓你可聯想到它住的社區環境。它也都笑著,沒有像芭比笑得這麼開,是種優雅節制地笑,企圖親民的偶像微笑,但同樣空洞,一切歡迎光臨的敬謝不敏。有著它彷彿可以什麼都不知道;特權式的純真微笑,比芭比更極致地塞進了個靈魂假設:我可以選擇什麼都不知道的無辜樣貌。
它們的笑容,都是意識到了別人在觀看才有的笑容,這是令人覺得不寒而慄的地方。是誰在看,有多少人在看,為何它總覺得有人在看?
對,這裡的人就給人這個感覺,彷彿非要透過另外一個人的注視,它才有了相對完整的拼湊,但其實都是「它」跟「它」而已,這……一定是我想太多了,它們怎麼會是沒生命的,它們都在動作啊,還在款待我。
我找了我女友商量,「這裡怎麼怪怪的?」但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穿著發皺棉衫的她看著我,一股生活氣息襲來,是來自我們一起折扣買來的洗衣精,我似乎安心了一點,「你們家的女傭……(為何笑得像莉卡娃娃)?」我怎麼能說完這句話,大家會以為我瘋了。那位女傭的笑容無情無緒,我不能說每個黑人的笑容在白人社區都會帶著警戒,但在這社區一點觀望總是有的,再怎麼安心,也不會笑得如剛出爐的第一夫人,那是多麼不安心,才能笑出了這般銅牆鐵壁?
一點訊息都不走漏的笑意,難道眼前這鳥語花香裡,有什麼活生生的兇殘?
 「你們家的女傭…(為何笑得像莉卡娃娃)?」
「你們家的女傭…(為何笑得像莉卡娃娃)?」
那位黑人男園丁,是這一帶比較像活人的人,因他會走漏點情緒,但那情緒像是某種異味在底部翻攪,不合時宜的駕馭,無來由的憤怒,認定自己是少數擁有發怒權力這類榮耀的人,這不太像一個白人家族的黑人園丁。請原諒我的措辭,你可能認為我有歧視,但「歧視」這東西,不只深植在歧視者腦袋,對被歧視者也有著深層的暗示。即使我活在歧視並不明顯的地方,但我們基本上知道,歷史的刮痕,那就算經過海一樣的歲月,它還是在骨子裡翻騰著同一種戒備,這就類似除非你從小就生長在動物園,不然一隻天生天養的野獸是會觀望猛獸氣味的。
但他沒有,他夜半跑步的姿態,像是擁有了一台跑車;也像是拿著聖火的運動員,不是在健身,他在測試機能的最大值,所以嚇到了我。當然,你可以說我講的都是疑神疑鬼的話,當然可能有個想參加比賽的園丁、有一個過度從容的女僕,在這個零種族歧視的理想國,連記憶裡的一點警戒痕跡都沒有,難道我心眼太狹小,但只有在蘿絲弟弟出現時,這裡才真走漏了什麼,他在餐桌上直接挑釁我所謂黑人的體能,話中藏有攻擊,固然惹人厭,但與他父親強調的兩次都投歐巴馬當總統相比……等等,你想提醒我,難道我認為被歧視才是正常的嗎?
我承認我在這社區是有點錯亂,就像我跟我朋友說的:「我覺得不對勁到有點發毛。」事實上,當你走進了一個長期被洗腦的地方,「歧視」並不會被當事人意識到,因他們根本沒注意那構成了「歧視」。
腦子是怎麼洗的,首先蘿絲的媽媽以極度平和的方式,逐漸產生了我的焦慮,彷彿她的平和是因為我哪邊有所缺憾,而無法達到的境界。這樣強大暗示性的平和,像是邪教的入會模式,「你要到我這裡來才會平和喔。」平和權是屬於那人的,莫名地被摘除了情緒調整權力,我的焦慮就愈發尷尬的,在她面前失能得像剛被捕進網的魚,但她卻暗示我的緊張不是因為沒有水。
他們先改寫了外界人相處的關係,讓你看到了這裡無法質疑的和諧,攔截了你對世道的認知,然後你感受到他們的眼目無所不在,你以為是你的錯覺,當然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只是你的一句懷疑,都會被回應:「沒關係,都這樣的,你怎麼了嗎?」一如蘿絲的反應,這裡的確是四周一團和氣的「那我是怎麼了?」
 八成是自己怎麼了,才會感到這祥和底下有密密麻麻的惡意。
八成是自己怎麼了,才會感到這祥和底下有密密麻麻的惡意。
然後無意間與女傭在二樓俯瞰自己的冰冷眼神對上,那麼祥和的日常,總偶有這一瞬間,讓你懷疑是自己錯看了什麼,以至於露西母親在問診室的「平和」有一定的高度,八成是自己怎麼了,才會感到這祥和底下有密密麻麻的惡意,正鑽進我的身子裡,要被栽種出什麼更巨大的「祥和」出來。
事後回想,那一場親友的聚餐,也就是我身體器官的競標大會。人們的確是祥和的,那裡沒有什麼稱得上歧視的,被認知到那件事真的存在才有「歧視」,本來不該存在的,對他們而言,一秒都稱不上歧視的感覺。那裡顯然已經封閉許久了,以隔離他們認為外界的「紛亂價值觀」,他們的封閉不是離群索居,而是有足以保障他們思想空中樓閣的位置,但那也是一種洗腦,他們看到的世界仍是城堡狀的,有巨大城池的劃分,而外面是狩獵的獵場。
他們對我的洗腦,則適用在各種人身上,以當事人不確定周遭真實的錯亂,提高了自我懷疑,從這認知縫隙中借力使力,揪住了你所不能釋懷的那點,然後像寶可夢一樣打開盒子,以你那磁鐵般的過去將你吸了進去,墜入那雙平和眼皮下的深淵裡,那平和下面什麼都沒有,就你被夢的重量拖住了,夢的那端怎麼像鉛球一樣,過去的沾粘性強,有時只消別人象徵性的把門重重一關。

那女傭被問及「還好嗎」的錯亂表情,與在宴席中被認出而恍然清醒的另一個黑人,被借用了身體的他們靈魂突然狂亂敲打著門,因為只有一瞬間能浮出水面。被抹去了、被扼殺了,因催眠被困在腦內記憶迷宮的最底層,「這是什麼地方,怎麼找不到門?」我終於抓到外面的一點線索而得以甦醒逃跑。
這可以是一個訴說歧視的故事,更可以說是外力能刪除他人自我的方式,人們不明白邪教的信眾怎麼會被控制,不見得是藉由催眠,光是製造出那個環境的完整,讓你成為那裡面的一個髒點、或成為那裡面一個至高無上的執行者,你可能就接受了那暗示,沉入那只有井向深度的地方,一生或許只有一、兩秒鐘的時間,你會呼出一口氣說:「逃啊、快逃。」
這表面上是個鎮,其實是記憶可被錯寫的一攤水,記憶一撲通,有人就跌了進去,那記憶的網裡綿綿密密,你分不清是被長期資訊催眠了而歧視,還是全部價值觀都被改寫,我女友蘿絲或許很早就沉進去,沒有活過似的,只剩「莉卡娃娃」那純粹為演繹消失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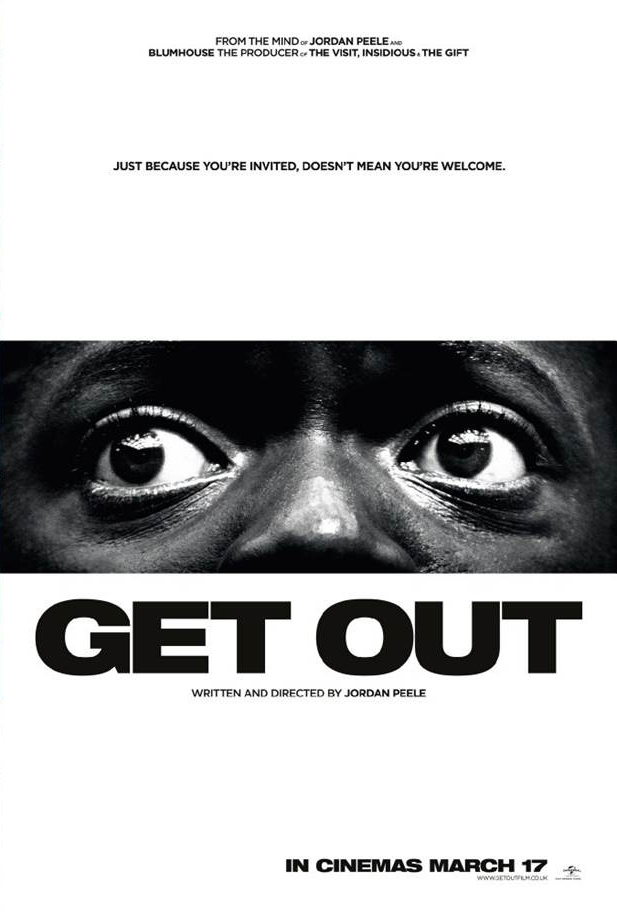
《逃出絕命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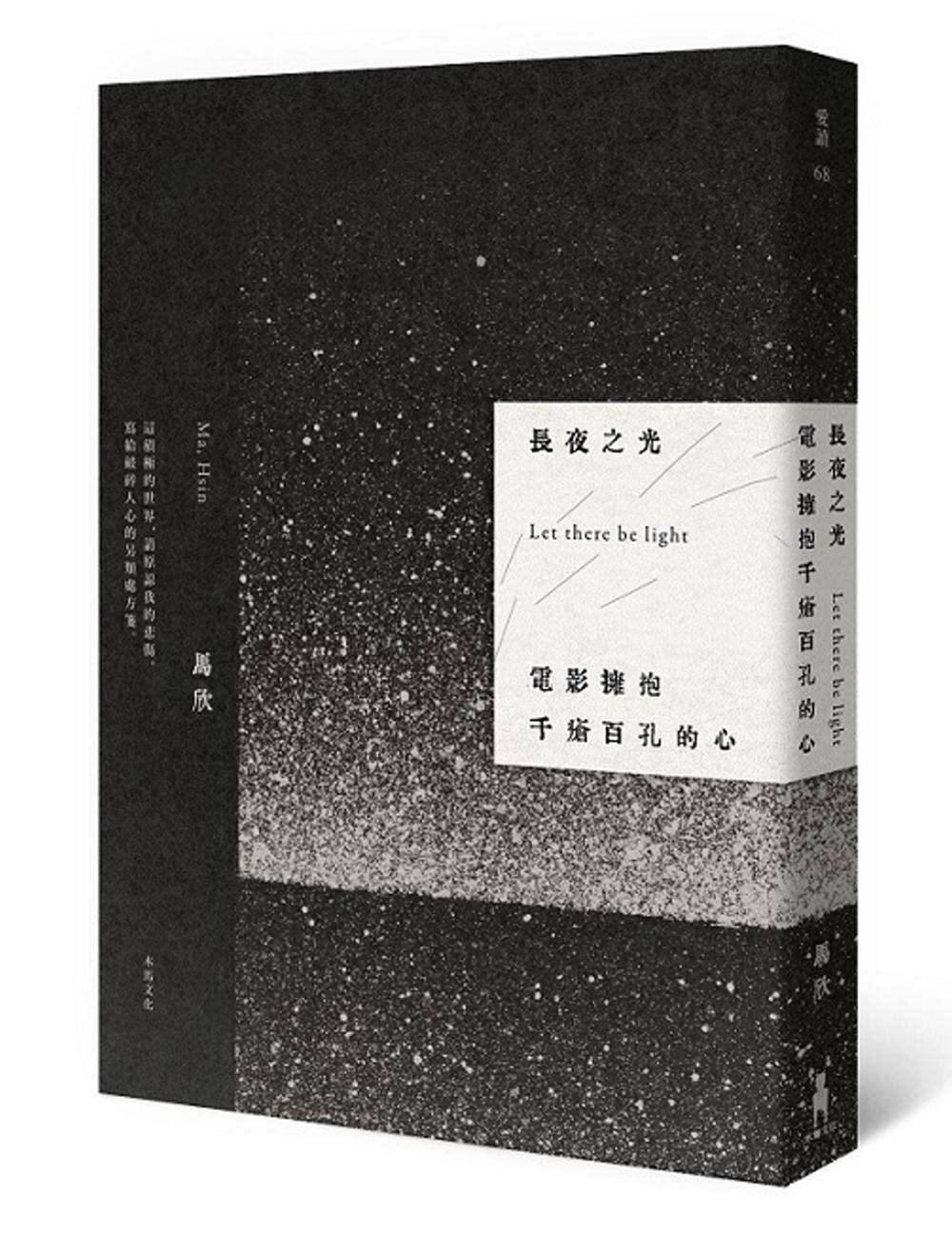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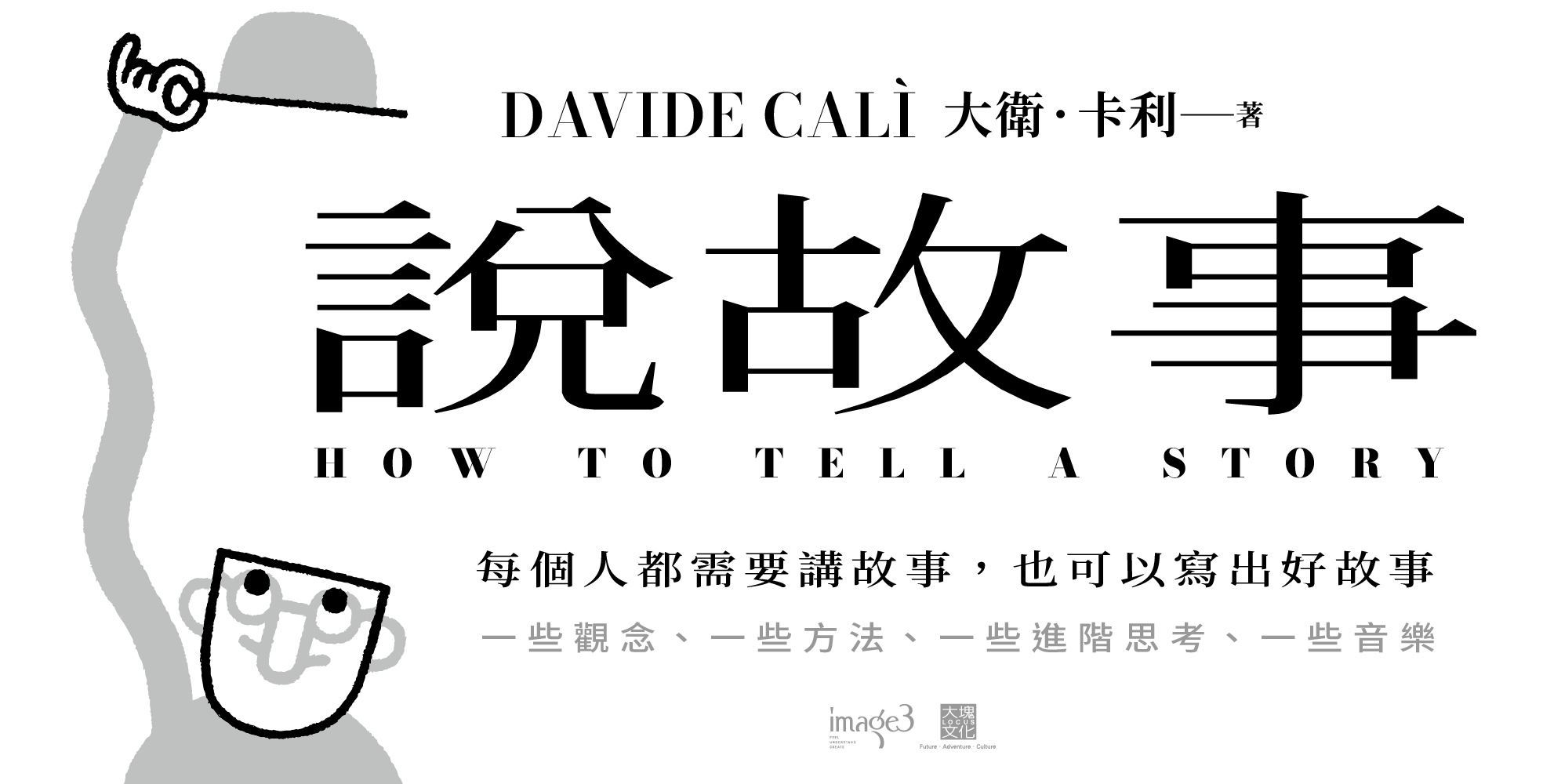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