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之初,我也曾被退稿。
編輯嫌我的翻譯太難懂,好心從對岸找來同一作家舊作的譯本,供我「參考」。在這之前,我只讀過這位大師級男作家30年前爆紅的禁書,淺顯易懂;但這一本主題嚴肅,筆觸偏硬,敘事者夾敘夾議,議多於敘,批判語近似引經據典、用盡生難字的老教授。我讀了編輯提供的簡體譯本,竟聯想起國中女同學之間瘋傳的《燭光下的羅曼史》叢書。我果真照這筆法簡化手中的這本難書,大師能饒過我嗎?
現在回頭看,那本書其實不算太難。十幾年前,我讀到坦尚尼亞裔英國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納 (Abdulrazak Gurnah)的簡介,在美國遍尋不到他的小說,上網才知他的舊作多數已絕版。2021年託諾貝爾獎之福,英國出版社終於重新推出他的作品,但在美國實體書店依然不見上架,難怪他得獎後感嘆,「但願讀者多一點就好了。」
BREAKING NEWS:
— The Nobel Prize (@NobelPrize) October 7, 2021
The 2021 #NobelPrize in Literature is awarded to the novelist Abdulrazak Gurnah “for his uncompromising and compassionate penet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lonialism and the fate of the refugee in the gulf between cultures and continents.” pic.twitter.com/zw2LBQSJ4j
英文非母語的古納作品難在文化深度,也難在複雜綿密的敘事風格。我在翻譯古納的《海邊》(By the Sea)時,見亞馬遜英國賣家有書可買,但鑑於大疫期間海運延誤的教訓不敢下單,只能照編輯給的 PDF 版列印裝訂成工作書,磕磕絆絆讀到第三章差點棄讀,總算親領作者知音難尋的苦處。
《海邊》敘事者是一個從東非桑澤巴群島(Zanzibar)冒名逃至英國的老難民薩雷,在異地省思宿怨,批判殖民時代怪象,充滿流落異鄉的愁緒。頭兩章由薩雷自述倫敦機場、拘留所、民宿的流程,混合些許往事,時序紛雜,一再提起他不想申請電話,開篇第一句就以家裡沒電話做文章。到了71頁,進入第三章,出現以下標題:
Latif
3
由於第一章上面寫著「文物」,第二章只標數字,我不明白「Latif」指的是什麼。沒關係,反正我工作的第一階段是抱著一般讀者的心,純欣賞。這一章開頭,敘事者說,「我在街上被罵黑摩爾(blackamoor)」,接著冗長詳述被歧視的前因後果。隨後,敘事者進辦公室查字典,研究「黑摩爾」的典故,追索出曾寫「黑摩爾」這字的古英國眾作家,進而扯到1960年代好萊塢鉅片,再從電影拉回19世紀英國玄學書裡提及的黑摩爾:「與現實之落差,一如太陽與黑摩爾人之別。」
我以為時光前進幾年,老難民薩雷在倫敦覓得教職,成了一個教詩寫詩卻恨詩的老師。怪的是,他不但有電話,而且還裝了答錄機。愈往下讀,眼皮愈重,腦霧愈濃。假使這本是閒書,早被我扔進回收桶了。文學譯者能如此灑脫該多好。隔天,我強打起精神,從頭來過,發現前兩章曾寫 Latif 是倫敦某大學的專家,才知第三章的敘事者悄悄被調包,換成了 Latif 。
第四章呢?只見數字 4。幸好開頭是「我曾拜訪過薩雷」,看得出敘事者八成仍是 Latif。這兩人年齡相差一代,但背景雷同,談吐用語也相近,家族祕辛有不少交集,我邊讀邊默念 Latif,避免又誤以為「我」是薩雷。來到第五章:
Silences
5
開頭是,「我在家門口看著他上樓來。」這次小譯者沒上當,立判敘事者換回薩雷,因為上一章 Latif 考慮去薩雷家。之後的「我」也全是薩雷。Latif 的自述共佔全書三分之一,我建議編輯為第三、四章換字體。
除了考讀者專不專心、有無耐性,本書還是一台練腦力的騎馬機。敘事者兩人的身世都很複雜,各有龐雜的親屬和續絃再嫁的對象,有些角色更有不只一個名字,以分別上下輩子或不同視角。此外,兩家糾結的亂源起於三方借貸和遺產繼承,而且回憶的時空不斷切換,頻頻岔題,這全是原文內建的難度,都屬於原著的內涵,譯者無權更改。但話說回來,作者古納的心願是多一點讀者,編輯也是,小譯者更不想再發表一刷即絕版的冷門書,於是下筆時能為讀者著想就儘量體貼,以不背叛原作為限。
東非人的姓名觀念有別於多數民族,傳統上是「名+父名+祖父名+曾祖名」,作者藉故事解釋過,譯者無需加註。提起 Latif 的酒鬼父親時,作者不厭其煩列出他的三代全名,更屢次附加他的工作單位,想必是為了避免人物混淆,我在處理其他角色時也比照作者意思,儘量在名字之外多加親屬稱謂和職業。有一大段,作者刻畫酒鬼的父親和祖父,說他的父親貪色也貪杯,到最後「他」是誰變成莫宰羊,我乾脆一律以「酒鬼的長子、Latif 的哥哥哈珊」為輩分基準點。段落落落長也是古納的長處,我選在敘事時空轉換的節點,建議編輯另起一段。
古納也愛倒敘插敘,常常先爆事件的結果,然後才慢慢說明由來。例如,薩雷在倫敦機場通關時,作者先寫「我在驗護照時被帶走。」緊接著:
我在海關人員面前呆立有點久,等著被掀底,等著被逮捕,等了一陣,海關才說,「護照」。
「被帶走」是下一段的場景,為避免誤解,我翻譯成「在我被帶走之前,我在海關人員面前呆立...」,也可保留作者敘述順序的原味。
此外,作者也常以人稱代名詞起始,句末才指名。以本書的開篇句為例:
She said she'll call later, and sometimes when she says that she does. Rachel.
瑞裘她說過,她晚點兒會來找我。當她說她會來,有時會果真上門來。
英式英文的動詞 call 有雙重涵義,作者緊接著界定這 call 不是「來電」:
她寄明信片通知我,是因為我的住處無電話。我拒裝電話。
在眾多角色之中,有個美國抄寫員也過來串門子。故事裡多次引用維爾梅爾1853年短篇小說《抄寫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 ),以形容職員拒絕配合、堅不妥協的姿態,純讀者只需心領巴托比的詭異冷峻和律師事務所老闆的無奈,譯者卻要延伸閱讀,否則會把兩百年前俗稱 Tombs 的「曼哈頓看守所」誤譯為墳墓。阿拉丁神燈的故事無人不知,作者寫了兩三頁介紹漁夫智取精靈的來龍去脈,巴托比的故事沒人聽過,作者卻零星東提一句西提幾字,苦了小譯者。哪個譯者心領之餘,膽敢在抄寫員初登場時加註兩三頁?
心領是讀難書的要件,看似累贅的描述和插播,若沒被作者或編輯刪除,在全書裡必定各有涵義,精讀能比跳閱多一層收穫,這正是同一本書為何有多種詮釋、每次重讀都有新發現的主因。例如,薩雷住進中途之家,逐一細數著房間裡的擺飾,表示自己對這些雜物絲毫不感興趣,懶得去揣測情慾暗湧的英國女主人為何珍藏這些小玩意。其中有個餅乾盒,畫著皇家海軍艦長四周堆滿日不落國盛產的果物,盒裡散置著鈕扣、徽章、羽毛。我讀到這一段不僅無感,還暗酸薩雷明知無意義還囉嗦這麼多幹嘛。譯完初稿後,我去英國一趟,新王剛登基的倫敦旗海飄揚,遙憶大英盛世的熱帶花果圖屢見,我剎然領悟:英國女主人雖以言行支持移民,私底下卻心繫殖民時代的霸業,而她和東歐小鮮肉難民的曖昧互動,可被解讀為帝國又妄想吃窮國豆腐。不過我相信,編輯和讀者都不准譯者在故事裡多嘴,作者更會跨海反對。
贅述不得刪也不得註,但譯者可以代讀者簡化怪句。大報書評人曾舉這句為例,可不是我手滑喔。
Can an I ever speak of itself without making itself heroic, without making itself seem hemmed in, arguing against an unarguable, rancouring with an implacable?
「我」這字為自己發言時,可以不把自己吹捧為英雄嗎?可以不把自己描述為腹背受敵、勇於向威權嗆聲、不惜與惡勢力結仇嗎?
譯者也可在小語種詞彙上幫一點忙。英文版讀者見外文,只需從上下文略知大意,通常不會查清這些外文的定義。伊斯蘭文化是古納故事的佈景,書裡常見阿拉伯語和斯瓦希里語的祈禱文、稱謂、問候語,也有印度文和波斯文,譯者都要善盡義務,但桑澤巴群島的族裔多元,加上作者常有自創的拼法,有些字百查不出真義。為了翻譯這本書,我認識了 Emilian M. Mbassa 先生,他為語言學習平台 Duolingo 撰寫斯瓦希里語教材,和作者是同鄉,幫我解決了不少難題,但連他都不清楚書裡有些字是什麼意思。例如:
They were sitting skut sakit until the danger was past.
我甚至猜不出 skut sakit 是哪種語言。是盤腿的坐姿嗎?或坐得很靠近?或如坐針氈?不得而知,只能向作者求救。古納更早期作品《天堂》(Paradise)的譯者何穎怡告訴我,她問作者也一直沒接到回音。於是我和她取暖之餘,請來《來世》(Afterlives)的譯者翁尚均集思廣益,分居三國的三個譯者共組何姐笑稱的「自救會」,互相照亮彼此的死角,最後由翁何判定 skut sakit 是「安靜不動」。(註:一個月後,作者回應了,正解果然是「安靜」)。
古納的小說再難,終究不敵千古奇書《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連西班牙文版都遲至2016年才問世。中文譯者梁孫傑教授表示,喬伊斯的這本小說循著「混沌語宙」(chaosmos)之邏輯,充滿新造字、混合字、文法錯誤、顛三倒四的語言,使閱讀本書至為困難,堪稱西洋文學史上最難懂的一本小說。書中內容雅俗皆陳,生死並俱,在浩瀚的文字迷宮中讓讀者暈頭轉向。閱讀既已困難,遑論翻譯?但他也告訴我,「翻譯是很困難,不過也是因為困難,才會有無窮的樂趣。」所以錢少又欠罵的這一行才有傻呆瓜前仆後繼。
根據《紐約時報》,古納1994年推出《天堂》至他獲大獎前,近30年在美國只賣不到六千本。如果何穎怡的繁中版能一舉衝破六千大關,讓古納看見台灣,譯者是否也該記功?以我的《海邊》譯本而言,沒被編輯退件、沒被讀者嫌難懂就偷笑了。交稿後,我刪除記憶庫,不想再憶古納,因為,比《芬尼根守靈》簡單的下一本難書正排隊等著蹂躪我。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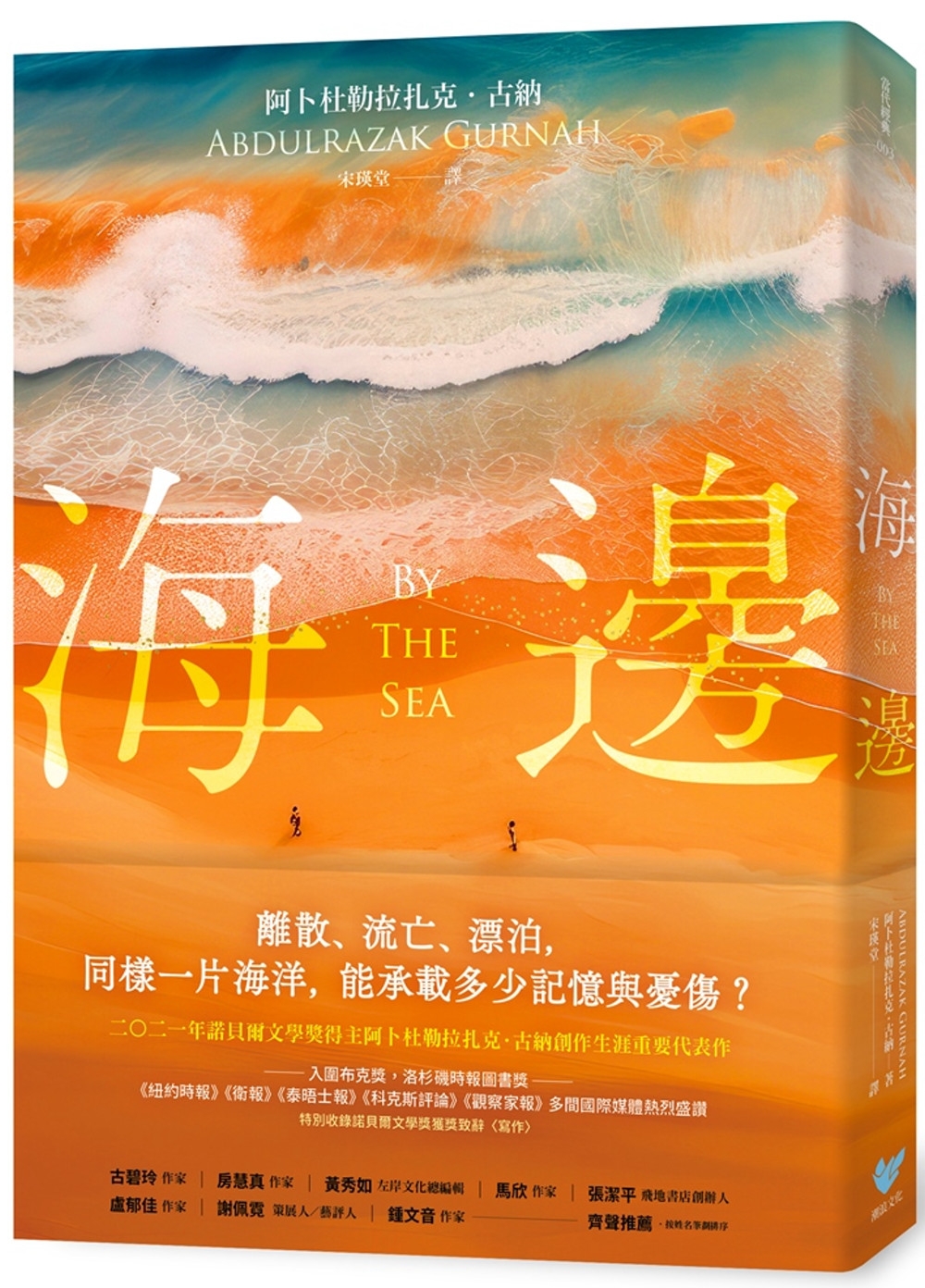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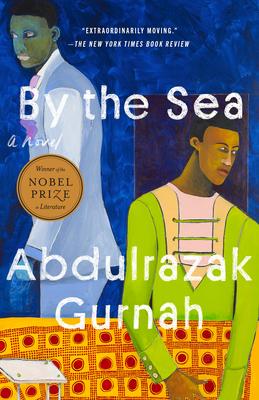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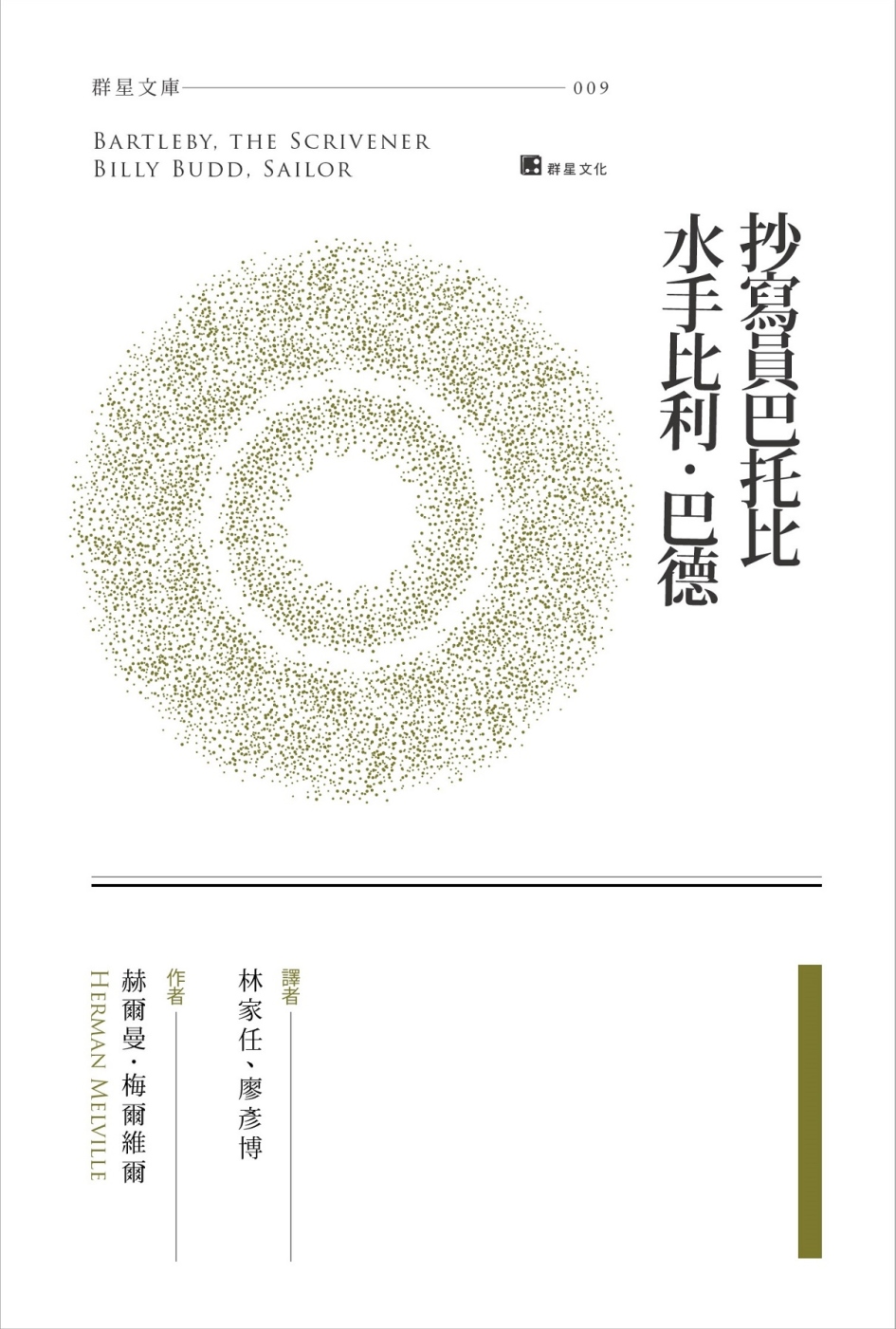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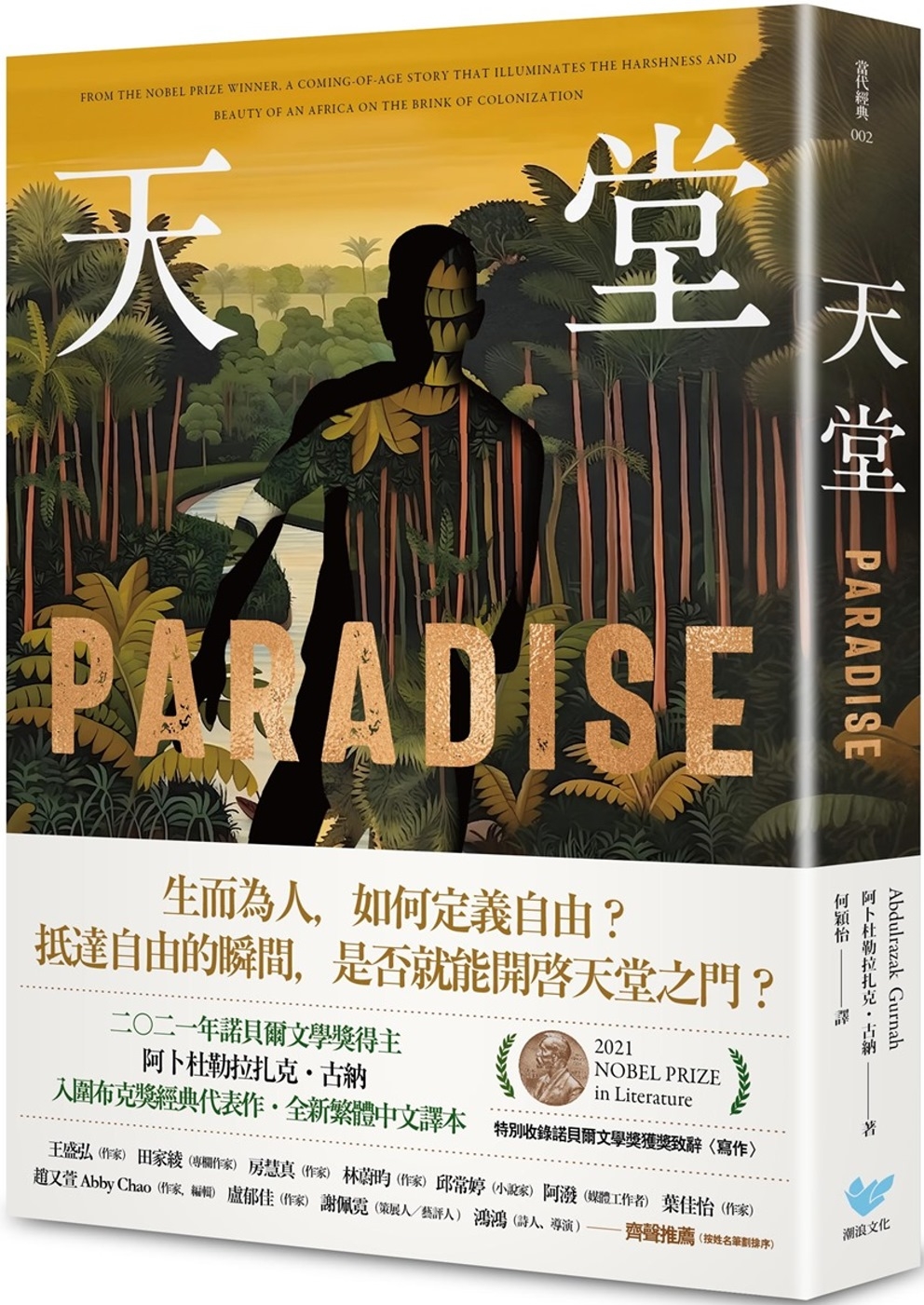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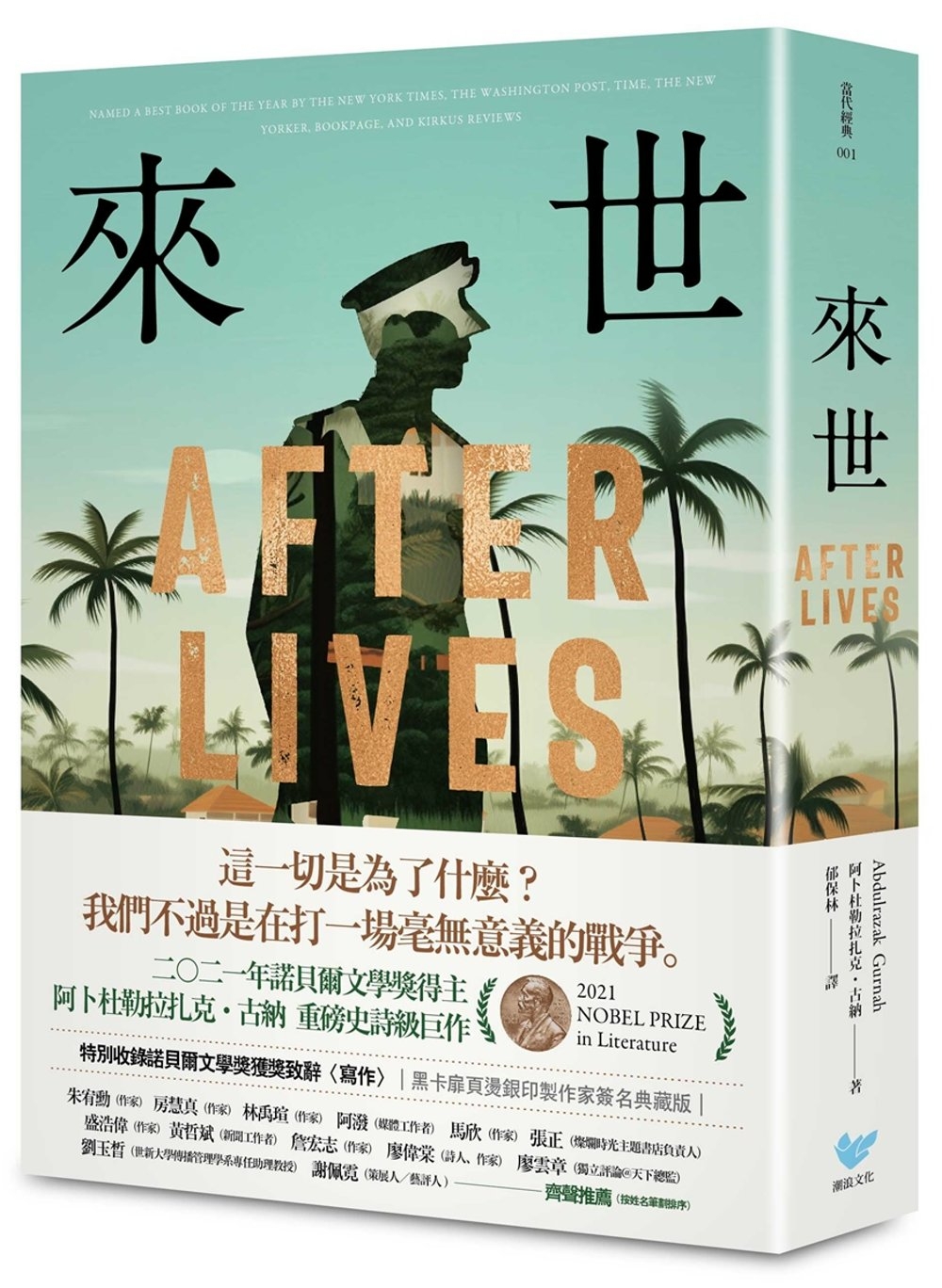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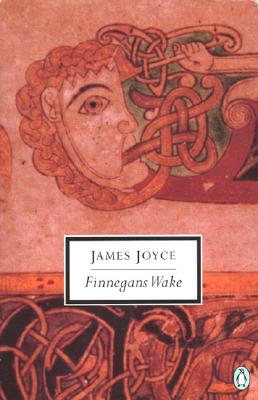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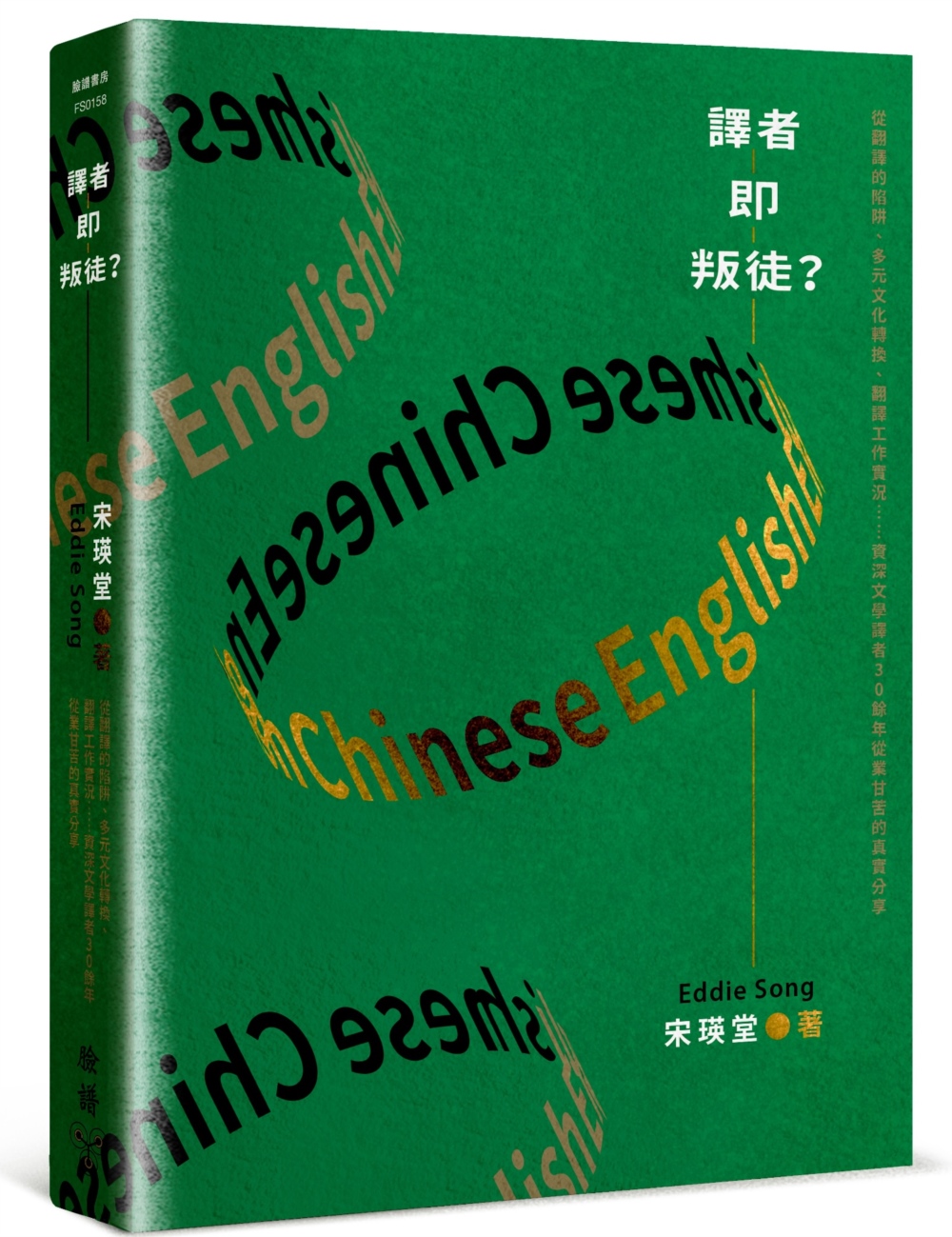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