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譯註要不要加?怎麼加?加在哪裡?(圖/pixta)
前進西班牙的美國正義型男死定了。
型男衝到塞維亞大教堂,躲進一旁的鐘塔,走迴旋梯溜上去,殺手尾隨而至,一次飆三階直追。一陣槍戰之後,型男死裡逃生,一次蹦四五階跳下樓,中彈的殺手倒栽蔥向下一直翻,轉了五次才躺平,只差12階就滾進院子。
西班牙這座鐘塔俾倪全城,是觀光客打卡的夯景點,走上去的人都知道,古塔為了方便驢馬車上下樓而設緩坡,不設階梯,絕不會發生作者描述的「階梯很陡,摔死不負責。」這小說鹹魚翻身爆紅後,塞維亞市府出面聲明鐘塔裡無階梯,並且強調:「本鐘塔落成至今900餘年,從未發生遊客失足致死之情事。」
一般讀者就算沒去過西班牙,英文停留在高中程度,左看作者是美國暢銷書名家,右看小譯者只翻譯過幾本冷門書,你認為讀者會信任哪一方?
何況,懂英語的讀者假如去塞維亞打過卡,上過那座鐘塔,也知道 step 是「步」也是「階」,會不會懷疑這譯者搞錯了,原作裡的 steps 在這場景指的是「步」而不是「階」?
剛出道的小譯者被卡在虛實之間,好為難,為了找台階下,於是在這裡加了一個譯註:
鐘塔並無階梯,只有35道緩升坡。
短短一句鐵的事實,竟引來讀者追殺:「這個宋瑛堂自以為是誰啊?」
看電影時,男女主角正要壁咚,前座觀眾竟拿起手機猛滑,後座驚傳K瓜子聲,戲裡戲外醞釀好久的情慾頓時被潑冷水,讀者在行文裡撞見譯註也同樣掃興,所以註解旁移後移是許多編輯的抉擇。
無論中英小說,現代原創作品少有註解,主因正是避免跳 tone 害讀者出戲。然而,原文勤加註解的經典小說比比皆是。1851年名著《白鯨記》(Moby-Dick ) 原文不僅下註20幾次,有幾章甚至可以說全是註解,例如第89章藉主人翁之口詳述捕鯨信號旗的古今用法,把作者的解釋全融入故事,分章詳述。網路流傳的免費電子書更把註解字體放大為正文,令讀者難以分辨。新譯本譯者陳榮彬教授告訴我,梅爾維爾「可能因為他的東西太駁雜,一來為了服務讀者,二來為了顯擺自己的知識,才會加那麼多東西,閱讀上的確非常繁冗,難怪今日世界的版本刪除那兩章,而且另外還刪了非常多東西。」陳榮彬接著引用「豐厚翻譯」理論,表示註釋可呈現文字背後的豐富文化背景。
無論用意何在,作者下的註解都非譯不可,由不得譯者做主。《湯姆歷險記》中,湯姆和哈克聽見一條狗在長嗥,嚇得半死,湯姆再仔細聽,認出這是「布爾·哈畢森」的悲鳴。作者馬克.吐溫在此加註:
如果哈畢森先生家有個名叫布爾的奴隸,湯姆會稱呼他是「哈畢森的布爾」,但如果名叫布爾的是兒子或狗,就稱為「布爾.哈畢森」。
既然湯姆知道這是狗叫聲,身為譯者的我覺得這註釋可有可無,但在百年後「黑人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的今天,馬爺的註腳更能平添一股黑奴不如狗的哀戚。
在同一本書裡,「西部」指當時的密蘇里州,不是現代人熟知的美西,譯者加註可澄清古今地理觀。另外,怪異的舉止「吸吮拐杖頭」不含性暗示,是那年代紈絝子弟耍帥的動作,我認為也需說明。
除了古今差異外,雙關語更是翻三漏四的譯者超難題,處理時以符合原文想製造的效果為主,無法兩全其美時只好加註。2015年奧斯卡熱門片《間諜橋》的原著《間諜橋上的陌生人》中,有一位畫家為鄰居畫一幅油畫,在一旁的桌上畫了一台短波收音機,畫家說這象徵畫中人具有「活躍的智識」。作畫者有所不知,這位鄰居其實是蘇維埃駐紐約特務。「智識」(intelligence)另有「情資」的含義,這畫家是否知情不報,耐人尋味。作者刻畫這一段,難道意有所指?既然作者詹姆士·唐納文(James B. Donovan)已故,我決定加註說明 intelligence 的弦外之音,讓讀者親領國民法官的滋味。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納(Abdulrazak Gurnah)擅長從被殖民者視角書寫非洲桑澤巴群島(Zanzibar)故事,當地位於中東、印度、東非貿易三叉路口,族裔文化複雜。在小說《海邊》(By the Sea)中, musim 出現28次,英文字典裡查不到,上網求 Google 大神卻被當成錯字,吐出的連結通篇是穆斯林(Muslim)一詞的搜尋結果,不熟桑澤巴風土的人只能順著作者的字,邊讀邊學, musim 也算是故事裡春去秋來的配角,有待讀者耐心去撥雲,慢慢內化這字隨洋流飄來的海角味。其實 musim 是斯瓦希里文的「季節」,譯者如果只翻譯成各地都有的「季風」,或在此加註,豈不洩盡作者的氣嗎?畢竟,作者大可寫全球都懂的英文 monsoon,不必搬一個小語種出來燒腦。有英文版讀者就笑說,故事裡是有不少外文,但不影響閱讀。由此可見,對部分讀者而言,古納的作品屬於跳閱式,求知慾薰心的讀者查到底也未必查得出學問。
翻譯作品因有文化隔閡,註釋有助於減少語義落失,能混進行文裡就無痕詮釋,例如「白廳」可翻成「英國政府」,上下文提到行銷時,「麥迪遜大道」可釋譯成「美國廣告界」。但在人物的對話中,在角色的嘴巴硬塞幾個字反而奇怪。以小說《該隱與亞伯》的續集《世仇的女兒》為例,1950年代紐約人攔下計程車,對司機說:「艾德王爾德機場(Idlewild Airport)。」假如翻譯成「舊稱艾德王爾德的甘迺迪機場」,像話嗎?翻譯成大家熟知的「甘迺迪機場」呢?略懂近代史的人知道,甘迺迪遇刺、機場改名是1960年代的事。簡單譯成「機場」最省事,又不用加註,但曾進出紐約的人都明白,紐約機場不只一座。不加註呢?年輕讀者會不會以為這機場遠在紐約外圍的不知名小鎮?
以對話為主的圖像文學更難下註腳。在《薩賓娜之死》(Sabrina)中,薩賓娜失蹤後,男友憂愁到不吃不喝,某人勸他看開一點:
Look at Patty Hearst. Anything is possible.
拙譯:
「報業鉅子赫斯特(Hearst)的孫女派蒂不也被綁架,一年多之後還活著。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派蒂·赫斯特被綁架後「棄明投暗」,被感召成壞人,成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教科書範例,以其傳奇事蹟為本的著作和影視不計其數,美國人大多知道她是誰。我為了幫助中文讀者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加了「報業鉅子的孫女不也被綁架,一年之後還活著」。但編輯覺得這樣還不夠,在同一頁底下另加:「於1974年被美國左翼組織共生解放軍綁架,19個月後被尋回,」以加深讀者對她的認知。
譯者加註的另一功能近似燒狼煙,提醒編輯留意哪些地方是爆發筆仗的熱點,因為除非譯者拖稿,除非譯者明言要求,除非譯稿裡出現難題,否則校對不會主動聯絡譯者。我曾經翻譯一本非小說,作者廣蒐資料,難免有錯,誤植的數據和事實多達十幾處,我花了好大功夫找證據提問,作者卻不回應。例如,書裡提及《魯賓遜漂流記》作者丹尼爾.笛福在另一本小說裡「虛構出一種稱為 Combinator 的機器,能把人從中國送上月球。」我查到笛福有一本小說 Consolidator,故事裡也涉及登陸月球一事,所以我加註說明作者可能誤植,編輯最後決定照原文翻譯成「結合機(Combinator)」。果真是誤植的話,錯在作者,責任不應丟給譯者去扛。這位英國作家也誤以為美國有個「西達科他州」,苦了繁中版編輯。
註腳無盡多,煩不勝煩卻也覺得不讀不行的例子也是有的。1996年,美國青年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發表後現代百科全書式小說《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全書近一千頁,結尾附「註解與勘誤」,共計388條,佔滿96頁之多。這些註釋有的能為故事增添背景,有些是正文的分支,令我覺得條條可能都值得一讀,所以特別在後面再夾一書籤以利查閱。當年有電子書該多好。其中一條註釋甚至長達八頁,註釋裡還另加註釋。難道是華萊士竭盡揶揄讀者之能,故意讓讀者出戲再出戲?作者這玩笑開大了,我中途氣餒拔除兩個書籤棄讀,所以至今不明白華萊士的用意。
譯註也可以無盡多嗎?《科技X愛X12則奇思妙想》中,作者珍奈.溫特森考證後認為,貴族詩人拜倫女兒愛達.洛芙萊斯(Ada Lovelace)不但率先寫下第一條程式,預見計算機的潛能,更翻譯了法文期刊裡有關電腦始祖「分析機」的文章,她「一面翻譯,一面加進自己的註腳,篇幅之多,將近原文的三倍。」結果這譯本帶動後世鑽研開發計算機。原來,善盡職責的譯者也可以開科技先河。
這個愛達.洛芙萊斯,自以為是誰啊?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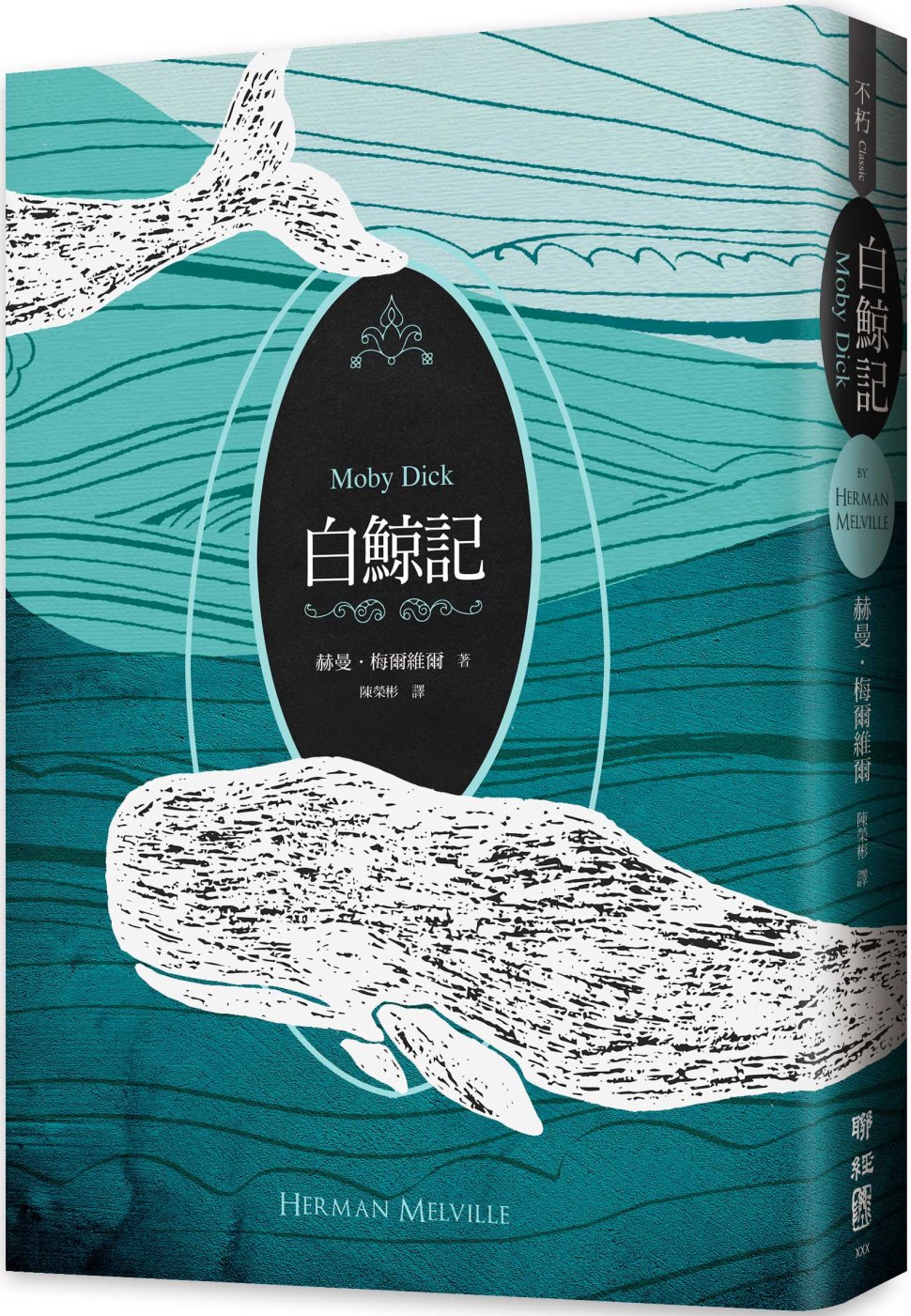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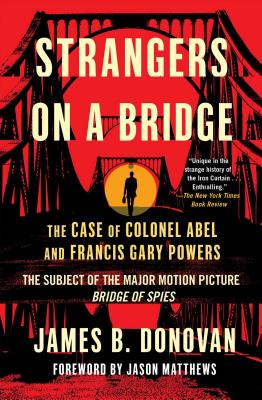
 間諜橋上的陌生人
間諜橋上的陌生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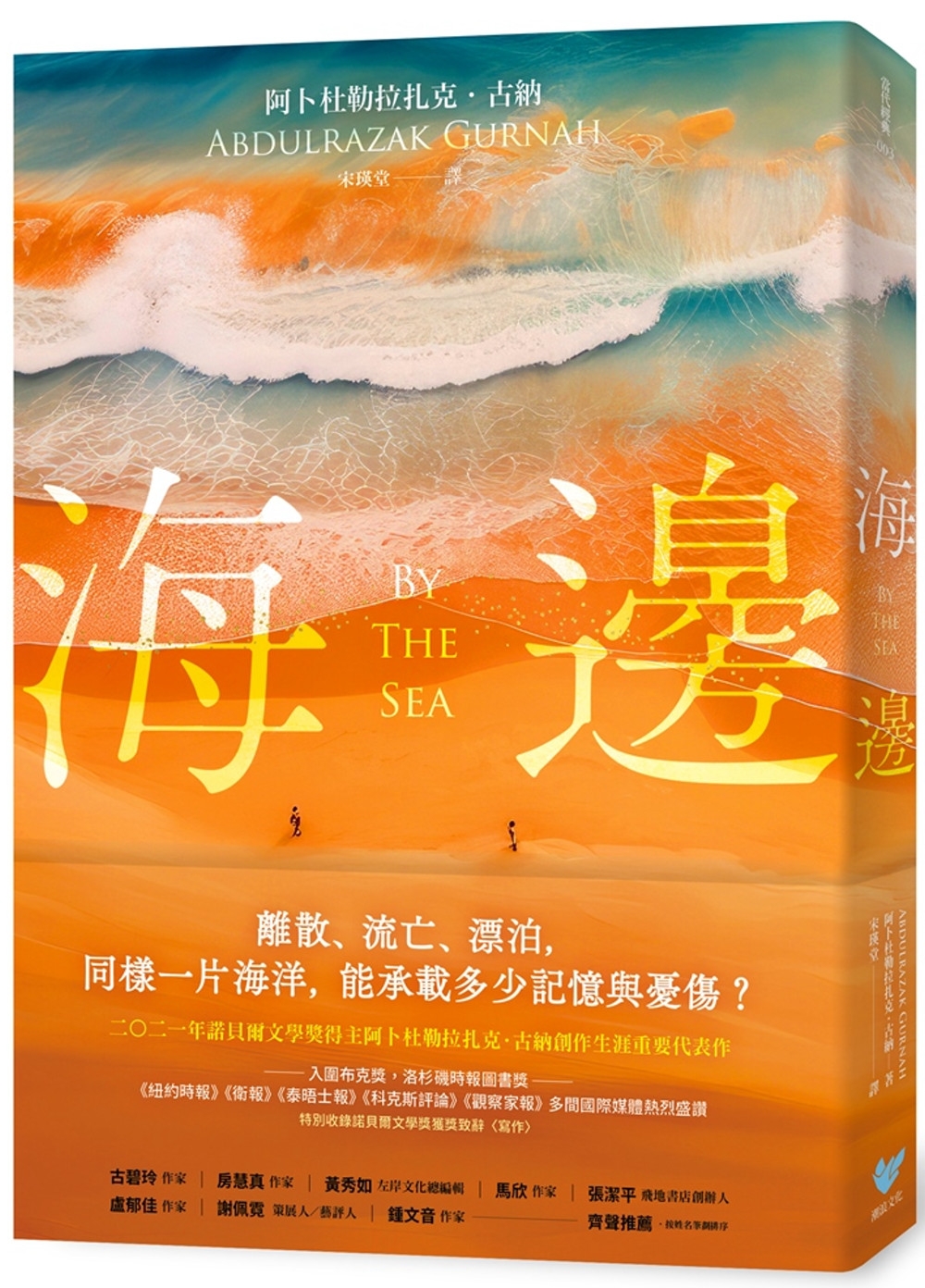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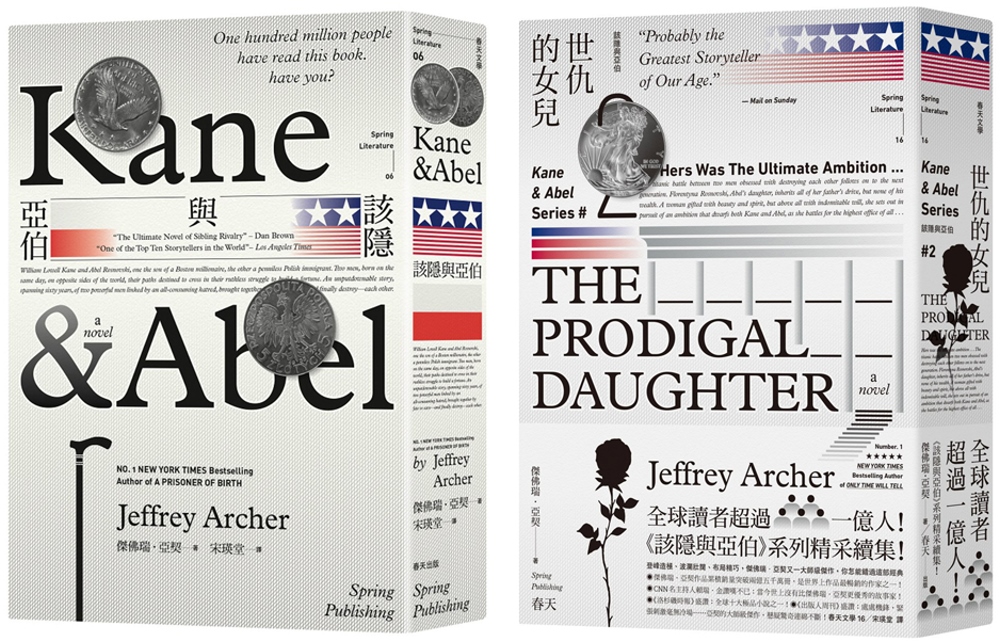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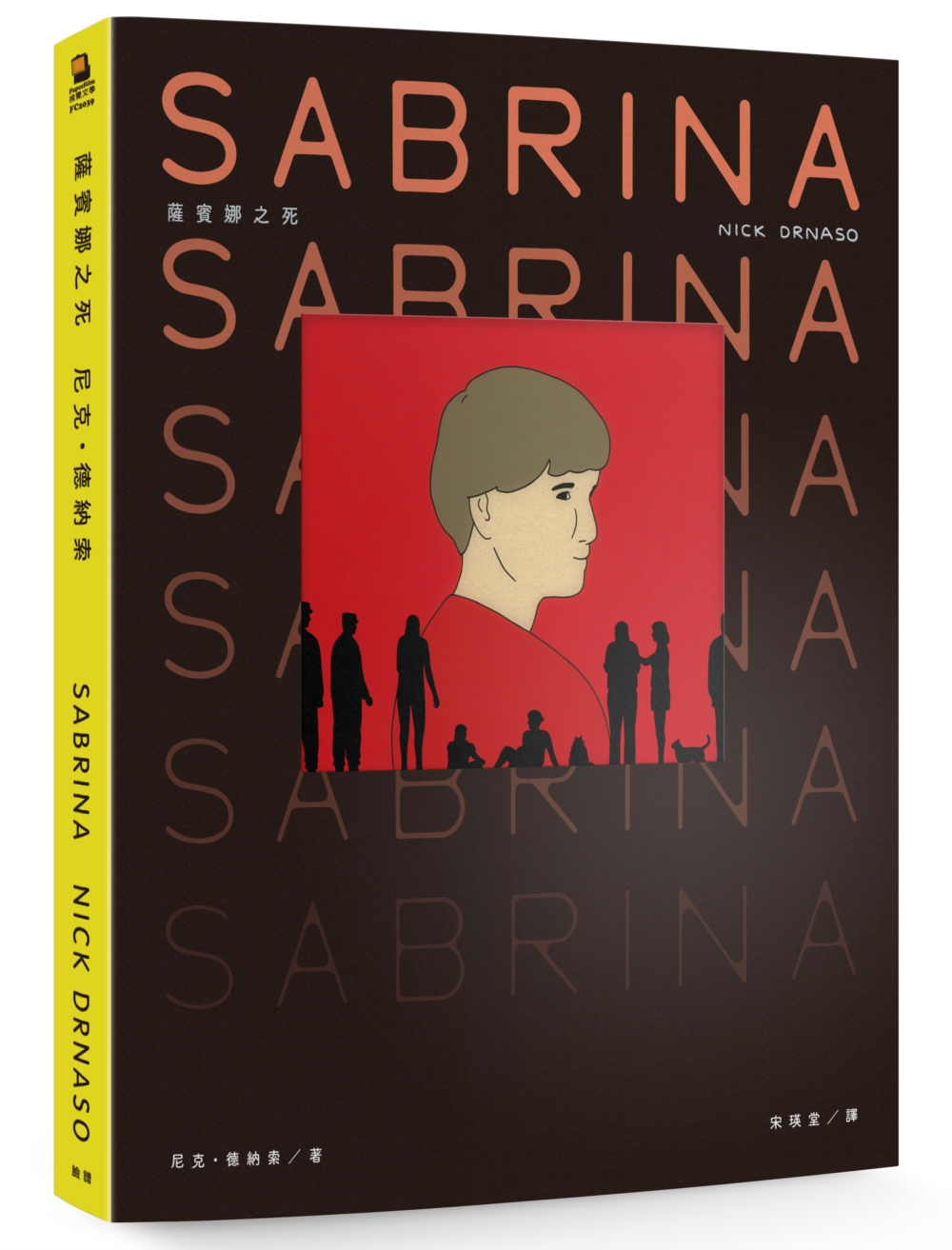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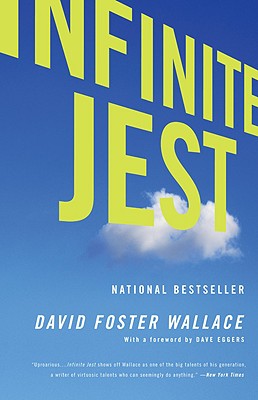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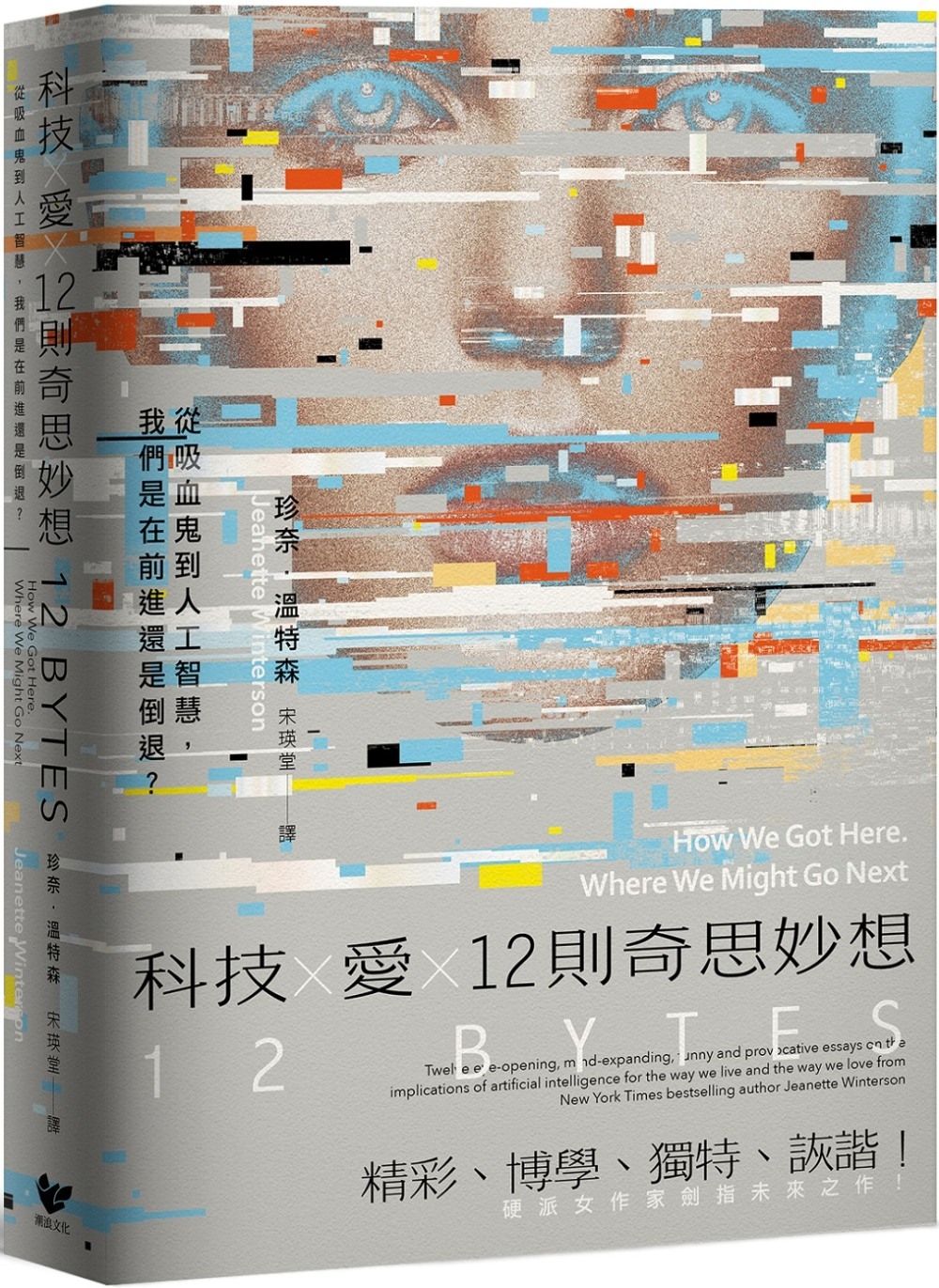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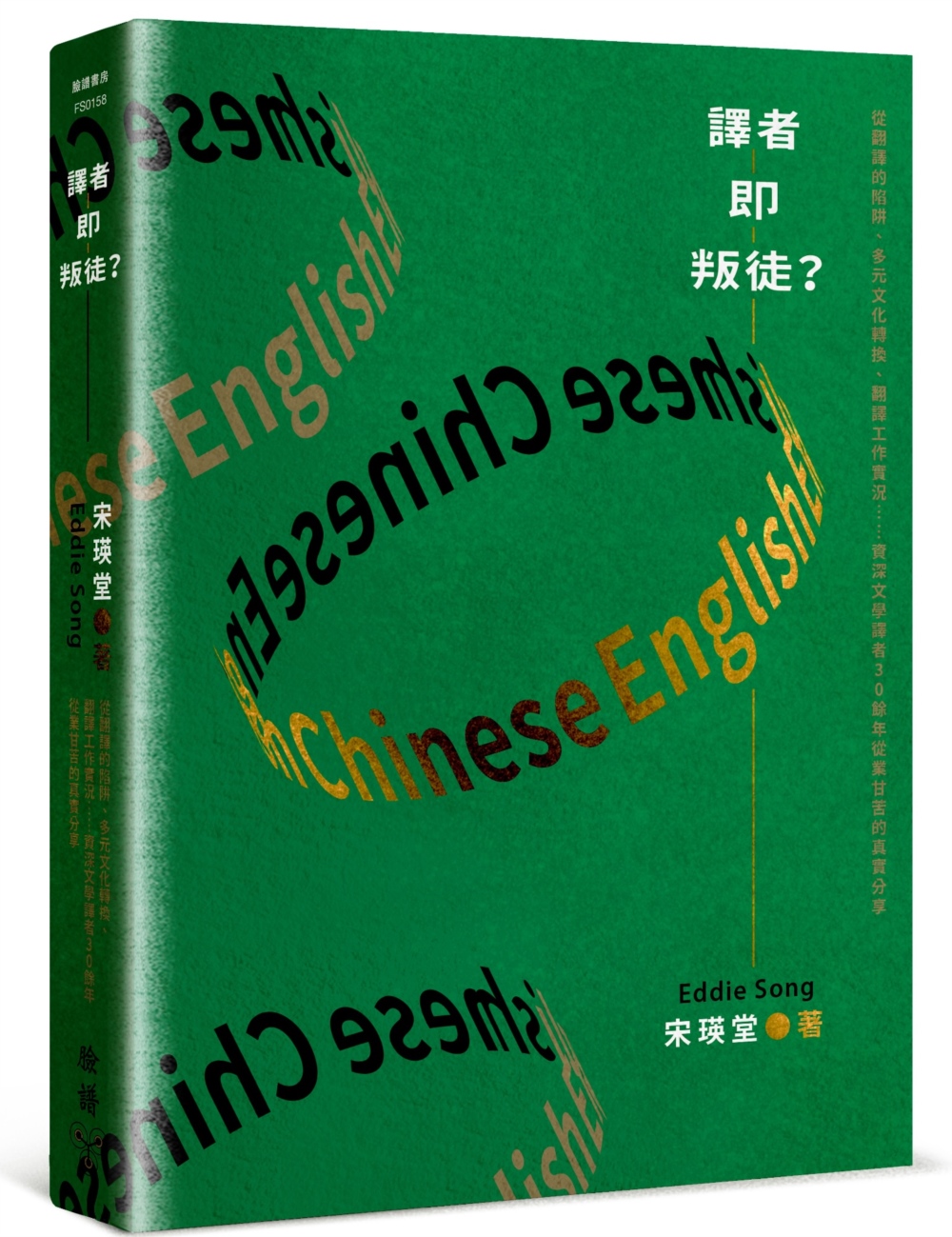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