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巴黎,難民美少女葛蕾朵坐在公園陽光下獨自哭泣。陌生俊美的男孩趨前關心,她抬頭,渴望被攬住、頭靠在他肩上。但她一開口,暴露德國口音。戰後德國人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男孩怒啐一口走開。她卻更渴望他撫觸,追過去要他帶她進樹林,對她為所欲為:只要他想,摑她耳光,揍她肚子,打斷她鼻梁。
他問:「你為什麼想要那樣?」
「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還活著。」
他起了性慾又反感,環顧是否有人旁觀,舔唇觀察她起伏的胸脯。但她一握住他的手,他抽開,罵聲妓女,拔腿就跑。
她從清晨開始遊蕩,回租屋處時母親爛醉如泥。
小說《那些破碎之地》濃墨重彩勾勒出受虐傾向與愛、性,像她三股髮辮般交纏難分,如影隨形長在她身上。痛苦、陰鬱、複雜,令人嘆為觀止,難以想像它是暢銷青少年小說《穿條紋衣的男孩》的續集。當時流行《追風箏的孩子》、《偷書賊》、《少年Pi的奇幻漂流》等,主角少年少女承受殘酷打擊,得到溫馨援助,卻是給成年讀者看的。孩子封殺掉自己受傷的情緒,認同權威,交換生存,成為大人;成年後再通過這些故事回溯、同理自己的天真無辜。愛爾蘭作家約翰.波恩(John Boyne)2006年的《穿條紋衣的男孩》可說是表現純潔無辜的佼佼者:九歲男孩布魯諾,隨爸媽搬離柏林豪宅,遠離要好的同學,住進遠方鐵絲網圍欄旁孤立的小屋,萬分寂寞,只有愛欺負他的姐姐窮追不捨。他想糾正爸爸,指出搬家大錯特錯,應該立即回柏林,但驚恐的女傭禁止他洩漏反意。
隔著圍籬,他認識了穿條紋囚衣的猶太男童,成為玩伴,從他口中才知道這裡是波蘭,奧許維茲。讀者領悟布魯諾的父親是納粹高官,在家宴請希特勒和情婦伊娃,決定了集中營、毒氣室的設計運作,並被派來當司令。
但布魯諾對集中營一無所知,穿上囚衣混進去探險。一切無可挽回之後,司令官才發現兒子已被當成猶太囚犯送進毒氣室、焚化爐。
讀者不捨好人受難,急切願意相信報應會自動平衡罪行的傷害,以彼之道,還治彼身,本書以此輕而易舉打動讀者、暢銷稱王。孩子受難越無辜,越顯得大人殘酷。
但作者的野心不止於訴說一個悲傷的童話。16年後《那些破碎之地》寫男孩的姐姐葛蕾朵,從91歲獨居倫敦回顧一生。她不像弟弟是個無辜呆萌亞斯,而是情慾與脆弱的二極體:蛇魔女般隨時舔唇垂涎男孩,挑逗男人,為玩弄男人的權力感而迷醉不已。但她又屢遭報復,每和致命的闇黑男人對峙,蛇魔女的全能感總如幻象消逝,現實是她被踹得傷痕累累。本書是傷口感染敗血症,毒液滲進內臟深處的各種化學反應。別人「以彼之道,還治彼身」要她嘗到猶太人被迫害的滋味,她也想讓納粹中尉知罪悔悟。每隻貌似無害的小蟲子都勇於施暴,各種暴力在像滅火器那麼小的鋼瓶內壁上互相撞擊。
她向第一任男友隱瞞納粹身世,第二次卻是她自爆,即使他百般抗拒,哀求她騙他,她也無法再忍受隱瞞。起先我覺得她憑什麼逼男友接納她的全部,實在強人所難,若她不說,也就不會被甩了。讀到結尾,大驚還真的不能不說。人人都有攻擊性,挨打會生氣、反抗,更不會自己討打。偏偏這個愛欺負弟弟的壞姐姐、不釣人會癢的蛇魔女,其實被剝奪了應有的攻擊性。自曝祕密,是她關鍵的成長。跨出這一步,她才能奪回攻擊性,恢復完整。
在 Instagram 查看這則貼文
讀這本書,會先看到官方版本的劇情,控訴納粹殘害人性。等眾多峰迴路轉的劇情都忘得一乾二淨,才會收到隱藏版彩蛋。
葛蕾朵的罪惡感有雙層。可見的外層,是六大門派圍剿光明頂,正義之士咬定魔教妖女有罪,即使她沒參與虐殺,誰叫她是納粹後人。隱形的內層,是弟弟之死有她在背後推了一把,但沒人知道,所以她從未因此受罰,而是不斷懲罰、攻擊自己。雙重的冤罪,使故事更加令人玩味。它並不是在講一個納粹千金,戰後成功潛伏到91歲還未曝光,像變奏史蒂芬.金的《誰在跟我玩遊戲》。不,它在講社會集體恨一個人,會導致這個人怎樣殘酷地攻擊自己、攻擊同類。
如果超譯公園難民少女葛蕾朵「德國口音暴露德國人/納粹身分」的劇情,其實那個地方就是新公園。她每一次的戀情,實際是一個男同志控訴主流社會,男子俊美健壯、開朗淫蕩,令他垂涎,原本怎麼看都該接納他。結果無論再怎麼親善的死黨,一見他暴露同志身分,就忙不迭作嘔而去。葛蕾朵叫陌生俊美男孩帶她進樹林、對她為所欲為,男孩反應矛盾,欲迎還拒。代表對方可能是直男,更可能是深櫃,既受男同志吸引,又痛恨自己受誘惑,把這種恨拋擲到男同志頭上、踐踏報復。「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男同志誘惑男人,男人覺得受辱,等於被抽了一鞭子,結果也要抽對方一鞭子。伴侶們互相施暴,暴力在密封鋼瓶的內部炸開。主流社會反同,連鎖反應等於在同志們體內引發一場又一場隱形的核爆。極端殘酷。
《穿條紋衣的男孩》第一章開頭,布魯諾回家,發現女傭在翻他的衣櫃,連他藏在衣櫃最裡面那些只屬於他個人、別人管不著的東西也被搜了出來。讀者無法想像,他哪有什麼祕密。到底是什麼東西,小說也沒提。這章結尾又重複說:連衣櫃最裡面,那些只屬於他個人、別人管不著的東西,也會全部遭殃。讀過《那些破碎之地》再回頭看這段,才看出力道:深藏在衣櫃裡的不是東西,而是被強迫曝光的恐懼。小說力陳男孩的無辜,實是被動反擊主流社會。
作者並沒自述身分為何,只說「我從15歲起就受到猶太大屠殺的強烈吸引」。我想,那是很多人性傾向覺醒的年紀。大屠殺對無數同志而言,並不是紙上談兵的過去歷史,而是當下的體驗。本書告訴了主流讀者,那加諸同志的隱密大屠殺是怎麼回事。希望我們永遠不忘。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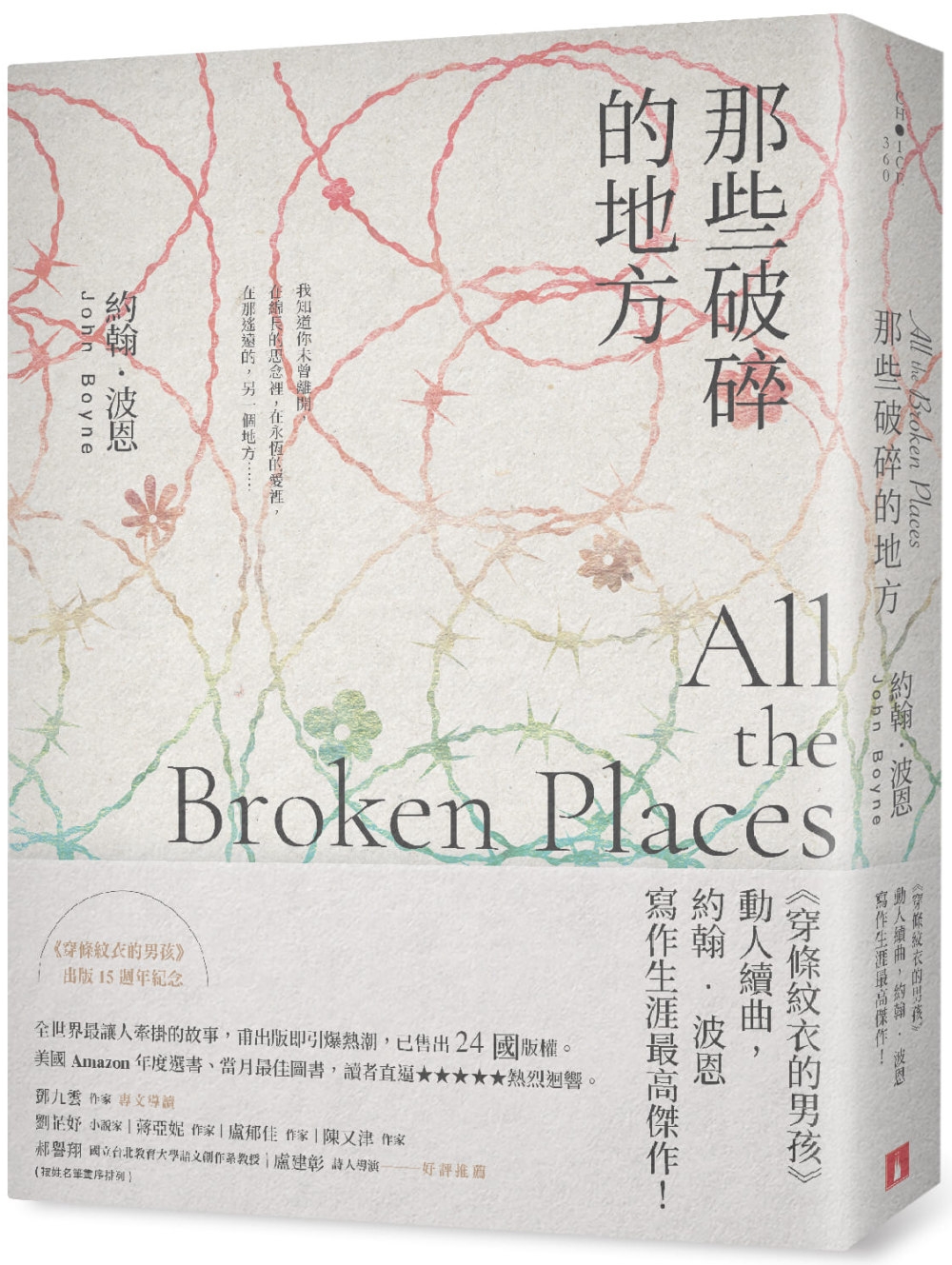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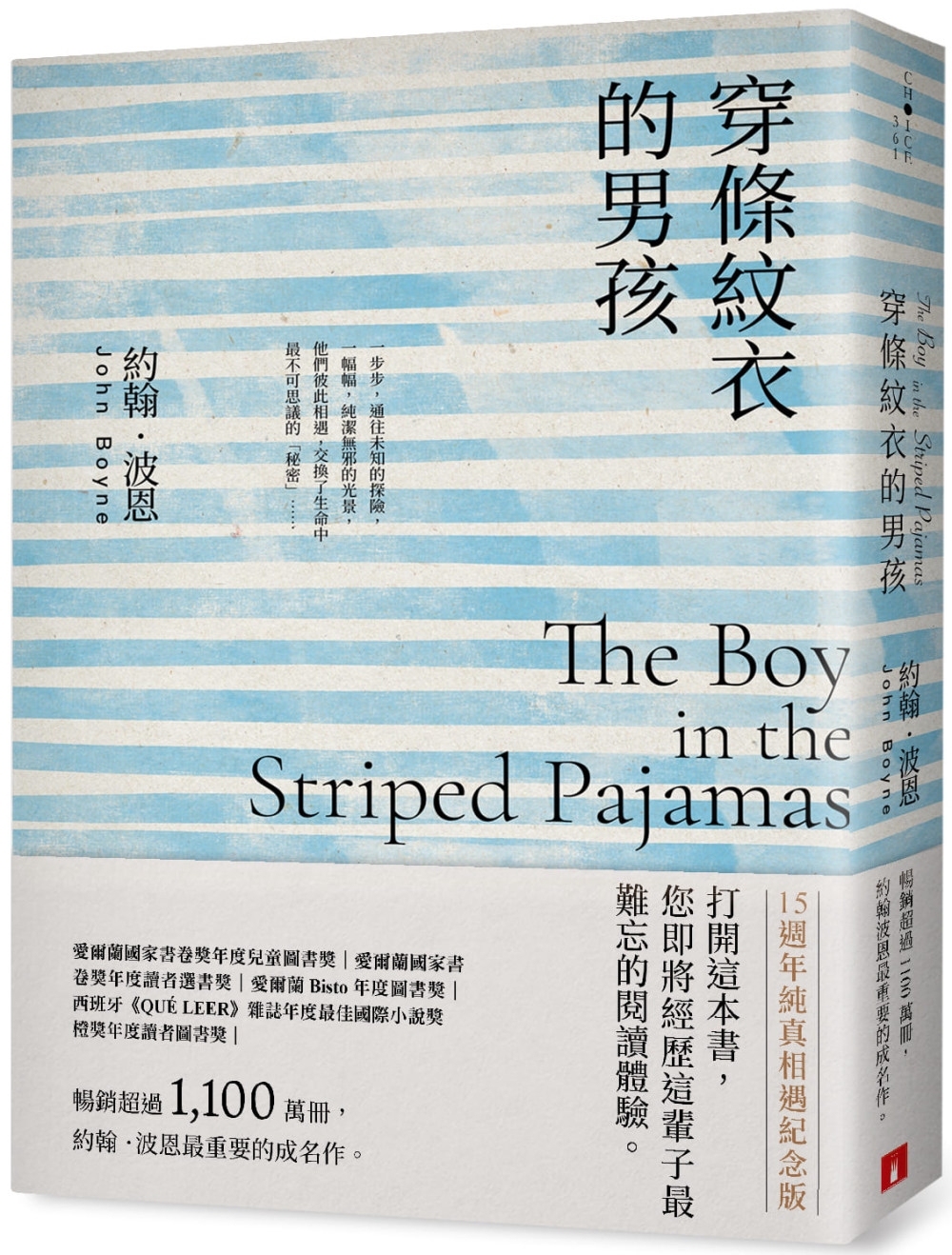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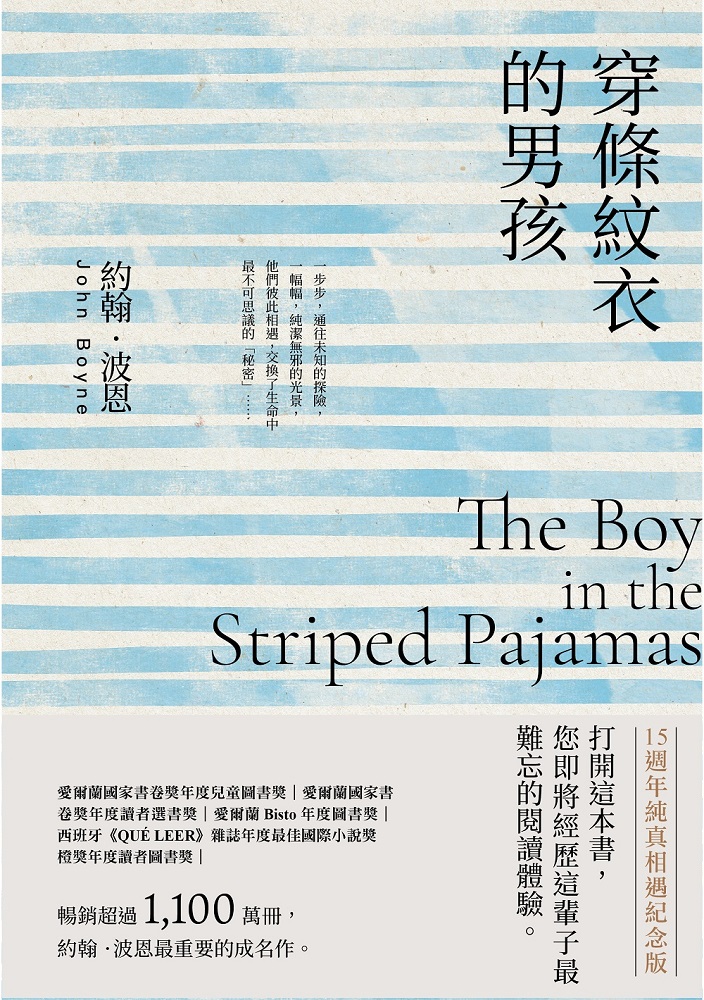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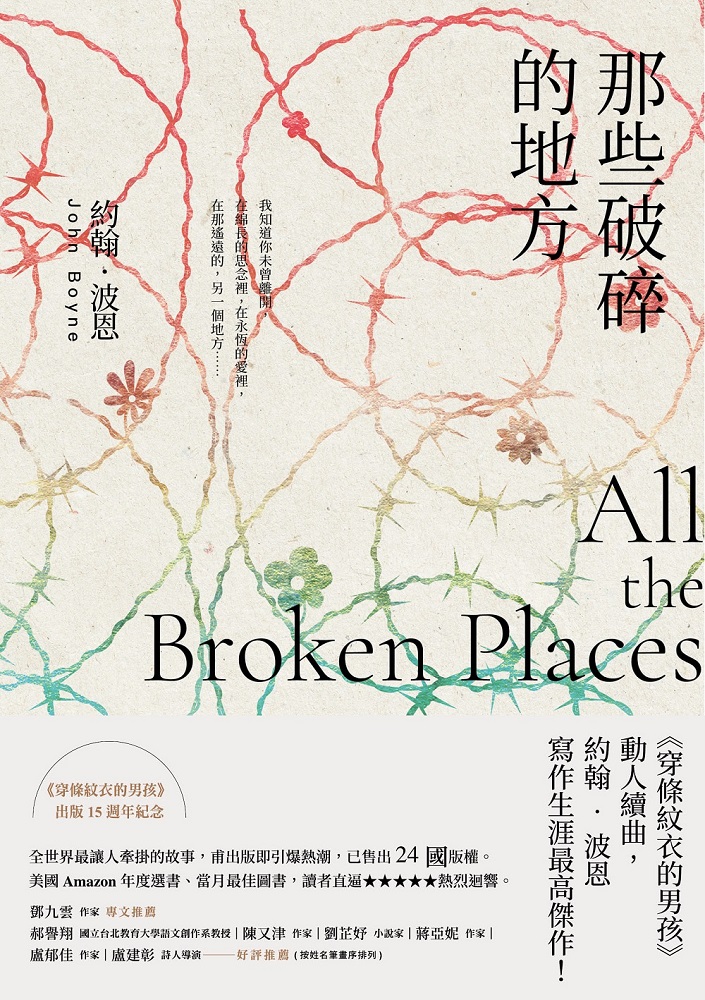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