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從來不只是「記得事實」而已,就個人層面而言,要構成記憶,首先必須遺忘,依據意識或潛意識裡輕重緩急的標準,將每一瞬間發生的無數事實進行篩選,編成一組有順序和意義的敘事。
要成為「集體記憶」就複雜了,不僅要將成千上萬的個人記憶彙整為一,反映集合體對當下的需求,如何在眾聲喧嘩中謀求多數人的共識才是關鍵。一旦群體做出選擇,勢必會放大、刪削,甚或扭曲群體內部某些族群的經歷,成為歷史敘事的定案。不管個人或群體的記憶,這種結論皆為暫時性,隨時會因為共同體處境的變化而鬆動、融解,開始新一輪的塑造。
法國史家亨利.胡梭(Henry Rousso)1987年出版的著作《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即是討論二戰結束後法國政壇處理「維琪政權」記憶的經過。
1940年夏天,德國攻下法國首都巴黎。一番政治角力之後,由法國一戰英雄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出面籌組投降納粹的「維琪政府」(1940-1944)。四年內,維琪政權一改法國的共和傳統,依循右翼理念,一方面打造保守的宗教國家,一方面呼應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建立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分支,協助德國統治,鎮壓法國境內的抵抗運動,並參與執行屠殺猶太人。
而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或由流亡英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率領的「自由法國」(1940-1944),他們不只是對抗德國,同時也在進行一場法國人之間的「法法戰爭」。四年並不算短,當然有堅守抗敵立場的鮮明人物,但前途茫茫,在「附敵」和「抵抗」構成的光譜裡,多數人都被迫在命運擺布下遊移於光譜之間,這讓處理維琪政權成為戰後棘手的難題。
 1940年10月,法國貝當元帥(左)晉見希特勒。(圖/ Wiki)
1940年10月,法國貝當元帥(左)晉見希特勒。(圖/ Wiki)
胡梭以心理學的「症候群」或「精神官能症」來形容法國政壇在二戰後到1970年代對「維琪」這段記憶的反覆。他把「維琪症候群」的演變分為四階段:一是戰後為了國家統一和重建,避而不談維琪的過往,採取遺忘的「未完成的弔唁」時期(1944-1954)。伴隨遺忘的,是對記憶的「壓抑」時期(1954-1971),此時人們一心附和戴高樂打造的法國榮光,將戰時記憶簡化為「對抗德國」的英雄史詩,沒人願意提起曾助紂為虐的傀儡政權。
這種假象,在1970年代遭到民間和學界挑戰,尤其紀錄片《悲傷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é)講述維琪政府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引發的討論,迫使人民直視戰時瘡疤,進入了「鏡像破滅」時期(1971-1974)。此後,像要彌補過去的忽視般,進入「執念」階段(1974- ),法國社會不斷召喚維琪的過往,無論是辯護或批判,或者新舊世代的對立,維琪症候群已化為政治、社會或文化現象,三不五時發作。
「每一年都有屬於它自己的新發現、新波瀾、新事件,以及記憶之間的戰鬥。」
藉由分析法國戰後對維琪政權態度的變化,作者指出:政府如何在不同立場的現實需求下,操弄/反操弄記憶,進而形成兩股對立的力量,影響人們看待過去的方式,也牽引著當下政治板塊的位移。經由官方、民間、文化和學術所提供各自版本的回憶描述,加上電影、書籍、新聞等媒介的傳播,誇張一點形容,維琪症候群已將全民捲入其中。
維琪政權之所以難解,在於二戰的起因相當複雜。當「邪惡納粹」已深植人心,從回望的角度,很容易把二戰視為好萊塢電影式的善/惡對決,忽視了一戰留下的未解傷痕,造成左/右翼雙方勢力在戰時迅速膨脹,各自都渴望以激進手段改變社會。此外,貝當政權和天主教文化緊密連結,擁護天主教價值觀,迥異於共產主義的無神論立場,讓左右兩派的對立更加複雜。同時,歐美社會也瀰漫對猶太人的歧視,特別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結合了種族歧視和仇富心態的排猶情緒,成為歐洲各國現象──不管是政客權貴或市井小民,往往在不經意之間捲入右和左的選擇,或陷入反猶的騷動中。
希特勒的崛起,是因為他和納粹黨人順應人心幽暗的趨向,在德國操作輿論和選舉奪得大位,並在維琪政府內部找到忠實支持者;換句話說,多數人都是程度不一的幫兇,或對暴行採取漠視的態度,像《盛會不歇:最屈辱的年代、最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所刻劃的,在德國占領下過著歌舞昇平的生活。戰後,左/右派持續對立並主宰著歐洲政局,對猶太人的歧視也依舊隱晦的存在。這是作者指出的,來自意識型態、宗教和反猶的三種症候群的脈絡。
正因為無力解決這些糾葛,所以不去檢討過去,不願面對並改變現狀。對新政權而言,「打造國家新形象」才是首要任務(忘掉過去、杜撰新的神話比較簡單);對一般平民而言,或許是不敢誠實面對自己的怯懦(當年為了生存,許多人都在遊走於灰色地帶)。作者說:
「經歷過占領時期的每個成年人,不論哪個年齡段,都想要把那個時期忘了,甚至是什麼都不想知道。也許是因為人們不能參與每一個做出決定性選擇的時刻,而生出了無法明說的羞恥感……」
正如全書使用的「症候群」隱喻,想要化解,第一步就是坦然面對。寫於1990年代的《維琪政府症候群》自然沒有「轉型正義」的概念,然而這三十年對維琪政權記憶的探求,重新清理個人或集體記憶的暗角,正是轉型正義最佳的示範。
史學家莎拉.瑪札(Sarah Maza)在《想想歷史》裡說:「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維琪政府症候群》正是這樣的一本書,它揭示了「遺忘過去」所造成的集體焦慮,唯有知道問題所在,就算答案一時無解,但也具有了基本的病識感,願意不斷重返過去,不再受制於當下的國族神話。
民主和歷史是互為支持的正向循環,兩者合作才能從「執念」階段昇華,就像近期出版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作者鄭安齊揭示了90年代德國建置「紀念碑/物」的經驗:藉由從民間出發的力量,打造多元對話的民主平台,讓不同世代的人分享、理解彼此的記憶,建立起溝通和連結,才能讓紀念碑發揮應有的效果。將《維琪政府症候群》和《不只哀悼》二書合觀,一前一後,完整彰顯了轉型正義的使命與方法。
兩本書的案例雖屬於歐洲,但對轉型正義議題進退維谷的台灣來說,都是值得思索或效法的他山之石。我們是否有屬於自身難解的歷史症候群?有多少來自於記憶的扭曲或誤解?在這硝煙四起的年代裡,值得我們多加思索。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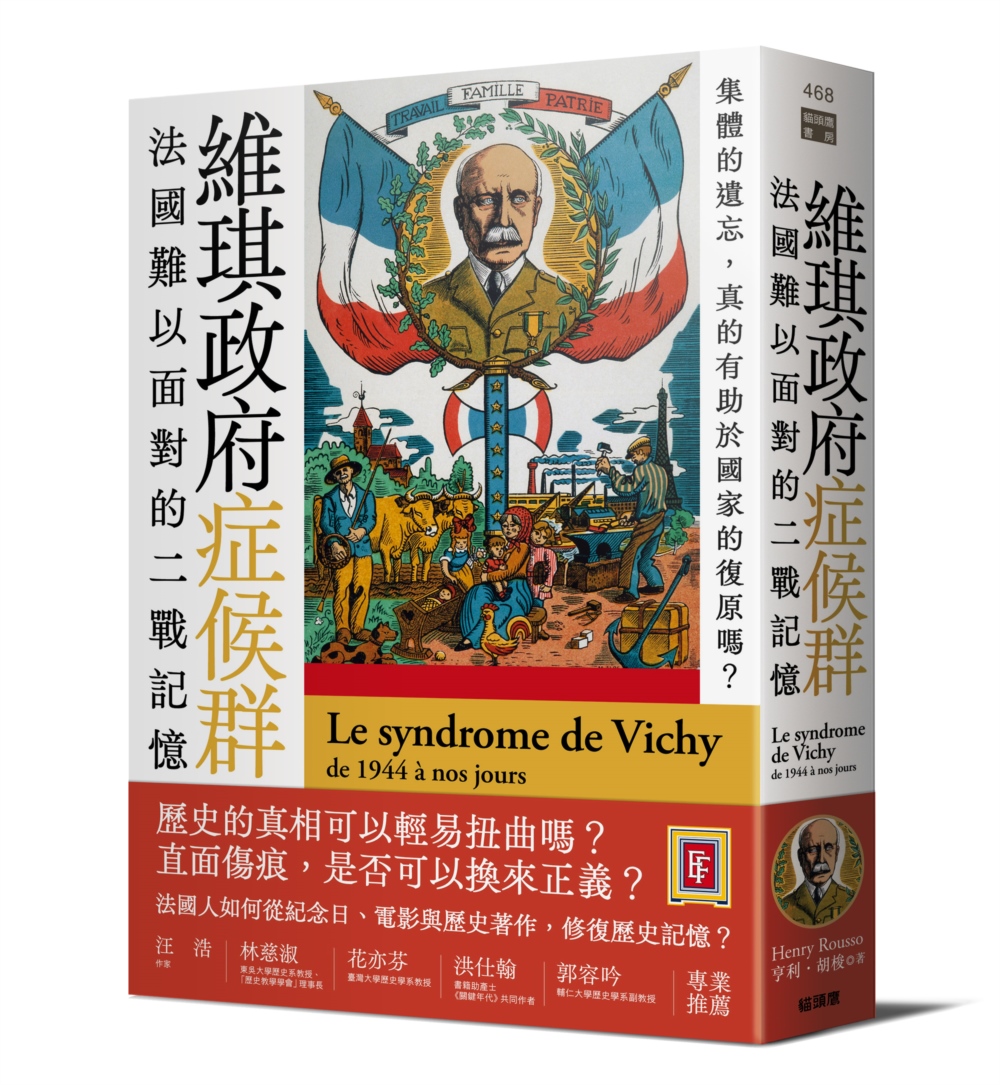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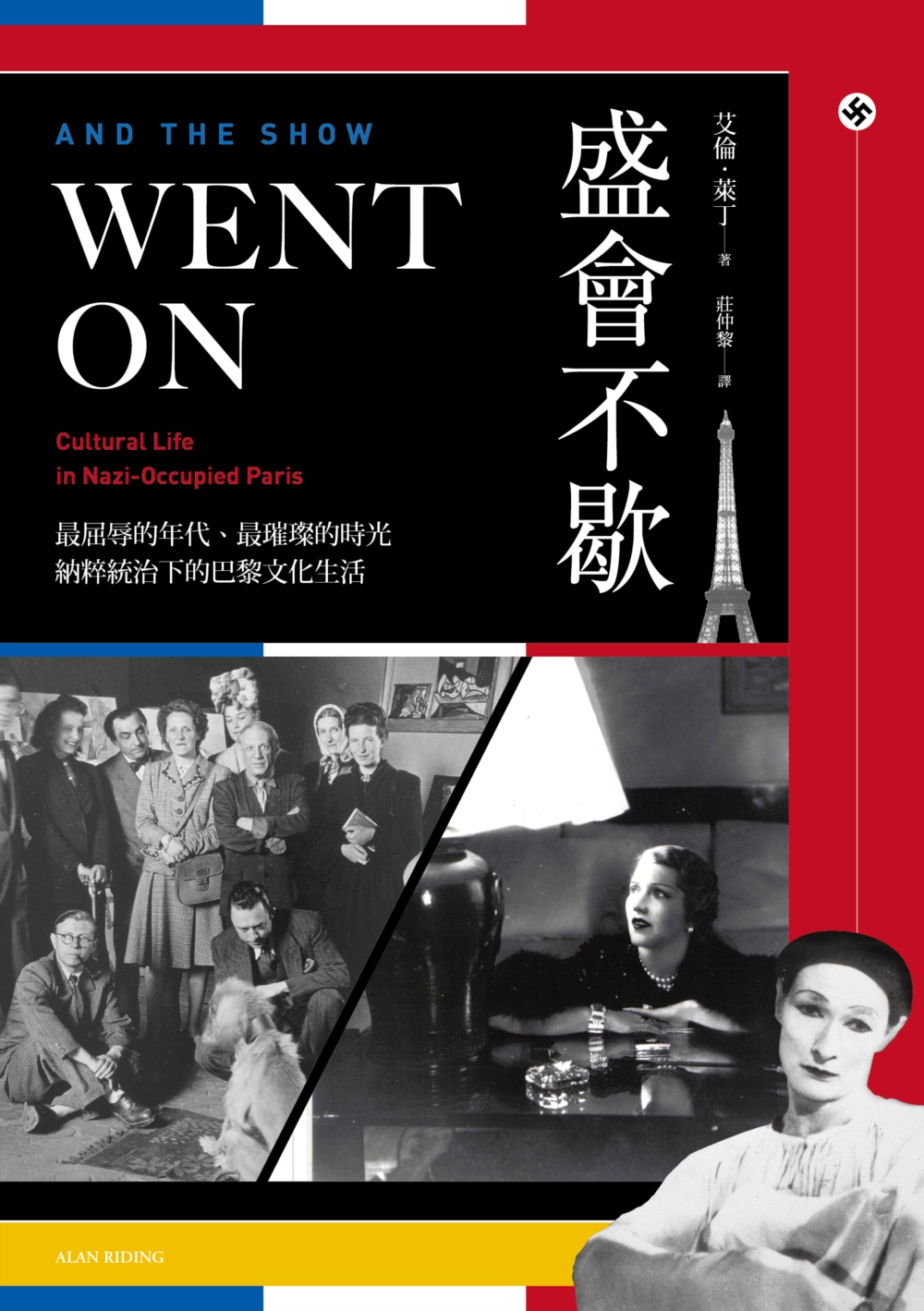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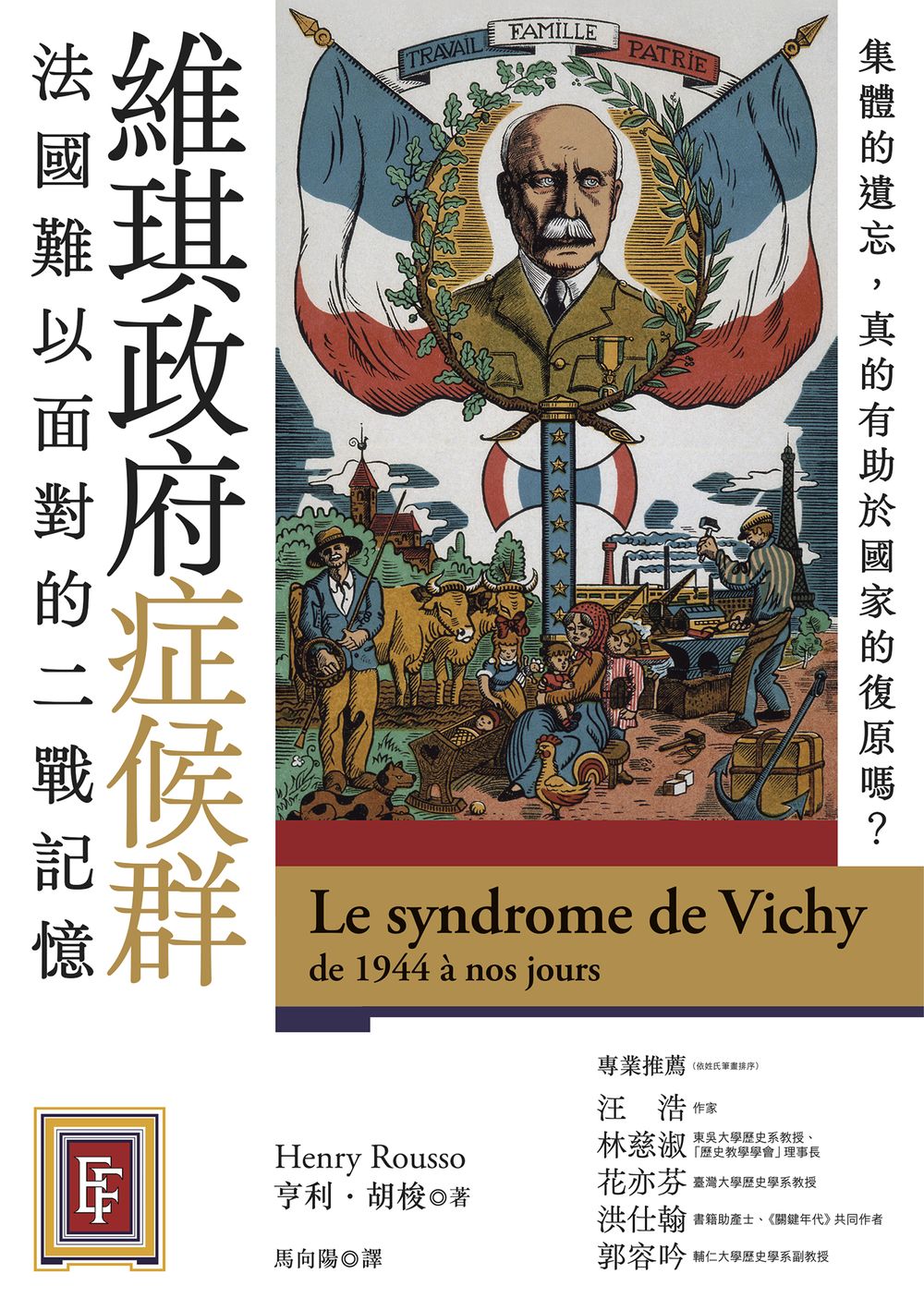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