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我可以稍微退遠一點看:看來《魔女》是一種殘響,在稍微帶點另類色彩的青年漫畫即將被台灣傳統漫畫出版社棄守(而臉譜出版、大塊文化尚未進場)的前夕,它與九○年代寒武紀大爆發式冒出的台版日漫中,那些從出生到死亡可能都無人聞問的奇異旁支(例如植芝理一《謎狐怪童》)遙遙共鳴。在當年那個網路資訊還不如現今高度發達的環境,對於只能仰賴紙本翻譯作品探索漫畫世界、但又渴望追求漫畫可能性的讀者而言,我相信《魔女》無異於一顆北極星。
十年前就沒有想那麼多了。當時只看單行本,不了解連載雜誌與其代表的商業、文化意義,缺乏「幫自己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作品」的工具,我於是在租書店裡想著,天啊,我不要再追長篇未完結作品了,集中來挖短篇集或集數少的漫畫吧。雖然粗暴,但不失為一個好方法,至少能直接過濾掉部分公式感強烈的娛樂作品。後藤雪子、柏木晴子,當然還有五十嵐大介,大約都是這個時期發現的作者。如果沒有這些翻譯版的微弱火光,我大概會放棄繼續看漫畫(那時已經幾乎不看動畫了),撐不到後來自己更有餘力去探索的時期吧。不知有多少台灣讀者有類似的感觸?
更具體地說,《魔女》之所以帶給我震撼,是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漫畫做為畫、語言、敘事的綜合體,是可把「畫」擺在主體地位的。這也許會被誤認為是在反駁「漫畫最重要的終究是故事(畫技不是重點)」的論點,實則不然。故事至上派想強調的,是漫畫不見得需要高超的畫技才能成立;而我所謂「把畫擺在主體地位」,指的是作品的新意、核心位於畫之中,情節和語言做為畫的軌道,由畫負責把讀者運到陌生的境地去。這類漫畫的讀者,在意的與其說是畫技高低,不如說是:漫畫家能否打破約定俗成的造型或符號限制,靠畫引導出強烈的悸動,或擴充讀者的精神體驗。
多摩美術大學美術系繪畫科畢業的五十嵐大介做到了。儘管他有意識地將女性角色畫得可愛一點(「我從《故事說不停》的時候就覺得,不把女生畫可愛一點的話,這種故事應該不會有人想看吧。」他在《文藝別冊:五十嵐大介特集》的訪談中提到),但人物以外的部分都悖離了主流漫畫傳統。背景線條大量運用原子筆,製造出時而寫生式的,時而抽象的質地,浮動卻充滿可塑性,能織出〈SPINDLE 紡錘〉中遊牧民族生活的野地的乾燥清爽,也能為同一短篇中的地下宮殿無機石壁抹上憤怒舞爪的表情。 (圖片提供:臉譜出版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圖片提供:臉譜出版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五十嵐大介在背景線條時而寫生細膩,時而抽象,充滿可塑性。
(圖片提供:臉譜出版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這自由操縱、融接畫面質地的能力,以及他對自然物的深入觀察,使他得以在《魔女》各短篇的奇幻情節高潮處召喚出幽遠深邃的異象──它們借用的形體,例如鳥羽、獸首、煙塵、臟器、腔腸動物、熱帶魚,都帶著寫實性。也難怪完成品不會在你腦中播放誇張激昂的配樂,它們能說服讀者這一切都不是戲劇效果,不是外於世界的贗品。世界若短暫裸露它的根部,恐怕就會是這模樣。情節是路,畫面是盡頭的魔境。因此你會願意一再重返。
 《魔女》中借用的形體,例如鳥羽、獸首、煙塵、臟器、腔腸動物、熱帶魚,都帶著寫實性。
《魔女》中借用的形體,例如鳥羽、獸首、煙塵、臟器、腔腸動物、熱帶魚,都帶著寫實性。
(圖片提供:臉譜出版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既然我認為「畫」是這部作品的火車頭,翻譯時我注重的要點就是語言的低限。原文本無絢爛詞藻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某些譬喻的運用相當新穎,為了讓大家直接去消化那些意象,語言的清晰和簡略更是必要。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有意識進行的操作有:
一,句子能短則短
例如,舊版開頭以台灣人比較熟悉且能接受的娓娓道來的說故事口吻開場,但我選擇還原敘事者的冷冽:「昔日,有魔女。」〈生殖之石〉的開頭也進行了類似的壓縮:「星星獲得生命,星星死滅成塵。」製造緊張感,但也要避免彆扭地使用文言文,因為原文平鋪直敘。
二,橫跨數個對話框(甚至數頁)的一段發言或一段敘述,必定要一併調整成符合中文語序的文字,再重新斷句。
這是實際翻譯漫畫前不會想像到的勞心勞力之處。翻譯小說、散文時原本就得按照中文習慣標上標點,重新安排呼吸節奏,漫畫更是會以對話框的數量、大小來逼你「強制換氣」。如果把每一個對話框都視為獨立互不干涉的單位,原封不動地翻譯裡頭所裝之物,很難得到通順的成果。
〈KUARUPU 庫阿路普〉當中的這一頁,就是把旁白框裡的三句話抽出來譯成一整段文字,再重新斷句所得:「過去有誰像她這樣嗎?/歷經重重磨練修練成咒術師,/卻不是為了『治癒』,而是為了詛咒去驅使精靈。」(剛開始翻譯漫畫時,我不知道每天投入一樣的時間為何得到的字數會比翻譯小說少,後來才察覺這個項工程有多耗時。)
 (圖片提供:臉譜©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圖片提供:臉譜©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三,運用對仗,製造節奏感,也能加快讀者掌握句意核心的速度。
例如〈生殖之石〉當中的這一小段:「這是喧鬧的夜晚,各式各樣的惡靈與死者一同復甦,四處搗亂。/這是焚煙的夜晚,為了保護家和家畜,不受他們侵擾。」我把「夜晚」提到最前面做為主題,舊版譯者則是使用「子句+夜晚」的句構;如果整部作品的語言調性更黏稠潮濕一點,我可能也會選擇後者那種連成一氣、讓讀者更燒腦的表達方式。
 (圖片提供:臉譜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圖片提供:臉譜 © Daisuke IGARASHI / SHOGAKUKAN)
由於我未來可能不會再寫翻譯相關的文章了,最後想借一點篇幅做個呼籲。
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的《大師的小說強迫症》有一段話讓我很有共鳴:「我的目標是從學生的作品中挖出十年後回首會讓他們自己感到尷尬的東西。」盜版字幕組,甚至某些正版出版品的漫畫翻譯,已使得翻譯腔中文成為御宅系統作品的「國語」,因此許多漫畫創作者的台詞寫作也自然而然使用「什麼的」、「啊啦」、「嘛」。這已經是一種次文化,譴責批判並沒有意義,我並不是要主張這些中文受到汙染。不過,能夠看完這兩千字的文章,而且有志創作漫畫的你也許可以想想:你創作,就只是希望所謂的動漫愛好者買單嗎?你可以答是,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如果希望各種不同背景、各種年齡層的讀者來閱讀你的漫畫,而且是他們待在原地,不用先變宅(掌握御宅行話)就願意拿起你的作品,那麼你也許應該要斟酌一下語言使用。用語中性、簡明通順的台詞寫作,可以讓讀者更順暢地沉浸到故事世界當中。有利無弊。畢竟你的漫畫不可能因為少了「什麼的」就頓失魅力和韻味吧?十年後的你會鬆一口氣的。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 「漫畫是讓讀者讀到以後才始稱完成。」吳明益 ✕ 五十嵐大介越洋對談
- 吳明益:五十嵐大介──身體在勞作,心靈在日夢的漫畫詩人
- 【不只聊漫畫】用身體勞動與料理體會四季更迭──《小森食光》與《山牧之愛》
- 黃鴻硯:去你的,眼球就只是眼球!──丸尾末廣《少女椿》創作背景雜記
- 【范湲|一個譯者的偏執告白】原作如此樸實,譯文豈能華麗?
五十嵐大介作品






 文藝別冊:五十嵐大介特集
文藝別冊:五十嵐大介特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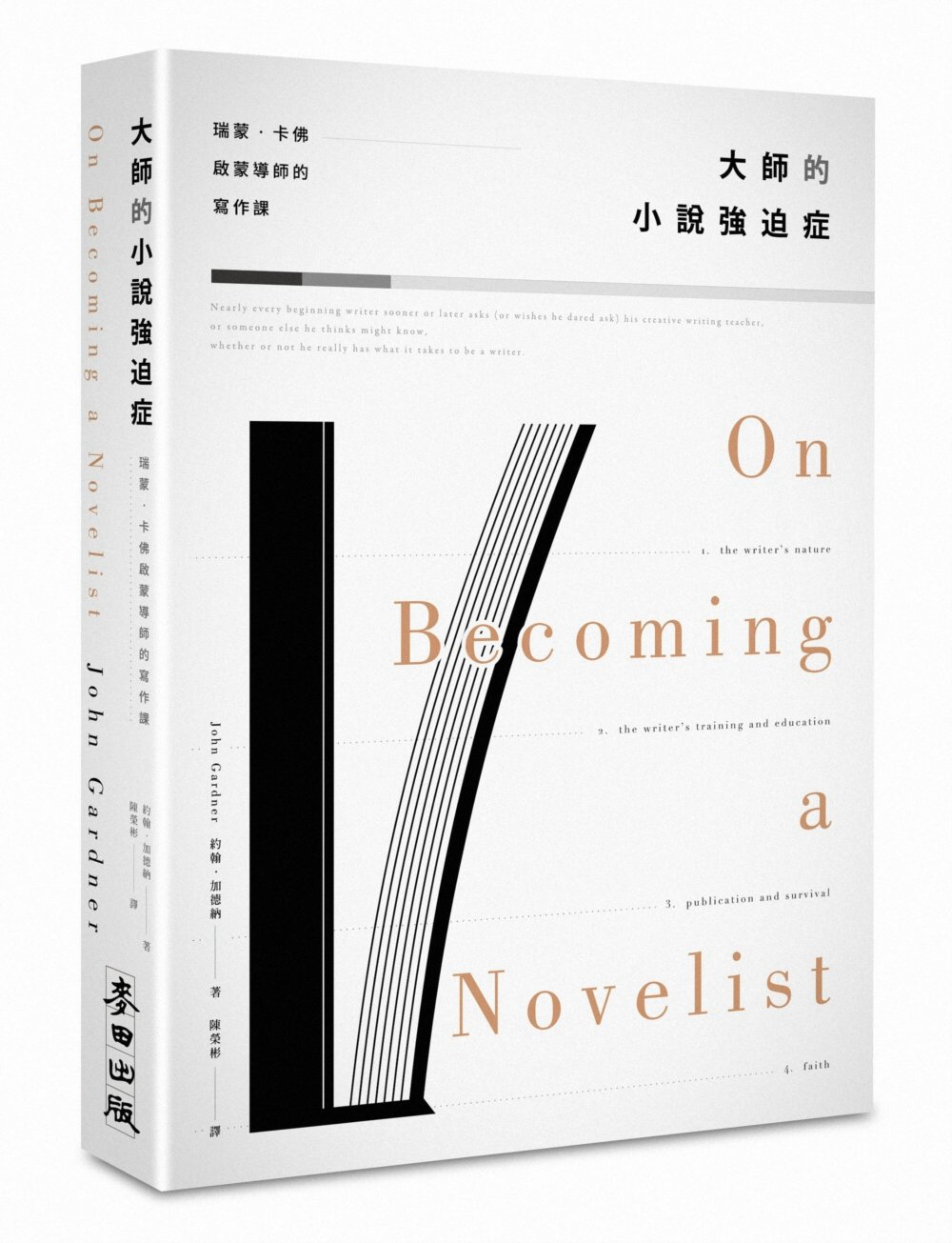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