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人自我形象的構成不僅包括你是什麼人,也包括你想成為什麼人,能成為什麼人,或曾經是什麼人。
──Karl Ove Knausgård,《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p.102
當出版社的編輯琬融將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書稿寄給我並且邀稿時,我立刻思考是否要推卻。原因是,我所收到的六十萬字書稿,不過是克瑙斯高《我的奮鬥》系列(我個人還是偏愛英譯為My Struggle 的寓意)的三分之一而已。而這系列早已在歐洲文壇備受關注的作品,是以一種稱為「自傳性虛構小說」(autofiction)的文體所寫成。這個詞被用在諸如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以及柯慈(J. M. Coetzee)部分作品上,指的是作者將自己的成長記憶添加感想,透過戲劇性敘事,加上臆測、想像寫成。敘事時通常採用第一人稱,並且會直接使用本人的名字,而不會像某些私小說一樣刻意取另一個名字來指涉「我」。
這類作品與作者本人經歷往往非常接近,加上連名字都直接使用,難免會把與自己周遭的人都拉進這個「具某種程度虛構性」的敘事裡,而引來窺探。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樣的寫作模式帶有某種危險性,因為總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任何一部分被陌生人閱讀並且品頭論足吧。更何況,這類作品凡是傑出的,往往都不避諱將生命陰暗面寫出,有可能會使得親密之人在網路時代受到極大的困擾。它的危險在於,寫作者認為不得不寫的藝術動力,極有可能帶給他人痛苦。
這真是寫作的意義,是寫作的本質嗎?
這問題與我的寫作歷程相伴相處,至今未有解方,這成了我沒有太大動力閱讀的最根本理由。但這寄來的書稿,卻又如此吸引我打開來。《我的奮鬥》出版於2009至2011年共計六冊,在挪威已售出五十萬本。由於挪威人口不過五百萬上下,這意味著它絕對算是國民暢銷書,何況克瑙斯高正是憑藉著它而備受國際文壇稱譽。如果我「拒絕」讀它,是否也意味著我的怠惰?
於是在思考如何回絕之前,我開始了這六十萬字的閱讀,讀著讀著,我的另一個疑慮油然而生——我能讀一系列作品裡的其中「兩冊」,來「導讀」這系列作品嗎?這個問題若置換一下,便可以感受到在這個社群媒體強大時代的一個重要提問:我們能以一個人一生裡三分之一的時光,評價(或知曉)他的人生嗎?而在這個資訊龐大、倏忽即逝,又不可避免地每天朝死亡前進的線性人生裡,我們哪有時間去「完整地」讀另一些人的人生呢?
這些問題在我閱讀時縈繞不去,另方面,我又漸漸沉浸入克瑙斯高的敘事,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與他算是同時代的人,彼時人們的成長史,已經被納入名為「地球村」的洪流裡,因此跨域文化的強度似乎超過了地域文化的強度。在台灣成長的我,與遠在挪威成長的克瑙斯高一樣聽Deep Purple、The Doors,一樣看《巴黎野玫瑰》,一樣覺得自己不被理解,與上一代漸行漸遠。透過這些元素,在《我的奮鬥1:父親的葬禮》裡,我對克瑙斯高筆下與父親對抗又想親近的情緒產生了共鳴。特別是其中一段還是少年的他有段時間被送去與父親同住,他跟父親反映說房子冷,而父親給予他輕蔑的回應。當他賭氣離家時,卻在走到路口的回望裡,看到屋子升起了煙。一個少年徘徊躊躇的身影,牽引了我閱讀的感情。
做為一個北國的作家,克瑙斯高的筆觸將綠意藏於冰雪之下,在看似平凡的敘述裡總站著一個眼眶濕潤的男孩、多情少年、苦惱的年輕作家,讀者跟著他偷偷運酒避過父母去友人家跨年、擔憂陰莖是否太歪、所愛之人不理睬自己,以及平淡人生與寫作志業的拉扯……這些記憶對克瑙斯高的人生來說都「已成定局」,只是作家透過寫作「再一次」經歷,並在我們閱讀時和他一同經歷。我一直以為,這種對已成定局的過往感傷是很親暱私密的,唯有傑出的作家才能把陌生的讀者拉進其中。
克瑙斯高把平凡的人生成長,透過像是提煉過卻又毫不在意的句子寫出來,產生了非凡的即視感,讓我幾乎找不到停頓閱讀的地方,於是我漸漸領略了克瑙斯高的魅力。對我而言,他不多但總恰如其分的寫景真是高明極了:「丘陵在另一處隆起,往下能延綿至海,水一樣是黑的。光從河流和丘陵間的一棟房屋傾瀉而出,強烈且明亮。而天邊的群星,與大地灰濛濛的色調過於相近,僅在夜空的更深處,才得以依稀見到一點。」這是挪威人才有的視野吧,這是冰雪國度的美學。
而我也迷上了他那些「直觀勝過邏輯」,卻似乎準確明智的話語,比方說這段:
十九世紀虛無主義與我們的虛無主義的不同,正是空虛與平等的不同。一九四九年,德國作家恩斯特.榮格曾說,將來我們會建立起一個世界政府。現在,由於自由民主制已稱雄於現代社會,似乎他所言不虛。我們都是民主主義者,我們都是自由派,各個國家、文化和人民之間的差異正在普遍瓦解。而這場運動從本質上說,又何嘗不是虛無主義的?「虛無主義的世界本質上而言,就是一個日益縮減的世界,自然而必然地與趨向原點的運動相符。」榮格寫道。有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這樣的縮減,那便是把上帝視為「善」,再比如那種要為世界上所有複雜趨勢找到一個共同特性的嗜好,又比如專門化的傾向,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縮減,又比如要把一切轉化為數字的決心,美、森林、藝術、身體,概莫能外。因為如果金錢不是一種實體,將大部分不同的事物加以商品化,那它又是什麼呢?抑或如榮格所說:「漸漸地,所有領域都被歸到這個獨一的共性之下,即使與因果關係所處的距離像夢一般遙不可及的領域也不例外。」在這個世紀,就連我們的夢境都是相似的,就連夢境都是可以出售的東西。注重平等不過是冷漠的另一種說法。
這就是我們的黑夜所在。
(《戀愛中的男人》,p.112-113)
漸漸地,我愛上了《我的奮鬥》的敘事(特別是第一本),我愛上他的毫無節制、囉唆、猶豫不決,以及冷靜的,屬於北歐色彩的感傷與銳利分明。也許是因為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明白了人生毫無停頓,也不能簡寫。當然,也明白了人不會同意(或不同意)另一個人的全部。
於是我回信說我會寫篇感想(而不是導讀),並且說明我會提到對這部作品的一些負面感受。在交稿前我讀了第二遍,漸漸明白了,我對這兩本作品的負面感受很有可能也是對同樣身為作家的我自己的負面感受。
在從事寫作的這段時間,我從未懷疑過記憶的意義以及回憶的意義,因為這是生而為人最迷人的核心。我們透過回憶的梳理咀嚼,並且在日常生活裡就像水獺築壩一樣在流水中建造自己的記憶建築。記憶當然不完全是美好的。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完全善良、正直、誠實的人,但幾乎都不是,至少不永遠是。所有人都做過自己眼睛無法直視之事。寫作一本宣稱「非虛構的自傳」時,執筆者往往會迴避那些非正直、誠實、善良之事。因此,自傳反而常是「虛假的」,多數自傳都是寫「他人」時誠實,寫自己不然,有時提及自身之惡,也是某些自我形塑的形象。我一直覺得,自傳是很好的他者材料、時代材料,卻不一定是很好的檢視作者自身的材料。
相對之下,在自傳體的小說裡,作者可以寫出那些他無法直視他人眼光做過的事,因為「虛構小說」一詞保護了那些藏在陰影裡的記憶。在我看來,第二部的《戀愛中的男人》,克瑙斯高的朋友蓋爾提到他在北挪威與一位十三歲女孩發生關係的事,就屬於此類介於現實與非現實間迴盪的話題——沒有人可以掀開那層簾幕,那簾幕後的事,只活存在書寫裡。小說裡的克瑙斯高否定後又懷疑自己真的做過,這是很困難,需要勇氣的真實的一刻。
只是,作者的勇氣,或許只能限於作者的自身。「勇敢地」把他人私密之事也憑藉強烈的自我觀點寫出來(除開那些公眾之事),是極其自我的行為。偏偏強烈的自我中心,是許多藝術家的人格本質(包括我在內)。
當我看到作者在訪問時提及把親友、情人的私密故事為了寫作傾巢而出,如同一種「文學自殺」(literary suicide),而後被書評、媒體廣泛引用時,我不禁感覺到「作者」此一身分的自大以及一種自我指涉的恐懼。為了寫作將他人的人生傾巢寫出,如果角色交換,我會說這必將是周遭之人的惡夢。這並不是文學的自殺,而是為了追求文學的成就,忽略其他人感受(我不願用到「殺」這個字)的行為。這或許不只是對這本書的保留,也是我從事寫作多年之後,對寫作者人格該是如何的保留。
在網路時代以前,不管是八卦新聞或是自傳性小說,即便引起讀者深層,屬於黑暗部分的好奇心,但礙於資訊的困難取得,不至於會大規模、長久地造成被書寫者的困擾。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要挖掘一個人的背景實在太容易了,即使是扭曲的話語,都會恆久存在,並被片面讀到,流傳下去。
在所有的傳統藝術中(我撇除了近代發展出的第八藝術),寫作是最容易把自己對他人、對價值觀、對自我生命評價暴露出來的形式。我們可以從音樂裡聽出作曲者的掙扎,但不會從作品的內容得到說明;同樣的,觀看一幅畫亦然。根據國外媒體的報導,從第一部作品的出版後,克瑙斯高父親那方的親友就提出了法律行動,而他的妻子也再次陷入嚴重的憂鬱症。據說克瑙斯高因此修改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刪除部分內容。這讓我相信,克瑙斯高絕對有過掙扎。雖然書裡確實提到希特勒,但我寧可相信克瑙斯高不是以中文的「奮鬥」來回顧自己的半生,而是掙扎、無止境的掙扎,當然,這也無法讓那些不願被寫的人釋懷一分。
那些不書寫,以自己的方式度過一生的人,在書寫的世界裡就是弱勢者,他們才是冰雪下的綠樹。他們沒機會為自己發聲,即便寫作者本身感情豐沛、並無惡意,但人誠實地以自身的識見、感情表達對他人的看法並成為公眾讀物,就可能對另一個人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讀者讀來或許「只是一件小事」,但對某些人來說,那可能是絕不想曝光給外人知道的刻骨銘心之事。
我認為許多寫作者,都真心厭惡那個不為他人所見的,心底的自我。這或許是My Struggle 的真正核心吧?
另一方面,像克瑙斯高這類動輒以百萬字計,將自己的人生幾乎是鉅細靡遺紀錄下來的作品,本身就充滿了「虛構性」。怎麼可能?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人生,那麼多的對話(包括第一次摸到女孩乳房時和死黨的對話)、那麼多的「第二天」、那麼多的景色、跳躍的思維,寫作時怎麼可能如此井然有序、細緻地加以陳述?只是這樣的虛構性又透露著真實感——我們不得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人的生命就只在於注視自己,以至於所有的記憶都圍繞著「我」維生,他們可能在很早的時候就寫作日記,隨著日子過去,在讀自己的日記時也會油然產生一種陌生感,於是,最終將新意識與舊紀錄遂編織成一部「小說」。
克瑙斯高在書中說:「文學的唯一法則是:一切必須隸屬於形式。要是文學其他的元素強過形式,諸如風格、情節、主題,其結果將甚微。這就是為什麼有著強烈風格的作家常常會寫出反響不大的書。這也是為什麼有鮮明主題的作家常常寫出沒有影響力的書。主題和風格上的強烈與鮮明必須打破才能讓文學有一席之地。這一破除我們稱為『寫作』。比起創造,關於寫的更多是破壞。再沒有比蘭波更清楚這一點的了。他的卓越不是因為他在騷動煩亂的年少時期就有此頓悟,而是他將此一原則也付諸於自己的生命。蘭波崇尚一切自由,他在寫作上是如此,生活中亦如是,這是因為自由被奉為至尊,他可以把寫作置於身後,甚至可能是必須把寫作置於身後,因為寫作也成為一種羈絆,需要被打破。自由就是破壞加上行動。」(《父親的葬禮》,p.222)或許他就是這麼沉迷於把寫作視為生命的核心,決心以這樣的形式去表現吧?
《我的奮鬥》並非以故事為主軸,它的形式在於滔滔不絕的陳述,以及無盡的細節。除了前兩冊《父親的葬禮》與《戀愛中的男人》以死亡與愛情為主題外,在未來即將出版的另外四冊裡,分別是: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此刻讓我們回到這篇文章一開始的自我提問:我們花這麼多時間讀另一個人的人生做什麼?
或許這也可以用克瑙斯高自己的語言來回應,他說:「知道的越少,它就不存在。知道得太多,它也不會存在。寫作就是將陰影裡我們所知的一切精神給呈現出來。這就是寫作。不是那裡發生什麼事,不是那裡事件如何展開,而是單純的那裡。這就是寫作的目標與方向。但又要如何到達那裡?」(《父親的葬禮》,p.217-218)
要如何到達那裡?那裡是哪裡?這是肯定句也是疑問句,我們總是一邊總結一邊提問,因為,有時我們的總結在他人的提問裡,有時我們的提問在他人的總結裡。
作者簡介
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單車失竊記》、《苦雨之地》,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
曾六度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好書,入圍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Prix Émile Guimet de littérature asiatique),獲法國島嶼文學小說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日本書店大獎翻譯類第三名、《Time Out Beijing》「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臺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金鼎獎年度最佳圖書等。作品已售出十餘國版權。
吳明益專訪:
《苦雨之地》,太初有字──重新定義小說的可能:專訪吳明益
細節打造的聖殿──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浮光》吳明益:最初之火微小而明確地被點燃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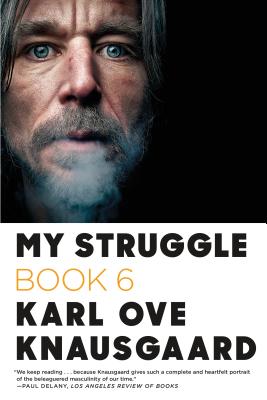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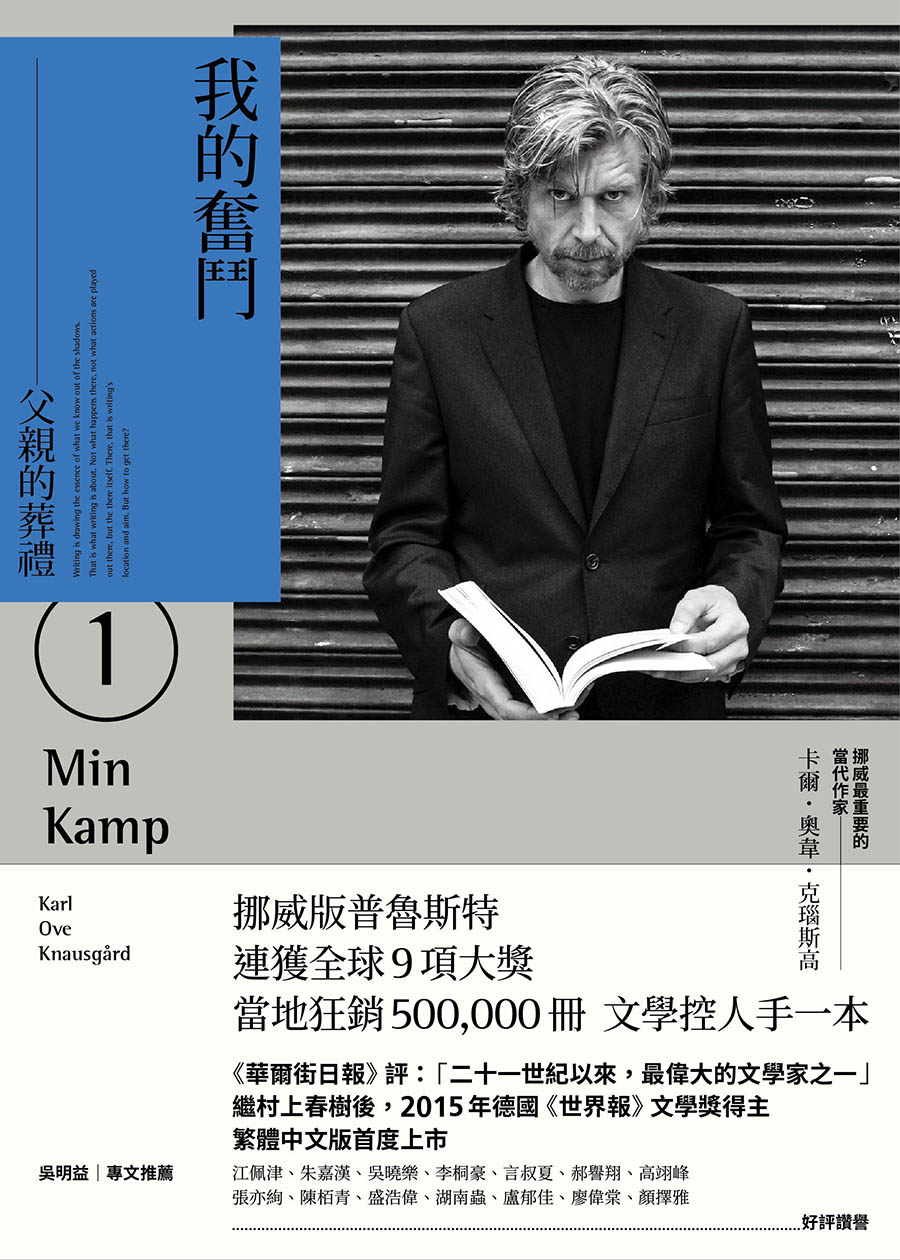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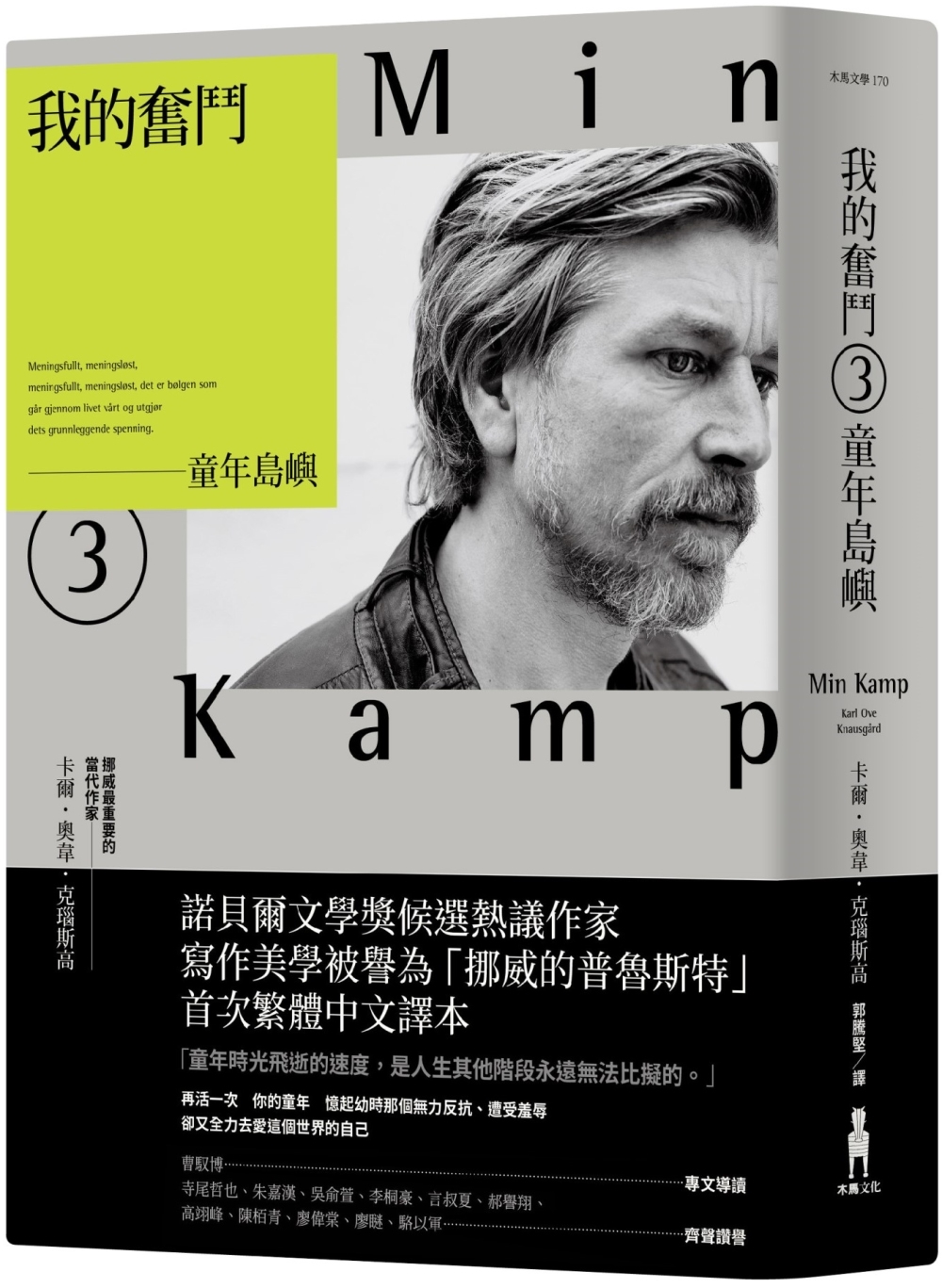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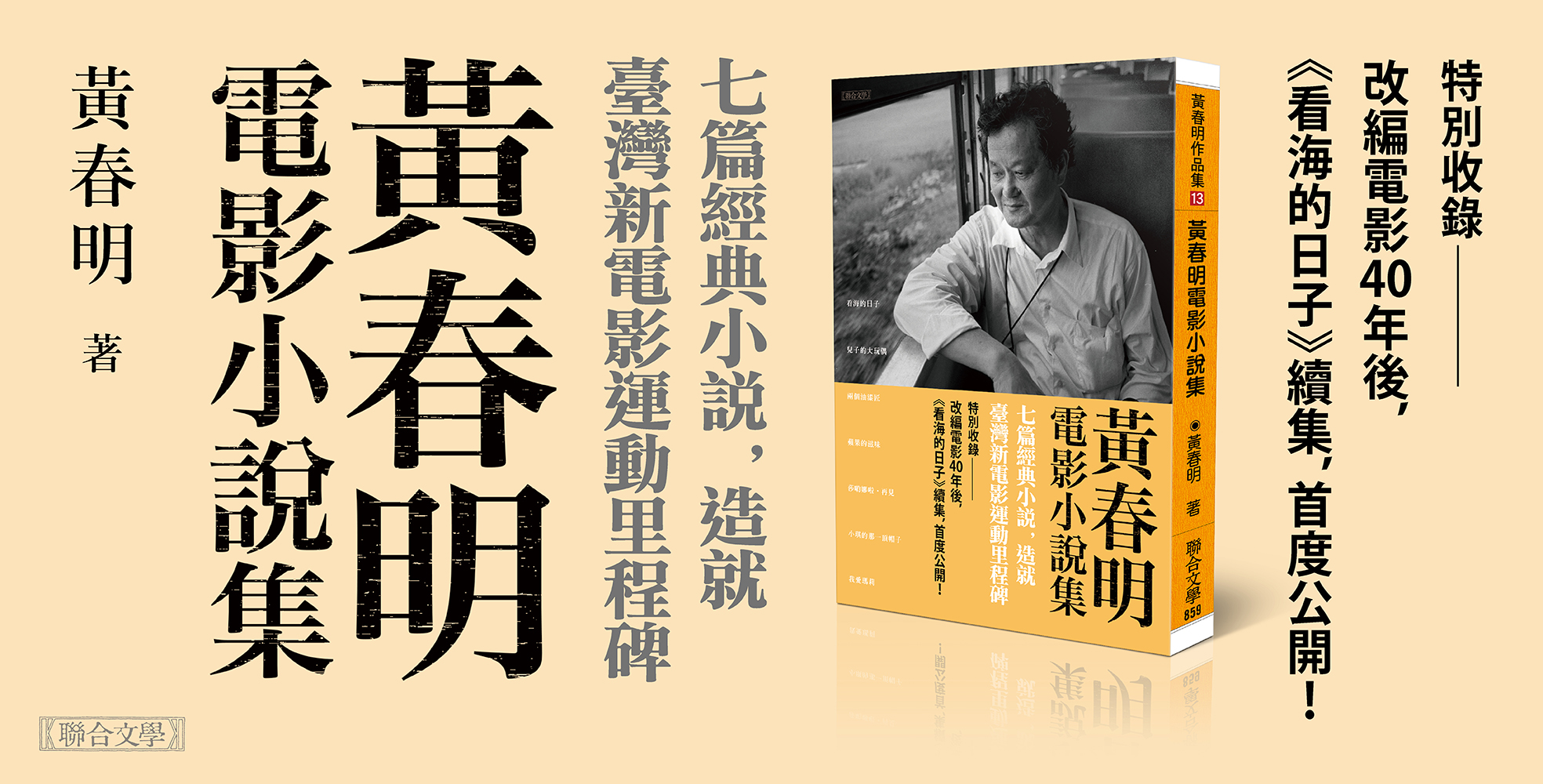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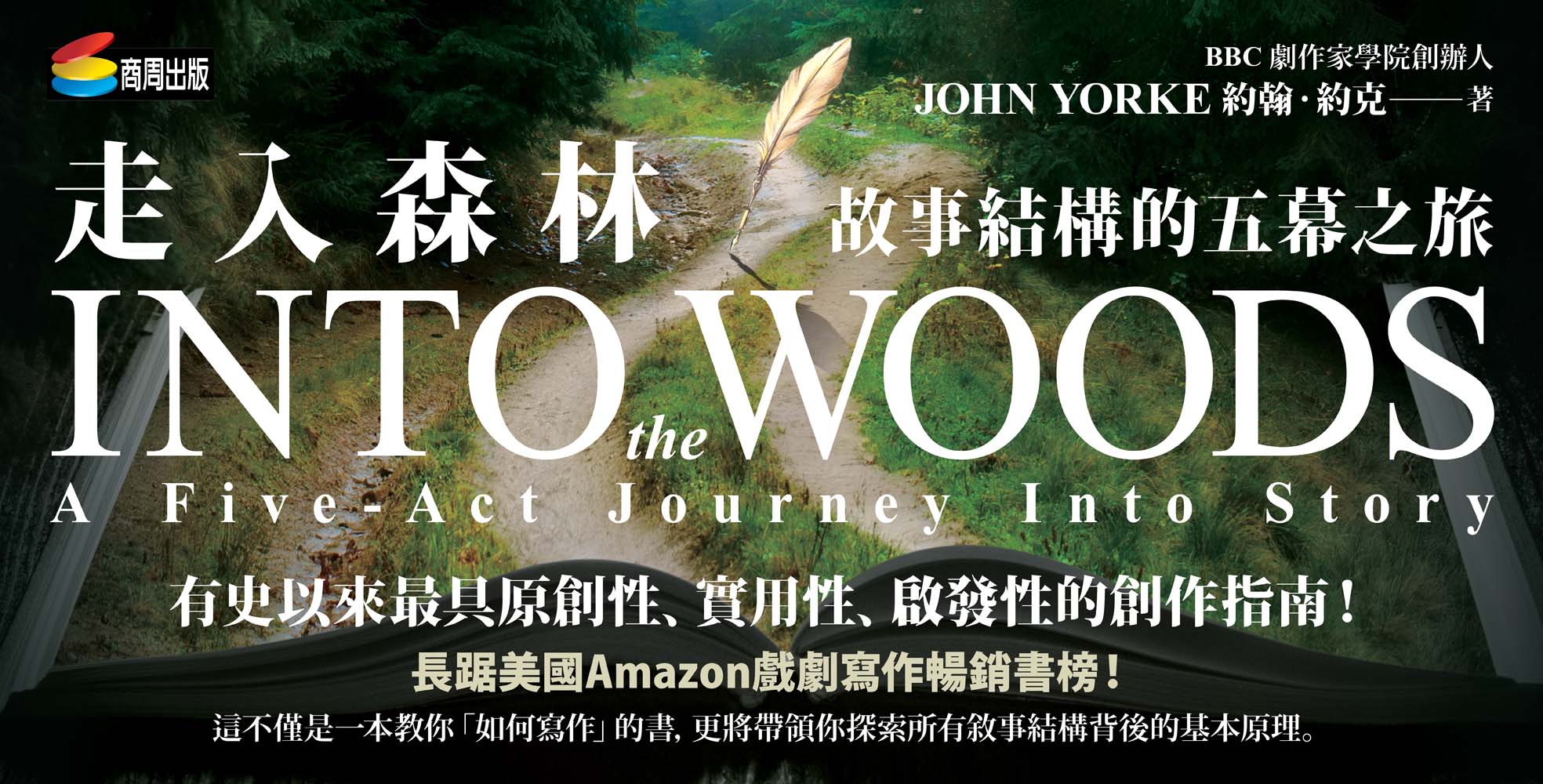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