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女》從頭至尾透過一個女性聲音(框外的〈史料〉不算的話),吐露在宗教極端主義的基列政權下的生活經歷。女性在身體、經濟、知識上皆受嚴格控制的。敘述者語調平靜,隱含怒意,精細地將外在與內在變化編織進故事的畫毯;細節重於情節。章節幾乎可比作摸黑在房間與房間之間前進。若說影集、圖像改編與原著最大的差異,可能就在於這種因受限視野而形成的封閉感。
《證詞》有三個聲音。即便不考慮愛特伍小說筆法的變化(更明快、邏輯更清晰的劇情推進,降低詩性修辭),三個聲音也帶來非常有趣的結果。敘述者分別是基列中長大的艾格妮絲;基列外長大的黛西;曾生活在舊世界,後被基列迫為收編的麗迪亞嬤嬤。三個向度的點,足以構成平面。《使女》的畫毯,有平整的表面與滿布醜陋的結的背面——反烏托邦小說的諷刺力道與危險皆源於此。而《證詞》的平面是另一種:當二與三加入,基列的盒子打開,那中間對話的區域,我稱之為「緩衝帶」。
▌實體:艾杜瓦館
在基列,為求門當戶對,婚姻自然是安排的。年輕女孩倘若不願嫁,有什麼選擇?其實就是《仲夏夜之夢》也出現過的兩條老路:死路一條,棄絕俗世(也就是出家)。成為死人或出家人,讓她得以突破社會規範的限制。比起一了百了的「登出」,後者更難以被歸類,彷彿住進特例的括弧,「成為嬤嬤不是權利是特權」。艾杜瓦館就是那括弧。
在夫人、使女、馬大之外,嬤嬤自成階級,負責使女、少女、新娘的教育與規訓,擔任婚配的中介人。收到「更高服侍的召喚」的她們,比起神職人員,更像女舍監或女特務,儘管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修女與尼姑擁有「多重身分」並不罕見。
愛特伍創造「艾杜瓦館」,讓聚光燈打亮嬤嬤們的活動足跡,原先看似扁平的基列政權因而起了摺曲。艾杜瓦館內,嬤嬤一手發明基列女性的儀式守則,延伸父權之惡;艾杜瓦館內,嬤嬤擁有絕對自主權,隱然又是女性「妥協中反抗」的最後堡壘。它正邪並存的特殊狀態,在小說的地理與心理層面上,形成了無法迴避的龐大曖昧。
嬤嬤們的力量來自於兩種知識:讀寫能力、祕密情報。受過訓練的嬤嬤被允許在館內,閱讀聖經原典——許多內容與政權所宣稱教義大有落差。她們必須去將自己在兩者間調和、或帶著這層「真相的薄膜」去過活。同時,嬤嬤們將祕密情報做為籌碼,暗中箝制主教、夫人,甚至彼此,艾杜瓦館相當於情報中心,操縱不可見的因果下的「正義」。館內與館外「知的落差」,致使它從外部看來,儼然成為空白地區。嬤嬤的力量來自於高深莫測。
空白瀰漫、煙霧四溢,自己也可能看不清楚自己。一旦獲得尊榮與人身安全的保障,復仇並不容易堅持。愛特伍選擇了希望。
▌虛線:跨越邊境
求道者嬤嬤在升格為正式嬤嬤前的最後任務是到海外傳道,兩人一組,發放小冊,吸收陷入(性別)困境的年輕女孩,投奔基列:「珍珠女孩負責採珍珠」。這是一種定期的人口移動。而另一種移動不那麼定期,從基列出逃的案例亦層出不窮(可能由反基列地下組織「五月天」協助)。
《使女》之後,《證詞》的視域突破了基列的邊界。隨著每一次跨越,拉出寬度、深淺不一的緩衝帶,在它們的張力中,事物可能裂成兩半。
寶寶妮可就裂成了兩半。身為使女的母親,將她偷渡至加拿大;此事引發雙方政府的角力。寶寶妮可的照片在基列聖人般複製,她的歸還,有「完璧歸趙」式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她也被反基列抗議活動運作為精神象徵(「寶寶妮可!自由的象徵!」)雙方都在掠奪,將寶寶挪為己用——而寶寶則在不知其為寶寶的情況下,長大成人。
偽裝也是一條緩衝帶。由外部滲透進去的黛西,必須張開羊皮戒慎模仿,而從基列出逃的艾格妮絲,則必須學習穿上狼皮。真假公主的戲碼是迷人老招——愛特伍從不避通俗劇。《使女》中對照(基列)現在之於(美國)過去,《證詞》則提出內與外的比較。
這樣的「比較」自然不是「眼睛對眼睛,鼻子對鼻子」的。交換身分的時候,遺漏、包藏、猶豫都會發生。愛特伍透過小說展示,對存活下來的見證者、存留下來的歷史遺產而言,跨越邊界從來不是一瞬間就從這裡到了那裡。邊界會轉印在人與歷史的身體上。拖泥帶水地,像與一條彈力繩搏鬥。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 我們每個人身處在歷史裡,都有各自的真相──讀《使女的故事》續集《證詞》
- 當女權與民主同時陷落:就忍著痛一次讀完「使女」的「證詞」吧!
- 在這些畫面裡,你甚至聽得見靈魂的尖叫聲──讀圖像版《使女的故事》
- 你有想過跟班們的感受嗎?《約聘惡棍跟班》反轉英雄片公式,改講配角的厭世職場
- 從《使女的故事》與《證詞》聆聽未來「倖存者的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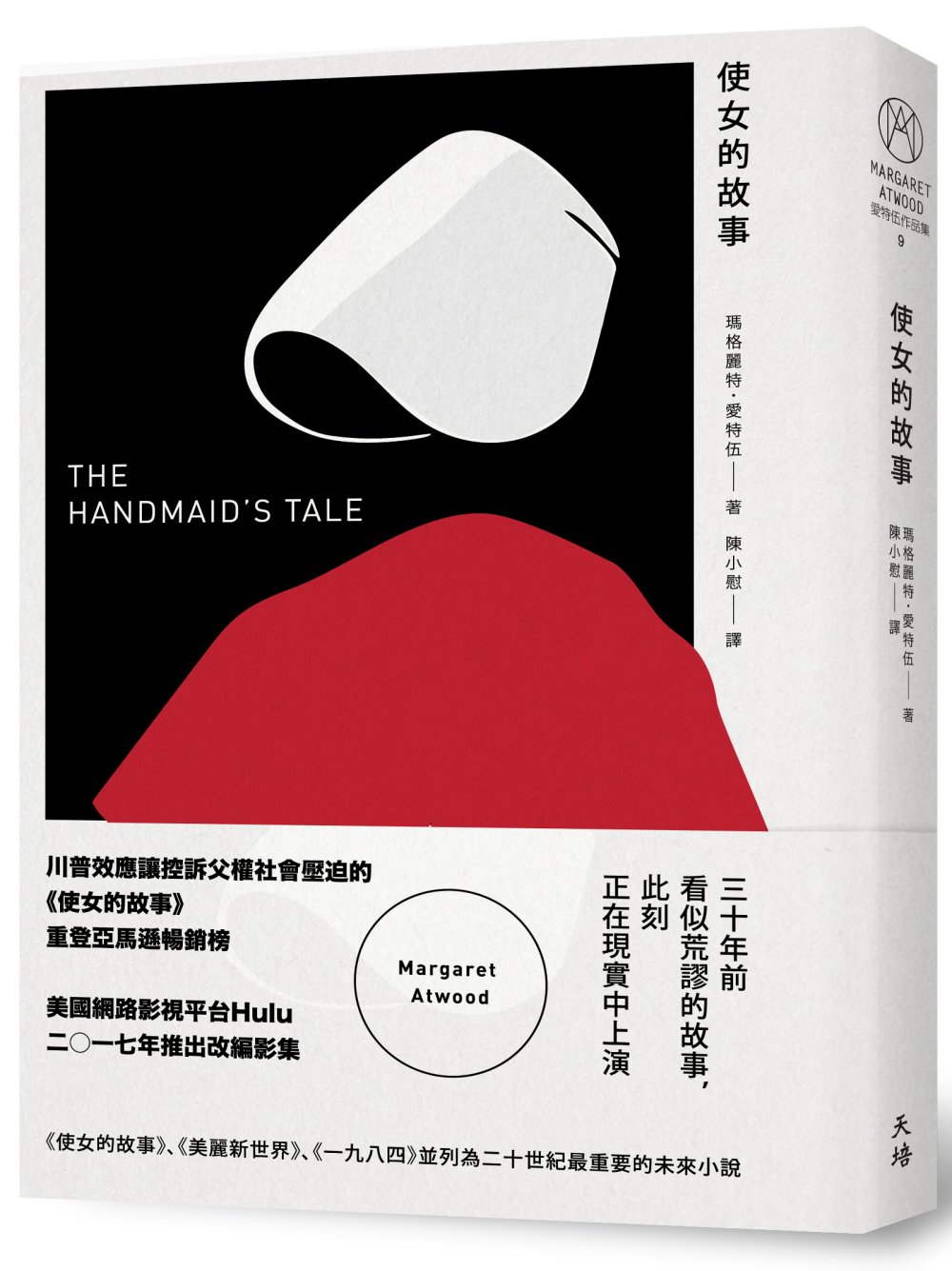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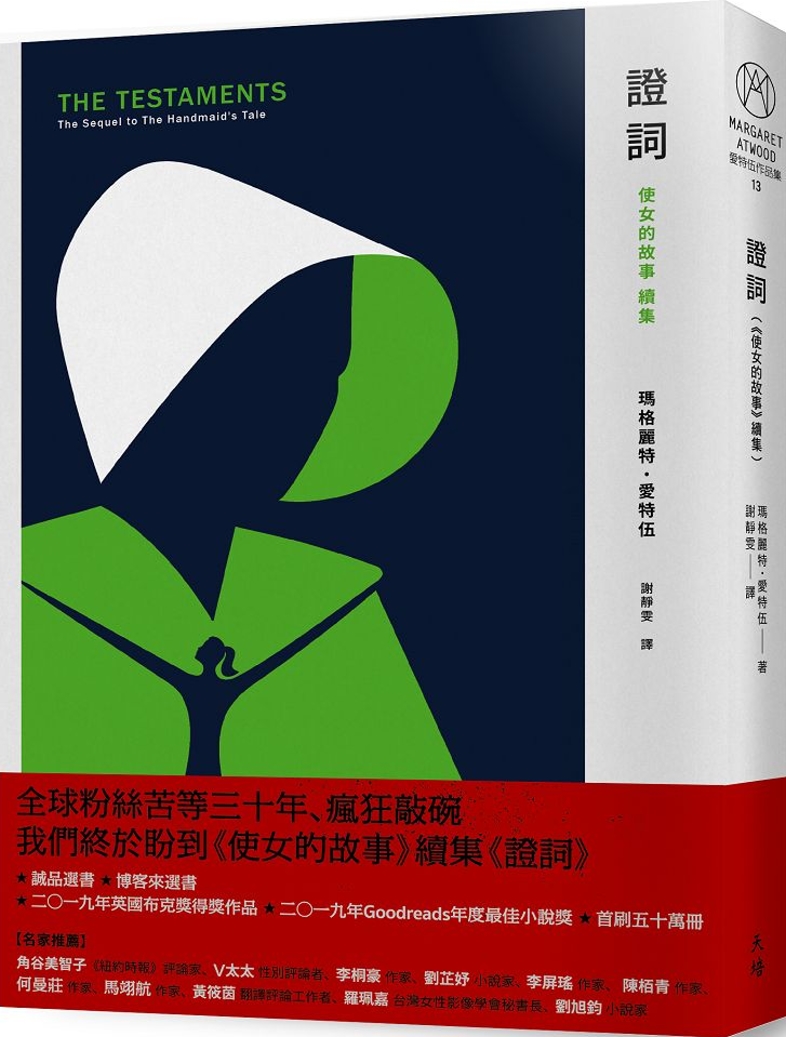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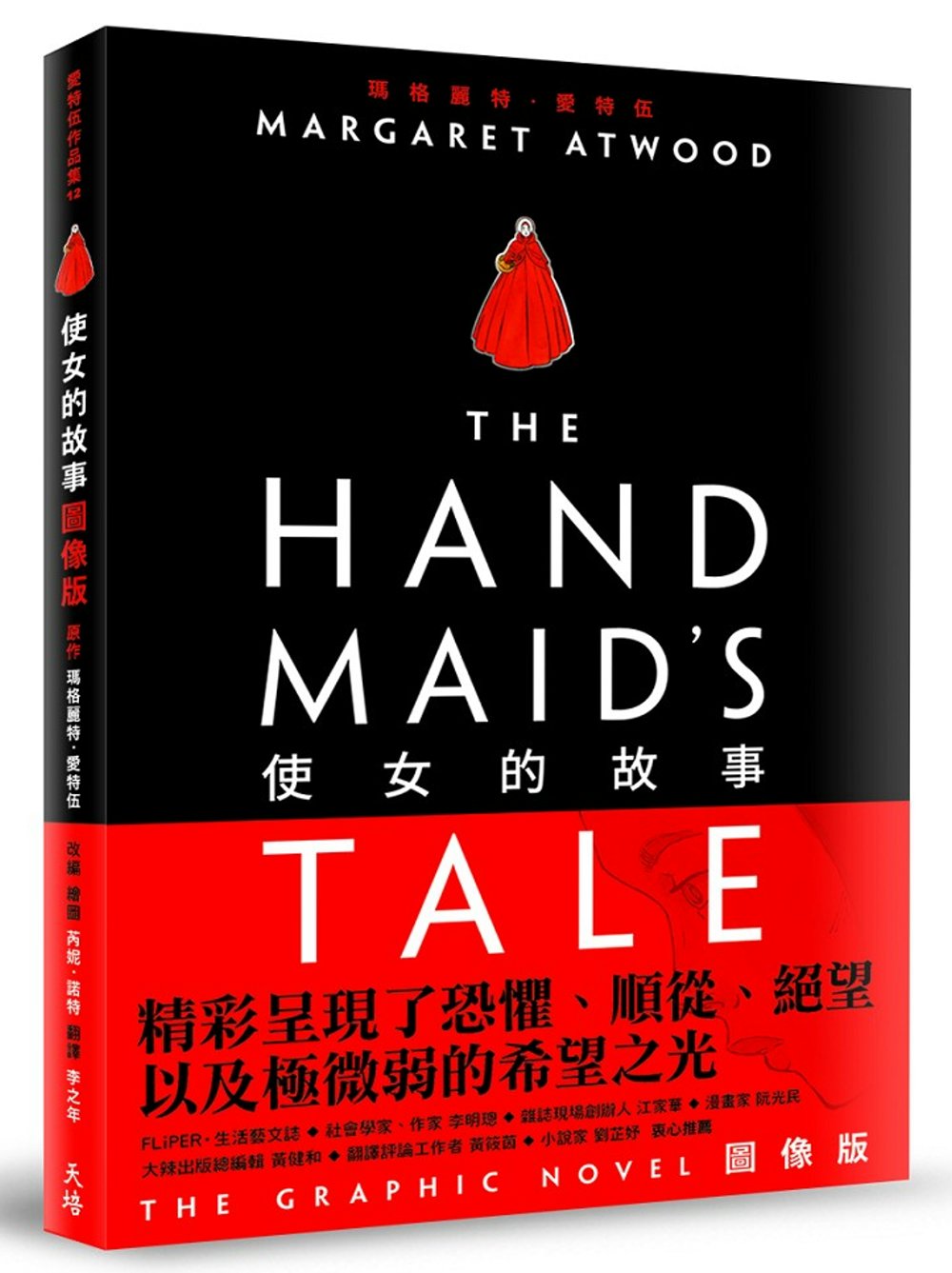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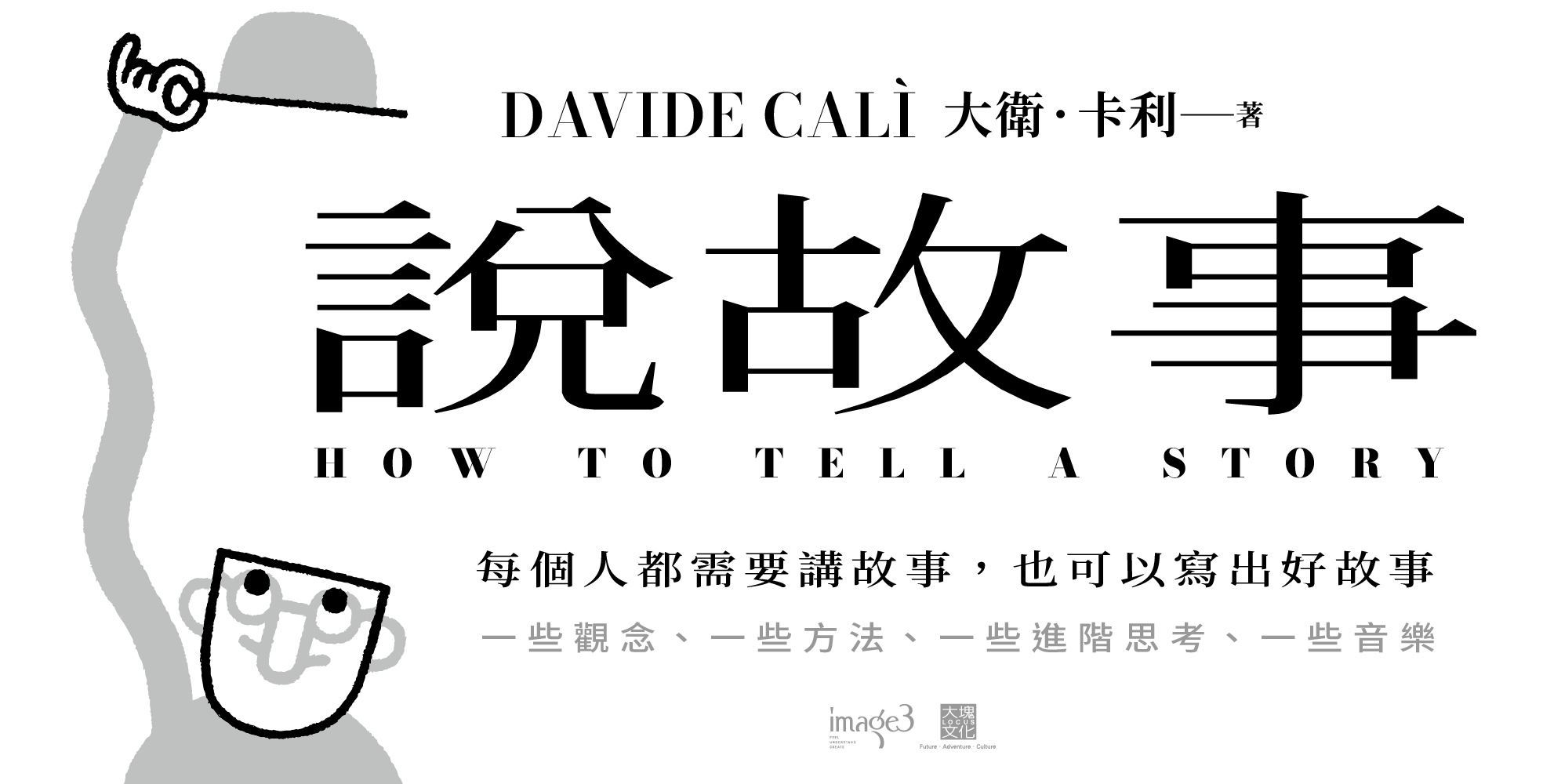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