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為走進廁所,結果沿牆推開卻是一道暗門,穿過木板隔起的狹小甬道,濃濃菸味竄上鼻子,耳邊盡是叮噹響,小瑪莉和老虎機畫面正在跑,777水果盤無止盡輪轉,周旁是一排大型機台,搖桿上的手鬆鬆放著,正宗格鬥遊戲高手還能空出兩根指頭夾著菸,尻大招的時候螢幕裡外都有星火點點,想熄掉就直接在機台木板上使勁一壓。陳信傑說起他機車環島經過台中時,誤闖一間餐廳後頭的電動間,順著甬道一探頭,眼前煙霧迷茫燈光閃爍的,卻是他的童年,活脫脫走回90年代的他的老家。
短篇小說集《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主打「台灣第一本電玩小說」,各短篇流暢打出各種大招,玩網路遊戲的男人鼻子對著RUSH小瓶子猛嗅成了德魯伊變身藥水、集合吧動物森友會疊合了台灣疫情……陳信傑用遊戲寫就自己的人生編年史,有時,是肉體史詩。
童年是小說家的永恆資產嗎?不過,陳信傑的童年資產,首先是爸媽給的一整麻布袋的五塊錢,讓他在自家經營的電動間無止盡地玩,《格鬥天王》、《越南大戰》、《棒球殺手》……電動間長大的孩子如今成為小說家,書的第一版書名正是《電玩故事販售所》,小說原始命題是:電玩如何影響當代人的精神?
大哉問。但先別管當代人,陳信傑人生的蛛絲馬跡在書寫裡先成康莊大道,電玩的分歧選擇則成了小說歧路花園。書中一篇〈雲蹤〉裡,有個「天明租書城」,他老家開的叫「明天租書城」。小說裡盤繞租書城姊弟半生的一款遊戲叫做《雲蹤奇俠傳》,設定像極了2000年大宇資訊推出的單機遊戲《軒轅劍三外傳:天之痕》,遊戲劇情是:陳朝後裔陳靖仇,被寄予復國之望,浪跡江湖結識江湖俠女小雪和拓拔玉兒。小說致敬遊戲,遊戲則影響了人生,陳信傑說他小時候為《天之痕》幾度落淚,萌生一種名為愛的情感,太愛太愛,廣及遊戲包含的一切,看到說明書上的人物詩詞「美人如玉刀如虹,琵琶儷影氣吞雄」,便覺得無一字不妥帖,也有幾分《紅樓夢》「香菱學詩」的感受,「偏是這幾個字才形容得盡,念在嘴裡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字中有圖畫,用對了字,像打到點,生出感覺。從此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興趣。國文課本裡說起鄉愁,台上老師舉什麼李白杜甫,他先想到卻是陳靖仇。遊戲代入性之強,「所以後來我讀了中文系。」


他甚至因為遊戲裡陳靖仇在鯨背上吹笛,而跑去學吹竹笛。新書發表會辦在誠品,他全無預告,忽地發難:「各位朋友我現在要幫大家吹!」說著就蹲下,站起身時從哪變出好大一根竹笛,不需要麥克風,男孩氣聚丹田,鼓盡十幾年攢聚功力,比他接下來要說的話,更像是對小說的相思,或是宣言。
因為太愛打電動,所以開始寫電玩小說嗎?並不,陳信傑說,「我大學去修教育學程,大家輪番上台報告自己童年,我說完自己的電動間出生,換得老師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我心中覺得很不對勁,家裡開電動間的孩子有什麼錯?」
「人總是會走向與初始設定不一樣的道路的。」〈雲蹤〉裡這樣寫道,該是他對世界的回應。
「早期大家認為電玩是不好的。我想打破這個刻板印象。你說電玩會帶來社會問題,但哪件事情不會? 」他家電動間因為政府大力取締電玩而關閉,不過幾年後,網咖興起了,「但那就是另一個形式的電動間啊!我那時隱隱覺得不公平,電動間不可以,但網咖就可以?後來我又想,正是因為這樣才可以。我要朝這方向去——電玩可以做更多。」
電玩一開始是娛樂,後來包羅萬象,它可以成為藝術。走向和初始設定不同。他這段對電玩有愛的人生,何嘗不是一個「靖仇」,也就是報仇的故事?陳信傑笑說,「我對自己這部小說集期許甚高,一直期待停筆那天,我將對著電腦螢幕肯定地說:『我寫了一部偉大的小說呢。』如今我已經結束這漫長的旅程,但浮現心底的不是剛剛那句話,而是:『我用一本書來證明我的人生不是錯的。』」

他熱愛《天之痕》,於是我們知道他玩RPG(角色扮演遊戲),「我喜歡角色扮演!我有一個宣言:如果遊戲可以變成藝術,這樣的藝術,必然發生在角色扮演的類型上。」陳信傑談起電玩眉飛色舞。那小說呢?他說起練功之道,是的,他用「練功」二字,這也驗證他所說的「電玩如何影響當代人精神」,「首先就是『譬喻』和『象徵』系統的對位——用電玩的語彙來描摹人生。」
他後來離開教育學程,跑去念台藝大,電影也摸了,遊戲夢做了。研究所又回到東華華文所,繼續寫小說,但體內集各家真氣,戲劇的、電影的、遊戲的,套句武俠小說的「功夫雜而不純」,他那時受教於作家吳明益(訪談間他稱老師是「大德魯伊」),經常被點出「如果是小說,應該是要……」,總是差那麼一點,於是他決定練好這門文字活,碩二的暑假,圖書館,一只碼錶,一本書,電玩少年苦練格鬥絕招那樣開始在圖書館閉關。
「我每天讀一本小說,而且不能是同一位作家的。還規定自己讀一頁不能超過一分鐘,一本書讀多久要按碼錶計算。讀完後還要每天寫一篇技術鑽研與破譯的專文到臉書上。」
按表操課,陳信傑成為練功狂,在那樣一個發現與探索的旅程中,他遇到了石黑一雄,「這就是我要的。石黑一雄的敘述很像聊天,既模擬人物的腔口,又容易讓讀者代入自己。主要是,敘述者本身竟是可以說謊的。只要他說句『我可能記錯了』就行,那產生了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小說中每一部分可以是事實,又能縫合作家的想像。」
這也成了《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收錄的大部分小說的基調,多是第一人稱,「我的確是用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說話的口吻在說故事。」正因為可能出錯,那個錯成了文學的對,容納更多謊言、似是而非與積非成是,開啟小說巨大的腹地;而陳信傑模擬人物,不正是把小說當成RPG在玩嗎?他玩笑道,「我那時人稱東華石黑一雄呢。」
那個暑假過後,陳信傑連得數個文學獎,功力大增,開始他的小說家RPG。
那東華石黑一雄的文學初戀是誰?「白先勇。」石黑一雄給他一把技藝的劍,白先勇給了他文學的心。陳信傑說,「我高中時從《台北人》裡感受到文學可以這麼美。有一度我覺得自己就是朱青,真愛已死我要去浪。」後來又讀《紐約客》,讀到「我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有時窗外的陽光落罩在他的身上,我看得到的只是一團淡金光暈中一個青春的剪影,那卻是一個咫尺天涯遙不可及的幻象。」高中男孩心頭一揪,竟在捷運上嗚嗚哭得不能自已。

白先勇小說是同志和文學的完美交集。上大學後,陳信傑開始補起同志文學學分。身為90後作家,如何看待發展至今的台灣同志文學呢?「白先勇前後開始茁壯,90年代至顛峰,而現在又要回歸沒有的時期。」他說。
在他看來,首先是議題操作影響市場,「社會上有一個龐大論述:『愛都一樣』、『不一樣又怎樣』,整體社會想要弭平那個鴻溝,但如果都一樣,你很難把它獨立出來,所以在市場上同志小說很難包裝。」
就書寫而言,韶華極盛,能寫的題材,能開發的路線,都已發展到一定高度,「作品若不具某種前瞻性的討論同志文化、議題,要叫『同志文學』可能會名不符實,不然就會是『老調重談的同志文學』。此外,我也不認為理念先行的同志文學是我想走的路。」
站在什麼都沒有的地平線上,陳信傑想走什麼路?當愛都一樣,別人倒先看出他小說的不一樣,作家王聰威讚美他:「避免同志小說過度的悲情,也不在乎意識型態的正確描寫,是可以輕鬆閱讀,讓人十分愉快的作品。」李桐豪則說:「腦洞大開,玩什麼,就寫出什麼,你真的,真的,是沒在害怕的啊。」前輩讀他的小說,幾乎像坐在電動間看別人打電動了,沒在怕,輕鬆加愉快。
小說集收錄一篇〈峻堯與明尉〉。回應是盤桓台灣同志文本一整個世代的經典命題,兩男一女,總是他愛他,他愛她,從《盛夏光年》《女朋友男朋友》到《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愛是單行道,陳信傑卻輕易用小說走出和上一個世代不一樣的路。他筆下的峻堯戳破明尉的保險套,「這樣你和你心愛的女人就有了,但說起來,那不也像是我的孩子。而我要慢慢接近你的孩子.....」
得不到你,就得到你的孩子。針尖一樣刺的小說挑破一個世代情慾和哀愁滿漲的保險套,何其大膽,前人以為重,他輕輕地讓一切洩了出來,長出一個新時代。

「以前可以覺得社會不公不義,是別人在迫害我們。但到如今,社會更進步多元了,我們有交友APP,我們知道誰是同志。但就算如此,我們還是感到失落,甚至更失落,那是為什麼?」陳信傑說,「我的小說想表現的,正是這樣強大的失落感。」
失落,也就是所謂的「愁」吧。陳信傑壯漢推車,偏用小說靖仇,也淨愁。何其重,卻又那麼鬆鬆愉快,我說這樣的小說好讀卻又讓人害怕呢,他笑說,「不會啊,我的小說特色就是『感傷,但是溫暖』。」
這形容的是白先勇吧。或許陳信傑說錯了,他不是東華石黑一雄。但他又對了,藝術會發生在角色扮演的類型上,對他而言,白先勇是一個NPC(非玩家角色),石黑一雄也是,被尊為「大德魯伊」的吳明益何嘗不是,德魯伊也是借自遊戲的稱呼,他們有人是傳功長老,有人是偉大師父,但給他的,只有技藝,是+9寶劍,而此前世代所有的努力,就是讓一切成為他口中沒有的,是他RPG大旅行的開端。
「我要寫的是我的生命史,是我感興趣的主題。」陳信傑終究不會是陳靖仇,恩仇兩忘處,江湖煙水裡,他是全新的人。一個全新的世代,從他筆下,或身上,要開始了。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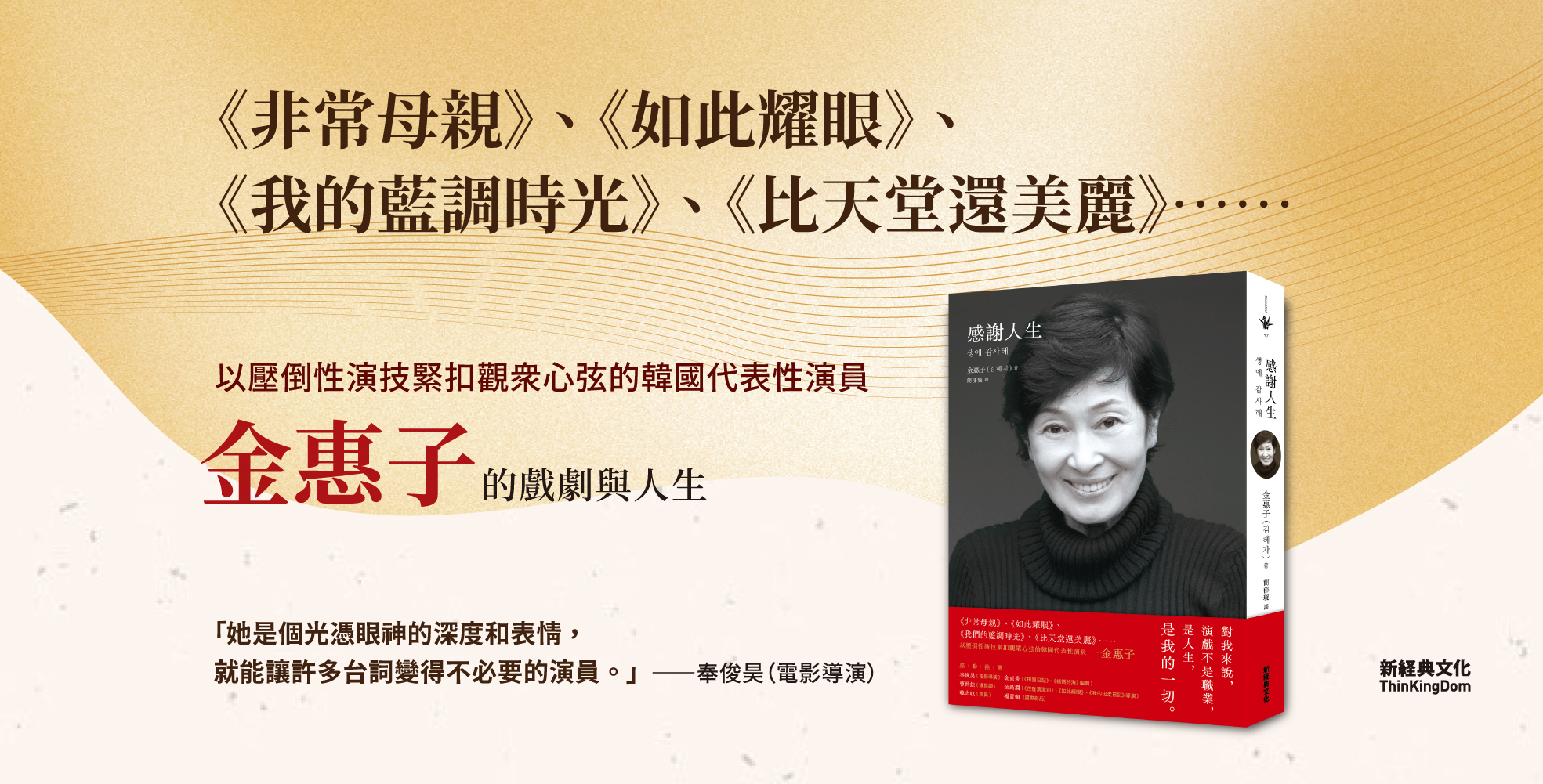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