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新版的《香水》,在書腰上華麗堂皇地寫著:徐四金70歲誕辰紀念版。除此之外,世界其實對他幾近一無所知,這樣的不知,大約是最好的生日祝福了。早在略帶自傳性的《夏先生的故事》裡,徐四金便在人生雪地與拔高樹頂上,繃緊了聲音告訴人們,如果你關心我、如果你愛我:「那就請讓我靜一靜!」
那就讓我們走近文學,《香水》歸《香水》、《鴿子》歸《鴿子》,祝他生日快樂。
 德國小說家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 1949- )。(圖片來源 / goodreads© Philipp Keel)
德國小說家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 1949- )。(圖片來源 / goodreads© Philipp Keel)
《波赫士談詩論藝》曾這樣定義了他眼中所見的當代創作景況:「深切感受到小說(創作)或多或少已經在崩解,不復與我們同在。」這是他在1967年秋天,客座哈佛大學講學的演講整理,那時波赫士應該已經因家族遺傳失明了。一路至1986年過世,想來,無緣也無法讀到徐四金於1985年出版的《香水》一書。如果他能讀見《香水》,與我們一起抬頭看那像燃燒到了盡頭的火炬那樣閃著紅光的巴黎日落,映照塞納河水如丟進幾百萬個金幣一般的純金光潮;南法繁花盛宴裡,以泥爛百花萃化一城精露的格拉斯,或許會理解崩解過後,才能重生。理解一代又一代,成功透過「史博式」寫作的寫作者們,可能已不只是小說家,而是能力者了。
自詡為法國作家的米蘭.昆德拉,是。與昆德拉同代,日本的三島由紀夫,我認為也是。稍晚於他們,徐四金與他的《香水》,當然是。舉凡有朝代傾頹、崴樓焚陷之處,總有文豪誕生。其實每一本小說,不過是小說家其人「世界觀」的再現。辨析《香水》的前中後味,抓到一縷藏在書間細絲般的線索,徐四金刻意露出的小說家之聲,藉著穿越時空再現18世紀,說的全是「現在」的思索:「沒有什麼是確定的,所有的事情都突然變了樣。」18世紀裡,雷電被製造、地球成了圓形,原來世界是幾百萬年的鍛造,而不只是上帝的創世七天⋯⋯徐四金引用數學家、哲學家巴斯卡的那句名言,「人類的不幸都是源自於不能好好待在房裡,待在屬於他的地方。」小說主角葛奴乙於是現身,向整個舊世紀提問:「那麼我屬於哪裡?」
雖然經常被誤以為是法國作家,但卻是道地德國人的徐四金,不管是《香水》與《鴿子》都選擇了法國的城市為寄生地。不管產地,《香水》是悲劇嗎?看過小說或電影的人,大約都無法否認。不成文的規定是,通俗流行喜劇,文學的通俗則是悲劇,可《香水》當然不是傳統的希臘式悲劇,將人與神的悲劇性,通往天定徒勞。《香水》的悲哀,是很德國的,應該說更靠近17世紀左右德國的「哀劇」(Trauerspiel),不只是簡單地悲鳴哭喊,神為何也苦?這些都省了下來,君王貴族、魚市粗婦都是發出惡臭的凡人,當世最好的香水,在葛奴乙的嗅聞中,也不過簡單粗魯的把戲。生而為人,就是有罪。
但我們已不在17世紀了,即使30多年前與現在此刻,《香水》的出版,都會造成同樣巨大的轟鳴。它既悲哀也通俗、它既復古卻現代,它勇敢的媚俗,比如每一個傷害過葛奴乙的人都遭到了報應,不幸也是量身打造,不怕死的就長命茍活、自私享樂的路死街頭。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報應雖然落俗卻很有力,就像善與惡,永不過時。而那奪走26個少女生命的殺人魔,卻是所有人物裡最善良的一個,善者為魔,多麼通俗多麼勇敢的一部小說。
於葛奴乙而言,香水不過是他氣味的遊戲。文字於徐四金,大概也有同樣感受。當我讀到他寫:「那些在他腦海中不斷浮現的美妙氣味概念,在現實世界中竟連一顆極微小的原子都造不出來。」即使是經過轉譯的文字,仍然深切傳出了小說家發出的一句悠然長嘆。氣味也好、觸覺也好、文字音樂都一樣,在世界的真實面前,全都太微弱了。任它是大河小說或每秒120格的電影技術,它都不可能真實,只能逼臨。
擬真的香水,再高超都是擬態,更何況每個人的「真」,都是不同面貌。巴黎羅浮宮有過一個香水企劃,沒有預算限制,請來當世八位拔萃的調香師,為八幅作品(畫與雕刻),從勝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到米羅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浴女(The Bather)創作,它們是晚香玉、香茅、橙花與廣藿香和沒藥和溫暖的佛手柑,它們是調香師的感官與世界觀。我曾拿起它們一一嗅聞,卻與我所感聞到的那些作品,傳來的心靈香氣,完全不同。因為我也有我的世界觀。
 (左至右)勝利女神、米羅的維納斯、浴女。(圖片來源/wiki)
(左至右)勝利女神、米羅的維納斯、浴女。(圖片來源/wiki)

巴黎羅浮宮「香水企劃」。(圖片來源/官網)
徐四金怎會不知道?電影版的《香水》裡,曾說道:「有一件香水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它不能使他(葛奴乙)如常人一般愛人與被愛。」天生無味無臭無香的葛奴乙,天生也無愛,當別人向他索求香,他要的從來是愛。徐四金並不希望有人聞見他的調香或魚市或南法的氣味,因為他知道,不會相同。可有一件事,卻能穿越文字語言香味顏色,比如他大膽說著的「愛」。徐四金的文字就是香水,被吃掉的葛奴乙,得到了愛;被作者瘋魔般完成與讀者貪婪吃掉的字,同樣也是出於愛,原來我們都會「因為愛而做了某件事」,於是,就超越了所有世界與各自的世界觀。
許多年前,曾在外網上讀見一則對《香水》的點評,評論者說:「《香水》不就是世界三十年、七十年、百年前的樣子嗎?」很可惜,我至今已能堅定回應:不,那也是現在世界的樣子。我們向前走的軌跡,前人早走完了。但不要絕望,世界還在呼吸。
當我們感慨著一個個巨人倒下,害怕再也沒有偉大的導演、可怕的小說家或球星與物理學家時,我都會想起漫畫《鬼滅之刃》,反派角色「十二鬼月」裡排名為「壹」的強人,執念於自己的生命消逝就再無強者,一念成鬼。比他更強大的孿生弟弟卻選擇輕盈地老去、死亡,但我相信他說的,新的呼吸永遠都在誕生,新的偉大永遠都會發生。
就像我相信,世界會一直出現如《香水》一樣偉大的小說。
就像我也相信徐四金,世界若有奇醜惡臭,也必有愛。
作者簡介
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 2017年出版《寫你》, 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OKAPI專訪】散文是「看自己」和「怎麼被看」的遊戲──蔣亞妮《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延伸閱讀
- 蔣亞妮:一場緩慢耽溺的東方大幻術──迪迪耶・德官與他的《林園水塘部》
- 【週二|反派壞壞有人愛】馬欣:美的最終復仇──《香水》葛奴乙
- 盧郁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和其他世紀瞞天騙局──讀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 膽敢「妨礙」革命的18歲女孩,她的下場是...?──讀安娜.伯恩斯《牛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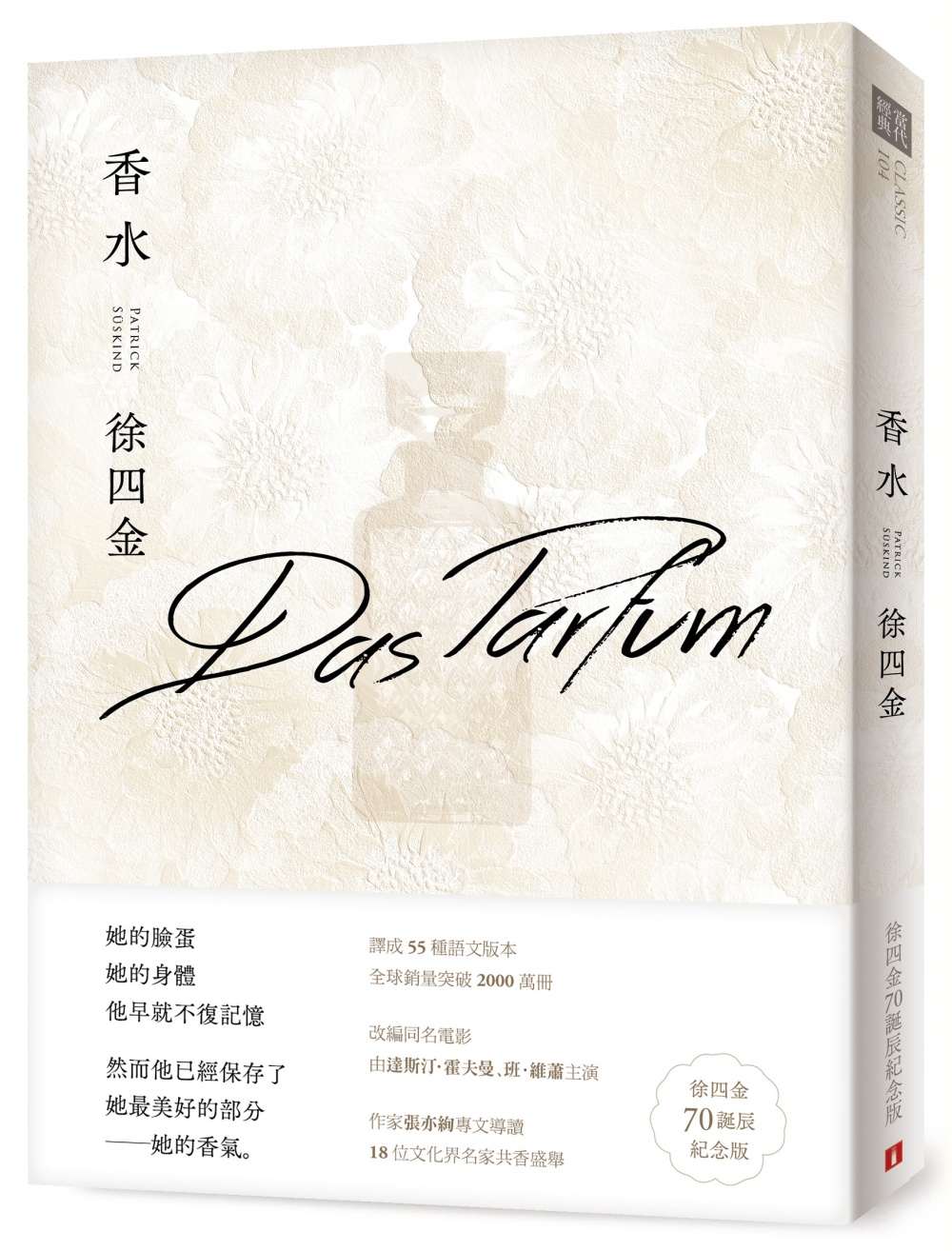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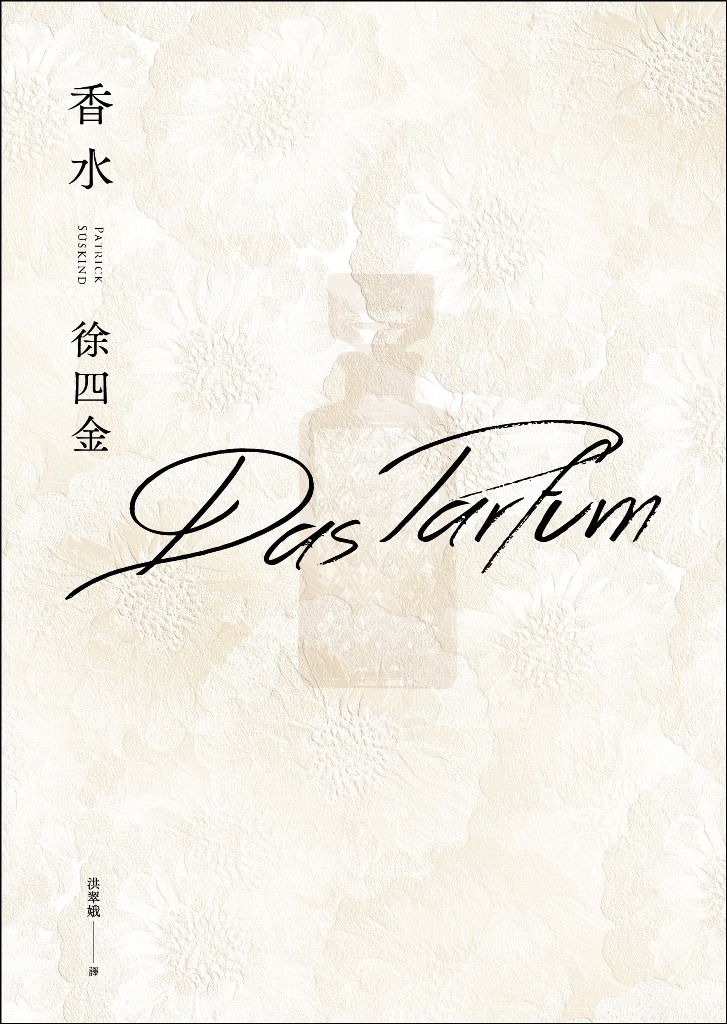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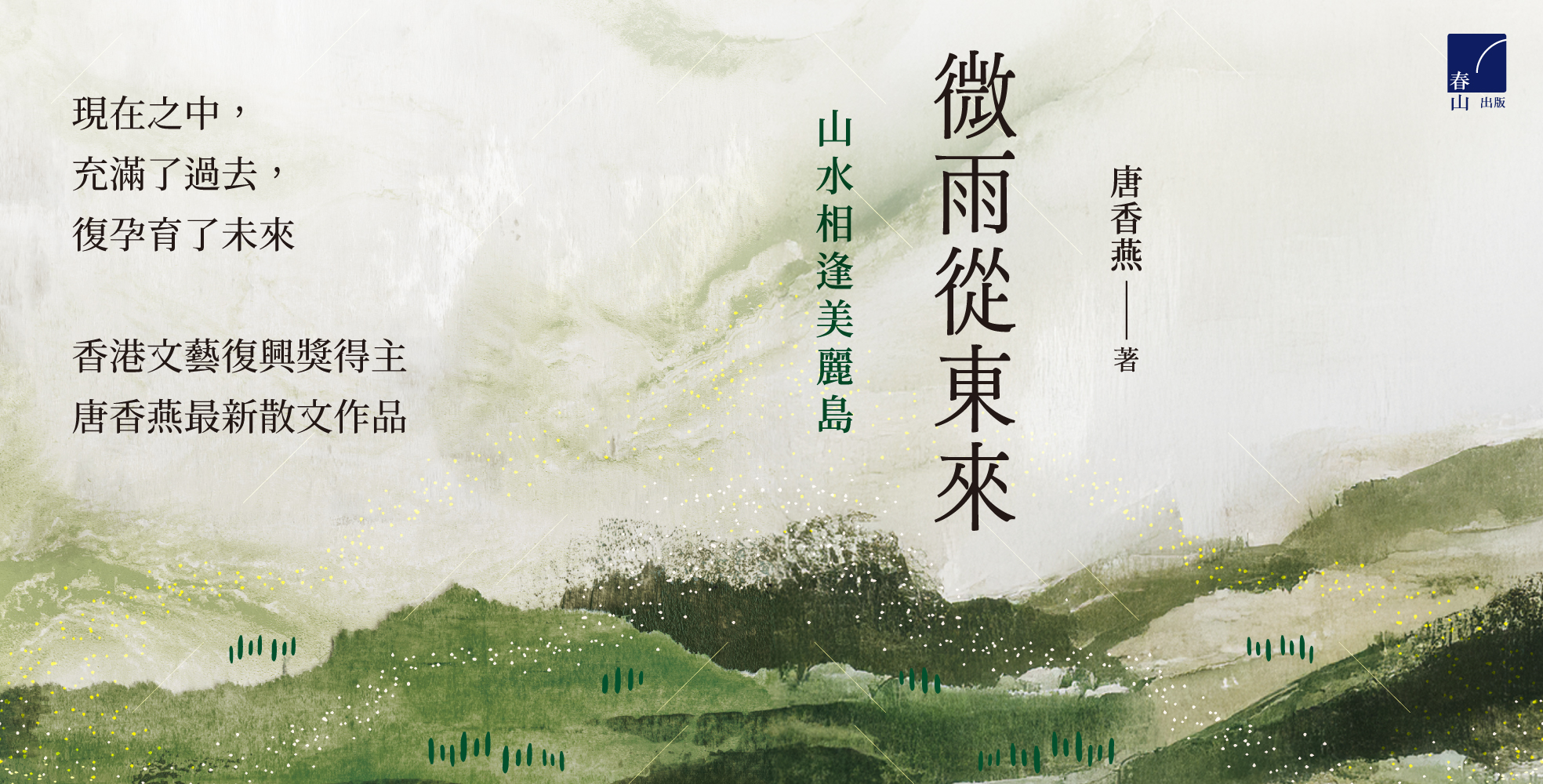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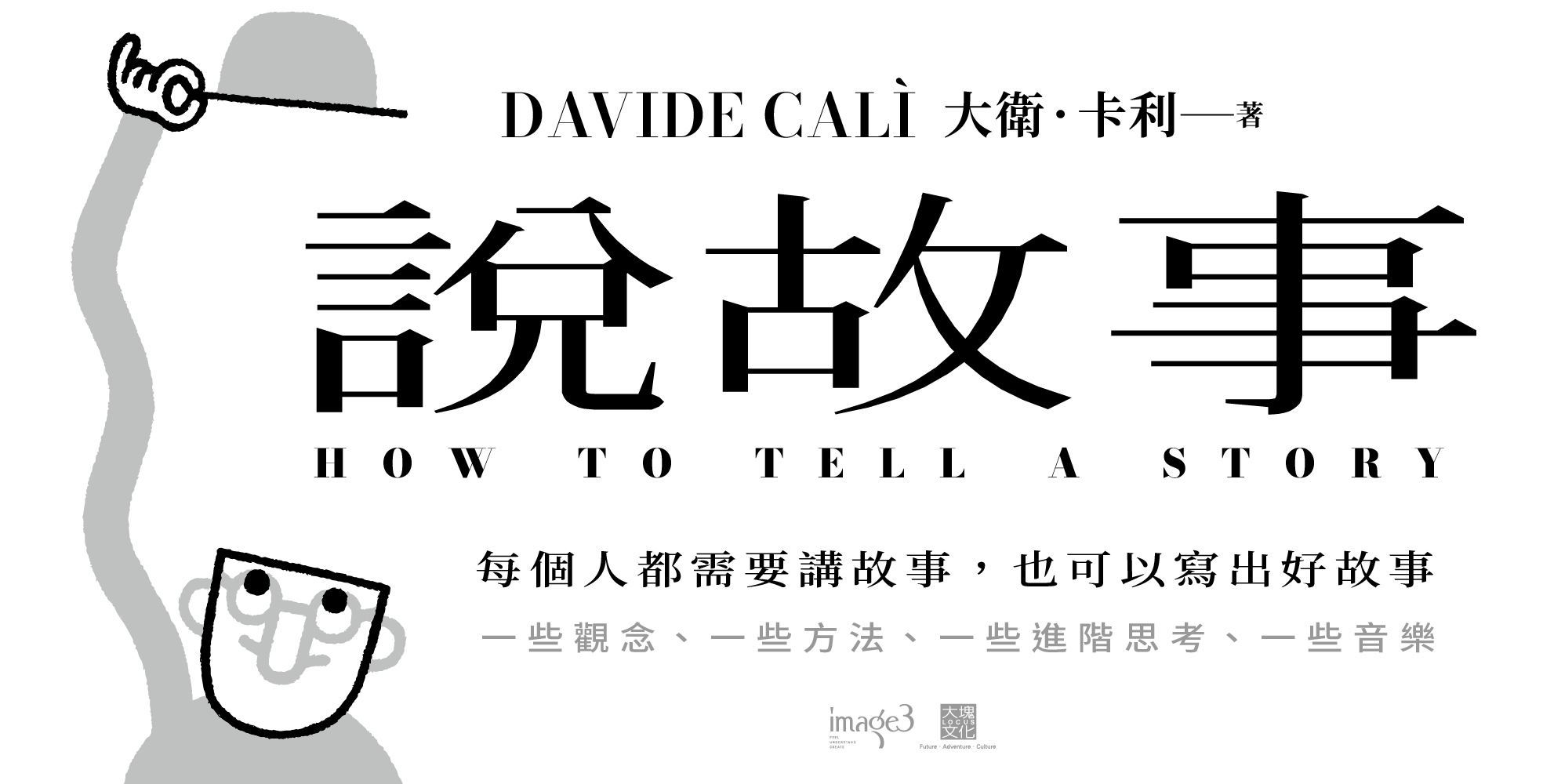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