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健三郎在《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提到了他的第一首詩,啟發於看露天電影時看到開滿櫻花的樹枝特寫:「就在那瞬間我被深深地吸引了。那小小的樹枝,還有那成串的花和樹葉,微微地顫動,微微地顫動,永不停息……」他想的是,看起來無風,枝葉為何會晃動?之後他親身觀察,發現果真嫩葉在不停搖晃,但臉頰上感覺不到風!
之後他開始觀察大自然,並體會了「如果不認真地觀察,那些東西什麽都不是,只是死的東西」,而後他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詩:
晶瑩的雨滴
映射出了風景
雨滴當中
有另一個世界
這四句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麽」的詩,大江認為,他往後人生的寫作,都是在寫那個「雨滴中的世界」,他認為那個世界能映射出他所處的世界;余華也有異口同聲之言,記者問他寫作動機是什麽?他答,「我想,是對虛構世界的迷戀。」他還有一句話是,「如果作家特別責任的話,用虛構的方式表達現實的真實性。」余華的「虛構」和大江的「雨滴中的世界」是否同為一物?
先撇開這創作觀不談。上面這四行句子,足以成為一個清晰的意象、image(請想像image此字由imagination〔想像力〕而來),從這裡對應伊朗導演阿巴斯說的:當我費心寫一首詩,我想創造一個意象的願望僅僅在四行詩中就得到滿足。詞語組合在一起,就變成意象。我的詩就像不需花錢去拍的電影。/…把這些意象拍成電影,要耗費多少時間?找到一個題材,把這些意象納入一部電影,有多麽困難?這就是為什麼寫詩如此值得。(摘自《一隻狼在放哨:阿巴斯詩集》譯者後記)
我是先看了《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Lessons with Kiarostami),對於一位電影導演以「詩」做為他創作的信念我很吃驚,可能是因為多少有點被明星、影星寫詩這件事誤導,若對阿巴斯不夠了解,以為他寫詩是寫來附庸風雅的就大錯了。這本書雖是「談電影」,卻也談了不少「詩」,例如:
所有藝術的基礎都是詩歌。藝術是為了披露、為了提供新的訊息。同樣,真正的詩歌把我們提升到崇高之境。它顛覆並幫助我們逃離習慣、熟悉、機械的常規。(頁49)
詩歌的精髓是一定程度的不可理解。一首詩,按其本性,就是未完成及不確定的,它邀請我們去完成它、去填充空白、去把點連成線。
真正的詩歌永遠比單純說故事更久遠。(頁50)
由這幾句也能打開了我們對「詩」的認識,甚至比學者講得更清楚。
這本《一隻狼在放哨》的詩都很短,三、四、五句上下,沒有題名,一段接著一段的意象看似隨機組合。
剛長大的野草
不認識
老樹。
贊美春天
責難秋天
能得到什麽
一個離去
一個抵達
......
今天
我賣掉果園
果樹知道嗎
對某些人來說
山頂是一個用來征服的地方
對那座山來說
它是下雪的地方
由這幾段(當然裡頭還有更多),我看到了他一再抛下「人」的視角,去站在樹的立場、山的立場、甚至野草的立場,站在一切所有微不足道的立場。
他的詩集其實很多本,本詩集分三大輯,原來是他三本詩集的精選(出版沒有明說,由譯後記方知),分別是a wolf on watch、With the Wind、wind and leaf。我喜歡把輯一「狼在放哨」看成是狼的視角;輯二「隨風」是風的視角;輯三「風與葉」則較模糊,「我」出現的頻率較高,像是詩人的意識流、詩人的禪定。
這樣一小段一小段讀起來很輕鬆,也很「好懂」,但若試試把這一大疊歸為「風與葉」的小詩,一邊看一邊想像意象、畫面,則會構成一部「電影」?比如這個畫面:
我去那個農場。
沒有農事
沒有農民
只有一個無頭的稻草人
我開車兩百公里
然後,
坐在方向盤前
睡了二十分鐘
又開了二十公里
沒有悲傷
沒有快樂
我只是
走呀走
我喜歡開車的這段,共鳴於很多人生階段,開了兩百公里,休息一下又再開,因為只能前進,詩沒在這裡告結,接著,他好像到了一個海灘、接著是描繪一個暗夜、接著是風在荒山安定下來、接著水拿了他的護照、接著又回到開車……。我不確定書裡頭所有短詩適不適合獨立拿出來引用?是否適合抽出幾段成為精選集?但無論如何,本詩集提供了中文讀者一個閱讀阿巴斯的機會。
作者簡介
本名不重要。出生於大馬。高中畢業後赴台灣迄今。
美術系卻反感美術系。停滯十年後重拾創作。
著散文《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沒有大路》;
詩集《我們明天再說話》《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繪本《馬惹尼》、《詩人旅館》、《老人臉狗書店》等數冊。
作品入選台灣年度詩選、散文選。另也在博客來OKAPI寫繪本專欄文。
偶開成人創作課。獲國藝會視覺藝術、文學補助數次。目前苟生台北。
Fb/IG/website keyword:馬尼尼為 maniniwei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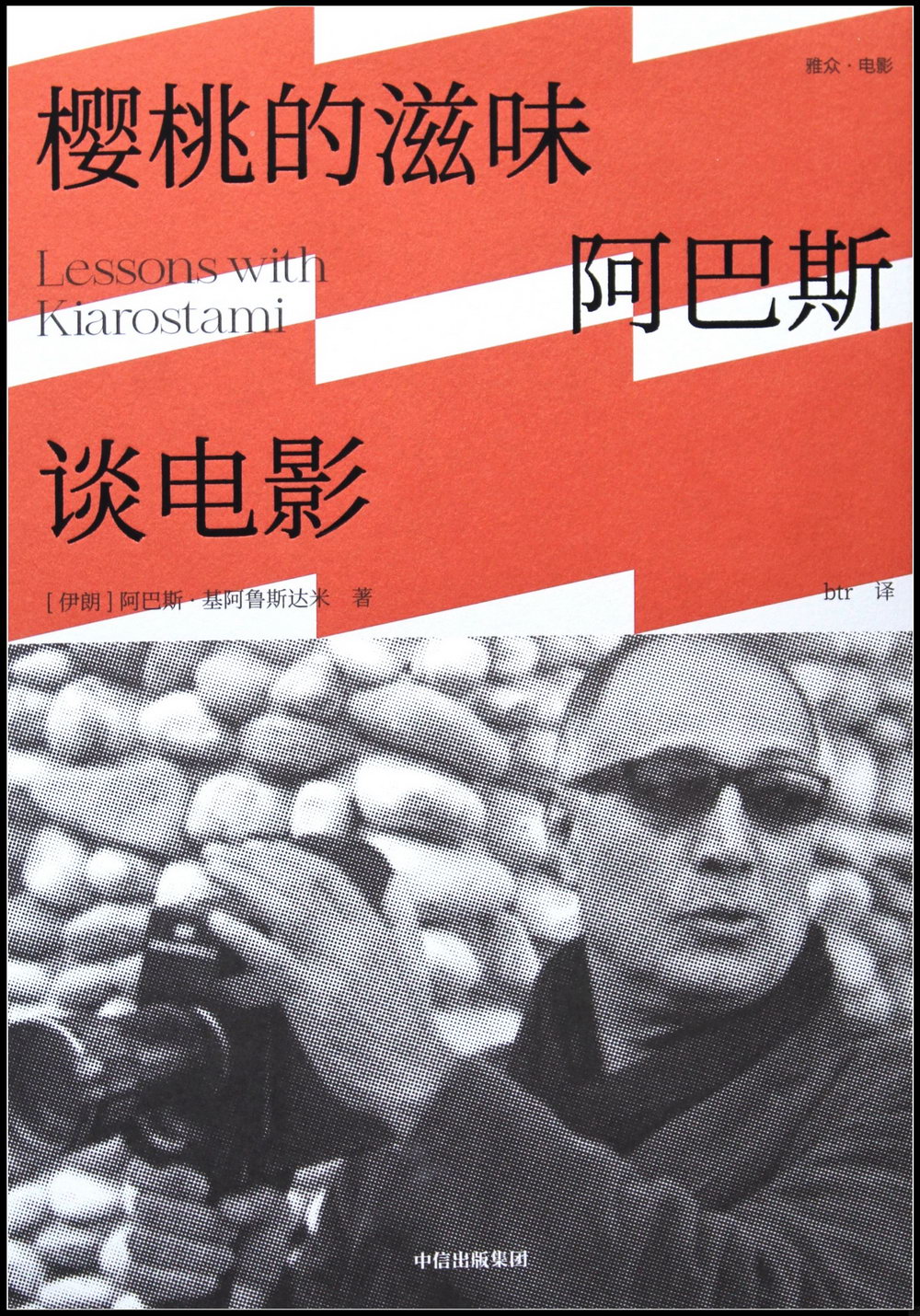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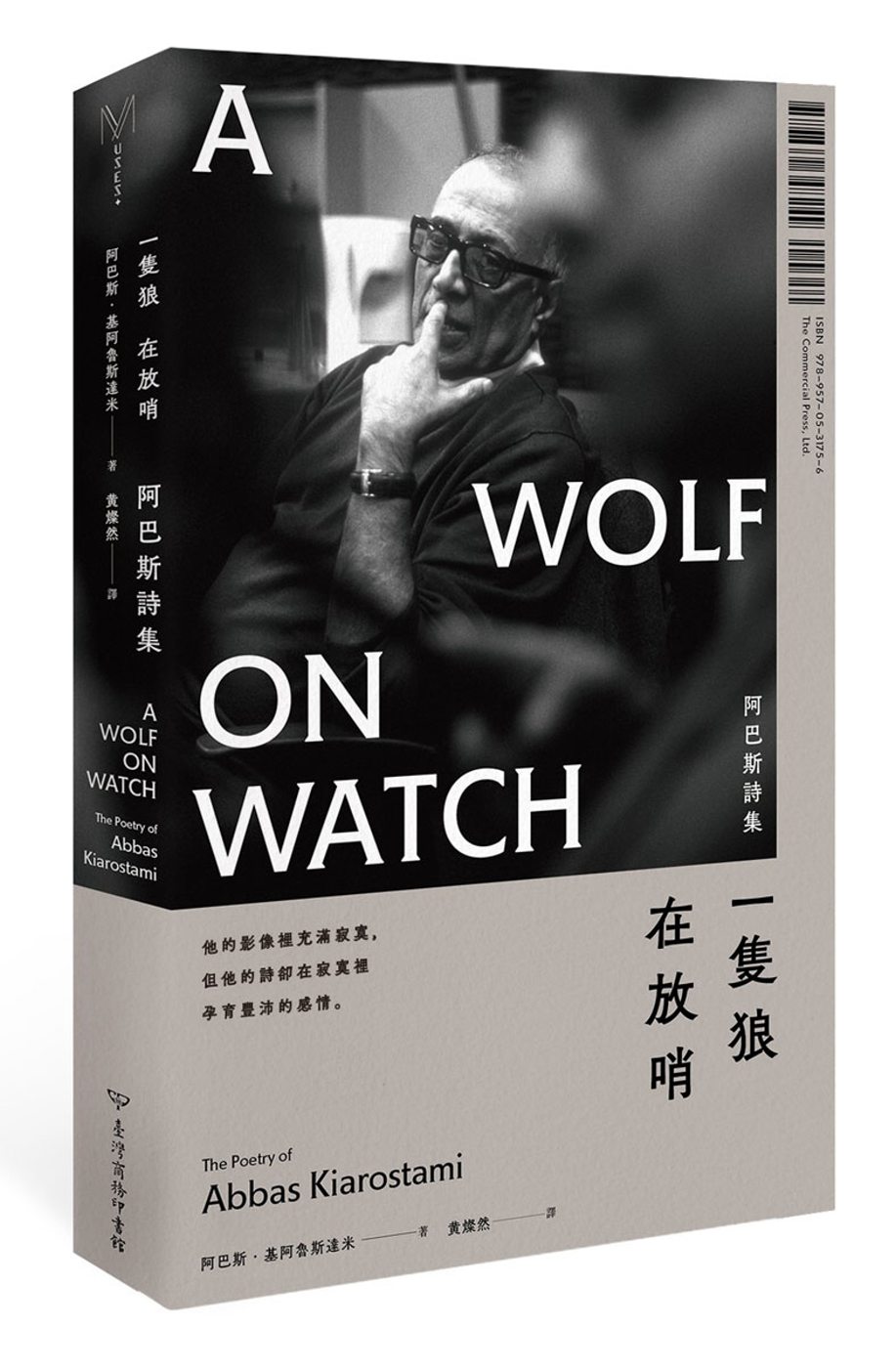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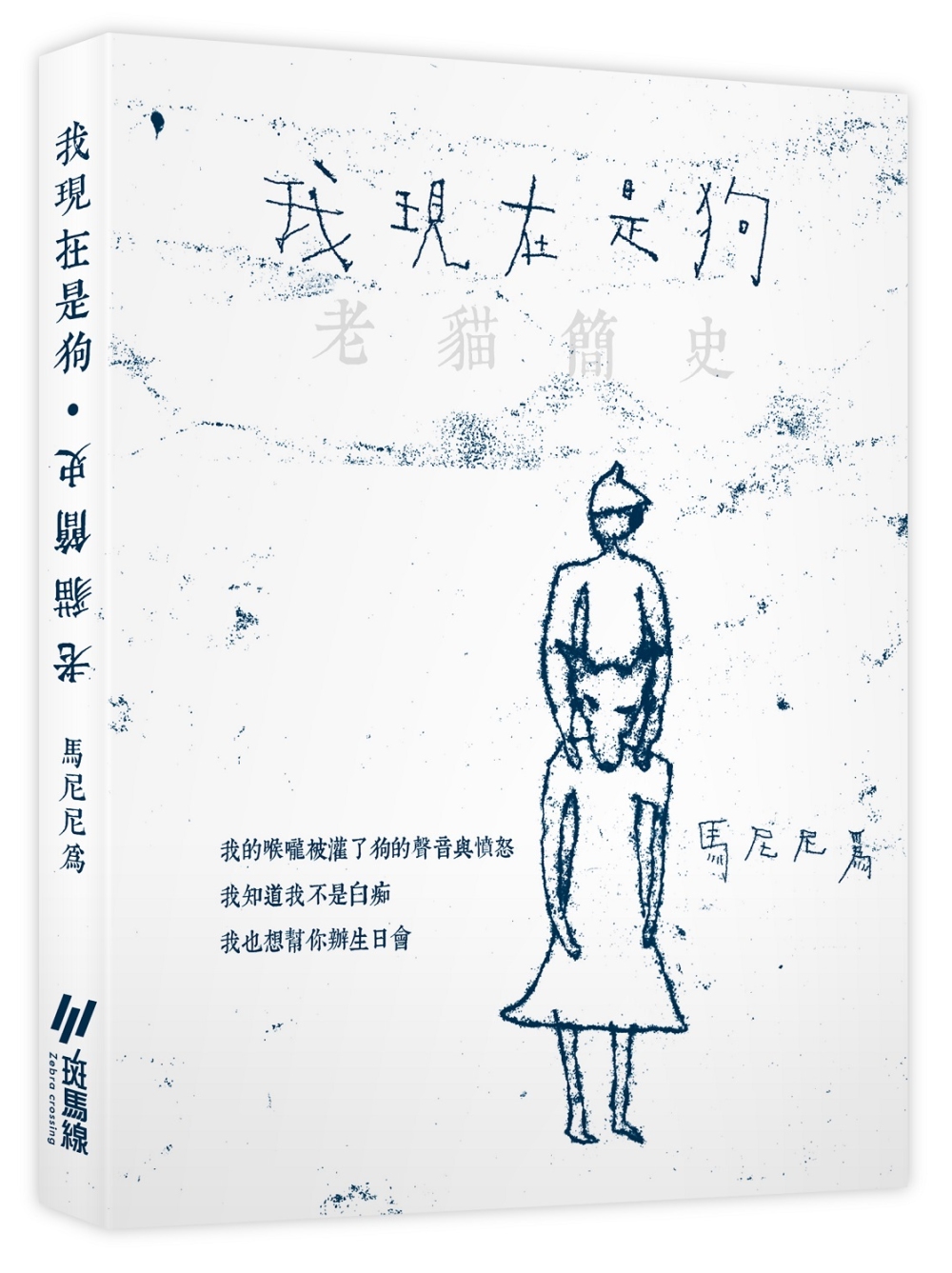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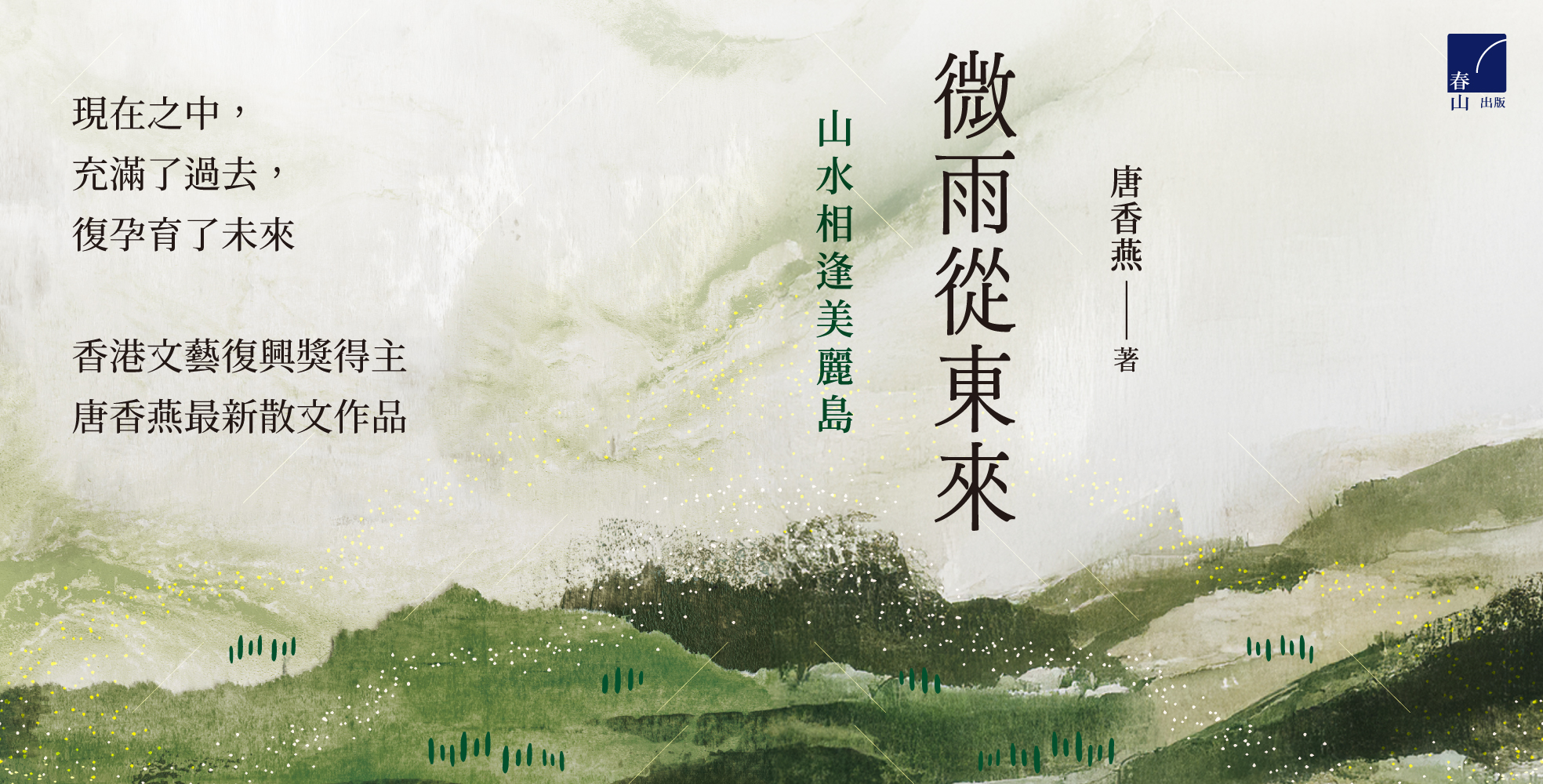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