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下去:韓國MERS風暴裡的人們》的繁體中文版被決定時,應該沒有人會想到它正好會誕生在一場新型瘟疫發生之時。出版那一天,COVID-19(武漢肺炎)新聞才正準備發燒,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尚未成立,第一起確認案例還在路上……,在警報響起前,這本以2015年韓國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危機為主題的小說就上市,呼應了2020開年最熱的時事話題。
MERS是世界衛生組織於2012年9月公布的呼吸道傳染病,病例主要集中於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等中東地區。2015年5月,一名曾到巴林工作的男子返回韓國後,在一週內發病住院,在醫生的敏銳之下,很快確認是MERS,並向WHO通報,但卻沒有準確且快速隔離病患,也錯失了被感染者檢驗的時間,加上「隱瞞病患就診的醫院」等一連串失誤,造成一場快速蔓延的災難。事件發生後一年,以「世越號」書寫在台灣打下知名度的金琸桓(김탁환),再次挑戰這場「人禍」。
「…報導MERS受害者的少之又少。就算有,內容也多半是按照確診順序編碼後、住進隔離病房發生的事。他們做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份子,卻沒有人報導這些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金琸桓在〈作者的話〉中如此寫道:「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麼,必須找回『人』,而非『數字』。」
例如小說裡的一個名叫冬華的出版物流商。她是個獨力扶養兒子,並照顧體弱多病妹妹的婦人,被感染那一天,她送妹妹去醫院、進了急診室──當時,一個後來被稱為「0號」的男人就在這幾百人的空間裡,這個人因與第1例同在一個醫院受到感染,卻因不同病房而被排除在接觸名單,於是「0號」出現症狀後,醫院毫無警覺地將他置放在急診室救治。
「沒有人出來解釋為何不斷出現MERS個案。漁網鬆了,大海廣闊無邊,越是拖延時間,大海越是無限擴大。」
冬華與小說中其他人物,就是在此時被傳染,接下來幾天,才被確認得到MERS,並成為案例上的一個數字。
經過隔離治療後,冬華出院了,試著返回工作崗位的她,這才知道住院期間,舉凡她的個人物品、接觸過的物件與她可能摸過的書,全數被銷毀;與她接觸過的人皆得居家隔離,公司停止運作一段時間。但該物流商的損失不只如此,員工居家隔離、出版社被排斥往來等等,皆對原就不易生存的他們造成重創。而承受副作用的冬華,失去了工作、再無法登山,連書都扛不起來,屢屢遭到歧視,甚至數次輕生。
冬華如此控訴:「這個國家難道一點錯都沒有嗎?如果沒有錯,那為什麼無辜的人會又死又傷?為什麼無辜的人會失去工作,被排擠?我看新聞只會爭論防制成功或失敗,只這樣為MERS事件下結論,太荒謬了!政府和醫院只要簡單的評斷成功或失敗就可以一筆帶過,那因為他們的失敗而遭受不幸的人呢?這根本不叫失敗,而是殺人啊。」
這段話,置於目前為COVID-19而緊繃的台灣,或無實感,但若放在現在的中國、日本,甚至是2004年無法有效處理SARS的台灣,都是扎扎實實的控訴。自《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開始,金琸桓就以當事人的經歷感受來質疑失靈的政府系統,而這個責任追究,到了《我要活下去》都無放鬆──青瓦台對災難事件的卸責、政府無法應對的窘況,不時從書頁中浮出──作者甚至將光化門的集會、追查世越號真相的律師都一併放入MERS風暴的故事場景裡,讓讀者清楚看見朴槿惠政權的無能,更能明確感覺到本可被救援、阻止、減少損失的災禍,是如何因政府的遲鈍反應而擴大,甚至失控。

南韓作家金琸桓(김탁환, 1968- )。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件發生,他深受影響,努力不輟的採訪相關人物,寫下世越號沉船事件著作,被文學評論家評為「世越號文學」的開端。(圖片來源 / 作者fb)
「…就是因為這些事故沒有釐清真相,世越號這樣的悲劇才會重新上演。我要強調的是,如果不找出世越號的真相,還會再發生類似事故。」《我要活下去》裡的律師於是這麼說:「到處都存在危險,無論是陸地,海洋還是天空,沒有安全的地方。事先掌握這些危險因子,然後清除它。發生突變事故要及時採取對策,徹底、透明的追查責任,然後反省。如果做不到這樣,事故只會重複上演,這只是時間問題。像現在這樣,如果國家不出來承擔責任,受害者只會陷在絕望中。這件事只是在光化門廣場上靜坐的人的事嗎?不,這不只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也是我們馬上會面臨的不幸,是會不斷上演的悲劇。」
讀到此處,我忍不住做了個筆記:這就是為何需要轉型正義。在真相被調查、釐清後,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過錯,而後反省,讓錯誤不再發生,就是轉型正義的真義。
從目前COVID-19的處理,可以感覺到在SARS的失敗與創傷後,台灣政府有記取教訓,而其表現也讓國民肯定。就在寫這篇讀書筆記之時,台灣確診案例為20人,出院2人,死亡1人。但為了保護病人隱私,這些病患化成數字,又為了簡明呈現疫情狀況,文宣只有標語和數字。社會對於這些受感染者的遭遇一無所知,不清楚他們經歷了什麼以及確切的感受。「人」在這個過程中,是看不到臉孔的,又因為每個人都隱身在螢幕後面,就也無法瞭解資訊傳播的問題與重量。
文學或閱讀,是要幫助我們有感受力與想像力,而不至於造成傷害或恐慌。
就如《我要活下去》的提醒:「我覺得用死亡人數來判斷危機警報太過單純了。死亡人數並不等於MERS給國民帶來的恐懼強度。應該更多方面去看MERS是如何給我們造成傷害,以及造成怎樣的傷害,再制訂危機警報等級。…要考慮網路和移動通訊等數位媒介。」
「不管只感染一個人還是很多人,數字不是重點,而是在這個國家、這個城市,存在確診MERS的病人。透過網路,全國都會陷入恐慌。為了遠離傳染病,會採取各種方法。與過去沒有網路的時代相比,就算死亡人數不超過四十人,但恐懼強度跟中世紀死了四百、四千甚至四萬人是一樣的。」
這是兩個電視台記者的對話,其中一位感染過MERS,另一位是醫藥記者,他們敏感地察覺媒介造成的影響,因此認為政府除了管控疫病,也有必要回應社會的問題,遏止流言與恐慌:
「政府沒有方法去推測和控制因數位媒介而大量產生的恐懼感,他們的解決層次只停留在嚴懲散布MERS謠言的水準。政府應該迅速解答民眾的疑慮和不安,而不是只會抵銷所有流言蜚語。…」
當然,2015年韓國政府的狀況,與現在的台灣不同──為了阻止謠言與恐慌,中央疫情中心一天開數次記者會,與其他行政部門一起使用社群網站澄清,以最開放透明的方式來防疫,且維持社會穩定;但即使如此,仍是無法控制人們內心的恐懼與魔鬼,污名與獵巫的氣氛遠較資訊沒這麼發達的SARS時期甚至瘟疫時代,更為劇烈;疫病沒有國界,網路亦然,於是,語言與情緒不僅光速傳遞與激盪,還受同溫集聚效應影響,恐怕超越疾病本身的傷害。
故事中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得到淋巴癌的牙醫,也是讓韓國MERS案例遲遲無法歸零的被感染者,因為各種官僚的原因,已無病毒傳播力的他,遲遲無法接受治療,最後死在隔離病房裡。院方敲定的死因是:淋巴癌。但他的屍體卻仍是以傳染病病人死亡處理方式處置的。
「一個人關在病房裡,一個人痛苦,一個人死去。就算死了,留下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數字。政府編碼的數字,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這跟關進監獄的囚犯編號有什麼差別?我沒有犯罪啊,我不是囚犯啊,他們為什麼像對待囚犯那樣對待病人。這是最讓我痛苦的。」
如同《謊言》透過潛水員來記錄船難,《我要活下去》亦是透過當事人來提出控訴。唯有把事件當中的人放大,災難或事件才不會成為資訊與數字的堆砌。我記得有一年到汶川地震博物館時,朋友指著大廳牆上的災難地圖說:「台灣,才死兩千人啊。」對於以萬人計算的中國災難而言,兩千確實只能算個零頭,但於我們來說,卻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與破碎的家庭,而且每個人物家庭的故事若能深入下去,讓臉孔放大背影立體,那些災難的發生與政治批判,才有價值和力道。
「把人當人看」,就是這個意思。
金琸桓以自己的筆,替186名病例填補了血肉,道出了委屈,讓我想到卡謬也做了同樣的事,他透過主角來描述瘟疫下的一切:「李爾醫生決心著手這份記事,以便他自己不成為那保持沉默的人,卻成為證人,為了那些被黑死病所襲擊的人作證,以便讓人紀念他們所忍受的不公與暴虐,以便直接了當說出在瘟疫的時期我們所獲得的教訓。」
於是疫病過後,就不會只有報告式的紀錄留世,因為我們還有文學。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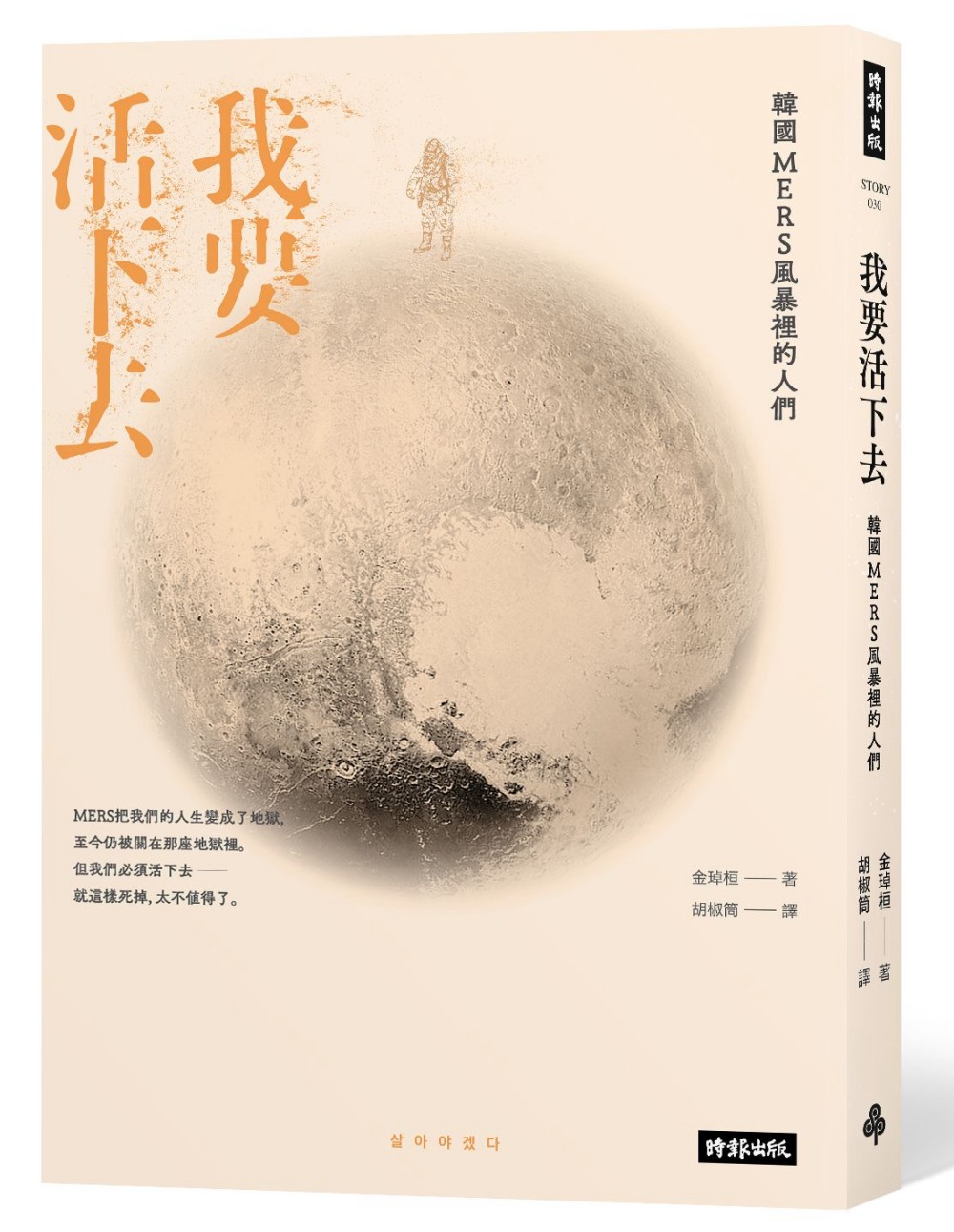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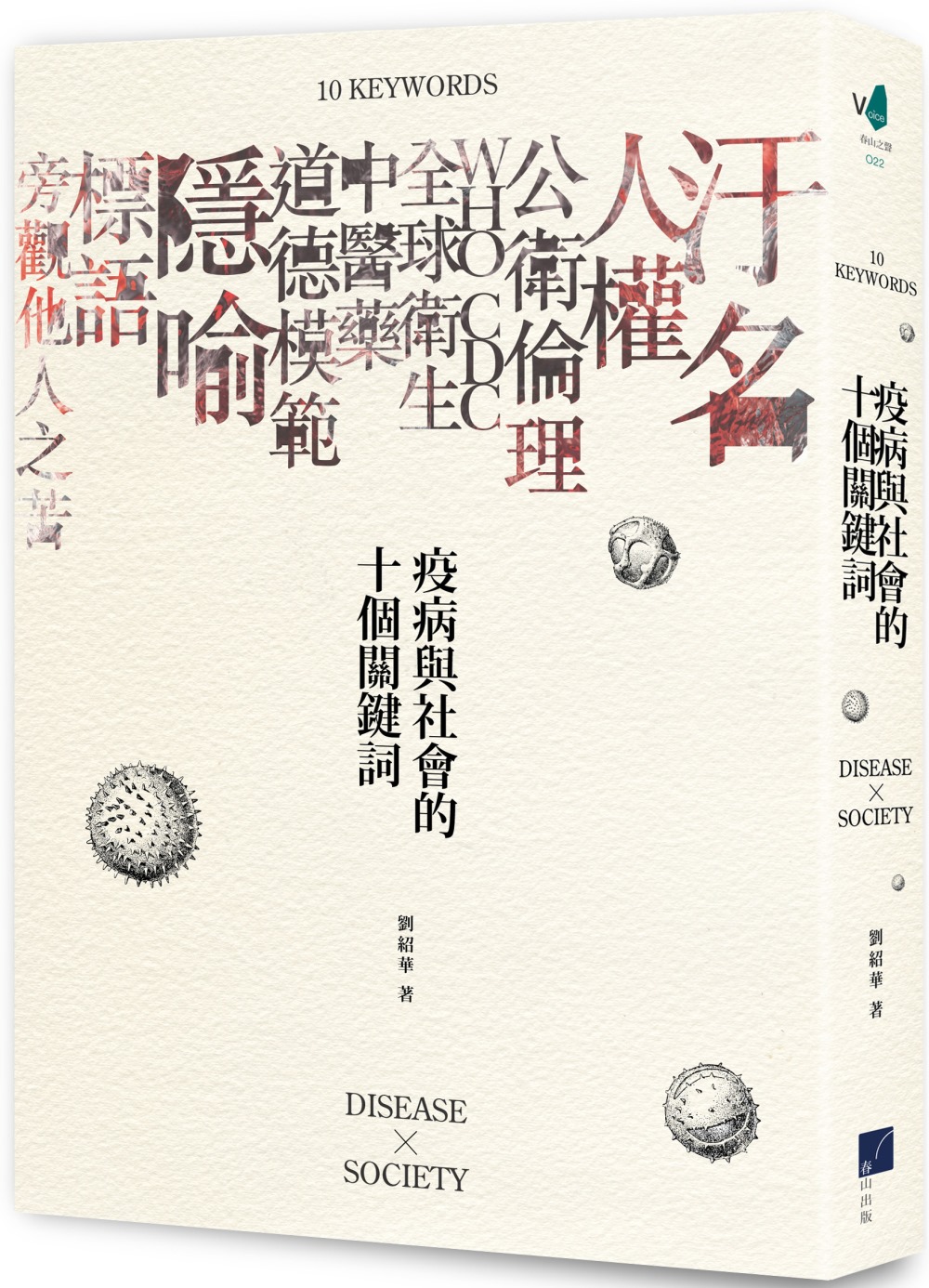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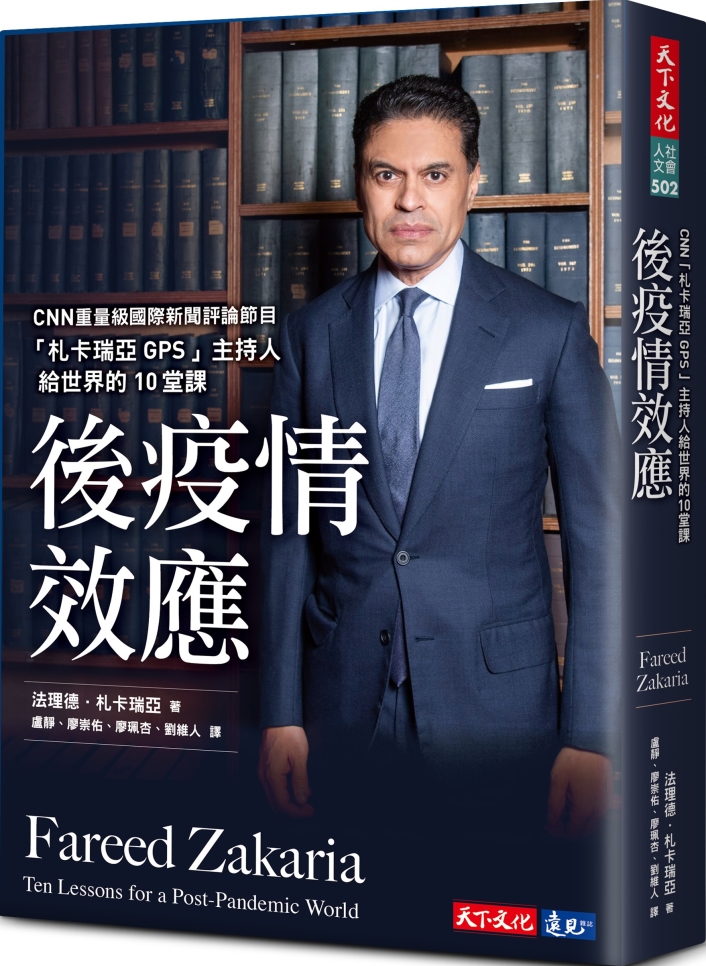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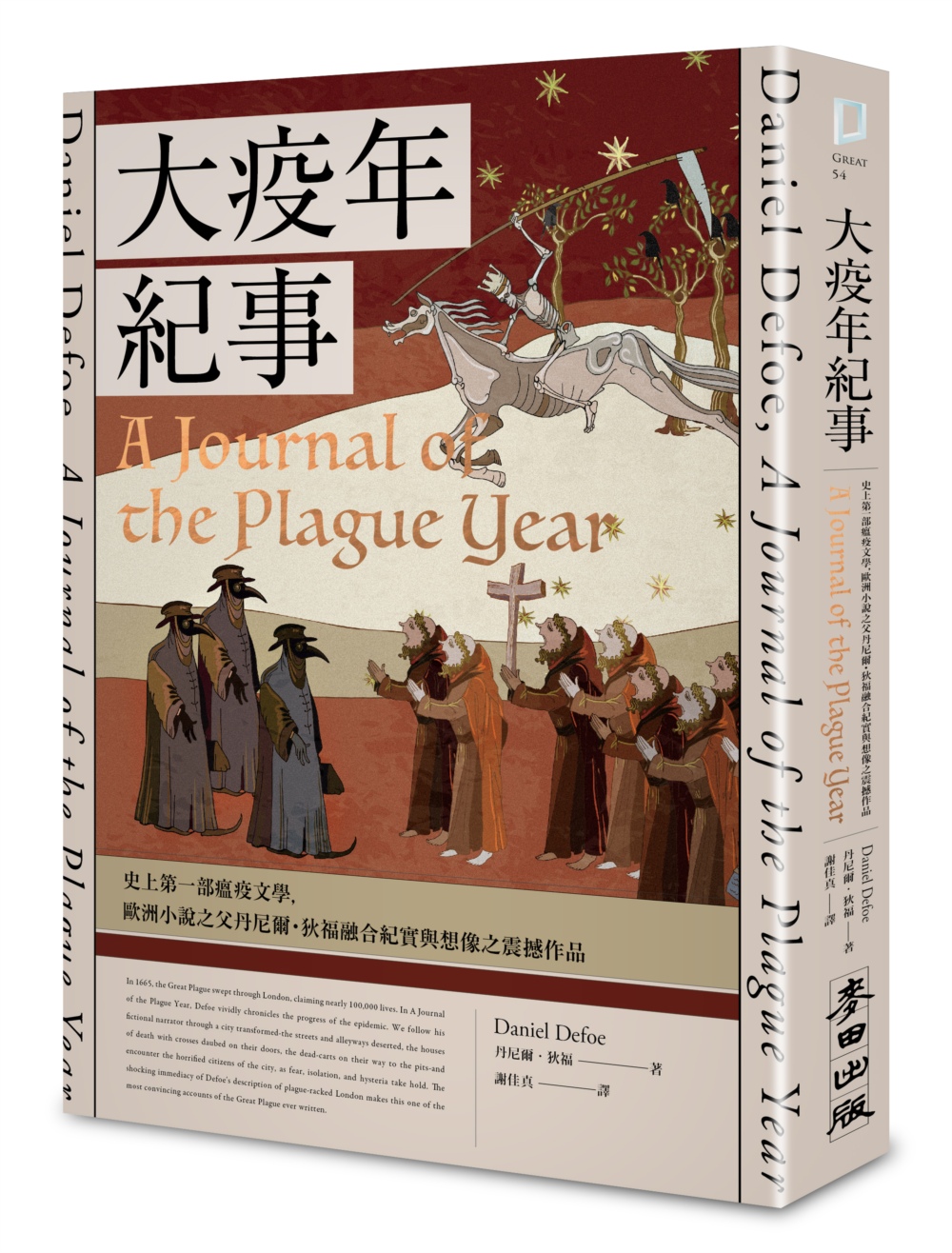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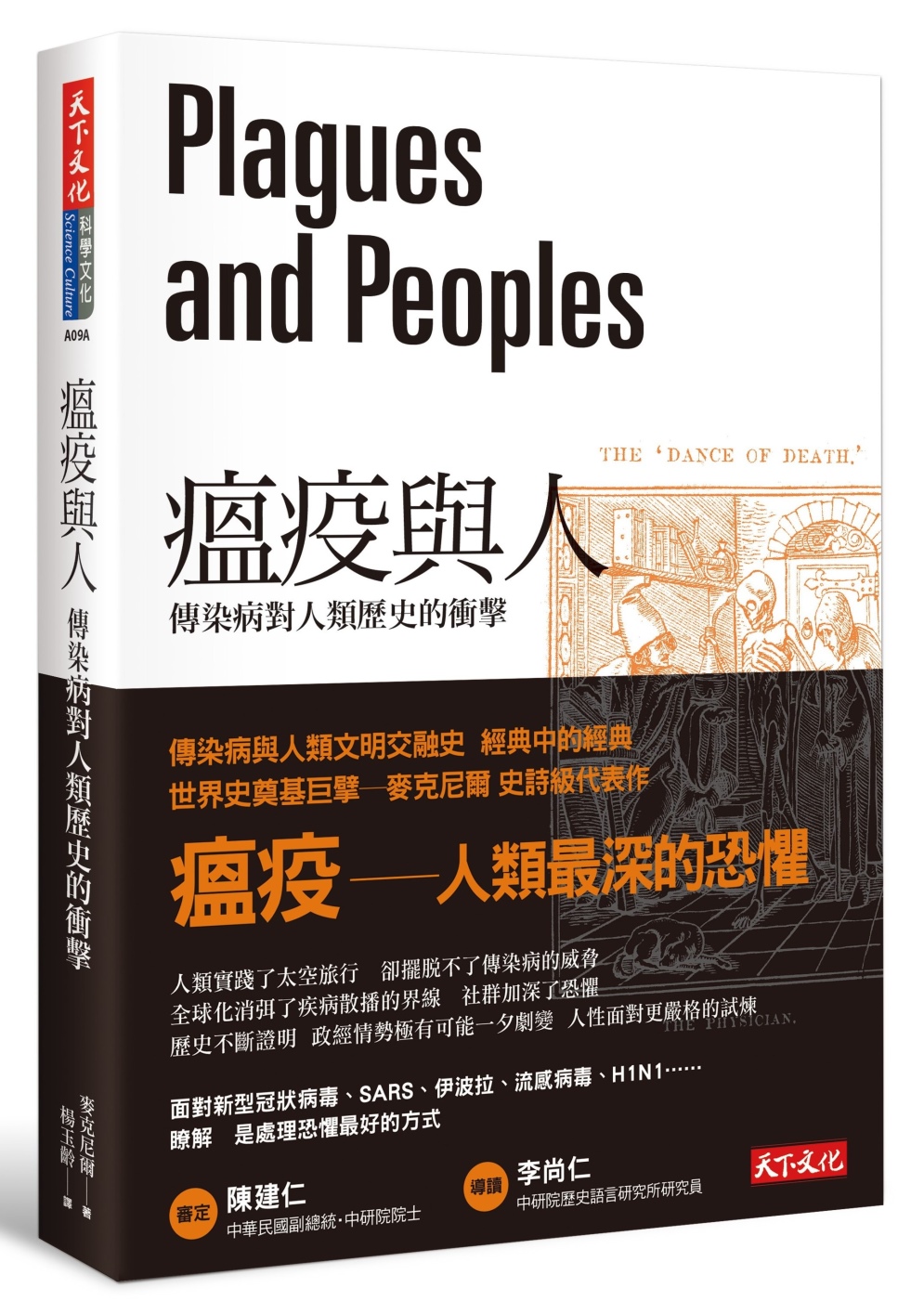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