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bienne在南喬治亞往南極的途中拍著一座冰山,我說:「不用拍那麼多,南極有更大更美的。」然後,我們經過了謝克頓船長(Ernest Shackleton,1874-1922)南極探險之旅被困住的象島,Matthew用長鏡頭連拍頰帶企鵝(Chinstrap penguin)可愛的面貌、捨不得放下相機,我說:「別擔心,到南極後,頰帶企鵝到處都是,用手機拍就可以。」
 象島(Elephant Island)是南極半島東北的一座島嶼。(圖片來源 / wiki)
象島(Elephant Island)是南極半島東北的一座島嶼。(圖片來源 / wiki)

成年的頰帶企鵝重約4.5公斤,以磷蝦、蝦和魚類為食。(圖片來源 / wiki)
又經歷兩天半的航行,早上醒來,透過窗戶瞧見南極大陸。旅人們興奮的站在五樓船艙的戶外甲板(簡稱deck 5)張望,等待登岸、和企鵝近距離的見面,但探險隊長卻要大家到會議室集合。他說:「現在風浪太大,我們無法登岸,今日所有的登陸計畫取消。雖然明天的天氣還不錯,但是如果我們明天仍留在南極半島,回程在德瑞克海峽會遇到超級風暴,非常危險。我們必須立刻返航,各位在deck 5拍照30分鐘後,船就要離開南極。」
會議室的氣氛降到冰點。114個人從世界各地來參加南極之旅,結果竟然無法抵達目的地。儘管過去一個多禮拜在南喬治亞、福克蘭群島的天氣和運氣都好到不行,看到極精彩的信天翁棲地和上萬對的國王企鵝,但此趟行程的高潮是南極。退休的以色列教授說:「沒有南極的南極之旅是天大的玩笑!」情緒還沒調整好,探險隊長試圖以啦啦隊長的振奮口吻說:「請大家到deck 5 喝香檳,慶祝我們抵達南極。」
就GPS的定位來說,我們是到了南極,可是就是沒有碰到,沒有摸到,沒有聞到企鵝屎的臭味,沒有在冰上跌倒,沒有機會反覆看著蒼白的大地說好無聊。總之,不算抵達。Febienne說:「天哪,之前我聽到有人沒去成南極都覺得不可思議,沒想到自己就遭遇到!」眼前的南極大陸被低矮的雲壓著,只見到朦朧的冰河,灰色的海水在岸邊翻滾,模糊的風景讓人按不下快門。
如果不是因為這是我第三次來,我應該會沮喪到喝不下香檳。
多數的旅人喝完香檳、拍完照後就回到舒適的房間或交誼廳,繼續聊著世界局勢或是未來的旅遊計畫,基本上此次的南極「探險」之旅結束了。雖然海圖上的定位是南緯65度,但我們在船艙做的事情等同於北緯23.5度,甚至餐台上還擺著老乾媽辣椒醬與龜甲萬醬油。
海風狂拍著我的臉頰、天空降下了雪花,看著眼前無緣登陸的南極大陸,有種荒謬感。近年南極之旅在華人旅遊圈很熱門,一直有標榜超豪華、超頂級的船加入這個旅遊市場。奢華之旅強調高貴的設施與經典的餐食,宣稱可以使南極之旅變得很有品味。但南極不是加勒比海也不是地中海,左右這趟旅程「品味」的並非私人飛機或是貴氣郵輪,而是讓人摸不透的天氣與天意。

Photo by Cassie Matias on Unsplash
眼前的浪越來越大,船的方向往北,但狂野的「風」景竟讓我捨不得離開deck 5,我坐了下來,任由身體跟著風浪擺盪,視野看著黑藍、灰藍與遠方的灰白大地。甲板另一角則是已經在南美洲旅行半年的瑞士女孩Febienne,她不斷的抽著菸,眼神失焦的望著南極大陸。穿著藍色外套的法國人Matthew則捧著長鏡頭靠著船舷,試圖捕捉信天翁隨著氣流展翅的畫面。而在deck 5 要進入船艙的入口處,站著德國女人Singrid,她不時用望遠鏡看著遠方。剛從學校退休的她,時常駕著帆船旅行,對她來說,南極之旅的魅力是海相。我們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看海浪快要吞噬了船、看信天翁優雅的滑行、看遠遠的鯨魚噴出水花。從船要駛離南極半島的那刻,我們這幾個獨自前來南極的旅人,很有默契地想要跟時速達70公里的風與平均標高4米的浪同進退,直到旅程結束。是會暈船的,但南極的風很冰很醒腦,世界就處在快暈又還沒暈的迷離狀態。
每天下午五點,我們會分享從福克蘭群島買來的酒,威士忌、Gin tonic、氣泡酒,跟著海浪一起傾斜,在海風裡發揮化學作用。Matthew說:「風把船傾向左邊,酒精讓我們傾向右邊,左右自然取得平衡,世界就會是平的。」喝酒衍伸出的哲理不多,多數的時候我們是以船上的八卦配酒。看似無所事事的旅程,人與人的關係卻暗潮洶湧。獨行的我們意外成為那些雙雙對對伴侶或是成群結隊團體的心靈導師,每天都有人來deck 5 跟我們抱怨或是講秘密:澳洲男吻了英國整形女還發現她的胸部是假的、船上的工作人員用西文問酒保有沒有多的保險套、偕妻子來的加拿大男人每天跟不同的女人調情。相較起來,誰的室友已經一個禮拜沒有洗澡、台灣團的晚餐餐桌上有加菜都是小新聞……。看不到盡頭的海上航行,喚醒了熟齡族的後青春期,在不斷搖擺的南冰洋上,有人吐到厭世也有人希望船不要停,關於愛的想像與動作可以持續。
當船穿越險惡的德瑞克海峽時,晃動劇烈,之前我總是嗑許多暈船藥躺在床上,但這回在deck 5 吹著海風,以眼神跟信天翁一起御風滑行,竟忘了海相激烈。Febienne說:「我花了快30萬,沒抵達南極、沒看到南極的冰山和企鵝,但成天在deck 5 吹風觀浪,在精神上似乎跟探險家謝克頓、史考特、阿蒙森有了連結。」Singrid則說:「百年前的探險家靠著簡陋的裝備就抵達南極,我們在那麼先進的船上,卻懼怕風浪,亟欲逃離南極真實的面貌。」長達一周完全不著陸的海上航行像場夢,尤其最後看到阿根廷烏蘇懷亞(Ushuaia)的萬家燈火,非常不真實,瞬間找不到和陸地溝通的語言。著陸後,deck 5 俱樂部帶著南冰洋染上的重感冒就地解散。
兩天後,Febienne傳簡訊給我:「我報了十二月初純南極半島的十天行程,總覺得沒有抵達南極很奇怪,想趁著長假再試一次。」Matthew寄了幾張照片給我,寫道:「我明年應該會參加南極半島的行程,還是想要完成南極的夢想。」我則是把隨身書《老巴塔哥尼亞快車》打包,託人帶回台灣。這本強調過程比抵達還重要的書,在此刻看起來是極大的諷刺,簡直是不祥之物。
下榻的青年旅店有旅人準備要登船去南極,他問我:「沒抵達南極會不會難過?」我說:「有一點失落,但也只能順天。」我沒有很難過,相較於前兩次,反而覺得這次的旅程非常南極(當然講這句話也很欠揍,因為我之前兩次都有踏上南極大陸)。南極本來就是不易造訪的地方,人的意志再強大都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知道世界上還有些地方並不是有錢就能如人所願的抵達,我竟鬆了一口氣。
作者簡介
個人部落格:享樂遊牧民族
Fb:享樂遊牧民族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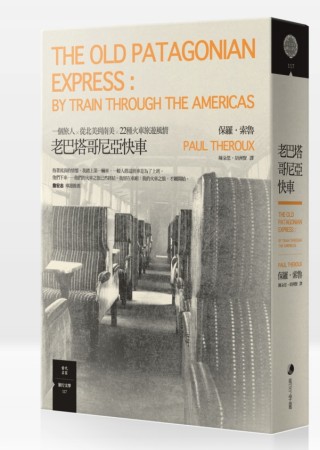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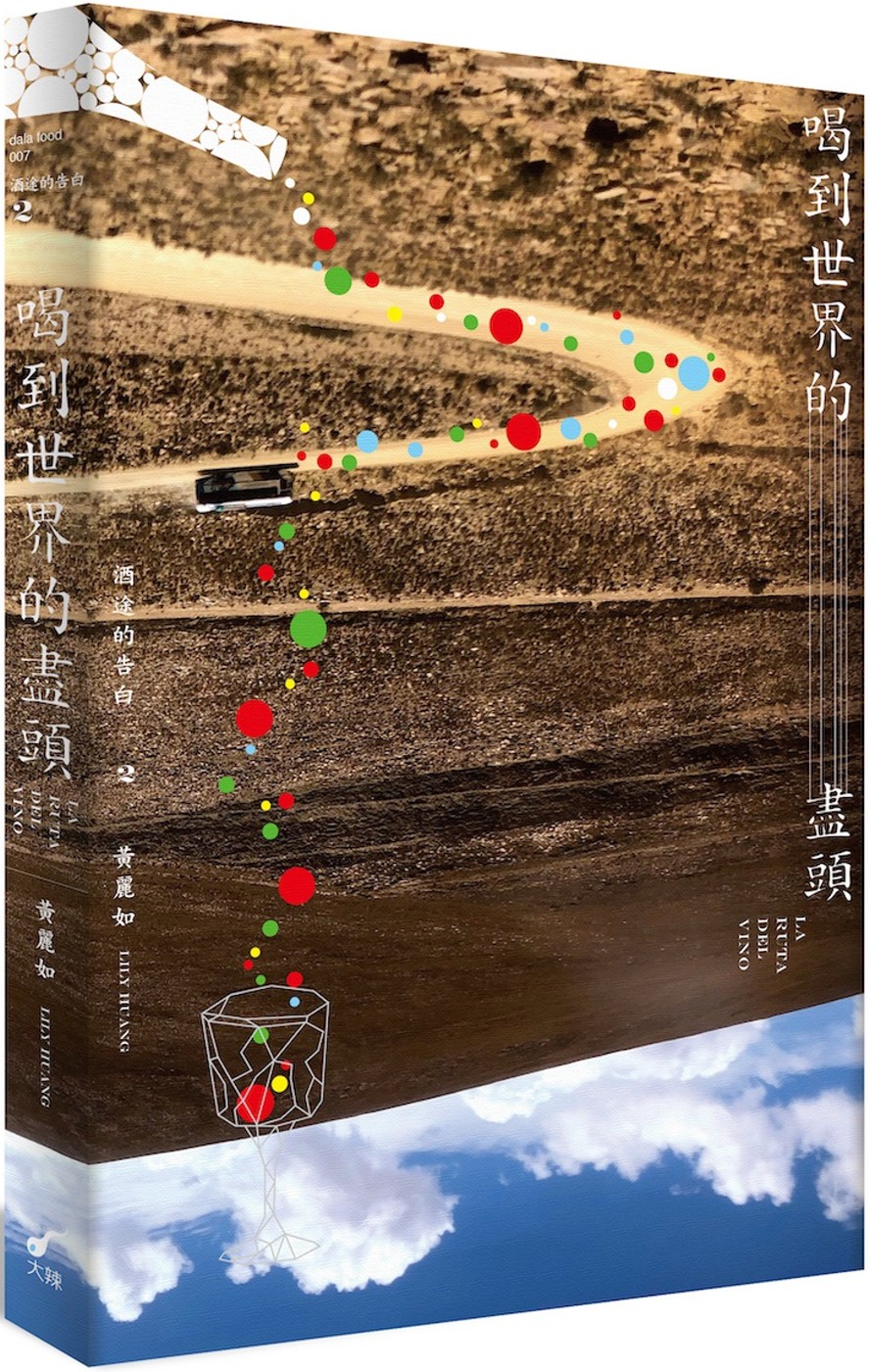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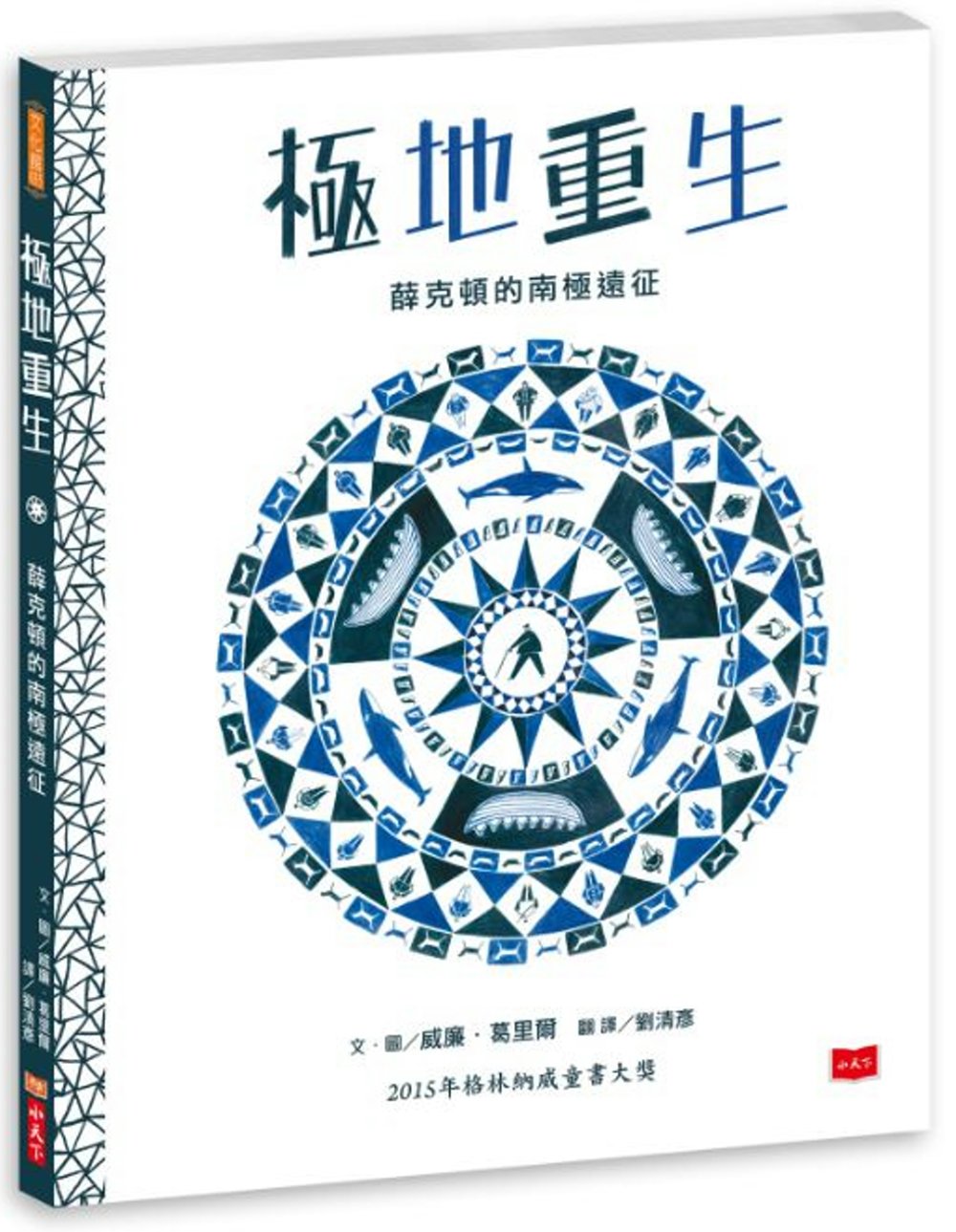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