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憶最新長篇小說《考工記》。(照片提供 / 王安憶)
我對上海最初的印象,是紛雜無邏輯的拼貼,若以現在慣用的標籤解釋,可能會是 「#張愛玲 #海上花開 #鬆糕 #凱司令 #浪奔浪流萬裡滔滔江水永不休」。大學畢業那年,我去了中國自助旅行,基於傳統中文系教育跟種種難以明確指陳的原因,在有限的時間裡,我只去了上海跟杭州,想親眼見見西湖跟張愛玲故居常德公寓。上海不再是文字裡的上海,而是增擴實境版本的上海,在那眾多版本中,有張愛玲的上海,金宇澄的上海,更有王安憶的上海。那是《長恨歌》《富萍》《海上繁華夢》到《考工記》的,從日常生活一步步滲透到巷弄裡的上海,城市在你眼前舒展開來,《考工記》裡的老宅也如此。
透過電子郵件,我對王安憶老師提出了一些疑問,希望讀到此篇的讀者們跟我一樣,在看到解答的時刻,也感到非常愉快。
提問=李屏瑤
回覆=王安憶
Q1:《考工記》是圍繞修葺房屋展開的故事,老宅處處都有來歷與源頭,為何選擇這個切入點?老宅的故事是何時觸動您,您又是如何決定「此事當寫」,書寫的源頭通常從何而起?
答:應該說,老宅子是寫作的起因,也是小說的基本材料。材料始終是我寫作的困頓,向內走的性格限制了從外部攫取經驗,同時呢,隨著敘事美學的認識加深,對材料也越來越挑剔,不容易滿意。一方面要求超越感性,另方面則必須和感性有所聯繫,方才能夠激起書寫的欲望。這種悖論聽起來不可調和,實際上呢,我以為正是小說寫作處境的常態,我們就是在悖論裡求出路,大約就是俗話說的「鑽牛角尖」吧!
這座老宅子確有其事,坐落在上海舊區的狹弄裡,人口密集的老城廂有著阡陌縱橫般的狹長街市,這一條的名字叫「天燈弄」,不知來自什麼出典。上海的地名,不止是空間的概念,還有時間上的,帶有城市發展史的意義,且是另一個話題。以我有限的觀察,似乎老城廂是現代城市上海的史前階段,它保留著原始草創的遺跡,它的街道不像租界地用洋文冠稱,之後也沒有演變成全國的地名;也不像江灣地區,至今沿襲國民政府新區規劃的雛型,以「國」和「政」字起頭。它的地名,多是出於用途,類似北京的胡同,區別在,京城是以供奉宮廷的分工司職為題,這裡呢,則體現了商貿關係,比如沿黃浦江自上而下,「鹹瓜街」、「豆市街」、「花衣街」、「蘆席街」、「會館街」等等。
這條「天燈弄」在城牆東門內,遙對江面,推想當年,商船由海口入長江,往岸邊徐徐而來,灘塗一片平展,那座老樓堪稱巍峨之勢,黑夜中的光明,仿佛海上生明月,不是「天燈」又是什麼?從上世紀80年代,我就進出這座老宅,與主人交往,但是,單憑這些遠不能化實有為虛構,還是要等待機緣。
Q2:您曾說過,書寫的形式跟表現,都是根據具體情形得來,書中的上海西廂四小開,朱朱、奚子、大虞和陳書玉,家裡分屬舊時代跟新潮流的職業,為什麼會做這些選擇?在考究職業上,又是怎麼下功夫的?
答:2016年,在紐約大學駐校,上一年寫完長篇《匿名》,按慣例,總是寫一些短章,調整節奏,於是就寫了《鄉關處處》和《紅豆生南國》,回來後又寫了《向西,向西,向南》,計畫再寫一個中篇,聚集一本,但中途因記敘紐約印象,又突發書評的興趣,出版社則認為以上三個中篇亦可成書,於是,這一個就擱置下來。直到下一年,也就是2017的下半年,即興的計畫都做完,安靜下來,偃息的欲望就又抬頭了,但是,材料的問題隨之而來,那就是,寫什麼?
這一年乍暖還寒的季節,無意中看網上消息稱,天燈弄的老宅開放公眾,憑門票而入,似乎已成景點。趁一個星期日去了,卻吃閉門羹。老弄還在,舊宅也在,外觀卻殘破得可以,毫無修葺的跡象。向鄰里打聽,個個諱莫如深,不願多說一個字,只得悻悻然離開。旁觀周圍,多是拆和建,城隍廟和豫園一派欣欣向榮,可所有的新氣象卻都繞過這裡,即便同一條天燈弄裡,這一點那一點亦有幾處變革,唯那座老宅子,自生自滅。不由好奇心生,找一位老李,《考工記》中的老李就有他的影子呢!老李他曾經任職舊區父母官,我在其任下掛職文化局,更重要的是,老李也是文學同道中人,因此結成忘年。老李動用舊屬,開通現任,約定又一個星期日,再次前往。房主已經去世,女兒留駐,出售門票的就是她。
老人曾經給過我一張宅子的平面圖,是他自己繪圖然後刻製,許多年過去,數度搬遷,無論怎樣翻找搜尋,終也無果。向他女兒索討,他女兒壓根不知道這回事,此時此地,地上物近乎全毀,頹圮成廢墟,無從推測結構,連方位都模糊了。當我決定寫一篇關於老宅命運的小說,卻沒有任何細節供參考。滬上掌故類文史中,所存的記載又極少,形勢變得猶疑,不知從何下手。茫然中,忽在一本舊書中讀到百來字小文,寫的是十六鋪碼頭,追根溯源,那初創者就是老宅子的房主。我不能確認這本雜憶類的書籍是信史,也許只是坊間風聞,無論如何,因它而起,人和事浮出水面,宅子退到幕後。這幅缺失的平面圖似乎在暗中指引,指引我向小說的本意接近,那就是寫人寫事。《天香》不也是這樣,繡藝是舟船,承載著人生世事,隨時間流淌。若多年寫作的經歷,不免會有一些天命的觀念,覺得冥冥中,有無形的力量,左右你的選擇,選擇對了,事事都在幫你,錯了,則一事無成。
Q3:您曾提到寫作是「無中生有」,找不到邊界與路徑,您是如何處理《考工記》的走向,如何確定這些人物漫遊的軌跡?書寫過程中有特別痛苦或艱難的時刻嗎?
答:小說是現世的藝術,「無中生有」的「無」是以總量計,具體到細部,還必須「有」。換一種說法,就是「有中生有」,但這「有」不是那「有」,此「有」非彼「有」。前者是「實有」,後者呢,大約可稱「無有」。就像方才所說,一旦決定,或者說發現,是寫那宅子裡的人,事情就變得有跡可循,那人自己就在向你要求,要求來歷、去向、交遊、遭際,這就是你要做的功課,編織譜系,空間的和時間的。
空間是前定,那所老宅子。時間呢?簡單說,故事從哪裡開端,這就和人有關,也和敘事的立意有關。那位老先生的音容那麼生動,活動在一個廢園裡,讓人傷感,又有一股子諧謔,然後是更深的傷懷,不期然間,滿足了我對材料的要求,超出感性,又觸動感性。我無意寫「眼看著起高樓」,亦無意寫「眼看著宴賓客」,我有意——其實是只能夠「眼看著樓塌了」,因這宅子就是在這時節與我邂逅。我讓那人,即「陳書玉」從大後方回到家中,家人們各自逃難,留下一座空樓,敘事由此起頭,時間和空間終於交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寫作中的困難還是在那座宅子,中間有幾次不甘心遺失那張平面圖,啟動搜索,可是,沒有了就是沒有了,仿佛有一隻無形的手將它收走了。等初稿完成,那時候正在香港中文大學駐校,春節放假,餐廳和校車關停大半,就去到廣州過年。廣州那地方,竟還保存著許多舊屋,祠堂和宅邸,提供了中式建築的格式與裝飾。廣州和上海都是商貿城市,望族以富戶為主,風氣豔麗繁榮。可此時,小說寫成,建成一座紙上宅子,自給自足,很難介入新的因素。走在這些修復的老宅子之間,反覺得它們是虛構,我自己的,才是真實。
Q4:上海始終是您寫作的對象,《長恨歌》是城市與女人,《天香》回到上海的史前時代,《考工記》則是老宅與男人,您的上海考古學下一步計畫跨往何處?
答:在某種程度上,上海是我唯一的材料。我不說我是寫上海,面對一座龐大的城市,沒什麼可商量的,怎麼可能去寫它,你只能被它寫。當我初始寫作的時候,個人的近期經驗積蓄得滿滿的,知識青年下鄉,鄉村的農家,社會批判,青春反思,壅塞了認識和表達,但等塵埃落定,生活和感情歸於平靜,進入職業化寫作,創造的欲望上升為動力,應該說,材料的問題就在這時候來臨,上海也隨之來臨。
應該感謝80年代興起的尋根文學運動,它將我們納入到潮流,洶湧澎湃,勿管有根沒有根,一股腦兒追尋而去。那時節,我寫作了《小鮑莊》,以此加入隊伍,沒有缺席進步,事實上,我也清楚了自身處境,我只是歷史中的個別,休想以自身映射全域。近代上海在中國歷史主流中可謂意外之筆,它不夠長,也不夠寬闊,它在中國的廣闊地貌的犄角旮旯裡兀自生長,這就是我的無可選擇之選擇。我其實一點不喜歡它,先前是因為它的冷清,如今則是過熱,前者是「五四」新文學中,它非啟蒙亦非被啟蒙的曖昧身分,恰是這曖昧,在小資產階級興起的時代裡,成為顯學。它沒有高古的往事,雅致的語言,優美的世情,空明的精神,這都是文學和藝術的大忌。可是我只有它,怎麼辦?唯有服從現實,不是說「從有到有」嗎?這就是書寫上海的出路吧!
剛剛寫完這一部,下一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所謂「計畫」都是事後的說法,之前,總是茫茫然大地真乾淨,就在空茫中等待,等待機緣來臨。
Q5:您在跋中寫,「世事往往簡單,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您認為小說的人生該容納哪些,才稱得上是好的小說?
答:應該以價值論吧!過去我們喜歡用「典型」的說法,這說法挺好,以量取質,確是稱得上小說的理想。但我還是有些不滿足,因是可應用於一切社會科學,小說的性格卻是在科學以外的。我的設想是,小說的意義在於它為「無名的存在」畫像。這世界在不斷地被命名,被語言物質化,小說卻是立足烏有。文學史將小說中的某些因素轉化為概念,比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納博科夫的「羅莉塔」已然進入詞彙表,賈寶玉的「意淫」,可是,我依然懷疑這些命名能否覆蓋,它只能指涉其中的一部分,全部的內涵遮蔽在命名四邊綽約的影調裡。好比天然鑽石和人工鑽石,人工鑽石模仿自然環境,製造的條件只是能夠分析出來的那部分,也許更本質性的部分卻被造物神祕地隱藏著的,天機不可洩露。
小說也是模仿,模仿的是那被隱藏著的,分析不出來的,無法歸類的模糊地帶。難就難在「無法命名的存在」卻要使用既定的命名,不這樣又能怎樣?共識是那樣強大,具有排斥力,就像一面篩子,形和形而上,一旦生出,便經過篩眼,留下的留下,留不下的濾去,被風吹散,轉瞬即逝。小說的工具是共識,表達的則是共識淘汰的。它即是世情,又不是,就仿佛海市蜃樓,經過光和水氣的折射,成為另一種人間。
Q6:您說喜歡看推理小說,您在閱讀推理小說時,最在意的會是什麼部分呢?
答:推理小說的理趣是我最最著迷的。我著迷它的形式,從現實裡來,抽象成邏輯,再回歸現實,就有了具象的面目。推理小說中我特別喜歡阿嘉莎.克莉絲蒂,就是因為她的具象性最生動。她的兇殺案總是發生在日常的場景中,讓人興奮,平淡的生活裡其實密藏著危險呢!無論是犯罪還是破案,她也都因循普通人事的因果關係。
她的小說好看,好看是小說的基本倫理。年輕的時候,出於狂妄,對讀者抱藐視態度,無視下情,其實不止是違反小說的原則,也違反了我們自己寫作小說的原則,我們不都是因為喜歡讀小說才決定寫小說的嗎?我常常想,小說從什麼時候變得不好看的?也許是學院派的文學批評改變了它的基因?如今,倒是類型小說保持著好看的遺傳,可是僅僅有類型小說又不能滿足精神的進取,這也是思想啟蒙運動給小說添加的負荷,讓寫作者陷入兩難。
Q7:寫作是寂寞的勞動,如果勞動真的太苦,您如何克服?
答:所以沉迷寫作,也許就因為喜歡獨處的天性所致,寂寞從某種方面來說,使人感到安全和自由。寫作者大多有一點自閉的傾向,害怕人群,害怕外部生活,疏於行動,就像貝類生物,棲身在殼子裡。
寫作的勞動是辛苦的,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苦」,它是一種苦「樂」,倘若不是領悟到其中的快樂,完全可以轉身離去,有很多人離去了,有的人一去不回,也有人離開了又回來,還有,就像我這樣,一直不離去,一直享受著「寂寞」的樂趣。
Q8:您有關注的臺灣作家嗎?有沒有喜歡的臺灣小說?
答:臺灣的作者和寫作,我始終注視著,他們比較我們,教育程度更高,中國古典傳統和西方現代主義,都更受教養,領得先聲。早在80年代,我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大陸臺灣小說語言比較》,臺灣方面,以宋澤萊小說《打牛湳村》為舉例;2000年以後,我寫朱天心《古都》閱讀心得《刻舟求劍人》;駱以軍《遠方》的《紀實與虛構》;我格外喜歡朱天文的《花憶前身》,它寫了一個文學世代,才情漫溢;今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授課,同學們熱議《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於是也找來看了;同學的閱讀報告中,有寫吳明益的小說《複眼人》,從報告中看,是一部隱喻性很強的小說,總之,我很留意在另一種文化語境裡的同行們的動態,它拓寬了華語寫作的幅度。
2018年9月10日 上海
〔補充提問〕
Q9:您在上海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原因是什麼?
答:上海變化很大,尤其近20年裡,並且還在繼續變化,幾乎很難找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滿目新奇,來不及和經驗建立關係。於是就去回憶中尋找,俗話說「懷舊」,懷舊成為藝術和時尚的一大主題,多少是在虛構,虛構時間和空間的交集,存放情感。
事實上,回憶是不可靠的,變形得厲害。我自小生活的地方,應該說是最喜歡,一旦去到實地,那喜歡立刻崩塌,一是消逝,二是頹圮,是落魄潦倒的同義詞。都市人差不多都是流浪者,搬遷頻繁,時間在空間的轉換中加速流淌。我真說不出這城市的某個地方是我喜歡,它越來越「炫」,越炫就與我越遠,個人的生活很遠地孤立地進行。客觀地看——就是這樣,你和它的關係越來越客觀,客觀看,它比大陸其他城市更具現代性,體現在它的秩序和紀律,可是秩序和紀律背離藝術的本意,約束著想像的活動,同時呢,它卻為想像提供安全。這就是虛構者的悖論,我們的精神很狂妄,現實生存中卻是低能者。
Q10:可否請您談談自己的日常一天。
答:我的日常生活很規律,因而就平淡了。每天上午寫作,下午休息,晚上繼續休息。真是毫無戲劇性可言,在外人的眼睛裡,要多乏味有多乏味,內中的樂趣也難和外人道。關於這個問題,實在沒什麼可說的。作家阿城說過,我們這種人,是將人生托出去,托給了小說,所以,就到小說裡窺視我們吧。
2018年9月14日補充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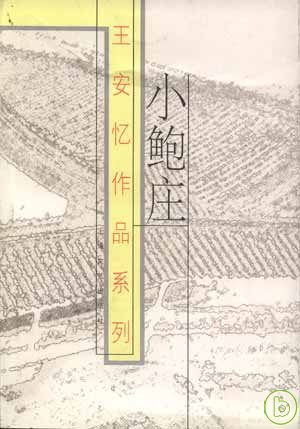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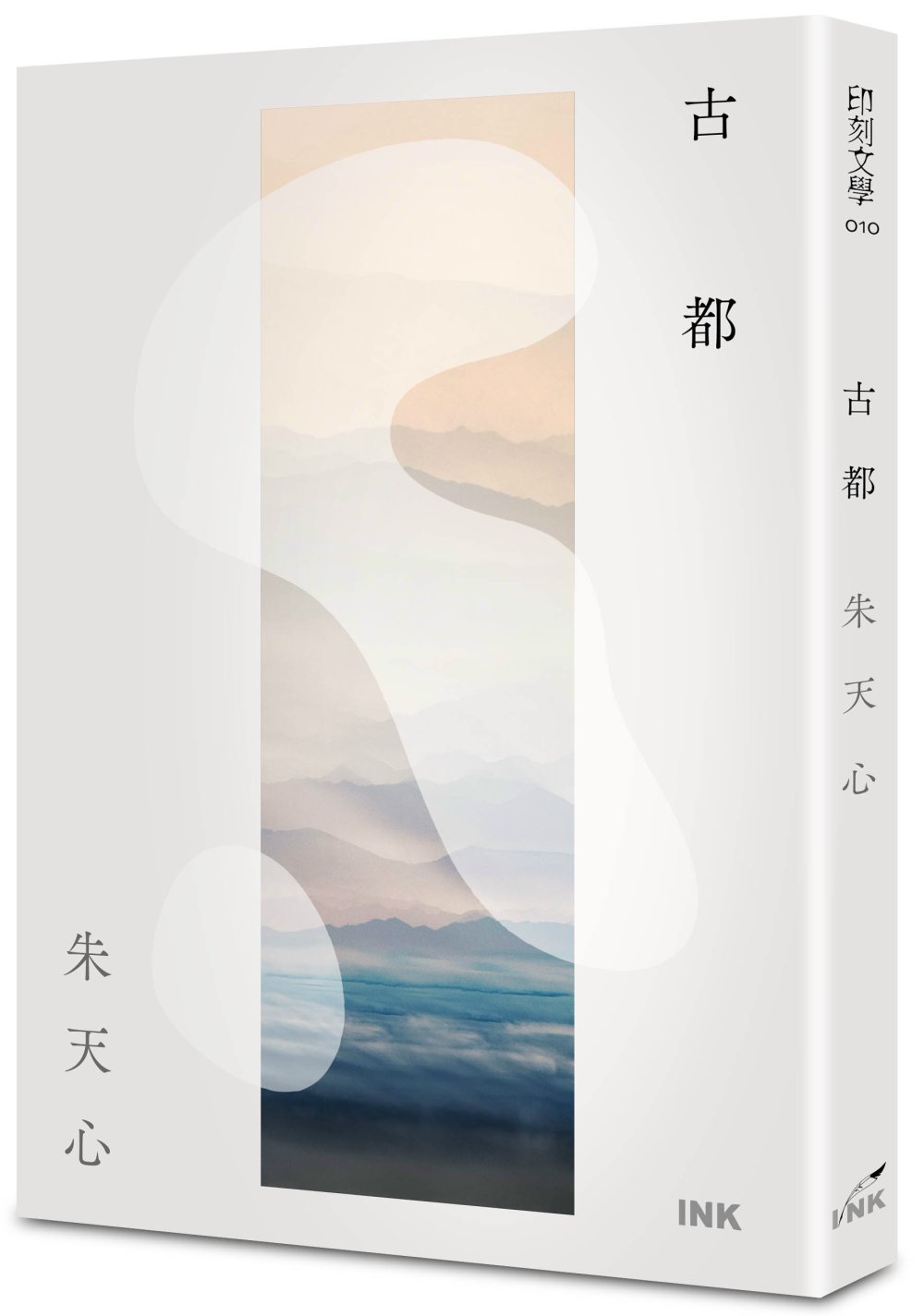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