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個社會的真相會展現在兒童身上。世間最美麗與最醜陋的,也往往是兒童經歷的人事物。兒童因此不該被當成下一代,而是完全的社會行動者,他們在形塑其日常經驗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專題評論《羅莉塔》、《最藍的眼睛》、《麥田捕手》、《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五本與童年有關且極度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這些少年角色做為行動者,深刻見證了種族、性侵、階級、性別認同的世間悲劇。評論者將帶我們到小說家描述的成長現場,文學使童年抵抗具備永恆的人性之姿。
殺死父親,穿過麥田而來
作家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出身曼哈頓公園大道富裕家庭,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愛爾蘭與蘇格蘭混血,身上擁有一半猶太血統。從小熱衷戲劇,愛好文學,期許自己能夠成為專業作家,作品曾先後發表於《週六晚郵報》、《君子》、《故事》、《佳人》、《紐約客》等,1941年著手撰寫《麥田捕手》,1951年正式出版。
二戰期間,沙林傑主動投入軍旅,擔任反情報官,從事蒐集情報、間諜行動、偵查納粹動向、滲透逆反顛覆等特殊任務。戰火持續延燒,沙林傑帶著《麥田捕手》前六章初稿經歷戰事,搶灘諾曼第,前進綠色地獄赫根森林(其隸屬的第四師死傷慘重,被殲滅殆盡)。二戰末期,進入剛剛解放的德國考夫囹四號集中營(Kaufering Lager IV,屬於達郝集中營的附屬營地),親自目睹納粹對猶太人執行的系統性種族屠殺後慘況。1945年7月,曾於德國紐倫堡(Nuremberg)求醫,短暫住院,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麥田捕手》的創作與出版時間,剛好是二戰和戰後初期,故理解此長篇小說,除了單純閱覽故事之外,若能參照當下的時空背景,或許更能瞭解作者的創作意旨。
整部小說,以時間性而言,由兩至三日的遊蕩展開敘述,並從中回想、穿插、記憶,此種型態,是文學傳統中常見的流浪漢小說(La Novela Picaresca)變形。抹除線性時間的工整紀律,大幅度擴充敘事,延展空間,使角色遭逢磨難,開啟感知門戶,得以內視,遂能明確感受精神的挫傷、痛苦與蛻變。另一方面,以空間而言,主線從離校之後返回紐約,分線則歧路散布於移動性交通工具,包含公車、火車、計程車,以及宿舍、夜總會、旅館、火車站、公園等半公共場域,逸離常軌成為激昂的敘事引擎,引領角色走向內在自我,同時走向外在社會。檢視故事,作者並非力圖創造新的書寫形式,亦非調動錯綜複雜的情節,或以各種寫作技藝大肆渲染;相反的,整體敘事趨於簡化,讓人不禁疑竇,如此化繁為簡,是否是作者刻意為之,抽空,篩濾,而讓閱讀者得以專注凝視,除了關注角色的內心情感世界之外,更進一步關注藉由單純敘事做為書寫策略的真正寓意。故事中,角色實踐的陌生化過程,是將自我抽離日常活動,置放於未曾接觸過的寬廣場域,擴張經歷,讓認知在短時間內產生劇烈變動,一方面賦予社會/世界全新的觀看視野,一方面卻在家園之中,成為真正的被放逐者。姑且借用薩爾曼.魯西迪的話語:「我們在自己的家園成為局外人,當麻煩出現,局外人總是比其他人都更早遭殃,而麻煩一定會出現。」
荷頓.柯菲爾德的位置,處於孤懸與介入、凝滯與流動、離去與歸返,種種彷彿探向兩處相悖的象限殊異中,迂迴彳亍,如同施展反復游離之術,讓荷頓成為自由跨入、跨出的彈性個體。做為一位暫時性的流離者,可參照薩依德所言:「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自我尚未僵化之前,必然充滿探索的混亂,而此流亡,並非單純指向內在,更指向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了獲得此種距離意識,相當程度,必須以某段時間的邊緣化做為代價。居於其中,卻不隸屬其中,被拉扯的個體四處行歷,來回互動,一次一次藉由他人的「否定」來觀照自身。在此,否定是重新發現自我的催化劑,疏離成為力量,有效懸置角色,同時逐漸加強內在的反抗意識。
整體而言,《麥田捕手》透過青少年的視角,闡述了兩則重要主題,其一,是父子位階的權力消長關係,其二,是個人意志如何抵抗社會的系統性馴化。本書以預科中學男生荷頓.柯菲爾德為主角,在面臨退學的威脅下,回返漫遊,接踵遇見諸多人物,如計程車司機、皮條客、妓女、男妓、修女等,而其意識內層,一直有條隱形支線不斷牽引荷頓,並且以此,暫時安撫內心的浮躁──那是荷頓的家人。荷頓圍繞的核心,是已死的弟弟艾利和妹妹菲碧。毋庸置疑,荷頓對離世的弟弟滿懷愧疚,這使得其對生者/妹妹菲碧油然生出呵護使命,換言之,透過對妹妹菲碧之愛,償還對死者的無限愧意。而其死者,並非單指艾利,還包含墜樓而亡的同學詹姆斯.凱索,以及無數向著懸崖奔跑而去的孩子。更或者,試著如此看待,其償還對象,其實是充滿悔恨卻無能為力的自我。自始至終的忠誠、純真與慚愧,無形之中,成為揮之不去的內在詛咒,為了繼續捍衛自身意識,勢必出走,晃蕩漫遊,以種種刺激重新確認自我。荷頓的短暫越界,如同遊魂,雖是十六、七歲青少年,卻歷經磨難,呈現早衰滄桑之貌。「我半邊腦袋──右半部──已經長滿了無數的白頭髮。」童顏鶴髮,隱喻其內在精神年齡。角色並未困於歷程,蔓延的時間空間,最終都得迫切面臨故事終結,以及必要的精神回歸。過程之中,失蹤、消失與死亡的意象從未斷絕,從自我的遁逃、中央公園消失的鴨群、親友離世,延展至暗喻般的木乃伊,最終,迎來帶有復活涵義的聖誕節。
《麥田捕手》的情感結構,具有雙股螺旋般的往復對稱性/抗衡性。一方面,荷頓向各個「難以稱職」的長者尋求協助,另一方面,又以其憐憫愛護之心,希冀自己能夠成為另一位長者,也就是理想中的麥田捕手。沙林傑企圖透過荷頓的遭遇、思辨與髒話式詛咒,再創另一位精神意識的父親。故事中,妹妹菲碧再三所言:「爸爸會殺死你,他一定會殺死你。」故事正如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的畫作〈農神食子〉,陰森殘暴,毫不留情,展現食子/殺子的準確預言。往內探究,「父對子」的殺子預言,其實隱含「子對父」的弒父宣言,這是對自我意識的完整確立,以及對他者的慎重割離;殺子與弒父成為詛咒,兩者糾纏,卻命運般相繼完成。小說中,荷頓始終感受被殺戮的威脅:「我是酒吧裡唯一在腸子裡有顆子彈的人。我捧住肚子,以免血流得滿地都是,我根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受傷了。」荷頓承受傷害,包含朋友的否定、學校的切割、師長道貌岸然卻充滿性愛意味的關懷等,他在接續而來的受創之中,以叛逆反抗,戮力謀殺精神上的父親,篡奪其位,予以取代,進一步履行父者本該承擔的職責。而此謀殺,正是書中透過妹妹菲碧所提及的:「仁慈的殺人者。」父者,除了指涉家庭關係中的實質父親,更是象徵整個社會所禁錮的規範、教條與虛偽互動,甚至,參照創作時空,父親的隱喻不禁讓人想起戰爭。如此,雙股螺旋的情感結構於焉成形,殺子的威脅,弒父的報復,兩者相互纏縛。我的存在,除了擁有個人的自我意識之外,還隸屬於社會一分子;而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則依靠個體、家庭與社群匯聚。兩者唇齒相依,互相指涉,卻在釐清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時矛盾對峙。
 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的畫作〈農神食子〉(圖/來自wiki)
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的畫作〈農神食子〉(圖/來自wiki)
基本上,青少年荷頓.柯菲爾德是位反叛者角色,而其叛逆,是透過種種撒謊、辱罵、怯懦、被學校開除、逃家、甚至是甘於墮落等事件特徵所完成。這使得反叛精神,成為本書必要探討的核心。對抗/反抗/抗辯必須針對某個系統,參與其中者,無論自願或非自願,均得在已被制定的結構、規範與價值觀限制中成長,漸次「被感化」。這如同作家福克納評論此書時的意見:「《麥田捕手》令我動容。我覺得它顯示一種──不是缺陷,而是一種邪惡,作者不得不全副武裝以自保,這種邪惡是我們文化中的一種壓力,強迫大家認同,強迫人人歸屬於某一團體。活在這種文化中,我們難以獨立自主。我認為,我在《麥田捕手》裡看見的是一場悲劇,而這悲劇可以說代表沙林傑個人的悲劇。」此種封閉系統,當然可以允許部分無效的叛變,而當反叛者無能以內在的原生動力去突破,充滿活力的質疑聲音,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安置」,並在後續過程之中,逐漸遭受他者扭曲誤解。
沙林傑並非直言描述,或以文字磚瓦搭建理想國度,而是透過悖反,經由窮盡身心般的近距離詰責,形塑無法抵達的可能。閱讀者必須透過抗辯之詞,逆向理解意圖,以此推測作者所欲重新建構的理想社會。然而,此種肉搏式的質問,或多或少,都將導致難以避免的自我瓦解。作者並非一味將投身者塑造成英雄,而是以揭露之完成,說明個體面對群體的同化壓迫時,自我成長的不可完成。甚至可以前展推論,角色必定落難,遭遇困頓,並在種種脅迫之下逐漸邁向毀滅。
慶幸卻又危險的是,此種符合角色的青少年語境,帶有嘲諷,充滿叱罵,展現強烈抗拒的不屑姿態,正是個體面對遠遠大於一己的系統或權力時,最易於激發的直接反應;於是,此種咒罵語境,或多或少屏除獨語困境,彷彿透過鏡面反射,將角色的個體予以溶解,進而擴充,塑造其不可取代的形象。如此,角色以其倔強抵抗的個性特徵,大幅打開可被借位的想像領域。閱讀者被邀請參與敘事,兩者相親,角色巧妙替換,開啟一段由閱讀者進入自我、進入角色、進入故事的多重想像,如同挪用個體的困頓經驗,將制約的互動關係,裹入小說火花般的積極批判,並且以此,移形換位成另一不斷同時發生的自我體驗過程。
叛逃者的角色設定,絕對是敘事推動的重要媒介,通向故事一端,閱讀者能夠輕易置入,而另一端,則是必須被推翻的偽善世界。角色以其批判、困惑、犧牲、詰問與鄙視,獲得認同,換取他人穿越個別載體的可能。孤立的時空,由讀者和荷頓.柯菲爾德所共享,兩者進行祕而不宣的交談,內在認同因而獲得支援,並從個別故事,搭建出青少年批判社會的精神架構。荷頓一一指認自身與自身對這社會的衝突,充滿痛苦,近乎絕望,彷彿不斷邁向懸崖邊緣,然而即使憤世嫉俗,內心依舊努力維持善意。沙林傑對這個世界還保有愛的可能,並且奮不顧身維護那不輕易放棄的愛,只是,那近乎宗教情懷的護衛精神,如同使命,勢必承擔整個社會難以面對的歷來傷痛,以及不曾削減的接續考驗,而這項無法完成的自我許諾,彷彿必須獻出餘生,將心力投注於迷途孩子,並以此做為最後的修復代價。此種獻出,並非是生命的剎那終結,相反的,沙林傑透過塑造理想的麥田捕手,將其巨大的修復任務,輾轉交付於共感共鳴的讀者身上。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麥田捕手》視為一本青少年啟蒙小說,但此小說之所以經典,不僅僅只是個體啟蒙之完成,此書更隱藏深沉寓意,以及積極的批判意識。小說不僅孕育於二戰,也同時孕育於美國戰後初期快速變遷的社會,《麥田捕手》在世局極度混亂的背景之中逐漸長成,成為沙林傑的慰藉,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心靈寄托。作家安迪.羅傑斯(Andy Rogers)甚至大膽指出,《麥田捕手》其實是一部戰爭小說。返國後,沙林傑始終無法脫離戰火所帶來的種種傷害,然而更讓他受挫的是,「戰爭的殘暴、愚昧、冷酷、驚駭被磨製為黏膩無腦的演講、歌曲、電影。問題不是民眾不懂戰爭的真相,而是民眾根本不在乎真相,既然如此,就算揭穿戰爭真面目也毫無作用。」(安迪.羅傑斯語)除了戰爭經驗之外,美國社會對於反芻二戰意義的草率、膚淺與視而不見,在在影響了沙林傑。於是,作者彷彿不得不以透析式的分離書寫,篩濾血淋淋戰爭場面,而讓《麥田捕手》輾轉透過拒絕直描戰爭的另一種「缺席式」直描,將內心時刻感受的惶恐、憤怒與創傷傳遞出來。依此脈絡,可以大膽論斷,《麥田捕手》不僅僅只是一本青少年啟蒙小說,更是一本不描述戰爭,卻深受戰爭影響的戰爭小說。
透過書寫《麥田捕手》,沙林傑不僅試圖撫平二戰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同時也透過這本書,隱喻戰後美國社會的集體氛圍,人的生理與心理雙重失能,整個社會似乎都陷入了「戰鬥疲乏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此書能夠歷久彌新,引起共鳴,正是因為閱讀者明確感覺角色的真誠、純真與善良,並且準確展現人如何以其初心,倔強地抵抗社會制度,而那樣堅定不移的批判姿態,正是沙林傑從自我創傷、對戰爭與戰後諸多現象的漫長思索中,逐漸形塑的重要主旨。角色荷頓不僅僅只是沙林傑的傳聲筒,更是美國二戰後人們孤寂卻又頑強的心靈縮影,甚至,穿越時空背景,我們依舊可以從中讀出其普世、永恆性般的批判精神。如此,便能更加理解沙林傑刻意的隱遁、抵抗與骨傲,那彷彿是經由自我餘生的奉獻,企圖療癒個人與社會內心深處的悲痛。個體的消逝並非代表意識的終結,生命的斲斷也並非空留殘餘,努力抓住即將墜落的孩子,不僅僅只是沙林傑一人,而是正在翻開《麥田捕手》這本書的閱讀者,一位又一位荷頓.柯菲爾德。
「我置身此世,但不屬於此世。」(I am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it.)作家沙林傑的自我消隱,其實正是自我療治,撫慰傷痛,餽贈空間,將世界留給一群又一群正在麥田之中自由奔跑的孩子們。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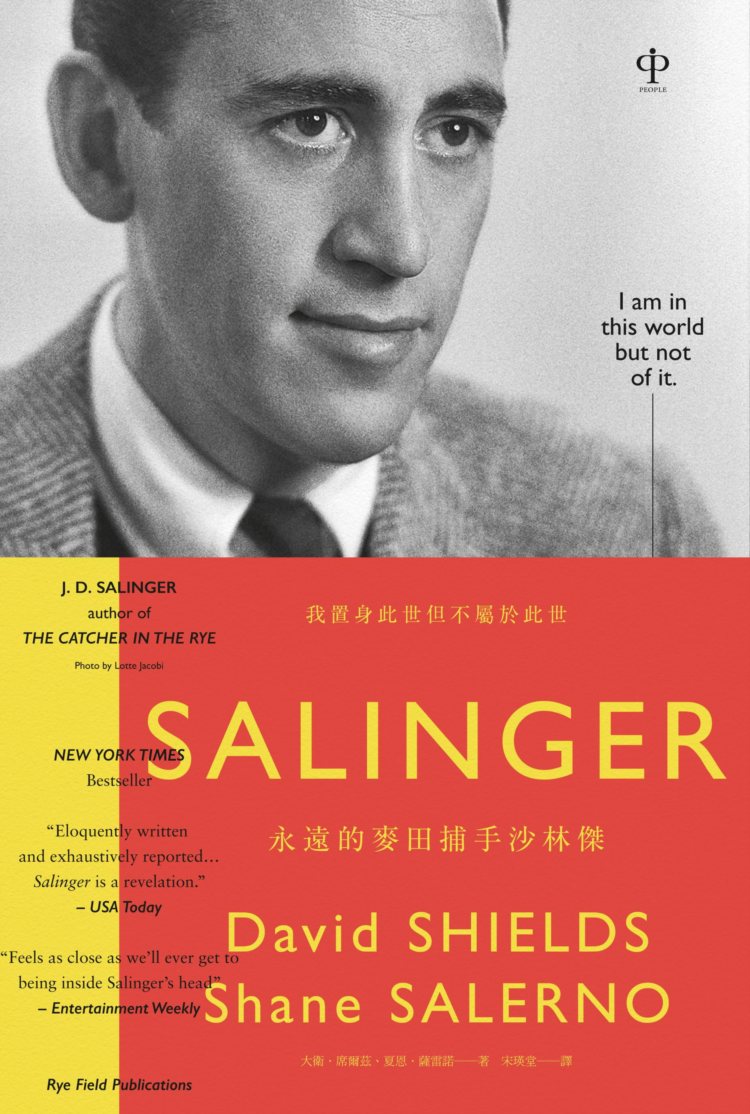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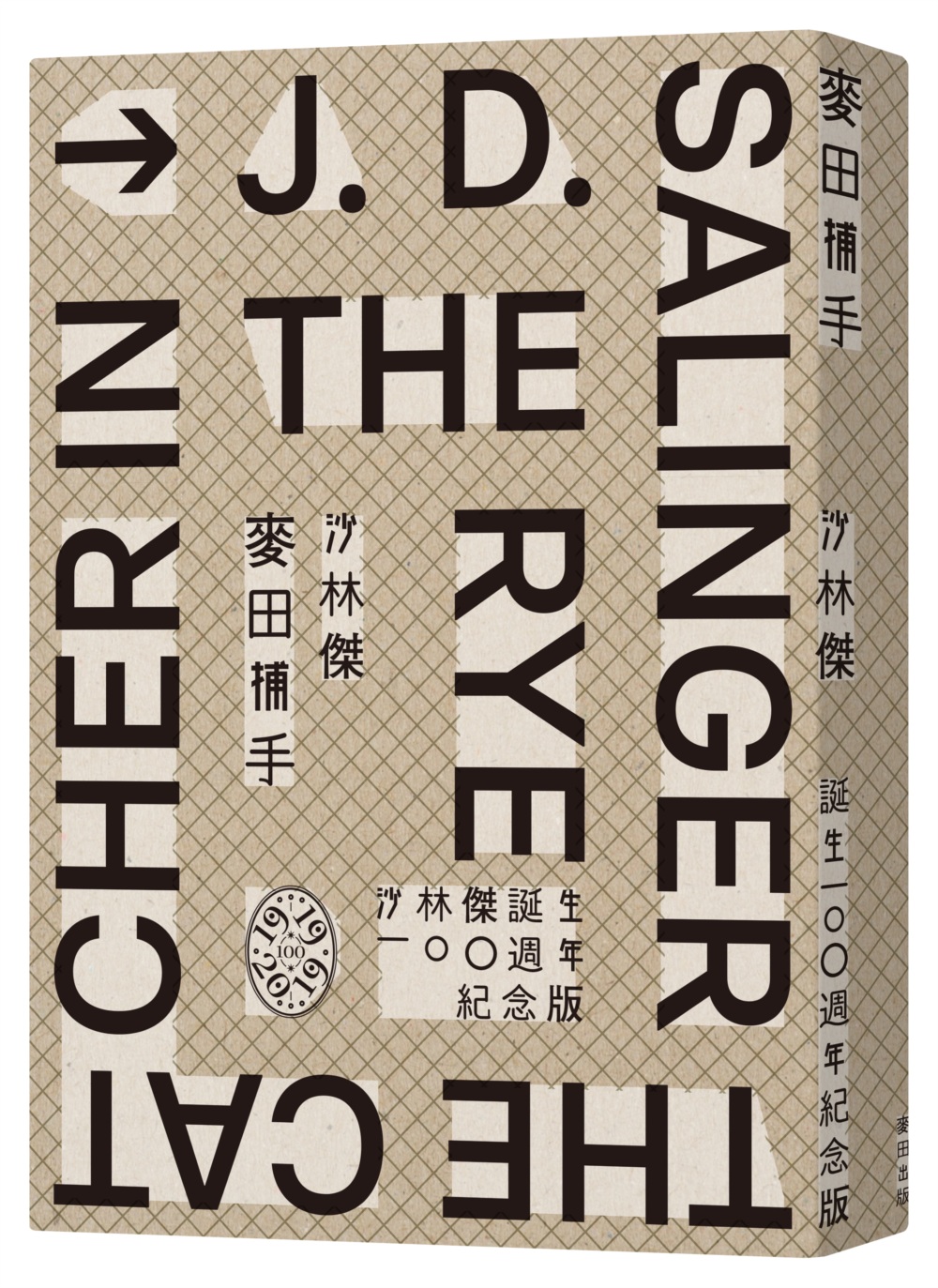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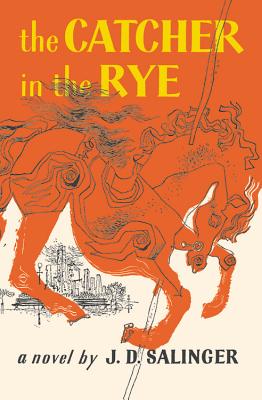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