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過地獄之路》非常需要譯者的蕪雜大胃口。
《行過地獄之路》非常需要譯者的蕪雜大胃口。
2014年曼布克獎作品《行過地獄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我翻譯過「最煩」的書,當然不是它難看,而是它指涉的領域太多。
我常覺得喜愛雜學的人最適合當翻譯。譬如書裡提到絞刑,詳細描述如何決定繩子長度──「他們說劊子手會根據他的身高體重決定絞繩的長度,這樣,他的跌勢才會正確,產生一舉勒斷脖子的最大力道。劊子手會弄一個跟崔相敏重量相同的沙包,綁在他的絞繩上懸掛一晚,讓繩子彈性疲乏,這樣明天崔相敏的身體跌落活動門後,繩子才不會反彈。繩子不彈,他的脖子立即斷裂。」
同一章節裡還提到某個韓國二戰獄卒在踏上fateful thirteen steps時大喊:「大韓帝國萬歲。」什麼是「決定性十三階」?我馬上聯想起我看過一部改編自亂步獎作品的電影《十三階段》,死刑犯翻案的故事,我當時很狐疑什麼十三階段啊?戒酒也不過十二階段。一查,原來 thirteen steps 不是階段,而是以前監獄的絞刑台常是十三階。
此類平日你根本用不著的知識,套句墨西哥導演 Robert Rodriguez 的電影《異星戰場》(Planet Terror)裡女主角 Rose McGowan 所說的,叫做無用才藝(useless talent)。《行過地獄之路》需要譯者本身就愛苦練「無用才藝」,譬如,你懂美式足球、歐洲足球,算什麼,你還得去研究澳洲足球(因為書裡男主角是澳洲人),搞清楚什麼是「定球」(mark),我很確定我的下半生大概都用不到「定球」這種高級字眼。
我記得翻譯的那一年半裡,我研究過「日本皇室用語」(因為小說一半背景在二戰日軍戰俘營)、日軍與澳軍軍階對照表、「森林大火專業術語」(因為書裡提到塔斯馬尼亞大火)、「澳洲人常吃的魚」(因為一名澳洲戰俘總夢想著回故鄉吃炸魚)、解剖學術語(因為裡面有長達十幾頁的開刀場面,用的還是自製開刀器具與麻醉藥)……。
如果你不是一個極愛蕪雜知識的譯者,怎麼撐得過這些?
有時光靠你勤奮查查查是不夠的。因為網路上給你的東西有時差一點點就差很多。翻譯這本書我碰到很多羅馬拼音日文字,要找出它們的日文漢字,網路上充滿一知半解的陷阱。譬如二次大戰時,日軍會發安毒給士兵提振精神,這玩意叫shabu(你知道的,涮涮鍋)。網路上說,因為炮製冰毒的過程像使用涮涮鍋,那你總不能翻譯成涮涮鍋吧?
這時就得找我懂日文的朋友楊麗芳,她告訴我,水溶性的安毒放在針筒裡搖晃會發出shabu shabu的聲音,所以成為安毒的黑話,日文寫做"シャブ",「沙霧」。
同樣因為楊麗芳,我才知道 binta 的日文漢字不要翻譯為網路上的「鬢撻」,要翻譯為「平打」。她說,鬢撻只是音譯。非正確。正確日文是平手打ち, ビンタ, binta = 平打。什麼是平打?就是甩耳光啦。
你問我,幹嘛「沙霧」不直接翻譯為安毒,「binta」直接翻譯為甩耳光就好?因為原書以英文書寫,中間夾日文拼音,而不是用 Amphetamine(安非他命)。所以翻譯時也該全書為中文,中間夾「日語漢字」。作者「動」,譯者就要跟著「動」。雖然較真了一點,但是比較符合原著的精神。
翻譯如果只是解謎,那叫長知識,不叫煩。本書作者一下子引用古詩、日本俳句,一下子引用澳洲叢林歌謠、新詩。這才叫煩。
 跟隨我三十幾年的朱生豪版《莎士比亞全集》是我比較信得過的譯本。即使有網路電子版可查,還是捨不得丟掉。
跟隨我三十幾年的朱生豪版《莎士比亞全集》是我比較信得過的譯本。即使有網路電子版可查,還是捨不得丟掉。
本書男主角愛引丁尼生的長詩《尤里西斯》,我至少花三小時去綜合與校正網路的五個版本,弄出我覺得比較正確的翻譯本。他又愛引莎士比亞。這時就得請出我的壓箱寶──朱生豪譯本《莎士比亞全集》(私認定比梁實秋版好)。
這套譯本出版於1980年,譯者是大陸人,那時還沒有版權法啦,反正印了出版就是。我1981年買的。多年來我翻譯碰到莎士比亞都是引用這個版本,就像翻譯聖經,我會引用和合本,而不是聖經公會本,因為前者典雅漂亮得多。
作者掉書袋,譯者花時間去比較譯本或者修正譯本,你認為辛苦?一點也不算苦。苦的是書裡屢屢引用英文翻譯的小林一茶、松尾芭蕉的俳句,我如果再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層層轉譯,確切的意思可能會跑掉。如果原作有夾雜漢字,那翻譯當然是要以原本就使用的漢字為準。準此,參考中譯會比較謹慎。
 鄭清茂老師翻譯的《奧之細道》看了令人垂淚,密密麻麻的註解背後是譯者一輩子的學問。
鄭清茂老師翻譯的《奧之細道》看了令人垂淚,密密麻麻的註解背後是譯者一輩子的學問。
為此,我還特地請人從台灣幫我帶來鄭清茂老師翻譯的松尾芭蕉《奧之細道》,細細翻閱。又在網路上不知查了多久。唉,找不到。只好硬頭皮自己翻譯。譬如點出本書精神的小林一茶俳句──
活在世間
如行走地獄屋脊
凝視花朵
美則美矣,也忠於英譯,但我不免懷疑如有日文直接翻譯的中文,會是什麼面貌呢?
譯者有時必須認命某些東西就是無法轉譯。譬如原文押頭韻,你的翻譯押不出頭韻,改押尾韻,給你50分,那字數對仗呢?又要押韻又要對仗,創作容易翻譯難。
譬如作者寫出了這麼一句話:incomprehensible, incommunicable, unintelligible, undivinable and indescribable。要把這句話翻得跟原文對稱,五個字都押尾韻 a(i)ble 與頭韻 in(un),再加上 undivinable 比較古意,來自 divine(神判)的動詞使用,字典還根本沒有,你得兼顧通俗與古雅,這叫做阿湯哥的不可能的任務。
最後的翻譯是「杜里戈的視線回到鐵路測樁,圍繞它們的是太多的無可理喻、無法溝通、無可理解、無法臆測與無可名狀。」只得對仗與頭韻,講究不到尾韻了。
他寫得像詩,我翻得像屎。有時譯者必須含淚接受一聲與三聲的差別!
何穎怡
政大新聞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婦女學研究,現專任翻譯。譯作有《時間裡的癡人》、《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嘻哈美國》、《在路上》、《裸體午餐》與《行過地獄之路》等。
延伸閱讀
1. 黃麗如:你的地獄,我的景點──讀《行過地獄之路》
2. 胡培菱:成王敗寇或許只是世事流轉──2014年曼布克獎得主《行過地獄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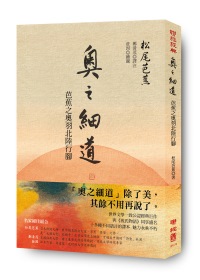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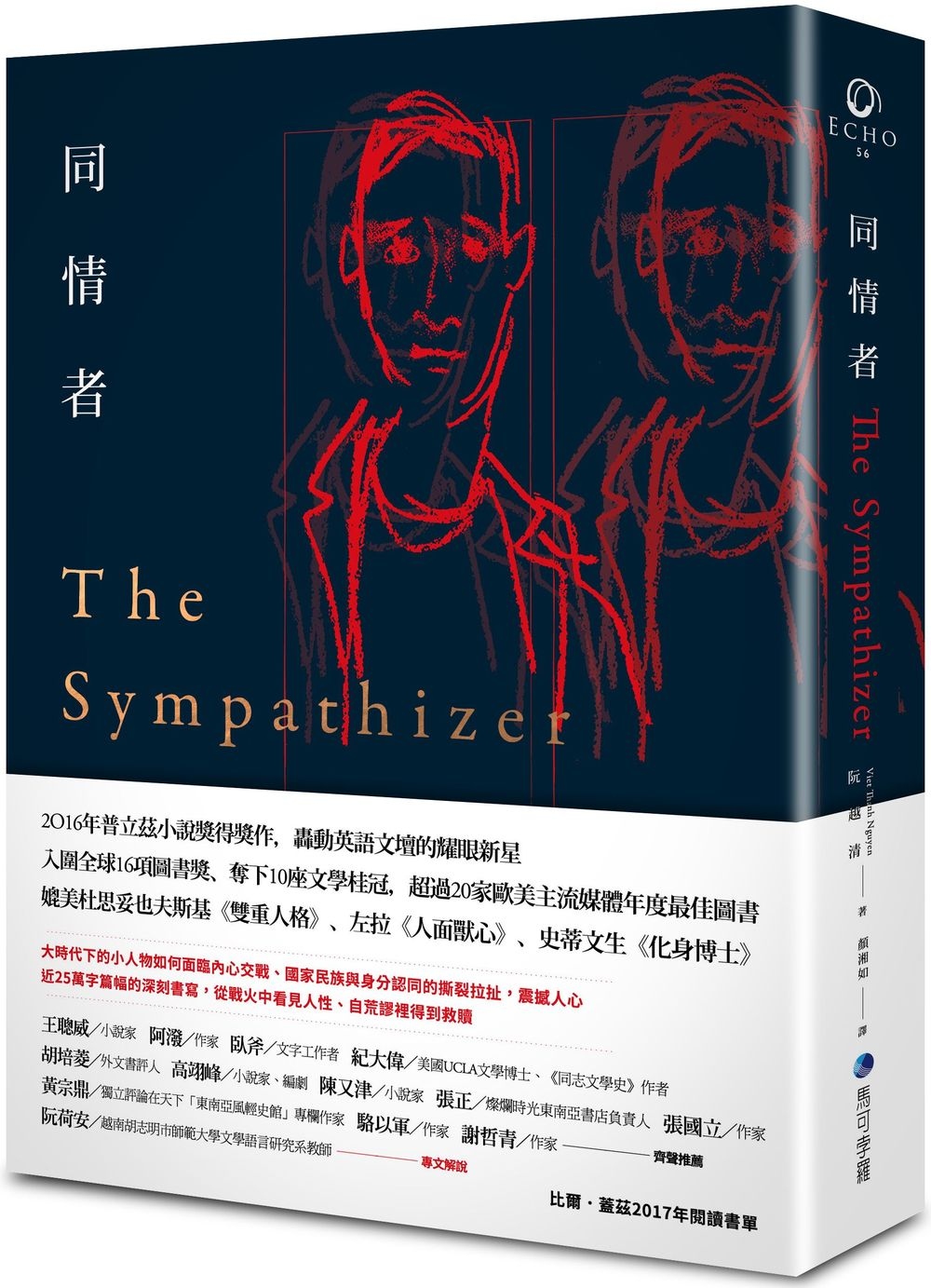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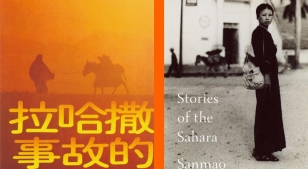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