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簡子鑫)
(攝影/簡子鑫)
〈我有權〉
- 我有權,被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直至死亡。
- 我有權,保持希望,雖然有機會改變。
- 我有權,接受帶來希望的照顧,雖然有機會改變。
- 我有權,用我自己的方法,表達我面對死亡的感受和情緒。
- 我有權,參與決定我的護理計劃。
- 我有權,期望得到持續的醫療及護理照顧,雖然治療目標已經由治癒變為紓緩。
- 我有權,不孤獨地死亡。
- 我有權,免於痛楚。
- 我有權,發問而得到真誠的回應。
- 我有權,維持我的個人意願,不會被其他不同看法的人論斷。
- 我有權,接受人們關懷、敏感、有知識的照顧,這些人知道我的需要,亦會透過幫助我能面對死亡,感到一點滿足。
- 我有權,期望我的遺體得到尊重。
這份「臨終患者人權書」(The Dying Person's Bill of Rights)是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護理系副教授Amelia Barbus在1975年主持工作坊時的集體創作,也是陳曉蕾在《香港好走 有選擇》開宗明義列在最前面的提醒──每一個生病的人,你不會、不該、也不能因病失去你對身體的自主決定權。
《香港好走 有選擇》《香港好走 怎照顧》以及《平安紙》是陳曉蕾《死在香港 見棺材》《死在香港 流眼淚》的前傳,從身後事往回推,推至人因病來到生命最後一段路時,所面對的種種景況。她透過採訪,匯整病者擁有哪些選擇、該有的心理建設與責任,到家屬應如何照顧病者與自身;乃至最後以一部《平安紙》,期望眾人都能趁著生時好好替自己爬梳、落好遺囑,提前做好人生終場的謝幕準備。

2013年「死在香港」系列後,記者陳曉蕾再推出「香港好走」系列,分為《怎照顧?》《有選擇?》《平安紙》三冊。
自「死在香港」的採訪延伸,三年的整理與觀察,匯聚得來的資料過於龐雜,讓陳曉蕾一度迷失報導方向。「一度想寫的角度是『現代醫療走得太過分了,如何叫停』,但這對我實在太深奧,翻來覆去憂鬱了半年,一直寫不出來。」如此折騰到自己都快崩潰,突地一個念頭:當你忽然知道自己病了,怎麼辦?於是一切檔案歸零,從頭開始。「因為沒有人知道要怎麼當一個病人。」她說。
「一般人只是學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工作、賺錢、買房、成家立業,沒有人會去想,當你病的時候,你要怎麼去面對、學習當一個病人。」疾病時常來得措手不及,病患肉體上承受折磨,心理混雜著對死亡與未知的恐懼,有些人不免封閉自我、自怨自艾,情緒上或許發洩了,卻徒增照護者的負擔。例如有個受訪者照顧生病的母親超過十年,陳曉蕾問對方,在這漫長的陪病歲月中學到什麼?他只說「以後自己要當一個容易被照顧的病人」;陳曉蕾也聽過有些人能明白說出自己的需求,例如有個50歲的女性病患確診後第一件事是去玩一趟希臘,另有個70歲的男病患坦白告訴醫生「不要搞我,讓我舒舒服服吧」,同意接受放射治療以舒緩病況。於是她更明白:理解現實、明確表達期望,是學習當個好病人的要項,也是踏出「好走」的第一步。

理解現實、明確表達期望,是學習當個好病人的要項,也是踏出「好走」的第一步(攝影/簡子鑫)
回頭問陳曉蕾,「現代醫療走得太過分」是什麼意思?與「好走」又有何關聯?「現代醫學已經不知道要停在哪了。一個人想要活,怎樣都可以讓你活下去──你可以不死,但你也不會好活。」她說。
「香港醫生很自豪,說香港人是全世界最長壽的,甚至比日本更長壽。但香港的高齡者超過70%有長期疾病,其中每5個就有1個同時罹患3-4種長期病症,雖然長命,但健康很差。」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維持住生命,一部分可能是身體底子還算好,另一個原因是醫生不斷開各式各樣的藥物,吃著不死,也不真的吃得活。
「而且香港很多失智症病患是插管的。」華人社會不允許讓人活活餓死,即使病患已無法進食,還是要以插管餵食的方式繫著一口氣。活是活著,然只活在一方床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躺著倒數人生。「所以我提出『好走』的定義,很簡單:病得遲、死得快。」只是這樣的定義在香港現實上是反過來的,或許在台灣也是。
現代醫學不斷追求延長人類壽命,但人為何如此執著於活著,且活得那麼辛苦?「如果你得了癌症,醫生說你只剩三個月,但你靠著各式各樣的醫療活了半年,你好像覺得多賺到三個月;為什麼不是這樣想:醫生說你只剩三個月,結果一個月就可以死了,還少受兩個月的苦。」

(攝影/簡子鑫)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親人能戰勝病魔、好好活著,不願放棄任何一點可能。「但如此一來,你的家人就可以僭越你的決定。」彷彿一個人只要生了病,便因為沒有好好管理健康在先,隨之失去了自主身體與生命的資格,所有人都能對你的病發表意見。
「最慘的香港人其實是有錢人,他們有能力住很好的醫院、獲得最好的照護,家人會一直安慰病患:你不要想太多,你看醫生在幫你,我們先不要談、也不要想,等你好起來再說……」而病患終究會去世,沒來得及在生前好好討論葬禮、分配遺囑,徒留無法挽回的遺憾,甚至造成家族的意見分歧。「好像只要醫生還在治療你的一天,你就不可以放棄。」
但,談死就是放棄嗎?
陳曉蕾對台灣目前還在討論、預計2019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注)頗感不可思議。「台灣到現在還會掙扎:如果家人生病了,要據實以告嗎?香港已經不討論這個了。」香港的醫生當然還是會看病人狀況能否接受,再決定是否告知,但不會家人說不告知就不告知。台灣醫師則會聽從家屬意見,與家屬達成協議、一起隱瞞病患。就這部分來看,陳曉蕾認為,台灣在「承認死亡即將到來」的態度上,可能比香港更傳統、也更逃避一點。
很多人不願意把病名確實說出口,好像說了就會成真。「但香港的醫護人員常常反問我:病人會不知道自己生病嗎?」身體是自己的,怎麼會不知道?而當你自己不面對、不決定、不堅持;當親人以愛為名,無視你的選擇,佐以當今無法遏止的現代醫學,活著,反而成了一件人人痛苦的事。因為停不了,也沒有人正視、尊重真正有權喊停的人。「到頭來,病與死,往往比結婚更無法自主。」
「有個教授告訴我一個案例是,某個醫生一直幫他的病人插管,插到完全插不進去。另一個資深醫生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我不做一點事,我過不了自己。」陳曉蕾聽了也不禁搖頭,「什麼叫過不了自己?你以為你是神嗎?但他好像非得把所有維持生命的方法都拿出來,不用不行。」無論是醫生或病患,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停、可以停或應該停,其實很重要。
在這麼多的發問之下,到底「好走」是可能的嗎?
陳曉蕾說,「我想是可以的。很多難過都是自己找的。」這句話指的不僅是病患,也指家屬。病是痛苦,照護應是相互減低痛苦的過程,包含肉體與精神。如何讓病者「活到死」,而非「死著活」,正是一個人能否好走的關鍵。
 (攝影/簡子鑫)
(攝影/簡子鑫)
注:《病人自主權利法》今年1月於立法院公布,預計2019年正式上路。法案授予病人臨終前預立醫囑權力,尊重重症病患本人維持治療的意願,也可減少因無效治療而消耗的醫療資源,和過去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相比,適用對象增加,保障病人自主權。(法規全文)
陳曉蕾「香港好走」與「死在香港」系列報導


延伸閱讀
1. 【書評】蘇絢慧:關於生命的退場,我們所知道的實在太少──讀《在我告別之前》
1. 【專訪】上一堂生命的實習課──專訪紀錄片《長情的告白》導演曾文珍
2. 米果:以照護為名,無奈的人生苦杯──讀《失控的照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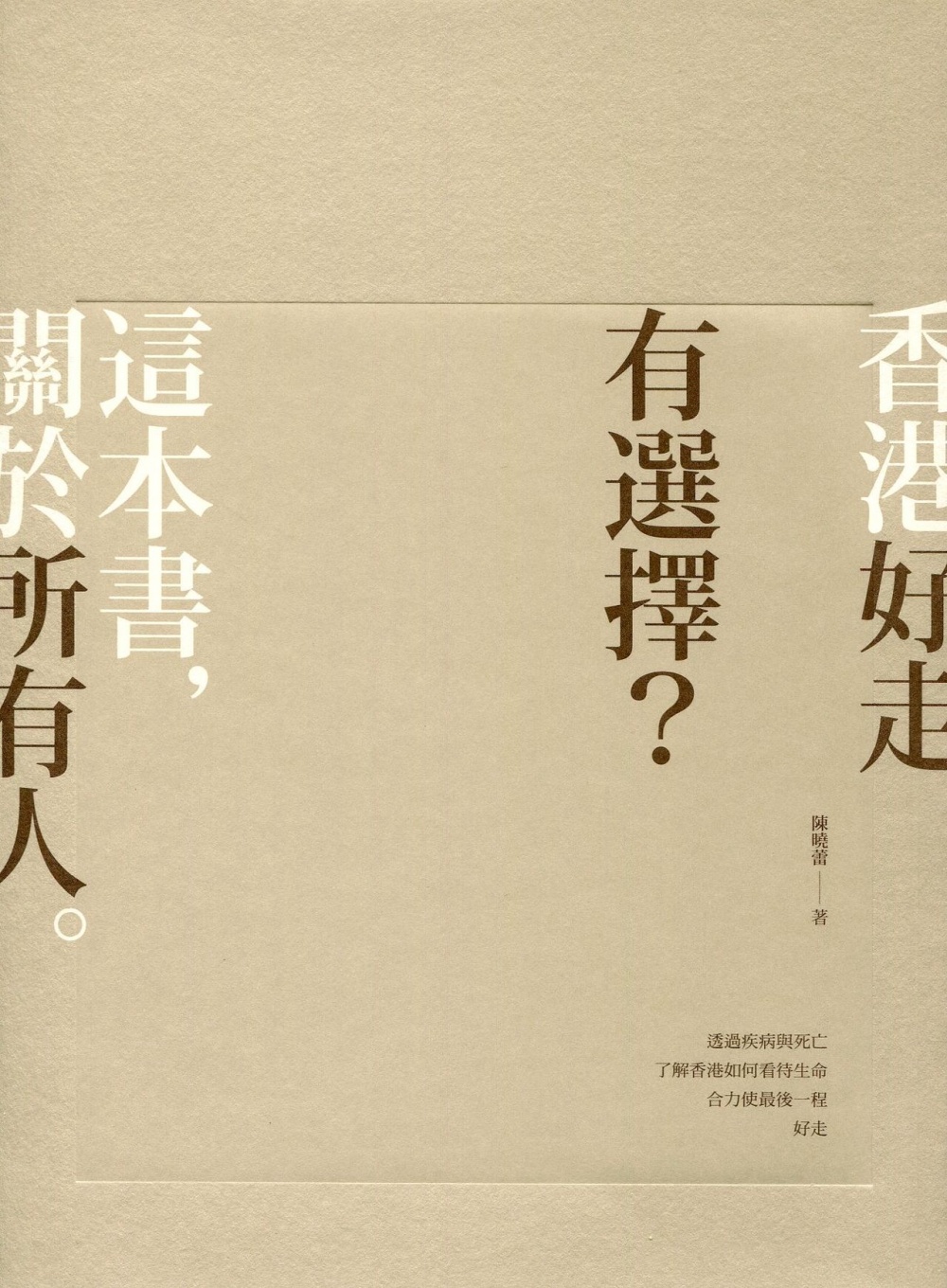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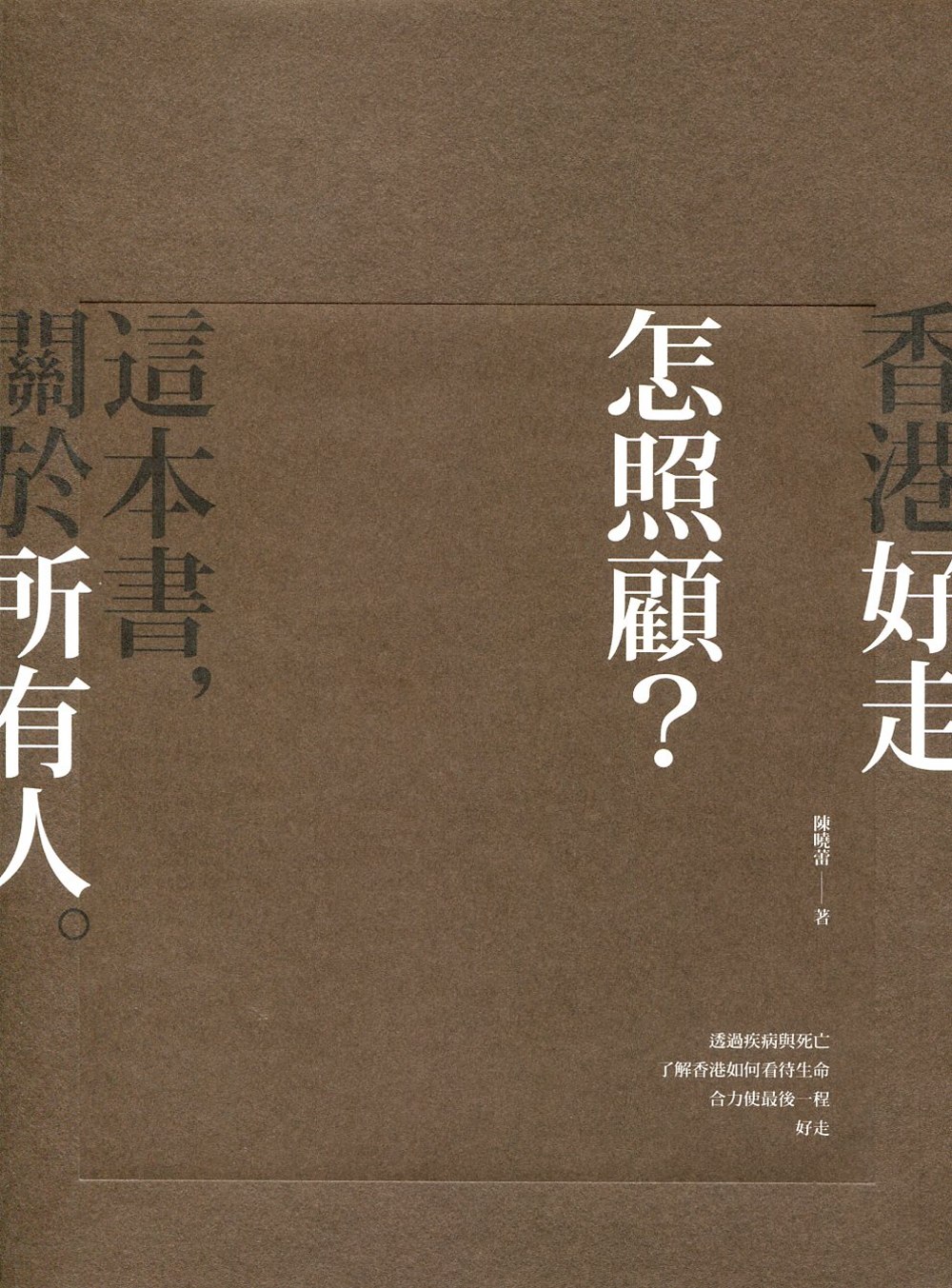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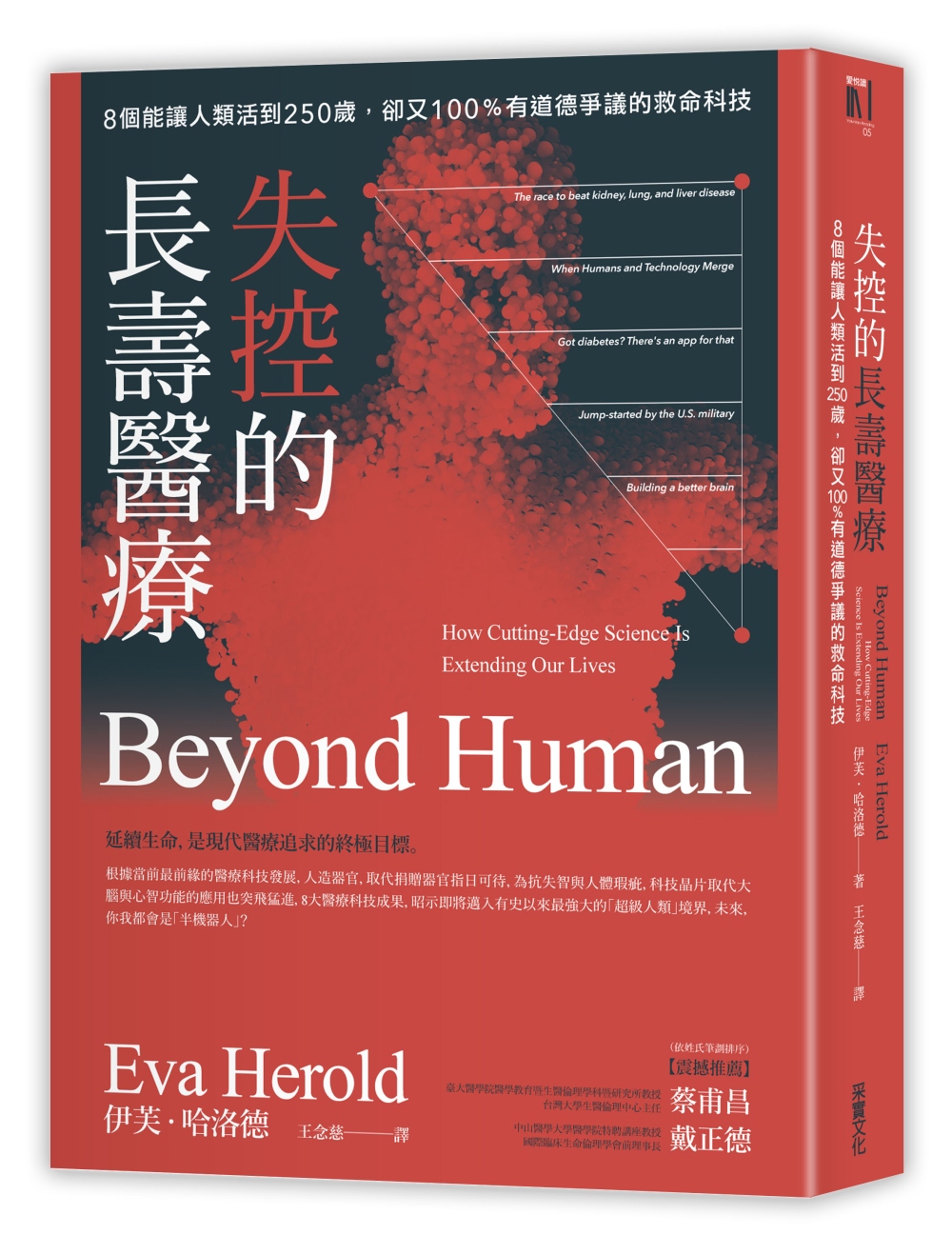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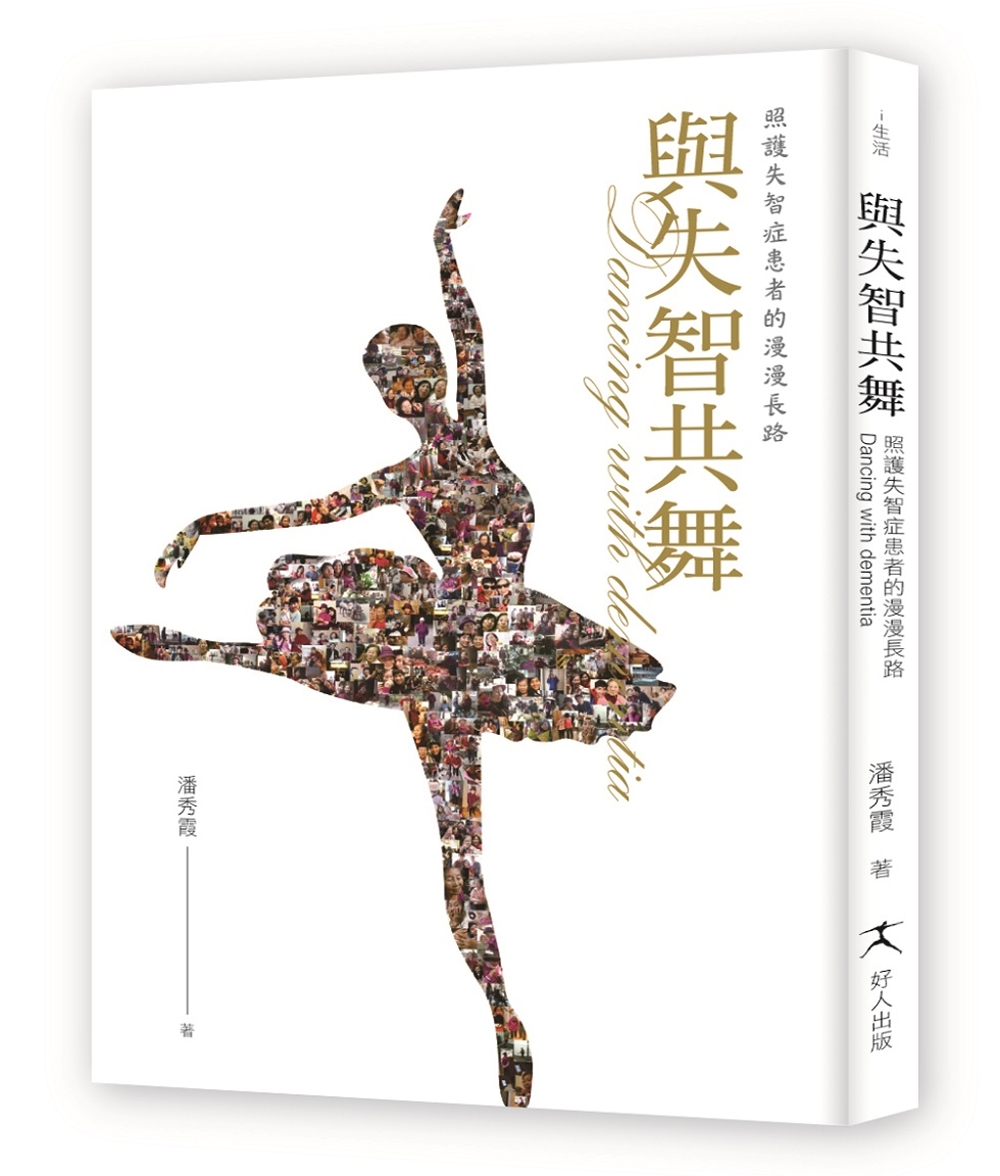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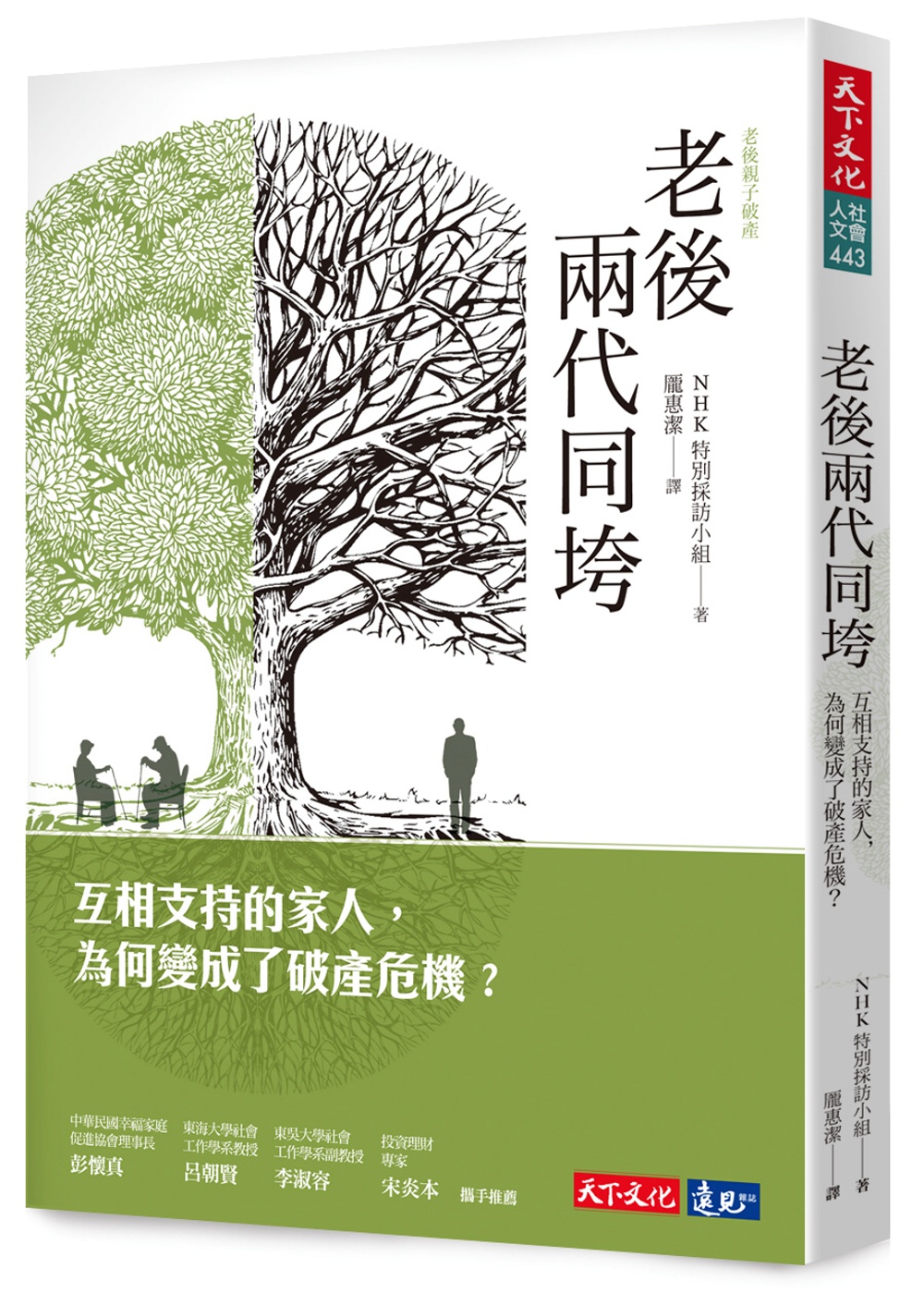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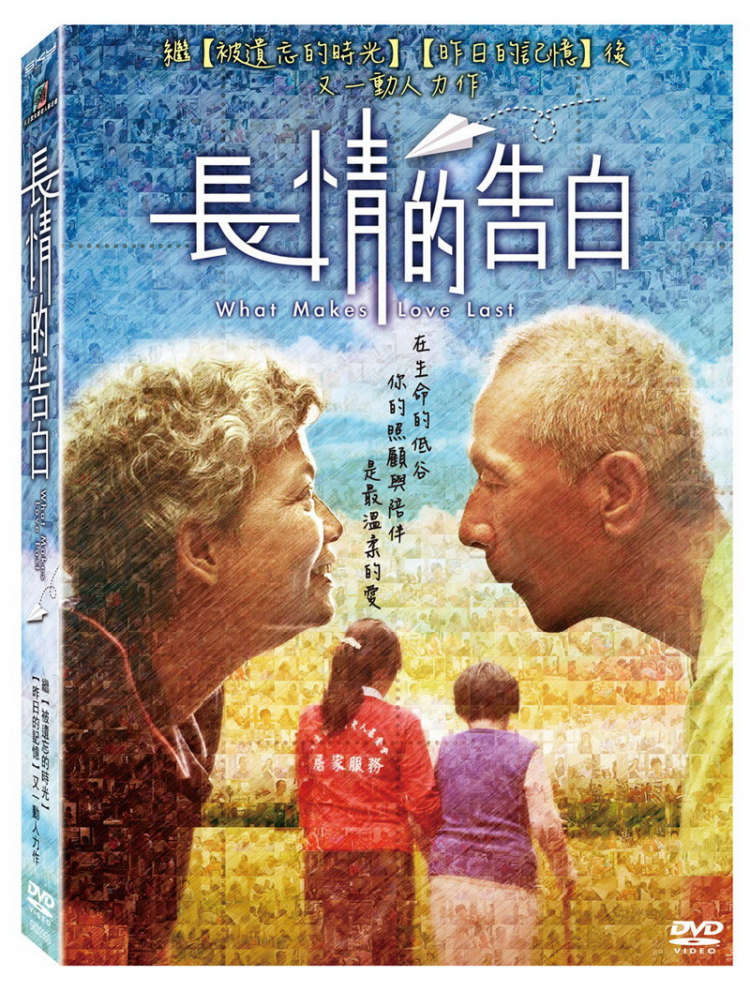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