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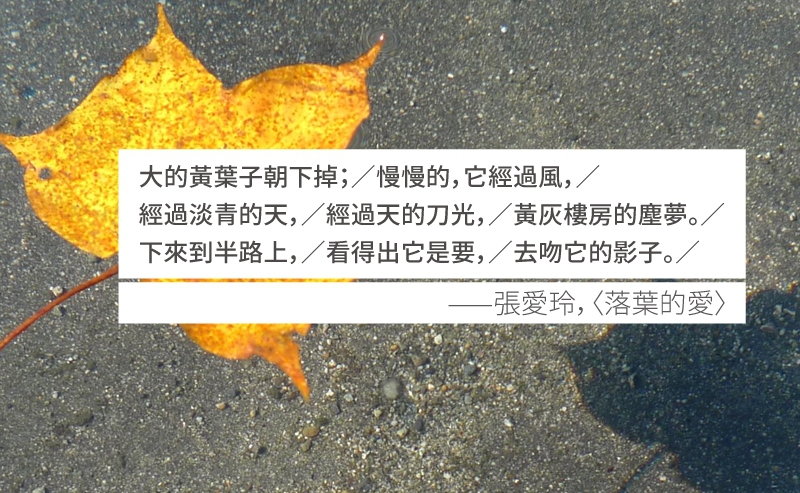
張愛玲以小說、散文名於世,其實她讀新詩,也寫過新詩。詩與小說,看上去很遠,其實能同時劈腿二端者(不是尚克勞范達美!)也不算罕見,瑪格麗特.愛特伍與瑞蒙.卡佛均是佼佼者。
在〈詩與胡說〉(不是何韻詩那首),她罕然地發表了對於新詩的意見,認為新詩從五四以來,胡適、劉半農、徐志摩、朱湘,都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彷彿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麼總說得不像話」,換言之,她認為這些「新詩」骨子裡並不新,都還是纔放了腳的裹腳女人。當然也許她當時沒有讀到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作品。而她在文章裡推崇的,是當時的「新生代」:路易士(紀弦)、倪弘毅,認為他們的詩「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極其生硬,然而不過是為了經濟字句,得壓緊,更為結實」。這裡說「吝惜」、「生硬」,都不是負面語,反而指的是能帶來澀感,超出期待視野,不是那麼熟極而流,滑過去就沒了。至於張愛玲為什麼會認識紀弦?和胡蘭成有關,胡資助當時經濟上並不寬裕的詩人。所以,「胡說」,不僅是談詩時的謙虛,恐怕也有愛情痕跡在裡頭。
讀詩如此敏感,寫起詩來如何呢?先來看這首〈落葉的愛〉:
大的黃葉子朝下掉;/慢慢的,它經過風,/
經過淡青的天,/經過天的刀光,/黃灰樓房的塵夢。/
下來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迎上來迎上來,/又像是往斜裡飄。/
葉子盡著慢著,/裝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金焦的手掌/小心覆著個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唔,在這兒了!」/
秋陽裡的/水門汀地上,/靜靜睡在一起,/它和它的愛。
節奏感並不柔熟,竟因此更能貼近大黃葉子往下飄落時,並不完全勻速的過程。淡青的天如刀光,黃葉以金焦色來描摹,這是張式筆調。「黃灰樓房」,滾滾人塵裡矗立著,可仍然有夢──是樓房在做夢嗎?像〈公寓生活記趣〉裡寫電車疲乏而乖順地回家,把富於情感的動詞與一般被歸類為冷漠無感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以都市人眼光來看,並不會比 pineapple 與 pen 來得不合理。不過,全詩最可愛的,還是葉子將落地,那迎向自身影子的姿勢彷彿捉蟋蟀一般,小心覆蓋著如同祕密,最後靜靜睡在一起。啊一個納希瑟斯式的鏡頭。
附在散文後頭的這首〈中國的日夜〉,也不太容易發現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雖然是打滿補釘的人民,因為是和自己同在一時一地的人民,是亂紛紛環繞於自己的青春,補釘看上去也像彩雲。一日三餐是生活的象徵,生活雖是沉重累贅,曬著太陽去扛起來,總讓人有一種切切實實活著的感覺。結尾可作二義解:既是「中國沉到底」,也是「到底是中國」,前者凝聚了中國近現代史裡的沖激與悲哀,千里赤地螻蟻般的求生,比累贅在手上買回來的一日三餐還重;後者則套用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句式,鄉土中國和城市中國似乎總被對立起來,作為城市代表的張愛玲,似乎更洋氣些,但是她自己說,到底是中國(人)。
最後,想提一下出現在《小團圓》裡的情詩,九莉寫給之雍:
他的過去裡沒有我,
寂寂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裡曬著太陽,
已經是古代的太陽了。
我要一直跑進去,
大喊「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呀!」
小說裡下了按語:「他沒說,但是顯然不喜歡。他的過去有聲有色,不是那麼空虛,在等著她來。」「太陽」在這裡是否與作為張胡之戀襯底的中日戰爭有關呢?九莉說,希望戰爭不要結束,之雍怒看她,說死了這麼多人還要打下去嗎,九莉:「我不過因為要跟你在一起。」如同張愛玲不寫紀念碑式的題材、認為男女愛恨才永恆那樣政治不正確,九莉這話,是一個傷心人的絕望。是私語,不是好戰。
楊佳嫻
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台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金烏》,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最新作品為《小火山群》。



![華麗緣 散文集一.一九四○年代 [張愛玲典藏新版]](http://www.books.com.tw/img/001/046/62/0010466212.jpg)




























回文章列表